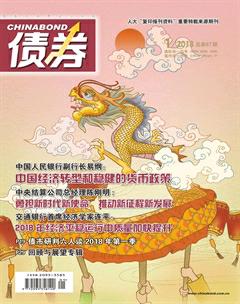CPI与PPI背离的成分特征与驱动因素解析
吕光明+于学霆
摘要:自2011年以来,我国CPI与PPI出现了持续分化背离的新特征。本文从趋势与波动成分特征、驱动因素分解两方面重点解析了CPI与PPI价格序列的背离特征,揭示了二者持续分化背离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调控 CPI与PPI背离 成分特征 驱动因素
从各国的经济运行来看,CPI与PPI整体上变动较为一致,虽然增速有所差异,但涨跌方向基本一致。近十年来,我国CPI与PPI价格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PPI的涨跌幅度远大于CPI的涨跌幅度,二者近年来出现持续分化背离现象。自2011年10月至2016年10月,CPI与PPI分化背离达五年之久,这其中大部分时间PPI处在通缩状态,而CPI则一直为正且保持低位运行,并呈现微波化特征。2016年10月至2017年底,PPI在穿越CPI后又形成了新的“剪刀差”,主要特征是CPI继续以低位平稳正向运行,PPI则大幅上涨(见图1、图2)。这种现象不仅扭曲了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也为我国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困扰。因此,有必要就二者波动的成分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解析,找出二者长时间分化背离的原因,以期为新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CPI与PPI背离的趋势与波动成分特征解析
本部分将通过CPI与PPI价格序列趋势成分特征和波动成分特征的对比分析来解释二者持续性背离的原因。
(一)趋势成分特征解析
图3为 CPI与PPI价格序列的趋势变动图,二者的价格序列趋势性成分由HP滤波得到。价格波动的趋势性成分反映了价格未来的走向。由图3可知,自2010年1月开始,CPI与PPI的趋势变动发生了背离。CPI趋势成分自2011年8月至2015年5月一直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2015年5月至2017年底,CPI趋势变动非常稳定。而PPI自2011年2月开始大幅下降,2012年9月至2016年9月一直处在通缩状态,自2015年1月开始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从目前CPI与PPI价格序列的趋势成分变动来看,CPI低位稳定运行的趋势并未改变,而PPI还存在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二者趋势性背离仍将继续,未来存在进一步分化的可能。
(二)波动成分特征解析
图4是CPI与PPI价格序列36个月滚动标准差趋势图。从整体来看,PPI价格序列的波动性要远高于CPI价格序列的波动性。PPI价格序列的波动性自2011年2月的6.12下降到2012年10月的3.77,之后又上升到了2017年11月的5.2,其波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大于CPI。相对而言,CPI近年來则呈现出微波化特征,CPI价格序列的波动性从2010年5月至2017年底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且自2014年11月波动性小于1,波动性变动趋势也非常稳定。总之,从CPI与PPI波动性变动趋势图来看,二者的波动性背离并无缩小迹象,未来可能仍将继续。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CPI与PPI呈现“双背离”特征,即趋势性背离和波动性背离同时存在。这段时期我国进入了经济新常态阶段,CPI与PPI的“双背离”特征则是经济新常态价格波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CPI与PPI的趋势性背离意味着二者的相关性由以前的强正相关变为弱正相关,甚至不相关。因而,趋势性背离也可以称为“相关性背离”。CPI与PPI的波动性背离表明,PPI仍然保持了以前的高波动性,而CPI则呈现微波化特征。CPI的低波动性与GDP波动性下降密切相关,从构成成分看,CPI更能体现实体经济状况。PPI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密切相关,大宗商品交易具有金融属性,这也使得PPI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因此,CPI与PPI的“双背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实体与金融的背离,或者说是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背离。
CPI与PPI背离的驱动因素解析
本部分主要通过对CPI与PPI构成因素进行分解,来解析驱动CPI与PPI背离的内在机理。
(一)CPI变动驱动因素解析
我国CPI构成成分按照产品类型划分,可分为食品、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三大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食品价格指数、非食品价格指数和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并依据CPI与其构成关系,可以推算出我国食品、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项目权重,具体推算公式如下。
其中, 为食品价格指数, 为非食品价格指数, 为食品权重。 为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为消费品价格指数, 为服务项目权重。 为非食品消费品权重。
我国CPI每五年进行一次基期轮换,各项目权重也会进行大的调整,并且每年根据实际情况也会对CPI各项目权重进行一定微调。根据上述权重推算公式,笔者推算出我国食品、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月度权重,在去除极端值并调整后,测算了我国2002年3月至2017年11月这三类项目对我国CPI的拉动率1(见图5)。根据我国CPI基期轮换时间,笔者也分别测算了各轮换区间内食品、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平均权重及平均贡献率2(见表1)。
由表1可知,在我国4个CPI基期轮换区间内,食品权重在2016年之前都在30%以上,在2016年CPI基期轮换调整后,食品权重下降为20.33%。非食品消费品权重除2011—2015年平均为38.97%外,其他时间都在40%以上,权重变动较小。服务项目权重在四个轮换区间内一直上升,在2016年开始的新轮换区间内其权重超过食品权重,达到36.56%。从四个区间各项目对CPI平均贡献率看,食品价格的平均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16年到2017年11月间,食品价格对CPI变动驱动的平均贡献率仅为9.77%。非食品消费品价格自2016年开始对CPI上涨驱动效应显著,2016年至2017年11月平均贡献率为31.68%。服务项目价格从2006年开始对CPI驱动效应一直呈上升趋势,2016年至2017年11月对CPI驱动的平均贡献率已达到58.55%。endprint
图5是2002年3月到2017年11月食品、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项目对我国CPI变动的驱动趋势图。从整体来看,我国CPI的波动主要受食品价格驱动,非食品消费品价格在2002年3月至2004年6月、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是CPI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在CPI上涨阶段驱动作用有限,服务项目价格自2012年6月开始对CPI上涨驱动效应显著增强,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服务项目价格对CPI驱动效应已超过食品价格。从2017年伊始,在食品价格通缩状态下,服务项目价格已成为驱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非食品消费品的驱动效应也非常显著。
(二)PPI变动驱动因素解析
1.上中下游产业链视角
按照我国工业行业划分标准,目前我国工业划分为41个行业。在剔除数据缺失的4个工业行业后,本文将我国PPI中剩余的37个行业按各行业属性,划分为上游行业、中游行业、下游行业,并将上、中、下游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作为其在PPI构成中的权重,以此推算出上、中、下游行业价格变动对PPI的驱动率(见图6)。此外,与CPI划分区间相一致,分别测算了各区间内上、中、下游行业价格的平均权重及平均贡献率(见表2)。
从表2可知,在各区间内,上、中、下游行业权重变动基本稳定,下游行业权重最大,上游次之,中游最小。从贡献率看, PPI波动主要受上游行业价格驱动,各区间平均贡献率都在74%以上,中游和下游行业价格对PPI波动驱动较小,平均贡献率合计在26%以下。
图6是2003年1月至2017年11月上、中、下游行业价格变动对PPI的驱动趋势图。由图6可知,我国PPI上升或下降基本全部受上游行业驱动,中下游行业对PPI的驱动作用十分有限。
2.产品类型视角
我国工业生产按产品类型,又可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同比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生活资料价格指数,按照三者构成关系可推算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PPI中的权重,具体如下。
其中, 为生活资料价格指数, 为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构成PPI中生活资料价格指数权重。根据公式(4)所推算的权重,本文测算了1996年10月至2017年11月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PPI波动的拉动率(见图7)。同时,根据上文划分区间,测算了各区间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PPI中平均权重及平均贡献率(见表2)。
由表2可知,我国PPI构成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占权重相对稳定,生产资料在75%左右,生活資料在25%左右。对PPI波动的贡献率方面,生产资料在各区间贡献率都在90%以上,在2011—2015年、2016—2017年贡献率都在98%以上;而生活资料对PPI波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从图7可见,PPI的波动几乎全部由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驱动,而生活资料价格指数对PPI波动的驱动影响不大。
(三)CPI与PPI背离主要驱动因素解析
上述CPI与PPI驱动因素分析表明,CPI与PPI持续分化背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构成成分的差异。在我国CPI构成成分中,不仅包含食品、非食品消费品价格,还包含服务项目价格。而PPI构成成分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分,主要反映工业消费品和生活消费品价格信息,并不直接包含服务品的价格。CPI中的服务项目价格可能是二者时常出现分化背离的原因之一。
第二,主要驱动力的不同。我国CPI在2012年之前几乎全部由食品价格驱动。在2012年之后,服务项目价格对CPI的驱动效应越来越显著,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服务项目价格对CPI驱动效应已超过食品价格,从2017年伊始,在食品价格通缩状态下,服务项目价格已成为驱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非食品消费品的驱动效应也非常显著。而PPI在产业链视角下几乎由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价格驱动,在产品类型视角下几乎由生产资料价格驱动,且PPI构成成分对其在整个样本区间内的驱动效应非常稳定。CPI与PPI价格上涨驱动力的不同是二者分化背离的主要原因。
第三,价格传导的阻滞。PPI内部上游、中游和下游产业链的价格传导存在阻滞,上游行业价格上涨并未引发中下游行业价格上涨。同时,CPI与PPI之间的价格传导也并不顺畅,CPI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未驱动PPI下游行业价格及PPI生活资料价格上涨,PPI下游行业价格及PPI生活资料价格波动也无法对终端需求,即消费品价格产生影响。总之,无论是生产链价格传递理论下的正向传导,还是引致需求理论下的反向传导,PPI与CPI之间的价格传导似乎都只是理论上的可能。
政策建议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新的阶段性问题,处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价格的稳定对于当前金融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对于CPI与PPI持续背离的现象,笔者提出如下治理建议。
(一)积极破除行业垄断,充分发挥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作用
我国CPI与PPI持续分化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价格传导存在阻滞。上游行业价格向中下游行业价格传导并不顺畅,终端需求的价格反向倒逼机制也不明显。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上游行业存在行业垄断壁垒,石油、天然气、矿产等上游行业资源属性明显,可以依靠行业垄断和价格保护赚取高额利润,同时也容易将价格上涨成本转移至中下游行业。而越接近零售端的中下游行业则越具备完全竞争细分市场特征,本身对成本转嫁的能力非常有限,这导致了CPI与PPI,以及PPI行业内部传导的不通畅,时常出现分化背离。上游行业的垄断属性也会引发资源错配,加大生产和需求的扭曲,造成产能过剩。这就需要大力推进价格改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破除行业垄断,充分发挥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endprint
(二)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
我国PPI的波动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国际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性质的大宗物資商品。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成为许多大宗商品的重要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但尽管如此,中国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影响力基本为零,被动地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接受者,这直接影响国内能源、初级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价格,驱动了PPI上涨。2016年,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货币篮子,迈出了走向国际化的一步。建议未来积极推进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通过输出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沿线资源和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规则,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重构定价规则,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能力。同时,国际市场多以权威的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要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还需要完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市场和公允的期货价格。
(三)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
我国CPI与PPI的“双背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实体与金融的背离,或者说是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背离。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背离,说明资本存在“脱实入虚”的现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化,泡沫不断积累会增加金融体系风险,最终拖累实体经济。建议未来逐步推动金融去杠杆、加快资本“脱虚入实”,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同时,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通过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本形成、完善公司治理和提供直接融资的能力,最终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实现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同向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国民核算研究院
责任编辑:印颖 罗邦敏
参考文献
[1] 汤铎铎,张莹.实体经济低波动与金融经济去杠杆[J].经济学动态,2017(1).
[2] 钟正生,张璐. PPI向CPI传导:直觉与真相[J].财经,2017(1).
[3] 吕光明,金蛟.我国CPI与PPI背离特征表现与成因分析[J].债券,2015(12).
[4] 彭文生.《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M]. 中信出版社,201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