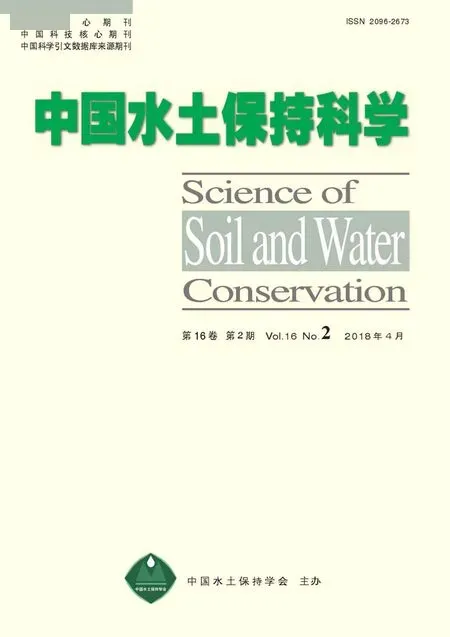中国防沙治沙60年回顾与展望
包岩峰,杨 柳,龙 超,孔 哲,彭 鹏,肖 军,姜丽娜,卢 琦†
(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100091,北京; 2.国家林业局亚太森林网络管理中心,100021,北京)
土地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挑战之一。全世界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1/5的人口、1/4的陆地面积受到荒漠化的危害,而且正以每年5万~7万km2的速度扩展[1]。中国是世界上受沙漠化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问题造成的生态和经济损失超过650亿元[2]。将近4亿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荒漠化问题的困扰,严重制约我国生态安全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3]。近60年来,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积累和总结了众多防沙治沙模式和典范。沙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更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 436 km2,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 980 km2,治理成效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和广泛认可[2]。
1 中国防沙治沙60年历程
沙漠与人类的“争斗”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其激烈程度不同。沙漠在我国最早出现是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侧重描述古人的风土人情、经济贸易和文化活动,没有对沙漠地质、地貌形成专门的著作。近代,随着一些探险和科考活动的增加,人们才逐渐揭开了我国沙漠的神秘面纱;但对沙漠科学的真正研究和开展防沙治沙的实践活动,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质的飞跃。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按时间进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
1.1 全民动员,进军沙漠——治沙工作萌芽起步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就已经开始重视我国的沙漠化问题,成立林垦部,组建冀西沙荒造林局,动员群众,开启漫漫治沙之路。1950年由国务院牵头,成立治沙领导小组,在陕西榆林成立陕北防护林场。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空前高涨,在我国的陕西、榆林和甘肃民勤等沙区,实现了首次飞播造林种草实验,治沙技术不断提高。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各领域众多科技工作者,对我国的大部分沙漠、沙地及戈壁开展综合考察,建立6个综合试验站及数十个中心站,初步形成我国北方沙漠观测、科研和试验网络平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治沙事业受到严重阻碍,并且由于大规模的开荒垦地,造成我国各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沙漠化问题日趋严重。
1.2 国家意志,工程带动——治沙工作初步发展阶段
197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项为期73年造林总任务3 508.3万hm2的工程,开启了我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的序章,唤醒国民生态保护的意识[4]。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荒漠化地区自然资源的保护及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巩固已有生态工程的治理成果,使我国防沙治沙工作进入初步发展阶段[5]。20世纪90年代,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1991年国务院召开第1次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议,之后又出台了《1991—2000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纲要》《关于治沙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相关政策,防沙治沙已经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完善。
1.3 以外促内,全面提速——治沙工作稳步推进发展阶段
1994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标志着我国的荒漠化防治工作正式与国际接轨,同时建立由林业部门担任组长,19个部(委、办、局)组成的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小组,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跨领域,齐抓共管的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从第1个提交国家履约行动方案,到成功举办第13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由以外促进,达到国际领先的新局面。2000年伊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试点等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先后启动,开启了新时期由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带动荒漠化治理的新高度。2001年8月31日,在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防沙治沙法》,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1部防沙治沙方面的专门法律,建立防沙治沙的制度体系,界定法律边界,奠定依法治沙的基础。2005年8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正式出台,同年,国务院批复《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05—2010年)》,明确了我国防沙治沙的长期目标和发展方向。2007年3月,召开全国防沙治沙大会,明确全国防沙治沙“三步走”的思路[6]。2013年批复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规划,明确了全国防沙治沙的基本布局、防治目标和任务。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荒漠化防治工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2016年6月17日,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后的第一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启动实施“一带一路”防沙治沙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防治荒漠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必要前提,荒漠化防治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使其进一步快速稳定发展。
2 科学驱动,技术支撑:中国防沙治沙技术体系与模式
2.1 沙漠科学基础性工作与研究
过去60 年来,我国沙漠科学在传统地貌学、气候学及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上,开创和发展包括沙漠生态学、风沙地貌学、风沙物理学、沙漠水土资源和沙漠化过程等众多基础研究领域。沙漠生态学方面,主要涉及沙生植物材料的选育扩繁和植物适应性研究,沙生植物的选育扩繁,是通过确定沙生植物的适生范围,建立品种基因库和试验林,引进和筛选出一批抗逆性强的沙生植物材料;沙生植物适应性研究,主要针对具有耐干旱、盐碱及抗日灼等生态特性的沙生植物,开展对其在艰苦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适应沙埋、风和风沙打击危害的形态结构和生长特征、旱生或超旱生的形态结构与生理特性、适应流沙的繁殖特性及水分利用策略等生态适应性相关研究。在植物生理方面,涉及沙漠化过程与植物生理变化的关系,以及植物对沙漠化的适应。在风沙地貌方面,对不同地区风沙流的形成、运动及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对风蚀雅丹、风蚀城堡、风蚀长丘和风蚀劣地等风蚀地貌的形成及发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在风沙物理学方面,在风洞中,对土壤风蚀进行系统的模拟实验,在风沙气固二相流、风成基面形态运动、风沙相似和风沙工程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建立相关物理和数学模型;在颗粒运动图像分析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建立了相关的数学模型;提出“固、阻、输、导”的治沙技术,出版《风沙物理与风沙工程学》等专著[7-8]。在沙漠水土资源方面,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水土资源的现状及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以水定地、水土平衡以及流域水土开发等方法,并在节水灌溉和沙漠土壤改良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中国风沙土》《河西地区水土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等专著[9-11]。在沙漠化过程方面,揭示沙丘的形成机制与沉积特性;在沙漠第四纪研究方面,建立两代沙漠格局,提出中国沙漠3种演化模式[12],出版《中国沙漠概论》《风沙地貌学》《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地貌研究》《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中国沙漠图》等著作[13]。
在沙漠科考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19支大型沙漠考察队伍开启对我国主要沙漠、沙地及戈壁正式科考研究。沙漠科考分别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以及青海的沙漠、宁夏的河东沙地和甘肃西部的戈壁,均进行了综合考察。对沙漠环境及资源、风沙地貌、沙漠植物、水文、土壤和气候等多个内容进行研究,基本查清了我国沙漠、沙地、戈壁和风蚀劣地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沙漠类型划分系统[14]。
2.2 机构建设与条件平台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的一门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荒漠化防治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综合运用地理学、生态学、林学、农学、土壤学、气象学和农田水利等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实现研究、培训、推广和生产实践的四位一体发展,具有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14]。目前,全国开设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专业院校共计43所,“985”研究生院校4所,“211”研究生院校10所,还有一些科研院所。沙漠科学工作者梯队化发展,呈现出学历高、年纪轻、基础理论扎实的势头,学习科学系统、业务能力强等诸多优点,为继承和推动我国荒漠化防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国家科研经费支持力度不断增加。荒漠化学科已经列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加强荒漠化防治学科基础及应用技术的研究,通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技术(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环保公益行业科研专项,国际科技合作等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为学科发展及基础和应用性研究提供经费支持,保障荒漠化治理过程中,急需解决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和突破。
我国沙漠科学试验平台快速扩展和完善。在科技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成立涉及沙漠科学研究的重点实验室,如地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地学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同时,我国还新建一大批野外沙漠或沙漠化观测研究试验站点,如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在宁夏沙坡头,内蒙古奈曼旗、阿拉善,甘肃临泽、敦煌,西藏那曲、日喀则和新疆塔中等地,建立稳定的野外观测研究和试验研究站;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新疆阜康、阿克苏和策勒,设立3个国家野外观测站;中科院应用生态研究所在内蒙古甘旗卡、额尔古纳和乌兰敖都等地,建立一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在青海共和治沙站、宁夏盐池、甘肃武威和民勤等地,也建立野外观测研究站及野外试验平台。另外,还有大批荒漠化防治工程中心落地,如2007年,由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中国防治荒漠化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成立森林生态与林业生态工程研究中心。
2.3 中国防沙治沙技术体系与模式
60年来,我国针对不同生物气候带,建立多种类型的沙漠化治理模式和系统的沙漠化治理技术体系,推动区域沙漠化的治理进程。如固沙植物材料的快速繁育技术体系、退化土地治理与植被保育技术、高大流动沙丘的机械阻沙技术、防风阻沙林带造林技术、水资源利用技术、沙漠沙源带封沙育草保护技术、弃耕还林还草防止土壤退化技术、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技术体系、沙漠和沙漠化土地遥感监测技术等防沙治沙技术。通过对这些成熟技术的组装和配套,实现沙漠治理技术体系与模式的集成和创新,如包兰铁路沙坡头段“以固为主、固阻结合”的铁路综合防沙治沙体系的模式[15-16]; 发挥政府、企业和群众的力量,发展沙产业,使沙区百姓脱贫致富的“库布齐沙漠生态财富创造模式”[17];干旱区半干旱区实现以水定林的“低覆盖度防沙治沙”模式[18]等。根据不同的气候、土地类型及经济、生态建设需求,有适用于极端干旱区的和田沙漠化防治模式[19],干旱绿洲的临泽、策勒模式,半干旱区的榆林模式,半湿润地区的延津、禹城沙化土地治理与农业高效开发模式,高寒区的共和县沙珠玉沙漠化防治模式等,不断打造出可以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模板的“中国模式”。
3 中国治沙对世界的借鉴意义
3.1 政府主导,依法防沙治沙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做好防沙治沙的总导演。我国是世界上第1个将防沙治沙纳入法律的国家,这在世界防沙治沙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实践,该法荣获了2017年“未来政策奖”银奖。此外,我国政府还制定实施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规划(2011—2020年)》《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等相关法律法规,推行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对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进行严格保护和集中治理,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政策、规划和考核体系,以及监测预警、工程建设、科研与技术推广、履约与国际合作体系,初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
3.2 国际合作,推动全球荒漠化治理
荒漠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防治荒漠化应携手全球共谋福祉。我国不断加强双边、多边和区域国际合作,积极主导和参与荒漠化国际机制的制定过程,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海湾组织合作论坛、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及东北亚环境机制等,都将荒漠化防治列为了优先领域。推广我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如援西亚非洲干旱半干旱地区飞播治沙造林种草,中国-联合国合作非洲水行动-非洲沙漠化国家防治荒漠化技术合作与沙产业开发,在援埃及荒漠化防治示范及技术中心项目中,推介我国植物生根粉,植物生长调节剂技术和产品合作、推介风成沙建筑涂料加工及利用企业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项目。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确定重点合作领域,如2004年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是涵盖众多领域、建有10余项机制的集体合作平台,在201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阿合作论坛2014至2016年行动执行计划》《中阿合作论坛2014至2024年发展规划》,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治理领域是在此论坛框架下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11年中国、韩国和蒙古成立了东北亚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次区域与网络的合作机制,该机制为推动区域防治荒漠化合作和减轻沙尘暴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6年6月17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启动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通过倡议提供的会议机制、信息共享和项目示范等多种机制,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开展荒漠化防治。
3.3 发挥我国防沙治沙优势,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国家高度重视荒漠化问题,将荒漠化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发展和外交总体战略。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和中日韩三国机制等双边和多边机制,结合“一带一路”总体战略实施,不断推动我国境外沙源治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探索与阿拉伯国家、非洲、中亚、蒙古等地区和国家荒漠化防治的深入合作。通过国家援外培训项目、与国际组织三方合作等,为发展中国家开展防治荒漠化技术和政策培训,“十二五”以来,已经为亚洲和非洲80多个国家、近300人开展了荒漠化防治技术和政策培训,广泛传播荒漠化防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如依托科研机构成立荒漠化国际培训中心,举办防治荒漠化高级研修班,启动中德合作中国北方荒漠化防治培训与支持措施项目等。主要国际培训班还有商务部主办、国际竹藤中心和国家林业局治沙办联合承办的“非洲英语国家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各省、自治区科研单位承办的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研修班和技术培训等等。通过荒漠化防治技术的培训,不仅将我国先进的防沙治沙经验推广至世界,还为扩大我国在荒漠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递出了一张“响亮名片”。
4 中国治沙走向世界
4.1 深化影响国际规则,引领全球荒漠化防治
中国防沙治沙的60年,不仅是引领全球沙漠化防治的60年,还是深化影响国际规则的60年[20]。国内方面,我国已经制定并发布了20多个有关环境保护的行政法律和法规,同时,将治理沙漠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经济和环境保护重点放在同步计划、同步执行和同步发展的联合形式上[21]。国际方面,通过不断加强合作,共同探讨防治荒漠化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模式,拓展荒漠化防治领域,发展沙产业,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积极参加国际荒漠化领域重要会议、谈判和磋商,强化多边话语权,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代表团先后多次担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缔约方大会副主席等职位,参加部长级论坛、议员圆桌等会议,并担任主题发言人,参加科技委员会特设专家组、政府间特设工作组、科学和政策建议专家委员会等重大问题的谈判。支持区域履约机制和加强科学技术支撑体系,推动公约10年战略实施、建立履约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和制定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防治目标。积极推动建立履约审查委员会,支持加强区域履约机制和科学技术支撑体系,提出设立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国际主题,强化宣传影响,倡导制定公约10年战略,设定全球防治目标等。通过多种形式国际、区域交流与合作,发出中国声音,影响国际政策。
中国在60多年的防沙治沙实践中,总结100多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荒漠化防治技术,这些治沙技术在非洲和亚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中国的荒漠化防治,为根治“地球癌症”,开出以政府主导、科技支撑、工程带动和榜样激励等全方位综合防治机制为基础的“中国药方”, 也为世界实现荒漠化趋势逆转,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4.2 认真履行国际公约,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自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签署至今,我国一直以积极的态度与行动,在世界荒漠化防治领域担当先行者的角色。根据公约要求,建立国家荒漠化监测体系,奠定科学治理基础,并与公约履约评估指标体系接轨,调整和完善履约评估和报告体系,认真履行义务,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工作实践,树立“世界履约看中国”的标杆[12]。近年来,中国不断发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治理沙漠化的道路,基本实现了由被动治沙向主动治理兼开发利用的模式转变,成效显著,成为世界上荒漠化防治成绩最显著的国家。
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利用大型国际会议和有影响的国际活动,传播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展示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成效和经验。我国先后承办1995年亚洲部长级会议、1996年亚非防治荒漠化合作论坛、2006年妇女与荒漠化国际会议、2008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2014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后续行动政府间工作组磋商等众多国际会议。2017年9月,在鄂尔多斯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向全球各国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生动讲述中国防沙治沙故事,分享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4.3 中国经验“走出去”,全球行动“动起来”
中国防沙治沙经验“走出去”。政府、民间、私营及科研等部门需要在区域乃至全球防治荒漠化问题上开展广泛的合作,搭建信息交流与经验共享平台,不断支持我国先进的防沙治沙技术“走出去”。目前,我国防沙治沙领域的技术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相关技术和成果为解决荒漠化这个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坚力量,“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多次收入荒漠化公约大会文件和最佳模式汇编,成为全球防沙治沙的典范。更多的中国模式“走出去”,不仅在于生态财富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传递治沙思路、增强治沙信心、丰富治沙方法,加深人类对沙漠的科学认识,合理开发利用沙漠,为世界上更多的沙漠变成绿洲,带来无限可能和希望。
全球行动“动起来”。携手防治荒漠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我国应以身作则,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示范,积极引领全球荒漠化防治的热潮。荒漠化防治全球行动应以国际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加强和落实区域和全球范围的双边、多边合作,不断推动全球荒漠化合作“动起来”。各国认真履行《荒漠化防治公约》,扩大《荒漠化防治公约》影响力,明确各荒漠化国家履约细则,提高各议定书约束力,促进联合履约。构建全球荒漠化监测网络,摸清全球荒漠化动态变化,编制各国荒漠化技术和需求清单,构建荒漠化防治技术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编制全球范围内的沙漠志,建立和建全国家沙漠公园,有效地保护自然沙漠(遗产)和沙漠文化(遗产)。
5 展望
60年来,我国的防沙治沙方略在沙漠化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示范。沙漠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未来沙漠化的防治仍然任重道远。
1)依法治沙,不断完善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律体系。
2)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加,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入中心,在政策扶持、宣传以及监管等领域,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3)科技治沙,发展完善沙漠学科理论基础,促进建立沙漠化防治理论与技术体系,推动提高沙漠治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4)中国模式,大力推广完善沙漠治理模式与技术。
5)评价体系,建立荒漠脆弱、退化生态系统分析和评价研究的评估指标体系。
6)国际合作,重视沙漠化防治领域的“走出去”与“引进来”,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广泛借鉴国外经验。
7)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思路,充分发掘新型能源,节约治理成本,重视经济作用,治理与利用两条腿走路。
8)沙产业,结合经济学、沙漠生态学和高新技术,把沙漠治理和经济发展结合,走沙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
[1] 王涛.中国沙漠与沙漠化[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5.
WANG Tao. Deserts and aeolian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M]. Shijiazhuang: Hebei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03:15.
[2] 国家林业局.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监测公报[EB/OL]. (2015- 12- 00)[2017- 06- 01].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9/content-831684.html.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ifth China National Desertification and Sand Inventory Monitoring. [EB/OL].(2015- 12- 00)[2017- 06- 01].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9/content-831684.html.
[3] 慈龙骏.中国的荒漠化及其防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5.
CI Longjun. Desertification and its control in China[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35.
[4] 林业部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方案[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30.
The Northwest-north-northeast Shelterbelts Construction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Forestry. The Three-north Shelterbelt Forest System construction overall-planning scheme[M]. Yinchuan: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3:30.
[5] 祁有祥,赵廷宁. 我国防沙治沙综述[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增刊):51.
QI Youxiang, ZHAO Tingning. Overview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2006,5(Sp):51.
[6] 王涛,赵哈林.中国沙漠科学的五十年[J].中国沙漠,2005,25(2):145.
WANG Tao, ZHAO Halin.Fifty-year history of China desert science[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5, 25(2):145.
[7] 董治宝.中国风沙物理研究50年(I)[J].中国沙漠,2005,25(3):293.
DONG Zhibao. Research achievement in aeolian physics in China for the last five decades (I)[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2005,25(3):293.
[8] 师玉环.浅谈沙生植物的生态适应性[J].生物学通报, 2010, 45(7):14.
SHI Yuhua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in Psammophyte[J]. Bulletin of Biology, 2010, 45(7):14.
[9] 肖洪浪.乌鲁木齐河终端湖区荒漠化过程中土壤植被系统的演替[J].地理科学,1990,10(4):379.
XIAO Honglang. The succession of soils and vegetation in desertification in the Terminal Lake area of the Urumqi River[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1990,10(4):379.
[10] 夏训诚,胡文康.塔克拉玛干沙漠资源与环境[J].中国科学(B辑),1993,23(8):889.
XIA Xuncheng, HU Wenkang. Deser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aklimakan Desert[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B),1993,23(8):889.
[11] 杜虎林,高前兆,李福兴,等.河西地区内陆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及其动态趋势分析[J].资源科学,1996,30(2):44.
DU Hulin, GAO Qianzhao, LI Fuxing, et al.Trend analysis of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and dynamics in the interior drainage basins of Hexi Area[J]. Resources Science,1996,30(2):44.
[12] 朱震达,王涛.中国沙漠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第四纪研究,1992(2): 97.
ZHU Zhenda, WANG Tao.Theory and practice on sandy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1992(2):97.
[13] 夏训诚,樊胜岳.中国沙漠科学研究进展[J].科学通报,2000,45(18):1908:1.
XIA Xuncheng, FAN Shengyue.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a desertification science[J].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0,45(18):1908:1.
[14] 周金星,韩学文,孔繁斌,等.我国荒漠化防治学科发展研究[J].世界林业研究,2003,16(2):42.
ZHOU Jinxing, HAN Xuewen, KONG Fanbin, et al.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China[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2003,16(2):42.
[15] 卢琦.中国沙情[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0:45.
LU Qi. Current desertification situation in China[M]. Beijing: Kaiming Press, 2000:45.
[16] 朱俊凤,朱震达,申元村,等.中国沙漠化防治[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25.
ZHU Junfeng, ZHU Zhenda, SHEN Yuancun, et al.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China[M]. Beijing: Chinese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1999:25.
[17] 郭彩贇,韩致文,李爱敏,等.库不齐沙漠生态治理与开发利用的典型模式[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53(1):112.
GUO Caiyun, HAN Zhiwen, LI Aimin, et al. The typical models of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the Hobq Desert[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2017,53(1):112.
[18] 杨文斌.低覆盖度治沙:原理、模式与效果[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75.
YANG Wenbi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with low coverage vegetation[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75.
[19] 胡孟春,贺昭和.西部沙漠化防治技术与模式[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9(3):12.
HU Mengchun, HE Zhaohe.Technique and model for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in West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2001, 9(3):12.
[20] 王涛.走向世界的中国沙漠化防治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沙漠,2001,21(1):1.
WANG Tao. Globalization of study and practice o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China[J].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2001,21(1):1.
[21] 卢琦,杨有林,王森,等.中国治沙启示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
LU Qi, YANG Youlin, WANG Sen, et al. China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pocalyps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