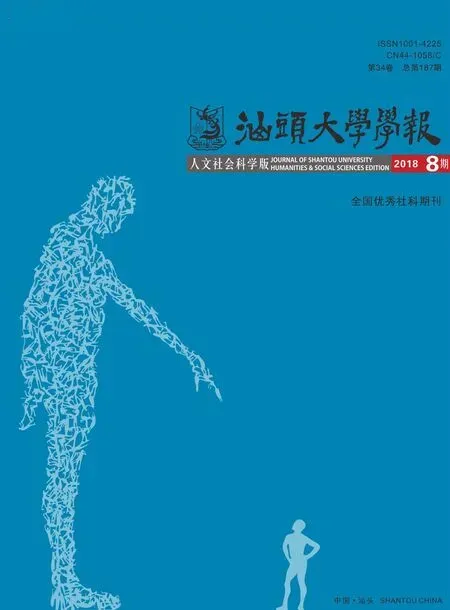鲁迅编辑实践之历史评价与再认识
李金龙,卢妙清
(1.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广东 汕头 515063;2.肇庆学院学报编辑部,广东 肇庆 526061)
一、被冷落的编辑家鲁迅
鲁迅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的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成就与高度毋庸置疑,相形之下,鲁迅投入大量的精力与心血所留下的编辑作品却应者寥寥,至少与同时代的知名刊物比,明显是相形见绌。不仅如此,鲁迅的编辑工作在当下的学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这种冷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界对于鲁迅编辑作品的研究与关注较为冷清,鲁迅研究学界最关注的问题集中在鲁迅思想、小说乃至翻译的研究,而且硕果累累、精彩纷呈,而鲁迅编辑工作的评价、鲁迅的编辑理念抑或编辑思想之研究则较为沉闷,无论是史料挖掘还是研究方法乃至研究结论都未出现令人满意的进展;另一方面是编辑学界对于同时代的编辑学家以及编辑史论述评说时,亦未提出有说服力的阐释框架,给人的错觉是鲁迅能跻身编辑家之列是因为沾了自身名气的光,因为无法列举出鲁迅特别值得称道的编辑成就。像陈独秀的《新青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四大杂志那样的名刊、大刊,因为它们或引时代风气之先,如《新青年》;或销量惊人,如中华书局的四大杂志;或生存周期长久,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如《东方杂志》。上述都各擅胜场,故能名重一时且为史家所重视。鲁迅编辑的作品则相差甚远,但他自身投入编辑事业的精力与时间绝不逊于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付出,可是能够说得全他编辑书刊的专业学者都很少,更遑论一般读者了,由此可见鲁迅编辑产品的受冷落程度。
确实,与风靡一时的大刊名刊比起来,鲁迅编辑的刊物简直就是小打小闹,编辑和作者群体也像草台班子,除了鲁迅自己外,几乎不见一位有名气的大家巨匠,根本难成气候,加之刊物生存周期普遍较短,故难入史家法眼。比如李扬主编的《民国文学名刊汇编》收录了7种名重一时的民国时期文学期刊,鲁迅编辑的期刊无一入选。编者明示其收录标准有三:首先是主编者均为文坛大家,号召力强且富有经验。(这一条鲁迅当仁不让地符合)其次是撰稿人多为知名作家和学者。第三是刊载作品粲然可观,最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1]事实上,这种遴选标准代表了文学研究界的一般看法,而鲁迅编辑的刊物除了符合第一条标准外,第三条也勉强够格,比如他在自己编辑的《莽原》中所刊载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阿长与山海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二十四孝图》等杂文也是现代散文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但这又涉及到杂文的文学评价问题,因为学界就如何评价鲁迅的杂文一向存有争议。关于第二条标准的不符合问题,实际上是鲁迅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他无论是对身边人许广平还是朋友都多次表示过,办刊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新人,“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所以《莽原》后来交给韦素园等人运营,《语丝》后期推荐柔石接编,《译文》走上正轨后让黄源独自挑大梁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鲁迅不仅仅是培养年轻的编辑,更主要是培养大批的年轻作家,这一点有众多文献可以证明,毋庸赘述。
尽管手上没有出现“名刊”“大刊”,但是就编辑本身的学养、能力和眼界来看,鲁迅与当时最优秀的编辑相比绝对丝毫不落下风,甚至是远超同侪的。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说法就是,鲁迅所据有的“文化资本”根本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不提陈独秀的《新青年》,还是以《民国文学名刊汇编》提到的7种“名刊”为列,《文学》杂志的编委会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组成,鲁迅在其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再比如主编《文学季刊》的郑振铎、靳以,主编《文季月刊》的巴金,主编《学文》的叶公超,主编《文学杂志》的朱光潜等,无论是文坛影响还是创作成就,比起鲁迅都差得远。简单的横向比较可以证明,无论以自身的能力、素质还是外部影响力乃至可以调动的文化资源来说,鲁迅都有足够的条件成为一流的编辑家,但偏偏他的编辑作品与编辑成就却未得到普遍认可。这种编辑者本身的高度评价与编辑作品的低认可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值得深入探讨。揆诸史实,可以发现,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报刊如《新青年》《申报自由谈》乃至靠出版新文学书籍起家的北新书局,很大程度上都是借鲁迅的作品和名望才得以成功。尤其是《阿Q正传》发表以后,鲁迅渐渐成为文坛最炙手可热的作者。从编辑与作者关系的角度看,鲁迅应该是最受编辑重视甚至是喜欢的作者,鲁迅的作品嘻笑怒骂,随意挥洒皆称杰作,不论什么内容都可以成为销量的保证,在鲁迅生命后期创作的《补天》《理水》《非攻》《采薇》《起死》等一经刊出,立刻导致刊物脱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有成就编辑杰作的能力和充分条件,但鲁迅编辑的书刊却并未如其创作一样脍炙人口,个中原因,值得深究。若要回答这一疑问,还是要回到鲁迅编辑实践,考察其编辑生涯的产出与作品,再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场域和历史条件综合考量,方有可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鲁迅的个性刚直耿介,想法也迥异流俗,当一众留学生同学高谈革命、救国方略时,鲁迅则转去仙台学医;当大部分人关注实业、社会、民生问题以求富国强兵之策时,鲁迅却偏偏又弃医从文,关注起国民精神的健康与完善。即使回国以后,鲁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习惯仍牢固地坚持下来。所以在民国甫一成立,处处欢天喜地的氛围中,鲁迅的《药》《阿Q正传》却不忘泼上一盆冷水,指出“换汤不换药”的实质及其荒谬性;身处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人人为革命气氛所激荡、鼓舞的情境下,鲁迅却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2]即使因此被所谓“革命文学家”们围攻,给扣上“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的帽子,鲁迅同样不肯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思考。1920年代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面对军阀的残暴和血腥手段,故都北平的知识界几乎集体失声,鲁迅却站出来,高度赞扬学生们殒身不恤的精神,声讨军阀的残暴和野蛮。1930年代,柔石、殷夫等左联青年被国民党残酷杀害,鲁迅不顾白色恐怖的巨大威胁,立刻站出来编辑出版了《前哨》杂志,以雄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声讨国民党的颛顼野蛮和专治独裁。由此可见,无论是声势浩大的文化围攻还是残酷野蛮的政治压迫,都未能迫使鲁迅放弃自己的立场,哓哓不休的诬蔑反倒成为鲁迅凸显个性人格的背景与噪音,正如鸟鸣与蝉噪适足以衬托出山林的清幽与阒寂一样。有这样的个性,鲁迅编辑的书刊不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在市场上表现一般似乎是可以找到答案的了。佩里·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复刊辞中说:“一本杂志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跟创办它的人密切相关”[3],事实上,不论是国民党右派文人还是革命左翼知识分子眼里,鲁迅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他既不会屈从于政治高压对无良的统治者歌功颂德,也不会因为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而对革命者的要求无条件地认同和辩护。对于读者来说,鲁迅的做法与办刊风格更是很难讨喜,从《新生》的流产到《域外小说集》的惨淡经营,无不证明着鲁迅在面对市场方面的“独到”眼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鲁迅总是能够成功地避开市场的热点和读者感兴趣的焦点,编辑出版一些既不受读者欢迎又很难令人评价的文化产品。
二、评价编辑家鲁迅的困难
从鲁迅编辑的书刊来看,他投入的精力和心血绝非泛泛。鲁迅一生共参与创办和编辑了17种报刊,另外编印《现代文艺丛书》(计划10种,因文禁只出4种,余6种被禁)《文艺连丛》(3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9种)《艺苑朝华》(5辑)等当时亟需的左翼文艺理论资源和《未名丛刊》(12种)《乌合丛书》(3种)、《奴隶丛书》(3种)、《译文丛书》《毁灭》《铁流》之类的创作典范,鲁迅还应时人之约编辑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其中鲁迅为《小说二集》撰写的编辑手记《导言》已经被奉为文学史研究的经典文本。旨在钩沉、保存史料的《嵇康集》《唐宋传奇集》《会嵇郡故书杂集》以及弘扬传统笔墨文化的《北平笺谱》(6册)、《十竹斋笺谱》编辑之工、印制之精良同样令时人叹服。
从编辑生涯来看,从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编纂出版开始,到1936年10月《译文》新2卷2期止,鲁迅在28年中几乎从未间断过编辑事业,这已经与其创作生涯相始终。从文字总量上看,鲁迅编辑经手的文字数量绝不逊于他一生的作品创作,甚至还略有超出,如果加上他生前自编的文集、手稿、札记,这一数量则更为惊人。这也从侧面证明鲁迅对编辑事业一以贯之的重视;从编辑工作的具体环节来说,从选题、组稿、校对、修订润色、选纸到印刷、装订,从封面设计、版型乃至行销企划,鲁迅无不亲力亲为,临终前在病床上还要许广平拿给他看《译文》的目录和广告,鲁迅亲自撰写的书刊广告达20余篇,序跋导言则多达70余篇,其中《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文本,以鲁迅的眼光和笔力,他所编辑的书刊内容质量绝对是非常过硬的,不提鲁迅自身操刀的创作,以他所编辑的《奔流》《译文》为例,大部分内容是经他选材然后或者是自己动笔翻译或者请相关的专业人才或者是学有所长的文学青年翻译,而且稿件到手后还要经过鲁迅一遍遍地反复修改润色,觉得满意了才会付梓印行。对于装帧、印刷乃至版型设计,鲁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大到版型、用纸、印刷方式,小到插图、版式、留白甚至标点的位置都要深思熟虑。作为文坛巨匠的鲁迅如此殚精竭虑的付出,最终结果就是毛边、封面简洁、图案质朴刚健、图文并茂、插图精美、留白疏朗、纸质上乘、印制精良等特征竟渐渐成为鲁迅编辑产品给人的特有印象。
文化产品“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由来有之,“叫好”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其内容质量上的优势所导致,毕竟在行家眼里,内容的好坏、质量的高低,很明显就可以判断出来。而“叫座”往往表达的是传播渠道的影响力与传播范围的广度。理想状态下,内容质量优势与传播渠道优势相匹配,内容质量的好坏决定传播范围大小。所谓“内容为王”,正是书刊出版乃至文化行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而在现实环境中,尤其是在内容生产相对匮乏的传统时代,传播渠道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与独立性,掌握了发行、宣传、售卖等渠道的书店、书局等出版机构,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影响广大读者的阅读消费需求甚至是对书刊内容质量的判断。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往往是单向的,以点对面的“撒网式”传播,很难与受众或者传播对象建立起及时的互动反馈,其传播效果也往往是等待时间来证实。反过来说,所谓大众读者或者市民读者,实际上往往缺乏对于内容质量的准确判断和独立思考,他们一方面接受书刊广告的宣传,另一方面又很难挖掘自身真正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渴盼,除了读者来函这种传统手段,他们甚至无法与作者建立起有效联系。“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在内容需求与审美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只有通过后者的提升才有望弥合,反之,通过降低“阳春白雪”的品格与质量来迎合后者,其结果不外乎媚俗。作为群体生活的蓝图,文化应该是导人向善、向上,而非向恶、向下,书刊的真正作用亦在于此。由此便不难理解,鲁迅为何对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品不假辞色,尤其在当时市民阶层刚刚兴起,阅读品味和文化需求刚刚成长萌发的时候,正确的导向和价值理念非常重要,而鸳鸯蝴蝶派对缺乏文化判断和鉴别能力的一般读者来说,其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劣书一方面会“败人胃口”,降低人的审美品味与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会像毒药一样侵蚀读者的心灵健康和精神世界。对于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有限的一般读者来说,阅读低劣的文化产品尤其有害,因为它无法提供有益的精神养分,更无法健全读者的心灵。
鲁迅独特的编辑导向以及其编辑文本造成的与通行评价标准的歧异导致其编辑的书刊在市场上表现不佳可以理解,但评价书刊的质量却不能以市场销量一概而论。事实上,书刊评价问题在今天也是个人言人殊的棘手问题,甚至专门发展出了以文献计量学为核心的不同评价体系,但无论是影响因子还是所谓H指数的评价指标,其本质实际上反映的是“该论文乃至该期刊的受欢迎程度”[4],并不能等同于刊物质量。以今天的编辑学眼光来看,评价书刊至少要从内容质量、设计质量、印装质量、文化导向以及社会影响几个方面综合评价。需要指出的是,市场销量与社会影响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一般来说,市场表现好可能是社会影响比较大,但是需要考虑的还有社会影响大与社会影响好坏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坏的社会影响大,那还不如没有。佩里·安德森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评价一个刊物的质量和价值,既不能以刊物寿命为标准,也不能单纯以销量论英雄,更应该关注的是其是否坚持正义、公平的办刊立场以及对良知、理性、道德等人类普遍价值的弘扬与阐发。[3]实际上强调的是编者和书刊在品格和精神上的追求与高度。王富仁先生在解释鲁迅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的时候也认为,鲁迅之所以给太史公崇高的评价,原因并不在于太史公的学识和《史记》中体现的笔法与历史学水准,更重要的是在于《史记》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史记》本身即是它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政治、经济还是其他目的服务的产物,太史公也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将揭示和呈现时代历史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和最高诉求。太史公所体现的气节与坚持、《史记》所达到的历史性高度是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5]在同样的意义上,作为编辑的鲁迅是一位真正的编辑家,他不屈从于政治强权,也不委身于经济资本,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刊,编自己的书,他是一位纯粹的编辑家,一位虔诚的“文化苦工”,他以编辑出版真正“于大众有益”的书刊作为自己编辑的最高诉求,为中国文化建设而殚精竭虑,鲁迅所达到的编辑学高度实在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因而,鲁迅的编辑实践不仅应该重新回到我们的研究中心,而且值得认真研究、揣摩、消化。鲁迅的编辑探索是留给我们的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毕竟,鲁迅身上不仅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而且还代表着另一种编辑路向和价值选择可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