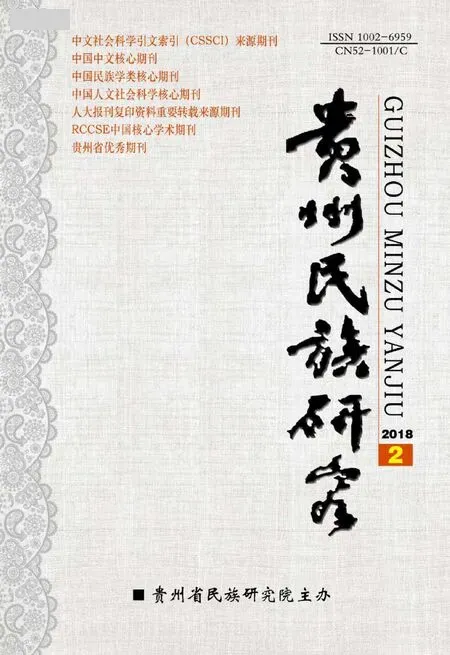古代河西走廊民族结构中的人口转移
张治国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 475001)
一、河西走廊历史上的人口转移及其对民族结构的影响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东西连接塔里木盆地,南北沟通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是中原地区通向西方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代以前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角逐的主要场地,随着匈奴游牧民族的强大,匈奴人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不堪匈奴民族对边境的不断侵扰和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汉武帝励精图治,派卫青、霍去病赶走了匈奴民族,夺得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古代河西走廊“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对西边控制西域,南边经营羌戎,北边抵挡匈奴等游牧民族都有重要作用,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关系着陕西、四川、以及中原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河西地区一直便是兵家争夺之地。为了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充分利用河西地区兵马供给的便利,汉朝以来的历代政权都采取了各种移民政策,通过南人北迁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另外,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及历史地理因素影响,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及隋唐五代宋时期,也有粟特、突厥、回鹘、吐古浑等少数民族陆续迁入河西走廊。至唐朝时期,凉州十城胡人有七城。虽然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但是只有匈奴、氏、羌、吐蕃及党项民族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而这些民族也没有最终沉积下来,随着各民族的移民发展及政治治理的推进,河西走廊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和氏羌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格局。[1]从根本上来说,河西走廊的民族结构变动由政治军事原因引起,但是最终的格局形成是由于各民族民众的人口迁徙,以及各民族文化融合交流共同作用而成。河西走廊的民族结构变动实际呈现了历史时期多民族人口的迁徙状况,反过来,多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也是解析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二、古代河西走廊多民族人口转移原因的总体归纳
总体来说,人口转移不外乎内外两种原因,内部原因是迁移目的地比当下居住地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外部原因是由于外力作用而造成的不得不迁移。虽然古代河西走廊民族人口转移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以上两种因素的交叉作用。
(一) 政治经济推动
河西走廊民族成分复杂,且距离中原王朝而言,又孤悬千里之外,因此对河西走廊的经略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的主要任务,虽然河西走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对于河西走廊的经营往往要受到兵马粮草供给的制约,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战争胜利的成果,防范附近少数民族的侵袭,自汉朝以来便开始“徙民实边政策”,为广袤的河西走廊迁移大量移民,解决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军队粮饷,缓解政府的军饷压力,且能免去内地民众辗转运输军需之苦。仅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四个郡县以后,“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另外古代劳动力的迁徙也为当地补充了大量的人力,壮大了西北边疆的军事实力,如在明清时期,当时朝廷提出了“耕战一体”的移民屯田政策,一边耕种,一边守卫边疆。最后,河西走廊的劳动力迁徙还有政府疏散人口之意,如清朝康熙时期,人口膨胀式增加,但可耕种的土地数量并未显著增长,也没有集约生产和机械化,人地矛盾日渐突出,为了确保民众温饱,朝廷不得不组织大量人员迁向人口稀少的河西地区。自康熙时期,清政府就制定了向西北特别是河西走廊地区移民的政策。这时候的劳动力迁移主要是通过招募、迁徙民户的方式来移民。请政府出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组织的移民,为河西走廊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这种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移民的决心。
(二)历史地理因素
移民迁入的方式有政府移民和民间自发移民两种方式,政府移民这种方式造成的主要结果是南人北迁;另一方面,河西走廊特有的历史地理条件也促成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众自发向当地迁徙。以魏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大量南迁为例,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在战国及西汉末年,青海河湟地区东北至龙门山,再向东北延伸至辽宁境内,存在一条农牧分界线,界线以北干旱寒冷,生产方式主要以游牧为主,界线以南,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主要以农耕为主。由于气候环境影响,中原地区肥沃的土地和适应生产的条件一直对少数民族都极富诱惑力,因此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时常侵扰中原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少数民族南下的趋势与地理环境的显著差异有直接关系。另外,游牧民族对气候环境有高度的依赖性,一旦气候变化,游牧民族的经济就可能濒临崩溃。根据史料记载,在东汉时期,气温下降较为明显,气候变化带来了植被面积缩小,草原面积缩小,少数民族游牧活动的范围也随之缩小,为了生存下去,少数民族不得不逐水草而居,向南方植被较好地区发展,可以说,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气候转冷是促成魏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南迁的重要原因。再次,自东汉时期,农牧分界线一再向北推移,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农耕区西边已抵达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植被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生产,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部分地区出现了沙漠化迹象,为了维持原来的游牧方式,游牧民族不得已继续南迁。[2]最后,汉末时期的政治混乱,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景象,虽然曹魏政权实施了一些屯田制度来改善,但是接下来的战乱又使得北方地区一片荒芜,这些都为民族内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3]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相互作用,促成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自发内迁。
(三) 区位优势
河西走廊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在地位位置上具有咽喉意义,不仅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也由于区位优势,使得更多的人们源源不断地穿过此通道,由西向东或者由东向西流动,该人口流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自汉武帝把河西走廊纳入国家版图以后,河西走廊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及至后来的西域都护府设置,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当地众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和商业交流提供了条件,加上大量的南人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农业物种,以及移民兴修的水利工程,使得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极大繁荣。先进的文化技术、丰饶的物产,相对发达的经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到河西走廊地区经商定居。特别是在中原发生各种战争动乱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域区位,也吸引了少部分汉姓大户迁居到当地避难。
三、历史上人口转移对河西走廊民族结构的影响
河西走廊民族结构变动由政治、经济多种原因共同促成,无论是何种因素,劳动力迁移都是最终结果,而这种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格局,更是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促成了当地多民族的融合发展。
(一) 促进民族融合
河西走廊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在连续不断的民族劳动力流动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频繁而直接,因此也形成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早在唐代时期,有关河西走廊就有“人兼北狄,俗杂西戎”之说,各民族之间的风俗相互濡染。南迁的农耕民族影响北方少数民族,北下的少数民族同样也在影响着农耕民族,如在魏晋墓壁画中便出现了汉人牧羊的图像,而随葬品也以马、牛、羊等为主,是当地汉人受游牧习俗影响的典型例证。在河西走廊,农牧并重是当地特有的文化传统,吐蕃时期,更使这种畜牧业的影响扩展到最大域度。民族之间的融合,在蒙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点从史料中的民族名称便可看出,在多民族杂居初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名号,如鲜卑族、羌族等,但是在蒙元时期各民族的历史名称逐渐从书中消失。到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各民族统称为番,有关番人的区别只是有民族风俗保留较为完整的生番以及生活习俗与汉族相差无几的熟番之分,民族融合度之高由此可见。对于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民众来说,无论是从哪里迁移来的民族,迁徙的原因怎么不同,最终都在河西走廊安家落户,成为河西走廊这个特殊地域的一员,河西走廊是众多民族共同的生存栖息地。各民族无高低之分,都是河西走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各民族已经形成了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他们而言,河西走廊才是他们最好的标示,正是由于这种意识观念,才使得当地各民族高度融合。
(二)促进文化整合
河西走廊贯通东西,衔接南北,在多民族的不断迁徙融合下,最终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居住的生存格局,独特的区位使得其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以月氏部落为例,由于匈奴追击,月氏部落大部分人远走中亚阿姆河流域,剩余部分人员退居走廊南山,则与诸羌共同居住,互通婚姻,与羌族文化融合。小月氏的文化轨迹是河西走廊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缩影,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都在河西走廊经历了相似的整合过程。虽然不同时代各民族移民进入河西走廊都会和当地的土著文化形成冲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在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广泛交流下,双方互相接受认同,互相融合,但是又保留着各种文化的特质,因此文化形态多元、体系繁杂是河西走廊的主要文化特征。总体而言,河西文化发源于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加上河西走廊的独特区位也成为部分中原文人和获罪汉族大户的庇护所,更是使得儒家文化成为河西文化的积淀。随着各民族的移民迁入,异质文化分子不同程度介入这种文化积淀中,因此也使得河西文化的文化杂糅和整合持续发生,但是基于儒学的统一根系,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又使得各种文化逐渐均匀一致,最终形成了高于原来民族文化层次的河西文化独有的文化圈。关于河西文化多元文化交融特征,季羡林先生曾经提出,敦煌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文化体系汇流的唯一地区,河西走廊文化交融整合的特征由此可见。
(三)推进经济发展
河西走廊的大量移民进入,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开垦耕种。在移民进入河西走廊后,便开始当地的开发建设,这种建设主要是农业水利建设,水利是农业之本,这在河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和河西走廊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河西走廊地区为干旱地区,水源主要来自祁连山的冰层融化。要使河西走廊迁入的大量移民能够生存下去,不仅要开荒,还必须建设人工水利工程,解决农业灌溉问题,这一点在清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史料记载,在关西地区沙洲卫一带,移民到达当地后,便对原有渠道进行疏通,又开挖了庆余渠、大有渠等五个渠道,在其他靖逆卫等四卫,同样也进行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建设。为了对所修缮的水利设施进行管理,清政府还特地设立了水利把总、看守闸夫、看守坝夫等编制,划出了水利官田,从修建到管理形成了完善的机制,为河西走廊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水利保障。大量水利设施建设,使得河西走廊开发出了良田无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4]另外,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优势,也使得走廊内成为东西南北货物流通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地或集散之地,而大量移民进入带来的消费契机,更是促成了当地商业的极大发展,南来北往的客商都聚集到此地经商。随着民间商业的蓬勃发展,清政府招募的商屯对于河西走廊的商业活动开展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凉州府一度成为河西走廊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业繁华极大地推动了河西走廊的经济发展。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南人北迁,由中原地区进入河西走廊的移民,把中原地区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也带入到河西走廊,先进的生产力成为驱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古代河西走廊民族结构变动中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启示
(一)劳动力迁移是民族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河西走廊民族结构变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民族劳动力迁移,西北少数民族的南下,中原地区民众的北上,官方组织和民间的自发移民,都在不断调整和重组新的民族格局,因此对于每个地区的民族结构分析必然不能忽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
(二)多民族劳动力迁移有助于区域文化的交流发展
对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移民,在多民族移民共同聚居时,必然会形成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文化融合,促进各族文化的更高层次发展,这种趋势并非人力可以阻挡。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同化,只要坚持文化特质,民族文化在交流中更高层次发展的同时,同样也能坚持自身文化的特色,河西走廊部分民族依然保持较为完整的民族文化习俗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白雪.魏晋南北朝河西走廊的民族结构与社会变动[D].兰州:兰州大学,2011.
[2]张俊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的特征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4,(11).
[3]张鹏立.魏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内迁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影响探析[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
[4]范富.清代康雍乾时期入迁河西走廊移民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