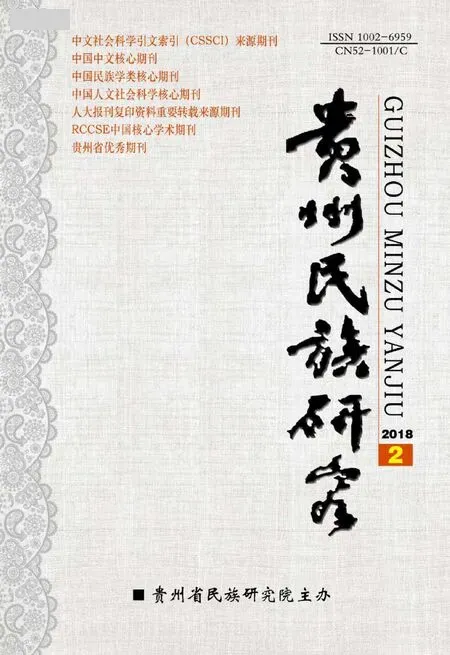明代至民国影响北川羌族认同变迁历史因素探析
安 波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一、地方族群和封建王朝的冲突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一)羌番族群活跃而张扬的行为成为地方冲突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唐代,广布羌氐族群的北川地区处于吐蕃与唐朝的军事交锋对峙下[1](P54),此后这一族群多样化地区成为汉地安全屏障,“内地依为长城”[1](P54)。自宋代及以后,中央王朝在此主要以羁縻施治,以大量封赐维护和实现了地区和平繁荣,“比宋讫元,谨知羁縻之方,予以彻侯之爵,至佩金玉印者相望于道,而州县俾得小康。”[1](P54)至明代,地区冲突骤然增多,史称“养痈而溃,至明世猖獗极矣”[1](P54),“凡遇粮夫经行,截杀无虚日”[1](P62)。自明景泰四年(1453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的112年间,史载石泉地区规模不等的“番”“蛮”的“寇”“掠”等冲突有15次。史谓“东路生羌,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相通,出没为寇,相沿不绝”。[2]这种不稳定状况一直为明王朝头疼。地方驻军对土著亦以顺迎为主,“诸番岁有赏赉,番恃强索要无已。其来堡也,有下马、上马、解渴、过堡酒及热衣、气力、偏手等钱。戍军更番亦俸以钱,曰新班、架梁、放狗、洒草、挂彩名目。”[1](P61)羌番这种频繁的劫掠以及对地方驻军钱费的索要,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剽悍和强势,戍边军队都对其有所畏让。在整体社会情景中,活跃而张扬的行为特征成为此时羌番恃力自雄的族群状态的生动体现,汉族身份与羌番产生关联尚且遥远。
(二)北川羌番与明王朝的冲突使其被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嘉靖乙巳(1545年) 冬所发生的“白草番”劫掠,引发了在皇帝朱厚熜严令下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由何卿、张时彻指挥约4万官军对石泉地区实施的行动,[1](P99)即今北川人所称“走马岭之战”。这次史载最大规模的冲突,给石泉地区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事件结束后,明王朝对“诸降附者,皆待以不死而责之赋。”[1](P100)石泉土著开始向明王朝国家体制纳赋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开始将石泉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的步伐。战后“青片、白草碉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1](P62)当地带有军事防御能力和族群符号象征的传统碉楼、碉房被夷平,代之以新式民居,农耕生产方式受到官方赞许。明王朝国家治理进程的开启,无形中成为石泉羌番后续族群身份认同变迁的重要前提。石泉地区自此不再有“番蛮”频繁劫掠的记载。
(三)地方冲突给当地“番蛮”带来的记忆让变易族属身份成为其寻求和平稳定生活的自然选择。万历年间,松潘南部的“番蛮”因劫掠被官军攻剿,曾常与之联合呼应的石泉番民此时唯恐惹祸上身,为“讨得安身”,万历七年(1579年),青片、白草两河流域“生番”“前来投降,愿做百姓”,“熟番全保等说,各番不会窝藏丢骨、人荒、没舌三寨蛮子。”[3]此时族属称谓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明朝官方眼中,已出现“生番”“熟番”之别;在熟番的表达中,曾与之往来密切的丢骨、人荒、没舌的番人被称为了“蛮子”,以示彼此之区别,族群认同的差异化已开始出现。这种原曾紧密关联的族群中出现的称谓区别,既是他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也可能是当地“一截骂一截”现象最早的开端。石泉羌番还“具言岁寨贡黄蜡一斤,赋菽粮二斗如故,今请益菽粮三斗,示不复为羌也。”[4],同时他们“俱愿更换姓名,每年万寿圣节、长至,各番俱叩头。”[1](P60)这种开始在每年皇帝生日或官员到来时承诺的叩头行为,象征着他们对王朝的归附。羌番“不复为羌”、“更换姓名”的表达,鲜明体现出地区动荡所留下的灾难记忆及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共同推动了石泉羌番对自我族群身份的主动变更。
(四) 明王朝开启并推进了北川羌汉融合进程,清王朝初期国家力量对其产生了间接巩固影响。石泉羌番的投顺让巡抚王廷瞻颇为惊叹,他在《处置风村白草投顺等番疏》[1](P60)中称各寨“一旦回心向化,诚是奇事”“一旦倾心甚众,愿为编氓,而变异番姓,从习汉仪,此二百余年蜀川之所仅有者也。”在皇帝诏令下,风村、白草等番地自此收入石泉版籍。[1](P60)石泉县令李茂元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他制作了多顶上书姓名的汉冠戴于诸羌头上“易其姓名”,诸羌兴高采烈“捧其首以谢。”[1](P60-61)这场仪式是象征性的,更是标志性的,“诸羌”由此开启了大规模的“变异番姓,从习汉仪”进程。在明王朝国家在场的强力背景下,以“汉仪”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主体文化特征开始成为“诸羌”学习、模仿的内容,它开始冲击着“诸羌”既有的文化传统,深刻改变着族群内部的认同观念。明清政权交替之际,国家力量在石泉地区弱化,史称番羌“凶悍自擅”,[1](P61)再次出现地区动荡不安,造成清康熙二年(1663年)又一次较大征伐,“松潘总兵何德成剿上下五簇番蛮,平之。”[1](P61)这次征伐宣示了清王朝强大的国家在场,此后当地再无因“边夷”而生的地区冲突,客观上巩固了业已开始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变迁过程。
二、“汉仪”教化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北川地区,“至前明而土司设焉,清代改土归流,化夷为汉,衣裳斑斓,言语侏离之辈无不感慨而遵道。”[5](卷之伍《土司》)但实际上石泉地区土司对所辖番寨控制极其有限,“番乱”频发即为明证,多次因“抚番无术”而受官府黜斥,[1](P47、62)早在清康熙四十二年便永罢土司,仅存抚夷,政归于县。[1](P61)当地虽有“改土归流即为汉”的说法,但北川羌族在清代发生趋向“汉仪”认同的实质变迁,却非“改土归流”所能解释,它蕴含着丰富的选择性的历史行为,官方所主导呈现出体系化的教化举措是重要的推动途径。
(一)封建王朝对羌民的教化主要体现为“汉仪”的推行,它呈现出多样进路,礼仪、习俗、服饰、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都是其涵化层面。在王朝力量的作用下,构造出北川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汉仪”文化场景。除了前述拆除碉楼、碉房、赐汉姓外,在地方官员“随时训迪之”的影响下,“婚姻丧礼”“与汉民一体”,到乾隆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1](P62)男女衣冠、装束已多如汉人。[1](P52~53)地方官府对火葬、艾炙、祈神治病等俗“详加晓谕……风亦渐止”。[1](P53)石泉县令姜炳璋还亲自劝说羌人纠改丧父焚骨、杀牛疗疾等习俗,说得地方土著“纷纷父老都点头,赭汉津津頞额流”[1](P117)。地方官员所推行“教化”从外在的符号象征涵盖到内在的文化逻辑,积几百年之效,极大推动了北川整体“汉仪”社会文化场景的构建。
(二)教育是整个教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它对推行“汉仪”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体系化教育的推行。一是科举考试,清代官府为鼓励支持石泉民众读书应考,为该“神禹之邦”小县分配了“文武童生各八名”的较多取士名额。还出现了周边县份豪民前来“买粮寄户”钻政策空子参加科考现象,官府对此进行了打击,以维护石泉“培植斯文”。[1](P42)二是县城官学,历史最久的是始于宋高宗绍兴年间的学宫教育,叠经损毁重建。清乾隆姜炳璋又建酉山书院,专供童生授业。[6](P622)这虽是特定人员才能享受的官学教育,但我们看到历代官方的重视,在明代羌番“向化”后,它发挥了当地高等教育的中心辐射作用。三是义学机制,清道光七年,设本城、陈家坝场、漩坪场、通口场义学。道光十年,增设片口场、让乡归龙寺(今香泉乡)义学。这些平民化教育的推行,使得更多的羌番后裔受到“汉仪”文化教育。四是普遍的国民教育,光绪、宣统、民国时期先后在全县广泛设立小学、国民学校。五是私塾教育,清末民国有村塾、家塾、族塾、门馆四类,在各乡多有设立。[6](P622~623)
其次是地方官员在教育的推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者往往持有在民族地区进行“汉仪”文化建构的动力倾向和目标情怀,在他们眼中这些“蛮夷”族群代表着愚昧、野蛮、落后,在羌番中推行“汉仪”使之向化是他们重要的教化之责,他们对此表现积极甚至亲履教习。如乾隆时期石泉地区正处于番、汉文化交混状态,姜炳璋在《白草歌》中记录了他下乡时的见闻感受,“儿童拍手呼阿叭,我欲与言称‘没煞’。咿嘤杂嘈难为听,唤译译来为予说。”当他夜宿农家“忽闻隔陇有书声,知是延师夜课读。跫然心喜唤出来,亲为授句再三告。”鲜明表露出姜县令对番语和课读诗书持有的不同态度。他还饱有宏愿立誓“愿将花雨洗蛮风”,“花雨”是指以“汉仪”为主体的文化形态,“蛮风”则指羌番文化形态,表达出姜氏对地域社会文化重构的愿望。对众多官员而言,在民族地方对“汉仪”文化的传播和建构,是政绩和文化双重动力驱使下的表达,这些动力倾向深刻影响了他们日常施治的行为和目标。
最后,带有浓厚功利性目标追求的科举考试教育在石泉县建立了一套人生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将当地人导入并固化其中。在北川流传的清道光年间白草番民刘自元为获得汉民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而改变汉、番界碑之事,[7]折射出当时石泉番民对科举考试的积极向往。这种向往,并非简单止于后来民国北川官方带有“汉仪”文化夸耀所说的“向慕文化”,它更承载了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价值。“当时科举盛行,知读书应试最为尊贵”,[5]读书科考,不仅可以摆脱番民身份及与之相伴的族群身份困境,更可能带来社会地位提高,受人尊敬,融入整个“汉仪”社会文化体系,拥有地道文明形象,整体改善个人生存境遇。可能正是由于对这种类似的意义象征和潜在利益的了解,为了和平稳定的生活和今后子孙更好的生存发展,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 青片、白草归降的番民就主动提出并获官府允许“送子读书”,此时石泉地区“汉仪”教育的大幕已经开启。
在读书问题上,官方为推行汉仪影响“番蛮”,羌民为求得更好生存境遇,双方基于不同立场出发形成了一致的选择,从而使读书科考在石泉地区获得强化推动,这成为了羌番族群价值评判和边界消解的重要文化根基。
三、地域社会族群认同张力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历史上北川羌番被纳入封建王朝的国家治理进程后,在当地形成的教化利益格局除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地方族群意识形态中对“汉仪”的接纳认可,同时在更广阔的民间社会建构起对“番”、“蛮”形象的排拒态势,地域社会的族群认同张力持续存在。“番”人在具象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交流中,其自身原有文化符号不断弱化,其自身族群身份认同不断遭受他我认同的冲击和否定并走向式微。在20世纪90年代原北川县政协常委乔邦成的记述中反映出,清末至民国年间,羌人进城卖东西常被“估买估卖”,遭遇各种抽头,不被接纳住店,其族群身份、服饰、语言常遭遇各种以族群身份为表达的差异化对待,其“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于是不得不改着汉装,连‘打乡谈’(即说羌语)也只好忘掉。”[8](P135)20世纪20年代,北川县小坝乡的人们外出都回避吐露自己真实的来源地。[9]羌番与其所在区域迁入较早的汉民还共同经受着被污名化的对待,往往下游居民将上游居民称为“蛮子”。
被污名化的身份带给当地人的是以族群身份为划分的社会差异化对待的困境和无奈的内心体验。这种惯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部分时期内仍有所残留。
虽然社会情境中彼时北川土著深陷这种族群认同的张力状态,但民间社会在影响他们普遍趋向接纳“汉仪”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乃是后来之事,因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明代和上述所现的族际互动中的巨大差异性。对于这一强大的地域社会族群张力状态的形成,官方贯之几百年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王朝并无民族平等的方针政策,现在北川当地政治文化精英将彼时族群治理措施称为“强制汉化”,[6](P173)[10]即指通过宣扬“汉仪”文化的优秀,解构当地族群身份和文化特征,以多样的“教化”进路来达到对土著文化的重塑和“汉仪”文化的建构,体现出对地方族群文化的涵化。官方权威的涵化影响激发了民间的表达,从而形成并强化了地域社会对羌番文化特征和族群身份差异化对待的社会认同表达,地域社会族群身份认同的张力表达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国民政府在民族政策上也鼓励西南土著人群汉化,[11]甚至把许多民族说成是汉族的宗支,[12]“五族共和”的光辉并未照到川西北这一隅,更未对这一较小族群有特别关注,地域社会在土著身份认同上的张力表达未有任何改变。
当族群身份成为社会污名,北川羌人鲜明感受到自己与他者的族群差异,但这种差异感的强化刺激并未维护和巩固其族群身份和意识,反而成为其回避隐匿既有族群身份和文化符号,消解族群认同,跨越族群身份边界,隐化原有民族标签,出现更多地接纳“汉仪”文化身份符号的重要因素。这展现出族群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群体建构过程,族群认同形成于各种吸纳和排斥的过程中的非独立性特点。这种巴斯式的族群理解视角,[13]在解析明代至民国时期北川羌人族群认同变迁中显得尤为有力。其动力因素便是在以族群身份为划分的整个社会场景中无时无处不在的张力状态,持续着从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多向度施力的挤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北川羌人所面对的族群身份差异化对待,造成了他们对其族群身份的隐匿回避。在这样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族群文化符号逐渐消失,族群认同出现新的选择。
四、人口迁入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在上述有关汉、番身份的种种利害关系影响下,北川历史上以四川内地汉民为主的人口迁入,既造成了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血缘交融,也给当地羌番带来了建构祖源记忆的契机,汉人身份成为他们借用来作为适应社会生存环境新状态的选择。
在长期经受“汉仪”洗礼后,北川羌番1932年尚有约18855人。[14]但在1953年人口普查中,北川全县自我申报为羌族的仅59人,1964年人口普查羌族为201人,[6](P163)族群人口数出现巨大差异。综合考察清代至民国时期战争、瘟疫、迁徙等影响人口数量因素,羌族人口不至锐减至如此之少。张国焘回顾1935年红军进入北川时,当地族群状况“汉番杂处”,“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区域,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番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我们到这里好像是身履异域,我军中占大多数的通南巴籍战士也不例外”。[15]这反映出当时北川不仅羌人数量较多,而且仍然具有一定的族群文化特征,让红军能明显感受到当地与汉区的不同。18年后在民族成分申报中所出现的这种异常的自我族群身份表达,正是前述种种历史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当地羌人实现了一种不约而同的身份共谋,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普遍倾向于汉族而非羌族的对自我族群身份的认同选择,现实的数据成为复杂历史动力影响下的简单表达。
在另一方面,民间的社会图景显示出在北川地区广泛存在着人们关于其祖源为“湖广”某地的传说。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招民填川诏》所启动的“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上人口变迁的重大事件,然而未必有大量“湖广”之人“填”入石泉县,因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石泉县志》对此重大事件竟毫无记载。当然我们难以否认在后来这些来来往往的迁徙人口中包含着带有“湖广”祖源记忆的人群,在北川当地也确有一定数量有着清晰祖源记忆并在四川内地如遂宁、蓬溪等地有着祖源明证的居住人群。北川地处四川内地通往西北民族地区的山区要道,是人员物资流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在县内重要流域白草河的小坝场镇边就有元代“茶盐道路通行”“打狗埋石为誓”的石刻,[16]至民国仍多有背夫客商出入北川。晚清民国以来,川内各地大量人员因从事罂粟种植鸦片贸易,或逃避战乱、饥荒、抓壮丁而进入该地,现在不少当地人还保留着这段尚不久远的清晰祖源记忆。这些人口的往来迁移给当地羌番和移民群体间提供了相互交往接触的机会,增进了族群隔阂的消弭,也创造了婚姻血缘交融的条件,并随之产生更宽广的亲属关系。现在北川山区,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格局,当地人喻之为“竹根亲”。
在地域社会生活环境的自我调适中,血缘、亲缘,甚至仅仅是移民事件,都给当地羌民提供了修改祖源记忆的重要契机。来自“湖广”的叙述,在这里就是作为典型“汉民”身份的另一种表达。“湖广”地理位置的遥远和“填四川”事件历史的久远,代际传承祖源记忆中的疏漏和含糊——这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可资利用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对族群身份解释具有更好的弹性适应力。对祖源记忆的修改或模糊化,为其在共和国初期人口普查时登记为汉族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追溯。而这种祖源的修改,正是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北川土著长期受汉仪教化的结构化引导鼓励以及族群身份认同张力影响所导致的结果。
历史上北川人口的往来迁移带来了羌人族群认同的变迁,但非单纯的人口因素所致,它折射出在国家、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当地土著在族属选择上的工具理性体现[17]。这种选择成为人口迁移与族群认同张力问题相遇的产物,人口的迁入正好提供了缓释张力的社会途径。族群及其边界的流动性特点彰显出族群认同建构的过程性实践整合隐喻[18]。历史上人口迁入北川,为面临族群身份困境的当地羌番提供了一个除从习汉仪、教化读书外有力地实现并佐证其族群认同变迁的重要条件。
五、结语
北川羌族从明代至民国几百年间,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以多种进路呈现出从远离“汉仪”文化特征到对“汉仪”文化接纳与认可的转变,到民国时期基本已自称“汉人”。地方族群与封建王朝的冲突、汉仪教化、族群认同的张力表达、人口的迁入成为历史上影响这一变迁的重要因素。其中的汉仪建构、教育培养、族群互动、祖源修改等等现象表达,体现出族群认同在主动与被动、国家与地方、血缘与亲缘、记忆与失忆的复杂交织互动中经受着多维度和力度的持续施力的变迁影响,其变迁过程折射出这种历史逻辑的表达。其变迁结果,既呈现出族群边界的模糊化或消解,也呈现出族群文化的交融。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基础,[19](P16)这种文化交融最终形成羌汉族群身份的高度融合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土著文化不断式微,以华夏主体文化为表达的“汉仪”发展演变成为其中最主要的话语表达,最终呈现出地域性的共融形态的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过程性和结果性表达,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族群历史演变发展的一个范例。
参考文献:
[1]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清乾隆石泉县志[M].点注本.陈朋点注.绵阳:绵阳市浩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008.
[2]张廷玉.明史,第二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23.
[3]邓存泳.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龙安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814.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2:451.
[5]杨钧衡.北川县志[M].绵竹商业场大美兴代印版,民国廿一年(1932) .
[6]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北川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
[7]北川羌自治县政协.民间文学集成[M].北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协.2013:73.
[8]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川羌族资料选集[M].北川: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M].1987:9.
[10]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协.羌地北川[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57.
[11]王明珂.当代中国民族政策下的羌族及其历史——兼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的“近代建构论”[J].中国大陆研究,2000(民国89年),43(7):2.
[12]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147.
[13][挪威]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4]北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北川县民族宗教志[M].北川:北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1994:5.
[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12-214.
[16]李绍明.北川小坝元代至元石刻题记考略[M]//北川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川羌族资料选集.1991:23-29.
[17]辛允星,赵旭东.羌族下山的行动逻辑——一种身份认同视角下的生存策略选择[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7.
[18]何虎.试论族群建构和文化认同[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7(4) :297.
[19]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