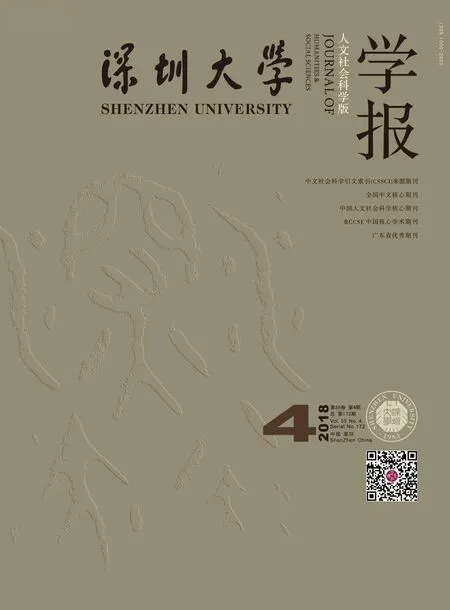有别·交胜·合一:张载天人思想的结构特质
刘 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源自于人类的生存实践。人类的生存既是对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与改良,也包括了对精神世界的勾画与建构,以此形成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类的延续,便是在物质与精神交织的网络中不断生成、变化。因此,天人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极具现代意义的研究课题①。
如果我们查阅现存的所有符号文献,对天人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但其正式形成则是以《中庸》《易传》为代表②。 《中庸》《易传》基本上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③,特别是汉宋。这两个时期的哲学家围绕“天人关系”进行了理论化、哲学化的建构。在宋代,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正式提出“天人合一”一词,对天人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诠释。基于对人类实践行为的反思,张载从同知用、合内外两个层面,论述了天人有别、交胜、合一的三种关系,形成了完备且自洽的天人体系。
一、从知看天人有别
人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是生存和延续的必要前提。张载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认识,特别强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1](P21),“天人异知, 不足以尽明”[1](P20)。但天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天地的运行及其对世间万物的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同于人因为思虑忧患而产生的行为动作。天地的运行没有心思和意识,天道只是一种客观行为④;人则因为有思虑和忧患,其行为具有目的性。人必须“用思虑忧患以经世”,这既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追求,也是人主体精神的真正体现。但这是一个不断演化与发展的过程。人类一直处于对天地法则的模仿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从天道之中分判出了“人之道”。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将天人混为一谈,人之道,不可以混通天道。正如张载在《横渠易说》中所指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则仁尔,此其为能弘道。”“天无意,……圣人之于天下,法则无不善也。”“天则无心,……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虽圣亦人耳……。”[1](P188-189)
张载分析“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时,指出:
天能为性,人谋为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故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1](P21,232)
天的能力是其自然法则的呈现,人的能力则是思维意识的表现。贤能的人能够体悟天地法则,并不会狂妄到将私欲的谋划随意凌驾于天地法则之上,只是充分发挥主体的认知本能以运用法则,所以说:“天地设立了上下之位,圣人仿效它来成就自己的才能。”
天地为人提供了存在和活动的场所、资源,人必须发挥、挖掘自己的才智,认知、弘扬天地万物运行的道理,承担经营、救济天下的责任,即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人道虽不同于天道,但可以弘扬天道,成为天地万物的主持者。所以说:“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圣人则有忧患,不得似天。‘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圣人,主天地之物,又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必也为之经营,不可以有优付之无忧。 ”[1](P185)
《周易》恒卦《彖辞》说“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里的“天地万物之情”以及“天地之大义”“天地之心”均不能理解为天的情感和意识活动,因为“天地固无思虑”,这些都是人的“思虑忖度”和对天地法则运行的赞美。
复卦《彖辞》说“复见其天地之心”,张载认为:
大抵言 “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尝有息?正以静有何期程?此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又有甚首尾起灭?自有天地以来以岂于今,盖为静而动。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于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静,则安能久?然必从此去,盖静者进德之基也。[1](P113)
天地之心,亦只是指天地化生万物的能力,人们认为这是天地最大的德行。复卦之象是“雷在地中”,象征阳气开始生长,天道运行又一循环的开始。天道运行没有休止的时候,一直是动静相因,循环不已,难以说什么时候是开始、什么时候是结尾。天地自产生到现在,从最初始的静止转动之后,天的运行“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一直生生不息地运行着,未曾休息停歇。人的德性和天道的动静之道相吻合,都有自己的存在状态和运行方式。如果人心的安静来自“造作安排”,那是不能持久的。心只有顺从德性,仿佛天道的运行一般自然,才是真正处于安静宁和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才能精进德性、近乎天道。
天道的自然运化,不存在思虑与私心。人常有思虑忧患,又有“意必固我”之私;圣人亦有思虑忧患,却能无私如天,“尽心知性知天”,与天为一。天与人虽有不同,但是“天人不须强分。”明确天人的区别,是正确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与前提。
张载对天的理解有三重,一是天的自然性,二是天的神圣性,三是天的哲学性。自然性是天的最基础属性,由此而赋予其神圣性含义,并在自然与神圣基础上对“天(太虚)”进行了本体化的建构。因此,基于天人的区别,张载对天与人的关系给出了两重答案,一则是交胜,一则是合一。
张载的这一区分,与自《尚书·洪范》及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说”不同。张载以天的“自然”含义为基础,摒弃了其“意志性”与“神秘性”含义。在《横渠易说》及《正蒙》的相关表述中,张载反复强调了圣人对天地的“效法”,突出人的主体性与认知性。因此,张载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知既承接了孔孟儒学天人一体、天人相通的思想,也十分重视老子及其之后的天人有别、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天人理论⑤。
二、从用看天人交胜
“天人交胜”作为张载对天人关系的第二重阐释,是他从人类社会盛衰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1](P20)。 张载解释《周易·系辞下》“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认为:“世衰则天人交胜,其道不一,易之情也。”这一论断可能与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命题有渊源。
刘禹锡在《天论》⑥中对天人作了一个定位,认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论上》),“天与人,万物之尤者也”(《天论中》)。 论及天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时,刘禹锡认为“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上》),“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所以,“天与人交相胜”(《天论中》)。此即是说,天的基本作用是“生殖”,是强者制服弱者的规律。人的主要作用在于 “法制”,规定“是非”标准并予以执行。社会安定,是非分明,“法制”具有效力,是“人理胜”;社会混乱,是非不明,赏罚不分,“法制”失去效力,则是为“天理胜”。
此外,刘禹锡还提出了万物 “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这其中也包括了天与人这对万物的代表。可以看出,在刘禹锡的表述中,“还相用”是万物“交相胜”的基础。天对人的作用是自然过程,人对天(自然界)的作用则是思虑谋划。刘禹锡认为,天无私无为,不存在与人争胜。所谓天胜,实质是人对自己无能的推脱而已。因此,他十分强调“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天论上》)
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思想,主要是对荀子 《天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吸收了柳宗元《天说》天人“各行不相予”的观点。刘禹锡强调天人相分,反对将天作为意志和神性理解,批评从董仲舒到韩愈的“天人感应”论说。
人类一直生活在一种奋斗的姿态当中,随着生存境遇的变化,迫使人类不断探索与挖掘自然界,必然容易形成与天地对立的局面。当人们团结一致时,虽然可以通过对生产力的提升来获取生存质量的优化,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破坏着世界的生态平衡。物欲的过度膨胀,又破坏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稳定,从而不可避免地激化社会矛盾,人类群体不断分化,群体力量被削弱。在这种境遇下,人类很容易丧失对自然灾害的正常抵抗能力。所谓祥瑞、天谴,亦无非是人类能否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双重稳定而已。
纷争总归是要结束的,张载、柳宗元、刘禹锡等学者基于天人之分,积极探讨了人类如何取得生存境遇的优化问题。沿着这一思路,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天人有别”与“天人交胜”则是“合一”的认识前提。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真正的统一性,乃是先假定了分离,而复于此一分离中重建其自身的那一种统一性。”[2]当然,张载这里并非是假设,而认为是一种真实。同时,这与从荀子到刘禹锡主张和侧重“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归宿不同,张载在自然基础上生发并建构了人文性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归宿,致力于人类自身的重建。
三、从合内外看天人合一
张载在《正蒙·乾称篇第十七》中指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1](P65)这便是“天人合一”一词的正式出现。这一论断,既是张载对宋以前天人关系问题的凝练,也是对其天人哲学体系的一种表述⑦。张载的学术目的在于,建构高度哲学化的儒家理论,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抵消佛老的不良影响,彰显儒学的理论特质,改善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境遇,甚至是实现万世的太平。
张载认为,通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的“致学—工夫”途径,使诚与明互相贯通,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 “得天而未始遗人”,正如《周易》所说的“不遗、不流、不过”恰如其分的程度。经由为学的努力,可以实现“成圣”的理想:在领悟“天”及“天道”本质时,以德性的修养与修炼为辅助,以“穷理”(“明”)与“尽性”(“诚”)两方面互为根据、交互为用[3]。张载这一理论的根源在《周易》和《中庸》⑧,其进路为内在省察与外在践履,并媾合在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理论架构中⑨。
如何实现“天人合一”,首先必须明确其内在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对天人及其差异的认知,二是对天人之联系的认知,三是对“合”的认知。最后凝结为“一”,即境界或境域(Situation)。张载对天人的异同与联系的理解,充分体现了其理性认知与价值取向,并且落实在工夫实践与生命境界上。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 ‘天人合一’之‘合’是一种境界之合,是美学目的论之合。用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的话说,这个‘合’就是即内在即超越、即道德即宗教、即存有即活动的智的直觉。 ”[4]
(一)“先识造化”
“穷理尽性”是一种偏向认知的进路。穷理又以“识造化”为开始,所谓“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1](P206)。造化指天地万物运作的动力和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蕴含着万物的变化过程及其秩序,体现着其各自的秉性或本质。张载认为:“不见易则不识造化,不识造化则不知性命。既不识造化,则将何谓之性命也?”[1](P206)⑩在世间一切变化的过程中,可以认知和把握“造化”,从而体悟性命之理。但张载强调“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1](P206)
穷理以尽性为直接目的,以穷尽人的天地之性为核心。“性”是指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体现其各自的秉性或本质。万物(包括人)均禀受了本原的天地之性和“形而后”的气质之性,且因气(气质)的“刚柔、缓速、清浊”而各有差异。人性的本原不是气质之性,而是天地之性。作为天地之性根源的太虚是“至善”的,故而天地之性在价值论上也是指向至善的,并具有了超越性、普遍性和永恒性[5](P545)。
在“穷理”与“尽性”之间,张载引入了孟子“尽心知性”的思想。张载在《正蒙》中指出:“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P24)“心”是指人特有的认知能力——合心官知觉与天地之性的“德性之知”、合感官知觉与气质之性的“见闻之知”。张载强调“尽心”,是要从宇宙整体、从造化之道去体悟“德性”的根源,以确立宏阔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5](P551)。
在心性论的前提下,人们应该通过 “变化气质”、“大心体物”、“虚心存养”、“知礼成性”等道德修养的工夫实践,糅合 “自明诚”与 “自诚明”[1](P21),实现学者至大人一节的生命提升。
(二)“穷神知化”
在“穷理尽性”之后,张载以“穷神知化”接续,强调大人至圣人一节的特殊性。这是从认识论向境界论转化的一节,或者说是知识的内在化与实践化的过程。张载认为:“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精义入神,养之至也。 ”[1](P216-217)又说“精义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则在思勉力行,可以扩而至之;未知或知以上事,是圣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犹大而化之,大则人为可勉也,化则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后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别隔为一节。 ”[1](P217)张载解释《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谓:“德盛者,神化可以穷尽,故君子崇之。”又谓:“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易》所谓‘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免哉? ”[1](P218)
张载将“穷神知化”作为德性上“天人合一”的最后环节。在解释《系辞上》“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十分慎重地告诫学者:“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 ”[1](P188)张载反复强调,大人至圣人一节不是人为的思虑可以强勉实现的,犹如乾卦九二至九五之变。这一过程,是大人德性成熟圆满的过程,需要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平,必须剔除安排造作和私意妄念。
“天人合一”作为在认识论基础上的道德修养,从“先识造化”到“穷神知化”集中体现了《易传》“仁智合一存乎圣”的思想。
(三)“与天地参”
“天人合一”的最高阶段是“德位皆造”的圣王,强调德性与事业(进德修业)的双重圆满,可以“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是与天地参矣。”[1](P187)张载的“圣王”的观念与《大学》“修身——平天下”的思路一致。然而这种圣王在地位上,已经不局限于现实政治的最高统治者这一角色,而更偏向于道德主体的社会贡献。
基于对《周易》作者“制作”之义的探求,张载很重视《易传》中“礼”的思想。作为社会秩序的“礼”,在形式和内涵上都是对天地之道的效法,亦是为了保障人类生存境遇的稳健提升。
张载在解读《礼记说·礼运篇》时指出:“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谓礼。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礼本天之自然”[1](P191)。 张载此说虽为《礼记》而发,然其思路与《易传》的乾坤观及三才之道完全相符。张载又说“知理则能制礼”[1](P327),这是将《易传》中“穷理”与“知礼”“制礼”“尽礼”的关系凸显了出来。此外,张载还强调心和情对礼的影响,指出“礼之原在心”,“人情所安即礼也”。在《易传》中则表现为圣人之心对万物万民的感通以及因情制宜的权变思想。
礼不仅关乎个人的德性修养,也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密切相关。礼学从周公开始,虽几经崩坏,但其维系人类社会的贡献却是无可辩驳的。张载解释《系辞上》“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时指出: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譬之天地设位则造化行乎其中。知则务崇,礼则惟欲乎卑,成性须是知礼,存存则是长存。知礼亦如天地设位[1](P197)。 又说: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如何变[1](P193)!
张载明确指出礼所效法的天地所固有的秩序,具有一种永恒性原则。即使是圣人,也必须知礼才能成性,才能弘扬天道。通过礼,可以实现“合内外之道”[1](P191),贯通天人之际。 知礼,则能对天人关系建立一种原则性认知,确立规范。这也是孔子“立于礼”精神的体现。
张载认为:“知极其高,故效天;礼着实处,故法地。 人必礼以立,失礼则孰为道? ”[1](P192)知礼,就是效法天地,人的主体精神才能有所确立;不知礼,则容易违背规则,便不利于弘道。《周易·系辞下》谓“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张载解释说:“君逸臣劳。上古无君臣尊卑劳逸治别,故制以礼。 ”[1](P212)这也是在强调圣人取法乾坤之道,创制礼典,规范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使上下能各从其分。
《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一语对圣人制礼之意则表达地更为明显,张载解释认为:
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皆是也。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又不可以一概言。……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方是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今学者则须是执礼,盖礼亦是自会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尽天下之事,守礼亦未为失,但大人见之,则为非礼非义,不时中也。君子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则自能比物丑类,亦能见得时中。[1](P264,328)
张载强调对礼的会通与时宜,认为君子当于前言往行中体会“时中”之义,不可拘泥于已有的文字和行为。人的境界不同,所见礼义亦有所不同,如常人与大人之别。大人是《周易》中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均体现在乾卦中。一指九二有德无位之大人,一指九五德位皆造之大人。九二是德性未显、德行未施的圣人,九五则是德性彰显、德行普施的圣人。二者没有实质区别,所处时位不同而已。张载认为:
庸言庸行,盖天下经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措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此颜子所以求龙德正中,乾乾进德,思处其极,未敢以方体之常安吾止也。[1](P73)
“庸言庸行”就是礼,是诚信的语言与严谨的行为,是天下所共同遵循的常德至道。圣人的德行也因之普施于万物,天下的礼乐制度也因之兴盛于四方。这种境界只有以“穷神知化”、通晓时宜的方式才能实践和维持。即使如颜回,在追求盛德中正之道时,也必须在德性上持之以恒,追求极致(穷理尽性),不敢以常规限制其德业的进修。
《系辞》三陈九卦之德,因其 “切于人事”[1](P242)。 首论履卦,认为是履“德之基”,“和而至”,“以和行”。《易传》认为君子效法履卦之象,确定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安定万民的心志,所以履卦(礼)是建立德业的根基;履卦所蕴含的德性光明,所以和顺而崇高,教人以礼,和顺行事。张载解释“履,和而至”谓:“和必以礼节之,注意极佳。”张载以礼解履,认为用礼来节制“和”才能赋予其最好的意义,这是对《易传》履卦德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天人关系的最终状态,也必然地表现为“天人合一”之“和”。
四、结 语
张载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P10)。其天人思想也符合这一原则。天人相互对待而有所分别,则各呈现其能力;随着自然时空的变迁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人类必然与所生存的世界产生冲突,或强势或孱弱;随着认知能力与德性境界的提升,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必然驱使着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因此,天人的这三重关系结构,最终所呈现的“合一”状态,既具有精神境界的意义,也涵盖了人们对社会伦理与自然秩序的执着。
“天人合一”既可以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道德修养实践,更应该成为人间社会与自然生态的现实。虽然这一境遇可能很难发生,但这一观念将会不断警示人们: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道德修为、制度建设、智力开发,人类才能够在精神领域、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中无限趋近这一理想的生命境界。因此,如果我们还立志于追求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张载“天人合一”思想必然是我们今天处理好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注:
①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历史地位及现代意义,请参见刘笑敢:《天人合一:学术、学说和信仰——再论中国哲学之身份及研究取向的不同》,载《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71-102页。
② 《中庸》的影响远不及《易传》,时至北宋因为理学的兴起,《中庸》的影响才逐渐明显,甚至超越了《易传》。
③ 也有学者认为,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归源于《易经》或者把《易经》的基本思想归结于“天人合一”是没有根据的。如李晨阳:《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地、人”三才——兼论儒家环境哲学的基本架构》,载《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第5-10页。
④徐复观曾指出“在孔子心目中的天,只是对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现象而感觉到有一个宇宙生命、宇宙法则的存在”,“决不曾认为那是人格神的存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88页。)张载此处似乎也是遵循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只是借用老子之言来作清晰的表述。
⑤ 关于儒家“天人合一”观的“天人一体”特性,可参考刘学智:《“天人合一”即“天人和谐”?——解读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一个误区》,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关于汉代以前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及其辨析,可参考张强:《汉前“天人合一”观的历史嬗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⑥ 关于《天论》的文本,可参考[唐]刘禹锡: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8-147 页;[唐]刘禹锡著,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987-995页。
⑦陈俊民认为,在“究天人之际”的问题上,张载思想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由周至汉是“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化论,由晋至唐是“天人二本”的宇宙“体用”论,张载则提出了“天人一气”的宇宙本体论。见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77页。
⑧ 《横渠易说》与“天人关系”的问题,历来有学者关注,如冯友兰、张岱年等前辈在哲学史类著作中早有论述。亦有撰文研究者,如刘学智:《<横渠易说>与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载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刘学智:《<横渠易说>与理学天人新义》,载《哲学与文化》1992 年第 5 期;丁原明:《<横渠易说>的新天人观》,刘学智、[韩]高康玉主编《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35页等。此外亦有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如谢荣华:《<横渠易说>的天人关系论》,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⑨ 有学者指出,“天人合一”的进路,主要有 “尽心—知性—知天”的内省察路线、“制天命而用之”的外行动路线、阴阳五行的宇宙系统论路线、“通天下一气”的宇宙生成论路线、“道通天地”的本体论路线五种。参康中乾、王有熙:《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的五种思想路线》,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此外,还可参考丁为祥:《论“天人合一”》,载《北大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关于张载的宇宙论与心性论,请参考林乐昌《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76页,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⑩关于“先识造化”在张载思想及其学派中的地位,可参考李存山:《“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