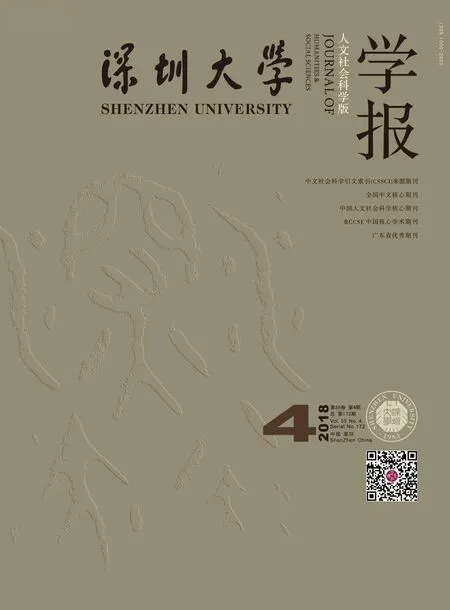基因编辑的良法善治:在谦抑与开放之间
田 野,刘 霞
(1.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072;2.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湖北 武汉 430023)
科学改变世界,人类在利用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以至于改造的对象超越了客观世界而延伸至人类自身,基因编辑(Gene Editing)就是这样一项神奇而充满争议的技术。基因编辑如上帝之手,在分子层面对缺陷基因进行替换、嵌入、删除等编辑操作,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人类大部分疾病都是由基因缺陷引起的,拥有了改变基因的技术,也就拥有了剔除疾病根源的神奇力量。然而基因编辑带来的不只是健康红利,还有一连串极为敏感而棘手的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1]。这项技术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争议不断,特别是生殖系基因编辑争议最大①。胚胎具有发展成人的潜能,对胚胎的基因编辑是否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目前尚难以确保,错误编辑的恶果将在后代中永久流传,给人类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人类还可能利用基因编辑“定制”超级婴儿,造成纳粹优生学复辟的风险[2]。为了避免技术的异化和滥用,必须以法律之力勒住其缰绳。基因编辑应当被允许还是禁止?合理利用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应给出明确指引。探索规范基因编辑之良法以求生命科学领域之善治②,是生物科技时代的重大法治命题。
一、基因编辑引发的全球争议
基因编辑是近几年生命科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字眼,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浪潮,而我国因一则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2015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人类胚胎中引发地中海贫血的异常基因,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Protein&Cell杂志上③,这被认为是首个公开报道的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这一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2015年6月2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西科学伦理鸿沟》的文章,认为中国科学家正在跨越西方长久以来公认的伦理边界[3]。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誉,乃至于成为一部分人指责我国科学家不遵守伦理操守的“证据”。然而,意见并不统一,科学界权威杂志《自然》将黄军就评选为2015年度十大人物[4]。
以黄军就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生殖系基因编辑正当性的大讨论。反对者主要是从安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生殖系基因编辑会给定制婴儿或其他潜在的技术滥用铺平道路,违背社会伦理和法律规定,故应当禁止任何形式的生殖系基因操作,同时应寻求其他可替代方法[5]。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时间会改变一切,生殖系基因编辑不可避免,完善后代基因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再者,该类技术可能是治愈部分严重疾病——如艾滋病、糖尿病唯一或最佳的手段,若禁止一切此类研究,人类则永远无法获得这些利益[6]。
极高的关注度、激烈的争论、混乱的认识,使寻找科学共同体针对基因编辑共识的任务迫在眉睫。2015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发起的人类基因编辑高峰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最终达成了一些有价值的共识: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在临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但许可将该技术应用于开展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前研究。这次峰会属国际学术团体的自发行动,所发表的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过其积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代表着面对基因技术风险人类自省的最初尝试,对于澄清混乱认知、凝聚共识具有重大意义。在黄军就事件以及华盛顿峰会之后,基因编辑的研究并未止步,事实上,英国、瑞典等国家都批准了一些新的涉及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研究项目。现实中基因编辑研究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探索更有效的规制基因编辑的法律之路仍旧任重而道远。
二、基因编辑的利益与风险
技术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该种双刃剑效应在科学领域普遍存在,基因编辑也不例外。然而,与其他科学技术不同的是,基因编辑改造的是人类自身,因此其误用和滥用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更加令人生畏。基因编辑兼具天使和恶魔两张面孔,而究竟是善的一面多一些还是恶的方面多一些,人类目前尚没有能力给出肯定的回答。当下十分有必要对基因编辑可能产生的各种利益和风险进行全面客观的考量,以作为未来政策制定和立法规范之准备。
(一)精准医疗视野下基因编辑的善用
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在近些年被大力倡导,成为医疗发展的方向。2015年,科技部召开了“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600亿元进行相关研究。此外,《“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精准医疗,精准医疗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若论医疗之精准,未有能超出基因编辑之右者。传统的医疗手段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共同生物特征科学认知的基础上的,极少针对单独的个体设计治疗方案。而事实上每个个体在遗传特征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忽略个性化差异的一般化医疗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现代基因技术的支持下,则可以根据个人的基因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开展更加精准的靶向用药。在基因编辑面世之前,人类只有检测基因和分析基因的能力,但是没有改变基因的能力。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则使人类有能力通过对基因的 “裁剪”在根本上革除致病的根源,从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精准医疗方面,基因编辑大有可为。首先,基因编辑有利于攻克人类重大疾病治疗的难关。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在目前仍被视为“绝症”,常规的治疗手段难以根治,基因编辑技术可能使这一局面发生逆转,使绝症成为可治之症。例如删除女性BRCA基因,对于治疗乳腺癌、卵巢癌有重大帮助。目前,争议相对较小的体细胞基因编辑已经“先行先试”,在临床上有一定范围的应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④。其次,基因编辑有助于提高生育质量和预防生殖缺陷。对于有遗传疾病的家族,生育的风险极高,获得健康后代的愿望难以实现。在具备良好监管和安全性得到确保的前提下,通过基因编辑对导致遗传疾病的缺陷基因进行修改、删除,则可以有效地预防生殖中先天残障的发生,由此受益的将不是一代人,而是以后的各代人。当然,生殖系基因编辑在目前还存在极大的争议,尚未应用于临床,但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是必要的。最后,基因编辑还有助于新药的研发和个性化靶向用药,利于产生更精准的治疗效果。
(二)基因编辑的问题与风险
相对于利益,基因编辑的风险更加受到关注。基因编辑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不确定风险下的安全性疑虑
基因编辑的初衷是出于善的目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然而其结果则具有很高的不可预知性。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尚不成熟,科学性、安全性、有效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然而,基因编辑技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目前比较流行的CRISPR-Cas9是第三代技术,第四代技术也正在研发中。随着技术的改进升级,基因编辑的安全性、有效性将不断获得提升。尽管如此,未知的风险永远存在。对于生命的奥秘,人类到底掌握了多少?永远是一个谜。即使是在当时认为绝对安全的基因修改,最终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和有害的。一旦对基因进行了错误的修改,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可能造成严重的疾病、功能障碍,乃至于产生新的绝症。特别是在生殖系基因编辑的情形下,不良的生物特征可能将代代相传。在电脑上错误的文件编辑可以撤销操作,基因编辑则具有不可逆性,没有后悔的机会。目前基因编辑的准确性并不高,在黄军就团队的基因编辑实验中,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靶”现象。广东医科大学进行的另一项基因编辑实验,有效率只有15%。在安全性没有得到确保的情况下,将基因编辑仓促应用于临床,显然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当前对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强烈抵制情绪,正是源于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对不确定损害的恐惧。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恐惧会产生某些积极效果,使人类保持高度谨慎,不敢贸然行事。
2.生命法益与人性尊严
生殖系基因编辑操作的对象是体外胚胎和生殖细胞,其具有发展成人的潜能,由此必然引发基因编辑是否侵害生命法益和人性尊严的担忧。关于体外胚胎的法律地位,在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对此问题见仁见智。从比较法来看,各国立法态度并不统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法律明确认可胚胎就是人,如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胚胎是法律上的拟制人,享有同新生婴儿一样的法律地位[7]。在大多数国家,并不直接肯定体外胚胎具有人的地位,不过毫无例外地均赋予其较高的伦理和法律地位,给予特别的保护。基因编辑要对胚胎进行“裁剪”,对于剩余的胚胎可能要销毁、抛弃,这是否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否违背伦理乃至构成违法?若要尽可能减小道德困境的阻力,应关注基因编辑对象的选择。体外胚胎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同类型的体外胚胎所承载的伦理意义及其风险是有差别的,应尽可能选择利用伦理争议较小的体外胚胎。例如,根据胚胎是否具备发展成人的可能,分为可存活的胚胎和不可存活的胚胎,应优先选择后者进行编辑。黄军就基因编辑实验采用的就是不可存活的体外胚胎。再者,胚胎是不断分裂的,对受精之日起14天内的胚胎才可以进行编辑,这也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做法,我国也是如此。在有充分的理由不得不对胚胎进行编辑的情况下,还应重视在实际操作层面对胚胎的尊重,以体面的方式使用胚胎。
3.代际同意问题
代际同意(Intergenerational Consent)是生殖系基因操作难以避免的一个棘手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好当代与子代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的相关研究、试验,均需以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为前提。胚胎作为潜在的人,对其进行基因编辑操作,从理论上来讲需征得由该胚胎发展为人的子代同意。问题在于应如何获取其同意[8]?显然胚胎的同意在现实上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其父母是否有权代其同意?若父母有权代理同意,则其代理权限该如何划定?权利如何行使?父母会不会因个人偏好和价值取向对胚胎进行基因筛选与改造,以打造心目中的“完美宝宝”?父母能否做到以未来子女的利益为出发点,尊重子代可能的自主选择,避免将子代置于当代人的掌握和控制之下,使之在出生之前就丧失了自我[9]?为了解决代际同意的困境,需要对潜在父母的代理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
4.基因优选与社会不公
生殖系基因编辑给社会的公平公正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因是以高、精、尖为特征的基因编辑技术具有稀缺性,加之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基因编辑技术很有可能沦为富人的专利。若仅有富人才有能力为其后代创造更为优秀的健康、智力等条件,则穷人及其后代的利益将被边缘化,最终陷入富人的后代会愈加优秀、穷人的后代会愈加落后的恶性循环。
5.其他 ELSI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外,基因编辑还可能带来其他复杂的伦理、社会与法律问题,国际上统称之为ELSI(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ssues)议题。 例如,生殖系基因编辑若被用于筛选优秀的后代,会不会导致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优生主义再复辟?基因编辑使人类的进化过程由天择到人择,人类可以扮演上帝吗[10]?会不会使人类原有的“先天+后天”的发展模式被打破,陷入基因决定论,使“先天不足”的人丧失生活自信?会不会导致大众对优良基因趋之若鹜,而对不够完美的基因予以摒弃,从而造成严重的基因歧视[11]?
综上所述,基因编辑利益与风险并存。一方面基因编辑给饱受疾病折磨的人类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令人不寒而栗。这种两面性造成了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基因编辑时立场的纠结,既垂涎于其健康红利而不忍完全禁止,又忌惮其风险而加以严格管制。这也决定了针对基因编辑的法律调整必须以平衡为理念,谨慎而积极地协调各种利益。应当看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而人性有善恶。法律的角色应是抑恶扬善,为基因编辑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
三、规制基因编辑的国际经验:从混乱中寻找共识
基因编辑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争议事件频发,加强法律规范日益迫切。对于这一新鲜事物,世界各国在管制立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12]。混乱是这一领域法律政策的基本状况,从混乱中寻找共识的努力正在进行中。
(一)欧洲国家对基因编辑的多元立场
在欧洲,对生殖系基因编辑研究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立场。英国总体上持比较开放的立场。2015年2月3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了允许对卵子进行线粒体DNA替代疗法以防止脑损伤、心脏病等严重遗传疾病的法案。该项立法实质上是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允许对人类生殖系进行基因干预的临床操作,这无疑为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合法化开了一扇窗。2016年2月1日,英国人类生育与胚胎学管理局批准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研究员Kathy·Niakan开展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的请求[13]。瑞典也对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研究持积极态度,2015年6月,依据胚胎干细胞研究法案及伦理审查法案,瑞典批准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弗雷德里克·兰纳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的申请[14]。与英国和瑞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由于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特别是二战时纳粹人体试验带来的灾难警示,德国在人类胚胎研究方面一直持严格限制的立场,同时对于生殖系干预采取以刑事责任威慑的态度。
(二)美国对基因编辑管制态度的模糊化
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对基因编辑问题高度关注。在中山大学人胚编辑事件发生后不久,2015年4月29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是一条不可跨越的界限,禁止开展此类研究,该院将对此类项目的申请不予批准,也不予提供联邦基金予以资助。然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模糊的,其仅是不予批准及赞助向联邦卫生研究院申请此类研究的项目,但由州政府批准、赞助及私人赞助的生殖系基因编辑项目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15]。正因如此,2017年8月3日,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联合其他团体及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的核心内容是:在伦理、法律等问题达成共识的大前提下,若人胚基因编辑技术处于严密监督且获得胚胎捐献者的知情同意,则允许对该人胚基因编辑研究项目进行资助。同时,在技术成熟、伦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公众同意、程序公开、医疗必要等情况下,不排除人胚基因编辑技术有被应用于临床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民间对于人胚基因编辑的研究与应用是持谨慎而积极态度的。
(三)亚洲国家对基因编辑的管制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基因编辑既无明文禁止,也无特别许可,不过有关生物医学研究的一般规范具有一定的解释适用意义。例如《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配子、合子和胚胎进行基因操作。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伦理原则》中规定:不得实施各种违反道德伦理的配子、胚胎研究和临床应用。日本是世界上拥有生育诊所数量较高的国家之一,不过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基因编辑作出明确规定。2016年4月,日本政府下设的生命伦理专门调查委员会宣布,允许日本相关机构在基础研究中“编辑”人类受精卵的基因,但出于安全和伦理考虑,禁止将该技术用于临床,同时要求胚胎基因编辑的研究进展需及时公开以保证安全、透明。在韩国,《生命伦理法》对有关人类胚胎的研究持高压立场,这与黄禹锡事件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在该法案下,生殖系基因编辑难有存在的空间。2017年8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正了未被植入子宫的、人类胚胎中的、与遗传性心脏疾病“肥厚型心肌病(HCM)”有关的基因变异。文章发表后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韩国媒体称是韩国学者(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导了这项研究,只是由于受到韩国生命伦理相关法律的限制,研究团队只能将开发好的基因剪刀技术拱手让予他人,提供给外国同行进行实验,最终的实验由美国研究人员为主的国际团队共同完成⑤。这一事件凸显了法律的宽严设置对科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此外,在以色列,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严格禁止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修正,但若经过咨询委员会的推荐则可以在相关法律中对此项规定进行修改,这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研究与发展做了铺垫[16]。
(四)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努力
基因编辑不是某一国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面临的挑战。鉴于基因编辑潜在的巨大风险,加强法律规制的需求日益迫切。而面对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法律则远远滞后。综观各国对基因编辑的规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确定、不统一是对现状的最好概括。对于基因编辑是否合法及其合理边界如何划定,鲜见有法律给出正面回应和特别规定。上述对各国立场的分析,都是基于既有法中关于基因研究高度概括的原则性规定或周边规定推演得出的,对于基因编辑法律始终欠一个正面的表态。法律立场的暧昧不清,使有关基因编辑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应用无所依归、去向不明。各国基于本国国情而对基因编辑选择不同的立场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对于这一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澄清过于混乱的认识、达成基本的共识仍是十分必要的。
不少学者倡导发展跨国基因编辑规制框架,然而究竟通过何种形式凝聚共识,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单从立法的层面来讲,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当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在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形成国际条约的难度极大。在当下,更务实的选择是由非官方的国际组织、权威的学术团体等自发开展广泛的交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认识,并形成行动指南、伦理守则等软法性质的规范。对此基因编辑华盛顿峰会开了一个好头,具有里程碑意义[17]。
华盛顿峰会通过激烈的讨论,在科学界自发形成了对基因编辑的基本共识。峰会的最终成果是一份被世界期待已久的声明,这份声明毫无疑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模糊而混乱的认识,对现阶段基因编辑的规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声明指出:对早期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进行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前提条件是,被修改的生殖细胞不得用于怀孕目的。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于临床是不负责任的,除非并且直到:(1)基于对风险、利益、可替代性方法的充分理解和适当平衡,相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2)关于被建议的应用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3)临床应用处于适当的监管之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临床应用符合这些标准。安全性还不够,具有说服性的有效案例十分有限,许多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禁止生殖系基因编辑。然而,声明同时也指出:科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认知也会发生演进和改变,因此对生殖系基因编辑应当定期进行重新评估。声明还提出了将论坛建设成为一个长效机制的倡议,以推动国际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可以看出,声明对基因编辑采取了既谨慎又开放的态度。峰会组委会主席、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在宣读声明时解释道:“基因编辑应该暂缓或禁止吗?我想声明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对这两个词都不想用,也没有使用。”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于临床的大门并没有被堵死,只是在当前条件尚不成熟。限于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前研究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在当下就是被允许的,但需以安全性、有效性得到确保和监管到位为条件。声明阐明的上述立场,可以说就是目前阶段人类关于基因编辑的基本共识。
四、谦抑而开放的基因编辑法律治理之路
鉴于基因编辑对于改善人类健康的重大意义与同时潜在的巨大风险,又由于该领域法律规范的严重滞后,探索规制基因编辑良好法律的任务如箭在弦。然而所谓的“良法”何在?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基因编辑法律规制的成熟模式可供遵循,整个世界都处在踌躇与探索之中。在笔者看来,基因编辑法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法的谦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即一方面持高度谨慎和严格管制的立场,另一方面避免过度保守而使科学裹足不前。
(一)基因编辑的法律底线:人性尊严
围绕基因编辑产生的所有疑虑、争议、问题与风险,其中心皆在于人性尊严面临的威胁与捍卫。大胆推进基因编辑的科学研究与应用,抑或是将维护人的尊严、避免技术滥用的风险作为中心,是主要矛盾之所在。人性尊严,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与庄严,维护人性尊严是法律的宗旨所在。人性尊严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包括来自科学技术的威胁。在所有科学领域中,基因科学与人性尊严有着最近便的直线联系,其原因在于基因是生命的密码,或者说基因就是生命本身。也正因如此,基因科学给人性尊严带来的威胁远胜于其他科学。而在基因科学场域内部,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又高于其他基因技术。如果说基因测序和人类基因图谱面世破译了生命密码,基因编辑则是要修改生命密码,显然后者对人性尊严的挑战更甚。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必须怀着最高的敬畏之心。
在技术上能实现的,在现实中都是可以做的吗?这是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提出的自省。在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中,应当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作出新的反思。应当看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立场上存在显著不同,前者关注的是“什么是我能做到的”,后者关注的则是“什么是允许做的”[18]。过去的几十年间,人类在基因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也因此渐渐形成了对基因技术的狂热气氛,技术痴迷导致的风险正在逼近。与自然科学家对技术的无休止追求不同,伦理学家和法学家对于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与人文价值危机充满忧虑,并试图将忧患意识传达给社会以引起警醒。伦理和法律就像是科学狂热主义的镇静剂,这种角色是绝对必要的。
自省是人类的宝贵品质,对于基因编辑这样的高风险、高伦理性技术,坚持自省更加弥足珍贵。基因编辑不能逾越人性尊严,这是应当在法律中明确昭示的底线。所谓底线,即人性尊严具有至上性,无论如何也不能突破。当多项均为正当的利益(如科学利益、产业利益、健康利益等)发生冲突时,其地位不是平起平坐的,人性尊严应被置于超然地位。
(二)法的谦抑性与开放性
基因编辑当前正徘徊在十字路口,面对不确定性,抉择十分艰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下,如何平衡法的谦抑性与开放性是基因编辑法律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法律应保持谨慎,对于基因编辑进行规制的法更是如此。由于基因编辑操作的对象是生命本身,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当前基因编辑技术在科学层面并不成熟,安全性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伦理层面的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解决,必要的社会共识尚未达成,有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地将基因编辑应用于敏感研究和临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放慢脚步、观望,进行风险评估,等到确定安全时再采取行动,才是明智的选择。目前对于基因编辑的法律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在根本上这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对于基因编辑的认识十分有限,没有十足的把握制定出妥适的法律。社会舆论一直呼吁法律对基因编辑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给出正面干脆的回答,然而放眼全球,迄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真正立法对此作出正面回应。在笔者看来,在前路未卜的情况下法律急于表态未必是明智的,而暂时的立法留白未尝不是上策。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一直对基因编辑保持沉默,而是要在法律规范中保持谦抑性。所谓谦抑性,一是要避免仓促立法和极端立场,为未来发展预留必要的弹性空间和各种可能性。法律对基因编辑给出的结论无论是禁止还是许可,在目前来看都是武断和仓促的。由于基因编辑兼有利益和风险,规范基因编辑的法律应避免结论的简单化、一刀切。二是要将风险降到最低,对于潜在的损害风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此立法对基因编辑应采取严格管制的高压立场,特别是对部分高度敏感的研究和应用,暂时不应允许进行或施加最严格的条件限制。总之,对于基因编辑的立法规范,在有十足的把握之前,适度的保守比冒进要好得多。
另一方面,规范基因编辑的法律又要避免过度消极的立场,造成科学和社会裹足不前。谨慎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的恐惧和停滞不前,科学与社会将无法进步。如果绝对禁止基因编辑,则一切风险皆可杜绝,但人类也因此无法享受其带来的科学红利。当前的争议和担忧皆源于损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在未来适当的历史时点,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得到充分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共识达成,立法是否还应当禁止基因编辑的进行?或者说生殖系基因编辑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被允许[19]?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针对基因编辑的立法在保持谦抑性的前提下,同时应具有开放性,以避免成为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声明没有对基因编辑采用 “暂缓”或“禁止”的措辞,而是采取在严格规范下鼓励发展的立场。即使是对于当前争议巨大的生殖系基因编辑是否应用于临床,声明也没有完全关闭大门,而是强调定期进行重新评估,保留了未来开放的可能性。
(三)基因编辑的有限许可与动态调整
科学与实践总是先行于法律,规制基因编辑的法律短期内没有办法完善。法律的缺位有可能造成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因缺乏必要的规则指引而陷入混乱,为此在当下就需要大概划定一个基因编辑利用的合法边界。基因编辑具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每一场景所涉风险的高低是不同的,伦理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技术的成熟度也是有差别的,其中有些基因编辑的安全性经过长期的科学实验已经得到较好的验证。对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不能指望一次完成,而应该采取分阶段动态调整的策略,成熟一些,就放开一些。
现阶段应当将一些安全有效性得到确保的基因编辑通过适当的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以结束无法可依的局面。根据风险分级和安全性得到确保的程度,应允许以下目的的基因编辑:(1)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前研究中的基因编辑。研究不是临床,风险被控制在实验室内,不会造成人类的实际健康受到损害。再者,研究是获得知识的必经之路,不允许研究科学就无法获得进步。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只有通过不断的实验才能得到提升[20]。对目前基因编辑实验中脱靶率高的不足,除了开展更多的科学实验别无他途。基础性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临床应用,这是从科学到应用转化的通常次第,其中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是临床应用的必要准备,且损害风险较低,故应当得到允许。针对生殖系基因编辑的基础与临床前研究也应当被许可,但其应当受到比体细胞基因编辑更严格的监管。(2)体细胞基因编辑与临床基因治疗。体细胞的基因编辑风险较小,争议也较小,相关的科学实验已经开展了几十年,其中一些已经被应用于临床治疗,并有不少治愈疑难疾病的成功案例。当然即使是体细胞基因编辑也并非是无风险,仍有确保安全性和严格监管的问题。
对基因编辑的法律许可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目前不被许可的基因编辑,如果未来安全性得到确保,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解禁。目前争议最大的是:是否可以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于临床?在现阶段,此类基因编辑不应当被允许,因为其尚不成熟,安全性没有保障。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将生殖系基因编辑应用于临床是否永远不应被允许?抑或可能在将来条件成熟时被允许?应当看到,此类基因编辑对于预防生殖缺陷具有真实的利益,因此具备充足的目的正当性。从华盛顿声明来看,对这类基因编辑仍旧保持开放性的立场。国际上其他一些开展基因编辑伦理与政策研究的组织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如英国的欣克斯顿小组发表的声明指出:当所有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治理要求均得到满足时,将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生殖也许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21]。此外,为增强目的的基因编辑在现阶段不应被允许,至于未来是否可能被允许,届时仍需要新的评估。
对基因编辑有范围限制、有条件限定的许可,以及许可范围的动态调整,是前述法律谦抑性和开放性原则相结合的具体贯彻,这一独特领域的法律既要观照现在,也要包容未来。
(四)基因编辑的监管机制
要使基因编辑趋利避害,现阶段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科学问题,需要依靠更多的科学试验完成;二是确保基因编辑被用于正当的目的,避免误用和滥用,这是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安全监管来实现。基因编辑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至关重要,该机制应以伦理审查为中心,目的在于确保拟开展的基因编辑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目前,我国对于基因编辑并无专门的法律规范,相关规定散见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以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这些规范对生物医学研究的监管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不足,例如过于概括、可操作性差、审查标准不统一、程序机制不合理等等,并且没有顾及到基因编辑的特殊性。考虑到基因编辑的重要性和风险性,应加强安全监管,以伦理审查为中心,监管机制的完善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建立中央和基层二级伦理审查机制。研究机构自身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虽可起到一定程度的过滤风险的作用,但容易受到内部因素的干预,难以保证独立客观性。建议由国家卫计委下的国家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对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预审通过的基因编辑项目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基因编辑研究项目才可着手实施。此外,伦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需具有多样性,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法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第二,长效的跟踪审查程序。我国当前伦理审查大多局限于研究初期,一旦研究机构通过启动研究的伦理审查后便高枕无忧,容易诱发后续道德风险。坚持跟踪审查原则的关键举措是实行研究机构定期报告制度,如研究责任人向机构伦理委员会作年度报告,机构伦理委员会向卫计委下设的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每两年作一次报告等。此外,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还可视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对违规操作、侵犯人格尊严等不良事件予以通报,并向社会公示,及时暂停、终止相关研究。第三,审查规程的统一与规范化。建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伦理审查章程及相应的操作规范,并根据技术的进步不断予以调整,为基因编辑的伦理审查提供统一、灵活的指导,同时提高研究机构进行项目申请的可预期性。第四,加强对科研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责任约束。对于严重违背伦理的科学不端行为,可依照危害情形的严重程度对相关单位或科研人员追究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第五,设立生物科技损害赔偿基金。基因编辑作为一项高风险性技术,难度大且复杂性强,出现失误在所难免。基因编辑的受益者是不特定的大众,而损害却仅发生在小部分人身上,若仅由该少数人承担损害则有失公平,由科学家或研究机构赔偿也不妥当,故国家应该有所担当,可设立生物科技损害赔偿基金对受害者予以补偿。
基因编辑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尖端技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针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应当被允许吗?这是科学进步向法律提出的拷问。基因编辑拥有天使和恶魔两张面孔,其在疾病预防与治疗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而其背后隐藏的不可知风险则令人生畏。基于这种两面性,规范基因编辑的法律应以平衡为要旨,兼顾维护人性尊严和科学进步。技术上的不成熟、安全性不足、社会共识的欠缺,是当前困扰基因编辑的瓶颈所在。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在有十足的把握确保修改生命密码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之前,谦抑的立法比冒进的立法更可取。与此同时,为避免形成对科学发展的桎梏,法律对基因编辑应保持适度的开放性,为未来的可能发展预留空间。
注:
①基因编辑是指借由一定的技术——如CRISPR-Cas9,精确定位基因组的某一位点,并对该位点上的基因进行删除、修改或者插入新的基因片段,实现对基因组的定点修饰,达到修复缺陷基因、治愈疾病的目的。依照基因编辑的不同对象,人类基因编辑可分为体细胞基因编辑(somatic cell gene editing)和生殖系基因编辑(germ line gene editing)。相比较而言,体细胞基因编辑的后果只会作用于受试者本人,争议较小,而生殖系基因编辑由于风险系数高、世代遗传性、不可逆转性以及其他伦理因素争议较大。
②“良法善治”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参见张文显: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48页。
③ 该研究成果最初投稿到顶级科学刊物《科学》和《自然》,但均因伦理争议被拒稿,后发表在国内刊物Protein&Cell。
④2015年11月,英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成功治愈女孩蕾拉的白血病,这也是全球首次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成功治愈白血病的案例。
⑤ 参见 “韩国将基因编辑技术拱手让人 伦理成 ‘拦路虎’”,http://www.sohu.com/a/164471758_119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