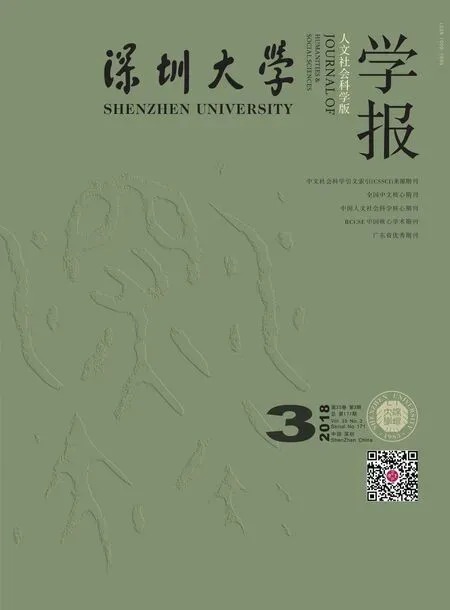规制与教化:明初礼俗的基层控制及其成效
孔 伟
(新乡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明初,百废待兴,基层百姓生活艰难,盗贼趁机为非作歹,如何加强社会控制以恢复社会秩序,关系到明帝国的基业常青,“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1](卷二六,P387-388)。 朱元璋采用礼法结合的控制手段以期达到重建社会秩序的目的。以礼化俗比只用法律来控制社会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有学者致力于明代礼制、礼俗的研究。罗冬阳考察了明太祖礼法并用的社会控制策略以及该策略对明代前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观点极具说服力[2]。张佳以“新天下之化”和“正天下之统”为主线研究了明初礼俗改革,并进一步揭示了明初礼俗改革的政治意义与历史影响[3]。赵克生聚焦于家礼传播与圣谕宣讲,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家礼知识“下渗”民间的社会礼仪化过程[4]。酒井忠夫以明清劝善书推行的动态过程为视角,着重突出明清两代皇权专制下教化政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影响[5]。以上研究成果都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明代的礼俗,但对明代礼俗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成效挖掘不足,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规制和教化为视角细致探析明初礼俗在基层社会中所发挥的控制功能及其成效,以冀对明代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有所补益。
一、改元旧俗以化育新民
因为元朝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其统治不得民心,所以“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6],因此“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7](P621-622)的口号才有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效果。元亡明兴之后,基层社会民风民俗均带有胡风胡俗的特色,要变革风俗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这是历史的惯性使然,但只有“去蒙古化”才能从意识形态上清除元朝的影响。如何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以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控制,如何推行新的礼仪规范以新俗化民,就成为明代建国之初的重中之重。洪武三年,鉴于元代风俗僭越奢侈、乡里之民衣食住行“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的历史教训[1](卷五五,P1076),和“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8](P665)的客观现实,害怕“习以成风,有乖上下之分”[1](卷八一,P1463),为杜绝此风气,朱元璋特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入手来整顿旧元风俗。
首先,改革旧元服制,恢复唐制衣冠。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易变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之旧”。鉴于此,洪武元年,朱元璋即命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士庶皆束发于顶,服四带巾,杂色盘领。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严令“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1](卷三〇,P525)。朱元璋命礼部考核历代颜色,建议“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1](卷五二,P1026),由“取法周汉唐宋”可以洞见明代“援据经文及汉、 魏以来故事, 以定其制”[9](卷一,P1245)和“援据经义,酌古准今”[9](卷一三六,P3939)的制礼原则,从服色所尚表明明朝是承上继承汉唐的正统地位,恢复汉官威仪。
其次,控制住行用度,杜绝僭越之风。传统社会以等级制为核心,臣民在衣食住行用等生活资料方面,都有一定的“礼”和“度”,“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骑有限,以防乱之源也。”[10]明代国家以等级制为准绳,以使“上下称其位,丰约适其宜”[11]。控制民众的生活资料,防止其在衣食住行用等诸方面的犯礼越分,以维护等级制的尊严。为控制违礼僭越之举和明确等级秩序,《大明令》详细规定了各阶层生活资料的等第,按照贵贱等级来排定次序,“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12](卷六二,P252)。 对普通基层民众的住行用等生活资料详细规定如下:其一,房屋如果超出三间五架就算违制,不允许用“斗栱及彩色装饰”[12](卷六二,P253)。其二,衣饰“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12](卷六一,P249);其三,帐幔只能“用纱绢罗”;其四,伞盖“许用油纸雨伞”[12](卷六二,P254);其五,鞍辔“惟用铜、铁装饰”[12](卷六二,P254);其六,日用器皿,“惟酒盖用银,余并禁止”[13]。洪武三年又颁行禁令进一步严明等级制度,以衣饰为例,要求庶民男女衣服 “只用细绢素纱……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1](卷五五,P1076), 如果违犯此规定就会受到处罚。洪武十七年,规定庶民器用之制,“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用磁漆”[1](卷一六九,P2574)。 朱元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僭越行为都予以严厉打击,对于僭越器物的行为,“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坐以重罪”[8](卷三〇,P665)。 又在《大明律诰》中专列“居处僭上用”条目,以扩大其影响。唯有涤清旧元的影响,才能恢复中华正统,营造贵贱有等、尊卑有秩的社会氛围。明初以法律的强制力量来宣扬教化,申明礼制,控制民众,从基层民众日常生活资料抓起,以达到“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14],即通过规范这些象征符号以辨别贵贱等威,以防止僭越犯分,控制这些生活资料的僭用可以明识尊卑,防止违礼败度,从而涤清胡风胡俗以“新天下之化”,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建立一个各安其位、秩序俨然、贵贱有等、尊卑有秩的等级社会。
第三,禁止称谓上的越礼犯分。传统社会由于国家权力主导一切从而导致了官本位思想。官称主要是用于下对上或平级之间的称谓。明初民众“民擅官称”是与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教化相背离,致使贵贱混淆,上下混同,因为“狂民越礼犯分,岂无祸焉! ”[8](卷三〇,P664)为了打击民擅官称之举,明确等级制度,朱元璋在《大诰初编》中专列有“民擅官称”一条:教导民众何时何地该如何正确称呼,如果随意称呼,屡教不改,违令乱称,则“迁于遐荒,永为边卒”[8](卷三〇,P664)。官称是社会官本位和词汇行政化的产物,称谓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政治地位和等级地位相关联,“民擅官称”是僭越违礼、蔑视皇权的表现,故国家明令禁止。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进一步把民众的正当称谓以榜文的形式加以固定,“敢有仍前违犯,治以重罪”[15]。正名是“正天下之统”的要目之一,名正则言顺,制定礼制意在建立井然有序的纲纪法度,并“以纪纲法度,维持治道之具”[1](卷一七七,P2679)。 “民擅官称”会动摇传统社会本已固定化的名分和地位,使权力符号的文化内涵受到挑战和质疑,会混淆本已凝固化的等级差别。明初以严刑峻法打击“民擅官称”的行为,是皇权对基层社会文化控制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称谓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个小类目,从朱元璋对此类目的规范不仅可以窥视出明初改元旧俗以化育新民的决心,亦可以窥视出皇权对社会控制的缜密性、广泛性与强制性。明代一方面要矫元代之弊以恢复中华正统、汉官威仪、汉唐衣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对社会控制的力度加大、刚度加强、网络致密度变密,此举意在以皇权之强制力来打造一个无差别的社会个体和整齐划一的社会群体,使其心悦诚服地惟皇命是从,以便于皇权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地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第四,规范婚俗以涤清旧元婚俗。为矫元代婚俗混乱之弊,朱元璋以专列法律条目的形式对下列婚俗予以禁止:一是转房婚与收继婚。严禁娶亲属妻妾如“弟收兄妻,子承父妾”等行为,对于收继伯母、叔母为妻妾的要处以斩刑,收嫂子、弟妇的“各绞。 妾各减一等”[13](卷六,P62)。 二是同姓为婚。“凡同姓为婚者,各杖六十,离异”[13](卷六,P62)。 三是近亲为婚和尊卑为婚。《大明律》禁止表婚、同姓婚、尊卑婚、同宗婚、良贱婚、奸逃婚、仇雠婚、卑幼婚,禁止娶同母异父姊妹、姑表姊妹、姨表姊妹,“违者,各杖一百。 ……并离异”[13](卷六,P62)。 近亲结婚,其生不蕃,败坏伦理纲常,朱元璋涤清胡元旧俗目的在于规范伦理纲常以 “正天下子统”,从今往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8](卷二九,P594)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最讲究伦理纲常,尊卑顺序,贵贱等威,旧元婚俗在儒家文化圈中是乱伦之举、禽兽之行,故大力禁止之。规范婚俗是朱元璋恢复中华正统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来引导基层民众的择偶对象,控制民众婚姻中的不道德行为,以维护伦理纲常,以便于控制民众思想,约制民众行为,敦厚社会风俗。
最后,申明礼制以定民志。礼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多层次的社会规范体系,“国家行政、司法、军事、教育、宗教、祭祀,乃至乡村规范、家庭伦理、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由上而下,由近而远,几乎无远不届、无所不到,这是一张巨大的网络,把所有人一网打尽,每个人都要在网上按照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按礼行事,井井有条,不得越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规范,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扮演自己的角色。”[16]洪武五年,朱元璋敕谕礼部:“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狈于浅近,未能狞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悼习以成化。 ”[1](卷七三,P1336-1337)朱元璋严明礼法意在确立等级秩序,控制僭越违礼的言行举止,以此来构建上下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行政体系,建立皇权专制的礼制基础。洪武六年,朱元璋又谕礼部尚书牛谅:“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1](卷八〇,P1449)。朱元璋积极实施礼义教化以导民善俗,稳定秩序,通过礼制教化来对百姓进行教育,使其明辨是非,自觉向善。明代国家把礼俗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维护皇权专制,以“去蒙古化”来确立自己的文化正统地位。只有“去蒙古化”才能使儒家教化思想、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在基层民众中生根发芽,才能加强中华文化认同,国家才能把“软控制”的手段与“硬控制”的手段相配伍,从而将国家的控制策略落到实处,将控制的效能最大化。
二、建构体系以落实教化
朱元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治教合一的国家教化体系:中央六部、布政使司、府、县、里甲。“凡任有司,职掌务在牧民。”[7](P826)这个体系以治为主,政教并举,以教为政,教为政本,以控制基层民众为鹄的,以维护皇权专制为旨归。各级地方长官都是皇权的化身,是基层社会控制的主体,是具体控制策略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他们肩负“宣扬风化,抚安其民”[1](卷一六一,P2497)的职责,教化民众是其秉承皇权教化意志的主要体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7](P469)被各级官员奉为圭臬。就明初的乡里社会而言,老人负责乡里教化,本地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须由老人将其善迹奏闻朝廷,请求旌表。里甲担负着治安管理职责,是维系明朝基层统治秩序的第一道屏障。为实现皇权全面控制社会的目标,朱元璋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来建构基层控制体系以落实教化。
首先,完善户籍,控制人身。明初,国家利用户籍把基层民众籍于土地,使人地得以结合,并通过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路引将基层民众控制在一定的地域内。每家每户的人口、土地、田产、家庭关系都被登记在册,使百姓一年到头忙于耕种稼穑,禁止随意流动,控制人身自由。明政府为了强化对生产者人身的控制,通过加强户籍管理以控制社会成员的谋生途径,通过严密里甲制度以迫使整个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训之以尊卑长幼之节,定之以冠婚丧祭之仪,戒之以疾病患难相救相扶之计”[17],教化使民众安分守己,实行邻里互助制度,使民众相互帮衬。通过邻里相互监督制度以涤清基层藏污纳垢之风。户籍是明初统治者控制民众最重要的措施,强制每一个人都著籍于官府,以户籍制度编制行政网络,搭建 “权力的文化网络”,将每个个体都登录在册,以控制流失人口。同时对基层社会进行广泛的法纪宣传,要求所有人不得漏口脱户,同时规定人丁外出,必须携带官府的路引文凭,否则就以私渡关津之罪论处。
其次,设置老人,落实教化。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于“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9](卷七七,P1878)。 老人多为基层精英担任,肩负着以圣谕劝民、教民的职责,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宣谕《圣谕六训》,“农民有等懒惰,不肯勤务农业……止是各里老人劝督……老人点闸不下田者责决,务要严督见丁著业,毋庸惰夫游食。 ”[18](P645)除旌表良善、查访奸伪、惩治懒惰之外,老人还负责处理诉讼,具有初级审判功能。此举意在使基层矛盾在基层就得到解决,以节约国家的行政成本。里甲老人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传播者、皇权教化的宣讲者、明政府的具体教化活动的执行者、实施者和贯彻者。他们通过打击奸盗邪淫来营造为善去恶的基层环境。老人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的舆论导向作用,促使民众把伦理道德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把礼俗教化作为自我控制的武器。在里甲之中设置老人,推行教化,宣讲礼法,是明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的区别于前代的主要特征。
三、教民礼俗以提前预警
礼法纲纪是立国之本,舍此他取,必然导致僭越违礼,颠倒是非,纲纪混乱,社会失控。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礼是先贤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出礼即入法。礼与基层习俗相结合便产生了礼俗。因为礼俗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基层社会的很多矛盾都能以礼俗来化解,所以礼俗在基层社会控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采用礼法并用、“软”“硬”兼施的社会控制政策,“圣人之驭天下也,必先彝伦而攸叙,立条置目,纲以张维之……故重其礼者,盖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 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 ”[7](P63)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看,礼是软控制的手段,法是硬控制的手段,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礼以教育感化为主,意在治心;法以严酷打击为主,意在控制行为。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惩于已然之后。“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9],通过礼来改造头脑,控制人心,进而限制人的行为。攻心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所以治天下当以礼乐为主,刑政为辅。“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1](卷一六二,P2517), 统治者如果只用严刑酷法来控制民众就会因缺少应有的和平之风而显得过于冷酷严峻,基层民众虽畏惧法律而不敢忤逆,但终究不会心悦诚服。
首先,先教后惩,提前预警。礼俗可以通过提前预警以达到“教之以先”目的,朱元璋先采用“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9](卷九三,P2284)的策略,先行德礼教化,教化不行再用刑法镇压,先教后诛,礼法结合,软硬兼施。积极实施礼义教化可以使百姓明辨是非,自觉向善而远离不道德。礼俗教化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皇权控制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学礼,无以立,明礼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能。此外礼俗教化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和一切领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20]。以礼教化民众就是以伦理道德教育的形式来控制民众的行为举止,“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1](卷二九,P496),提前预警就是先对基层民众进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来改造思想,以达到改造人心的目的。
其次,导民向善,励民自控。朱元璋鉴往知来,实施了以礼化民的社会控制手段,“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 ”[7](P515)礼俗可以为民众指明行为方向,导民向善,使社会贵贱有等,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等威有辨。因为礼俗与基层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举凡接人待物、为人处事、一举一动、言谈举止都离不开它,以礼俗化民能使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控制而浑然不觉。“礼义者,御世之大防”[7](P621),礼是控制民心的切实可行手段,“礼仪是尚、以礼为教”[7](P190)的治国策略既是对元朝控制策略的校正,也是“去蒙古化”的必要手段。治理天下“必定礼治以辨贵贱、明等威”[7](P462-463)。朱元璋鉴于元末社会失控、伦理失衡的现实,通过礼仪教化来确立尊卑有别、礼仪是尚的等级社会。朱元璋还通过旌表、谕俗、学校教育、圣谕宣讲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教化形式对基层民众进行伦理规范和思想品德教育,教育民众自我控制,老老实实地作国家的顺民,遵纪守法、和睦邻里、安分守己。
四、力行教化以移风易俗
鉴于风俗演变的历史惯性,朱元璋看到基层民众受元朝旧俗的影响,衣食住行与公卿无异,崇尚奢侈,违礼越制,“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 ”[1](卷六六,P1248)唯有力行教化,敦厚风俗,荡尽胡俗,拨乱反正,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建设走向正规。“天生烝民有欲,必命君以主之。君奉天命, 必明教化以导民”[1](卷二五三,P3653),“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7](P441)。 推行教化,改善风俗成为明初社会建设的要目。
儒家教化具有极强的社会控制功能,“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21]。教化可以移风易俗,基层民众对皇权教化的接受程度关系到国家兴亡。教化不行则皇权不彰,“凡以教化不立则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22]。皇权教化是为了使民众从心理上接受国家所提前制定好的道德伦理规范,按照国家的要求身体力行,自觉自愿地遵从。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看,礼俗教化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改造民众的思想观念、矫正民众的行为举止,严厉打击任何不同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行举动,因此明初的礼俗教化以服从国家社会控制为旨归,以服务皇权专制的需要为目的。
朱元璋秉承先师先哲的遗训,身体力行着“治国之要,教化为先”[1](卷四六,P924)的治国理念,这与朱元璋个人的生活阅历、人生感悟以及对元末明初社会的深刻洞察有关。民俗之善恶与教化休戚相关,如果不推行教化,就会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1](卷二〇三,P3035)。元朝重法令而轻教化,结果民众无所适从,不以犯法为耻,对法律无所畏惧,因不懂法而被罚、被诛者比比皆是。不教而诛,是为残暴,元朝地方官员不知教化为何物,只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打击“暴民”,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结果“暴民”不减反增,从而激化官民矛盾,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导致元朝速亡。鉴于明初“风俗陵替”的局势,朱元璋力主“教化为先”的策略,先涤清元代的旧风俗,再推行新风俗就会势如破竹,“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1](卷二六,P400),在基层社会中,风俗以约定俗成的惯性控制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以其潜移默化的形式塑造着基层民众的人格,影响着基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建构着基层民众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伦理。“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0](P510),风俗的醇厚浇漓是社会失控与否的主要表征。朱元璋以礼来移风易俗,整合社会,控制社会,约制民众,以达到加强皇权专制的目的。
为响应朱元璋的皇权教化策略,各级官员或建言献策,或身体力行,或积极推行,或总结心得体会,或从历史上汲取先贤治国齐家的经验,或从与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礼文化入手,提倡以冠、婚、丧、祭四礼作为涤清胡风、敦厚风俗、移风易俗、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如陈章应即上书明太祖曰:“今民间徇俗废礼,加冠于幼稚,娶妇而论财,丧亲者惟惑于浮屠风水之而或缺衣食棺棒之具,祀先之典虽衣冠士族亦莫之行,宜定其礼颁示天下使遵而行之,亦厚风俗之要务也。”[1](卷一七二,P262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齐才能国治,推行和宣讲朱熹的《家礼》以教导基层民众修身齐家,则是切实可行之道。明初统治者利用皇权的力量把家礼推行到基层,便是把皇权教化的触角深入到千家万户,以《家礼》作为控制民众思想行为的工具。《家礼》成为基层官吏教化基层民众修身齐家的教材。明代县官虽是亲民官,但县级行政单位和最基层的民众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行政空隙,再加上民多官少,根本无法实现基层民众和地方官员的无缝对接。《家礼》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行政机构对基层社会控制之不足,使皇权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完成皇权教化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和无处不在的社会控制目标。
五、广建学校以育才化民
朱元璋对学校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有深刻的认识,他于洪武二年,诏令天下府州县皆立学;自洪武八年诏民间立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至洪武二十八年各边地、土司皆建立儒学传授儒家经典。正是看到了学校在社会控制中的重要作用,朱元璋才大兴学校以便于推行教化。他视学校为“国之首务”[1](卷一四五,P2281),提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要,学校为本”[1](卷四六,P924),“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如是为治, 则不劳而政举矣”[1](卷二六,P338)。学校是育才之地, 是 “风化之原”[1](卷一〇六,P1764),“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21](P484)。朱元璋通过广建学校来育才化民。
首先,培育人才,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人才是实施教化的主体,只有广育人才才能把厚风俗、美教化的梦想落到实处,朱元璋说:“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而经纶抚治,则主要在于文臣,所以“二者不可偏用也。”[23]文臣来自儒生,他们通晓“治平之术”,拥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明初天下刚定,“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1](P471),则必须依赖儒生。 于是朱元璋诏令各府州县皆立学以培养合乎统治需要的人才,“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1](卷四六,P925)。因为明代各级学校都“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4]。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范本,要仿照宋代经义,代圣人立言,士人们为谋求政治出路以改换门庭,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朱元璋以八股取士之软控制手段来行科举摧残之实,他说:“吾有法以柔天下,则无如复举制科”[25]。学校是朱元璋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主要场地,以学校来批量地培养唯皇命是从、循规蹈矩之人,这些人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后便成为国家 “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结点,就不折不扣地将厚风俗、美教化的战略目标落到实处。
其次,以理化民,控制思想。朱元璋排斥一切儒家之外的学说,严厉打击一切诋毁儒家圣贤的言行,把一切违背程朱理学的言行都视为异端而严惩不贷。各级各类地方官学是实施社会教化的机构,“天下政教本乎庙学,……教之以孝弟忠信,……八刑以纠之,五礼以规之,而民无不治,俗无不化,是有政教而县以治矣”[26],明代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通过各级学校贯彻到全国各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9](卷六九,P1686)。朱元璋此举不是单纯以理学来钳制士人的思想,扼杀士人的反抗精神,消磨士人的斗志,摧毁士人的独立人格,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举国臣民都学习领会儒学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处事原则,并借其思想资源来达到控制臣民、稳定社会的目的。
明初统治者把学校作为化民成俗的工具和道德教化的场所,以学校为主要场地对民众实施控制,“学校之设,……正欲使市井闾阎熏诸生之德,而善良耳”[27]。明代教育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教育思想,以八股文为取士标准。明代各级各类学校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着伦理道德教化的功能,社学是基层社会实施皇权教化的主要场地,通过宣讲圣谕、宣传律法来引导基层社会的公序良俗,并以学校为辐射中心把皇权教化的精神辐射到千家万户,以造成天高皇帝近的局势,使皇权借学校得以渗入基层社会,并控制住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明代学校实际成为“国家对地方社会和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和道德控制的机构”[28]。
六、大兴儒学以普及教化
孔子是儒学鼻祖,代表了学统和道统。弘扬道统可以为皇权专制提供无穷无尽的思想资源;弘扬学统可以为皇权教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朱元璋,明白征服人心比武力杀戮更能长久的道理,所以极为重视儒学教化。
首先,礼敬孔子,大兴儒学。普及教化必须大兴儒学,大兴儒学就要尊崇孔子。朱元璋派遣使者到曲阜以太牢礼祭祀孔子,并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 ”[9](卷五〇,P1296)因为孔子是天下读书人的崇拜偶像,礼敬孔子就是向天下臣民表明其治国理念。太学新落成之际,朱元璋亲自向孔子行“释菜”礼。 并强调“于先师礼宜加祟”[9](卷一三六,P3933)。礼拜孔子是朱元璋向天下表明其重儒重教的决心,是拉拢天下士人的策略,是鼓舞天下士林的韬略,是朱元璋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民众、以忠恕和中庸之道教化民众的征候。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下举国上下掀起了读书向学之风。读了儒家的书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就会按照儒家的行为方式为人处世,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培植臣民的忠孝节义的思想。儒家强调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教育,以文行忠信教化民众,增加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以家国情怀影响民众,增加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明初,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控制民众的利器和致治资源,达到了弘教化、正人心的社会控制目标。
其次,设置教官,普及教化。朱元璋兴办学校的诏令颁布之后,各地官员闻风而动,纷纷以兴办各级各类儒学为己任,明代兴学立教之风,大行其道,“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9](卷六九,P1686)。兴学立教的国策为明代兴盛奠定了人才基础,为教化的实施提供了场地,使基层社会控制战略得以落实。“我朝酌古为治,自府州县以至坊隅里巷莫不有学,在府州县曰儒学,在坊隅里巷曰社学。社学之教主于明伦敬身,儒学之教主于明经修行”[29]。明代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是实施皇权教化的主要场地,在育人才的同时,维护着地方社会的公序良俗,发挥着社会控制功能。“养民之道莫若礼,而礼之所先,莫先于学校”[30],明代皇权以各级各类学校为主要场地,纵横交叉,把全国连成一片,加强了东西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也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远播边疆地区,教育教化着当地民众,改善改良着当地的思想文化精神和伦理道德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地的民风民俗,起着社会整合的作用。
教师是实施学校教育的主体,“大小教职咸有风化之责”[31],朱元璋非常重视各级教官的选任,多选任品学兼优者为之。因此各级各类教官的责任也甚为重大,“一郡之治本乎太守,一郡之化始于教授。治出于政,必太守贤而克理,政斯治矣。教授贤而克举,化斯行矣”[32]。学校是基层精英的养成之所,基层精英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控制的效果。学校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主要传播基地,是“大传统”的象征,以学校为场地可以实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接,充分发挥“大传统”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教官之任甚受国家重视,“官之重无如教官,……国初以学校为首善之地,当时以起家教官为第一荣进,匪朝廷滥耀此官,则教官实称此职也。”[27](P416)明初各级各类教官身负风化之任,是国家礼俗教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是基层文化的传播者、国家教谕的宣传者和基层精英的培育者。朱元璋以学校为本的教化思想通过各级各类教官得以落实,他们雕塑着基层民众的精神面貌、思想文化和言行举止,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把程朱理学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传播到千家万户,影响着基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七、规范祭俗以彰显教化
明代的祭祀主要包括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祭祀天地是皇权受命于天的象征,是明朝合法性的标志,因此朱元璋对民间祭祀礼俗极为重视,并敕令说:“自昔圣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严于祭祀。故当有事,必内致其诚敬,外必备其仪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诞膺天命,统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庙,以崇祀事。”[1](卷三〇,P507)。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郡县访求应祀神祗,以便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祀,用国家礼典来规范民间诸神的祭祀。为明确各个阶层的祭祀对象,朱元璋又命中书省定议郊庙及百神祀典,将州县与民间的祭祀活动纳入国家祭祀的范畴,祭祀礼仪严格按照等级秩序而设定,基层民众只能祭父祖及里社土谷之神,并得祀灶。其余不当祀者,并加禁止。并将这些制定“载诸祀典”[1](卷三六,P668)。 “祀典正则人心正”[9](卷五〇,P1307),等级不同祭祀对象也截然不同。“天子亲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1](卷三六,P668)。从国家角度来看与最高神“天”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明代帝王通过垄断对上天的祭祀权来垄断与上天的沟通权,明初,不准民间祭天地、山川、令士庶各祭所宜,违者罪之。普通民众只能与较低等级的神沟通,从而将神人关系等级化。明初所制定祭祀之法标准非常明确:受祭祀对象或法施于民之功臣、或以死勤事、以劳定国之贤臣、或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之能臣,“是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非此族也,不在祀典”[33]。洪武三年,朱元璋又以“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其礼既同,其分当正”[1](卷五三,P1036)为指导原则,去诸神历代封爵,皆以其神称,将诸神由人格神转为非人格神。变更名号意于“去邪导正,使诸神听命于天,而众鬼神听命于神。庶天神权纲之不紊也。 ”[1](卷五六,P1088)与君、臣、民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相应,构建出天、神、鬼的神鬼等级秩序。这一制度的构建为加强精神控制奠定了认知基础。明初国家祭祀活动是以有神论的形式实行公共生活规范演示活动,地方官吏在利用民间宗教信仰的力量强化地方社会控制。
首先,利用乡里祭祀,控民信仰。明初把对土谷神的祭祀推行至最基层,并以法典的形式加以固化,令基层民众自己出资举行,以里为单位祭祀五土五谷之神以祈求五谷丰登,祭祀完毕举行会饮,会饮之前宣读“抑强扶弱之誓”,誓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34](P348)。 读誓词毕,长幼依次就座,“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众人一起对神盟誓,就是把神作为公正无私的裁判,接受神灵的监督,若有违犯誓言之举便被视为对神灵的大不敬,神灵就会对其降罪以示惩戒。这是利用神灵来对基层民众进行心理恐吓,以心灵暗示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胁迫控制。明初,基层民众还要祭厉,意在扬善抑恶。“厉”为城隍管辖下的无祀鬼神,把“祭厉”纳人国家祭祀体,意在利用因果报应和鬼神信仰来扬善抑恶,利用神权来控制基层民众,“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34](P348)。以里为单位每年于清明节、中元节和十月初一祭厉三次,祭祀乡厉坛就是利用神权来控制厉鬼,把人间式的社会礼仪规范照搬到冥界,不许厉鬼为恶,危害乡里,并利用城隍神的权威来威慑其治下的厉鬼,不许其作奸犯科。民众祭祀神灵以禳灾求福就会敬畏神灵,心存敬畏就会自觉自愿地慎言慎行,都会心甘情愿地自我约制、自我控制。
其次,打击淫祀,规范等级秩序。不合礼制的祭祀就是淫祀。淫祀是越轨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以正视听。明初,国家严厉打击信巫鬼、重淫祀、迷信之风。国家明令“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无得致祭”[1](卷五三,P665)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打击淫祀,使淫祠、淫祀无立足之地,“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杖八十。妇女有犯。罪坐家长。 ”[12](卷一六五,P28-29)因为淫祀非礼是对国家正常祭祀的干扰,“野鬼淫祠,充闾列巷,岁时祭赛男女混淆,甚至强盗打劫亦资神以壮胆,习俗兴讼,必许愿,以见官”[35]。淫祠淫祀使百姓思想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其不当奉祀之神,而致祭者杖八十”[13](卷一一,P87),洪武三年,朱元璋又下诏禁淫祀,制曰:“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犯分,莫大于斯。……礼部其定议须降,违者罪之。”[1](卷五三,P1037)在打击淫祀的同时,还严厉惩罚妄言祸福企图迷惑民众的江湖术士,“凡阴阳术士,不许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妄言祸福,违者,杖一百”[13](卷一二,P95),还对僧、道建斋设醮加以限制,不许奏章上表,投拜青词。塑画天地神祗与扶鸾、祷圣、书符、况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1](卷五三,P1038)。通过法律来控制祭祀对象,通过正祀典来正人心。朱元璋是通过规范祭俗来强化现实的等级制序,缩小基层民众的祭祀权力,将其祭祀范围限制在祖先神之内。“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与神耳”[36],而“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僣差”[1](卷五三,P1034)。明代国家通过规范祭祀礼仪来垄断与天神、地祗、人鬼的沟通权力,通过独掌“奉天地,享鬼神”特权来为“皇权神授”披上合理性的外衣,在借助神权来控制基层民众的同时,又以祭祀礼来规范现实之外的鬼神世界。
最后,规范祭祀,实现对接。规范祭祀仪式让百姓接受精神文化的洗礼,以便实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接。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令全国郡县访求合乎祀典的神祗,“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9](卷五〇,P1306)。洪武二年又诏“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时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毁”[1](卷三八,P760)。 神祗们的等级地位是根据他们对国民的贡献来确定的,被国家立于祠中加以祭祀的神灵,要么是前朝功臣元宿有大功于社稷,要么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立言不朽,要么有大德于世,立德于世流传久远,无论是立功、立德或是立言都符合儒家三不朽教义。祭祀先贤可以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序良俗,因为先贤功业可以励民仿效,在鼓励百姓祭祀先贤的过程中,国家借此把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深入到基层社会之中。基层公共事务活动成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联系中介。民间祭祀活动中,以政府官员为主导,以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为主体,可以借此机彰显皇权,而神权是皇权的化身,彰显神权便是彰显皇权。在祭祀活动中,地方官员利用祭祀礼俗来彰显朝廷教化,地方士绅利用祭祀活动来划定自己的“场区”,民众在祭祀活动中受到了教化,受到了精神洗礼,祭祀成为国家搭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政府治理权与神权、绅权取得了合作性博弈,明代是一个“小国家、大社会”的传统格局,皇权必须借助中介才得以下县,自上而下,士绅、祭祀、神权都可以成为皇权得以下县的中介。
八、引礼入法以控驭万民
朱元璋继承了前代统治者明德慎罚、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采用礼法相维、软硬兼施的控制策略来控制民众。
首先,以法行礼,强化控制。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朱元璋将《大诰》颁行天下。令家家户户都有一本,这使《大诰》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又把《教民榜文》颁行全国各地,里老可依此榜,导民善俗,平乡里争讼。教民榜文是朱元璋把基层所容易出现的问题加以简化而制成的管理制度,以圣谕六言的形式劝勉基层民众和睦相处、遵纪守法、自觉遵守传统伦理规范,采用综合治理、惩防结合的社会教育的方式来达到导民善俗的目的。里老以圣谕六言为蓝本积极努力地秉承皇权教化的宗旨来塑造基层民众的灵魂,陶冶基层民众的性情,雕塑基层民众的品格,培养他们的思想和品德,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以适应皇权专制的需要。教民榜文和圣谕六言的规范就以里老为中介转化为基层民众的内心信念和自觉行动,里老通过辨明善恶是非来提高基层民众的道德认知,以知辱明耻来激发基层民众的道德荣誉感。皇权教化以里老为中介深入到了基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使其不敢乱说乱动,真正达到了“人皆向善避恶,风俗淳厚”[18](P636)的社会控制效果。《教民榜文》重在社会教化而非刑事处罚,利用基层民众全身远祸、趋利避害的心理来教导他们安分守己,远离邪恶。国家以法的力量保证礼的推行,以法威慑,以礼化俗,以法监督,以礼诱导,礼法互补,相得益彰。以礼的精神力量和法的强制力量来达到教化基层民众、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既保证了皇权的权力触角向基层社会渗透与延伸,又维护了皇权专制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设立二亭,惩恶扬善。洪武五年,朱元璋在基层社会普遍设立申明亭以申明教化,惩恶扬善,使民知禁令,“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1](卷七二,P1332-1333)。各州县设立申明亭 “里民有不孝、不弟、犯盗、犯奸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俱书于板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37]罚一儆百,以儆效尤,通过舆论监督和心理暗示的方式来 “劝善惩恶,使有所警戒”[1](卷一四七,P2302)。鉴于有司“以百姓杂犯小罪书之,使良善一时过误者,为终身之累”,为了给过误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对申明亭所书罪人有所调整,“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1](卷一四七,P2302)。因为打击面过宽,就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反而达不到预设的社会控制目的。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社会控制效果更好,国家通过抓大放小,宽严适中,反而会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服从国家控制。因为申明亭是皇权教化的象征,所以毁坏申明亭便是蔑视皇权。明律规定凡是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坏榜木者,处“杖一百,流三千里”[13](卷二六,P435)的刑罚。此外在基层社会还设旌善亭以敦厚风俗。旌善亭于洪武年间普遍建于基层社会,为旌表忠勇孝悌、贞女节妇等道德楷模,因为“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朱元璋“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 ”[1](卷二〇六,P3069)朱元璋“命礼部录有司官善政著闻者,揭于其乡之旌善亭”[1](卷一七四,P2632),临桂县民李文选因事母至孝,“言有司, 请表其行于旌善亭”[1](卷一七四,P2648)。彰恶与旌善是明代国家两个密不可分的社会控制手段,瘅恶扬善的最终目的是以控制民众为旨归。
总之,朱元璋以国家强权的力量来推行礼俗教化,以瘅恶扬善来营造为善去恶的文化氛围,以强权威慑的方式来保证其化民成俗控制效果,以国家力量来维护社会控制体系的良性运转,以至于明代的礼俗前所未有地下渗到民间社会。由此亦可以窥视出明代享国长久的历史成因。
[1]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影印本,1962.
[2]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4]赵克生.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M].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皇明诏令[A].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5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
[7]张德信等编.洪武御制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1995.
[8]钱伯城等编.全明文(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刘向.说苑全译[M].王瑛等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743.
[11]陈锋等.中国病态社会史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62.
[12]申时行.大明会典[A].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怀效锋.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4]张瀚.松窗梦语[M].盛冬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76.
[15]杨一凡等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三册)[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24
[16]孟天运.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140.
[17]宋如林等.(嘉庆)松江府志[M].清嘉庆松江府学刻本.
[18]朱元璋.教民榜文[A].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19]韩非.韩非子新校注[M].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65.
[20]钱玄等.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1]周礼译注[M].杨天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8.
[22]董仲舒.西汉文纪[A].四库全书(第 139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6.
[23]吴乘权.纲鉴易知录[M].施意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2573.
[24]陈鼎.东林列传[M].无锡:广陵书社,2007.38.
[25]查继佐.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8l7.
[26]章纶.章纶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37.
[27]吕坤.实政录[A].官箴书集成(第 1 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
[28]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the Nineteen Centuary[M].Washington: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60.244.
[29]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75 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629.
[30]王衡.缑山先生文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9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6.84
[31]欧大任.欧虞部文集[A].四库禁毁书丛刊(第47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28.
[32]刘三吾.坦斋刘先生义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5.96
[33]徐一夔.明集礼[A].四库全书(第 64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4.
[34]叶春及.惠安政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35]张萱.西园闻见录[A].明代传记丛刊(第124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7608.
[36]宋濂.洪武圣政记[A].丛书集成初编(第3959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2.
[37]薛允升.唐明律合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