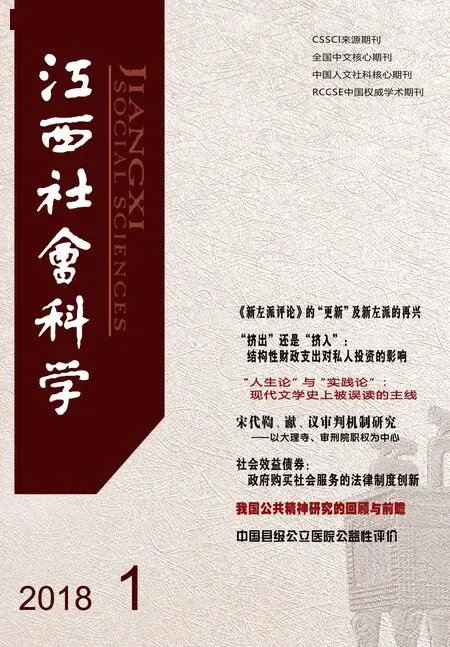投资者权利性质的解构与国际投资协定的革新
一、问题的提起
晚近,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东道国规制权的侵蚀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反思。国际投资协定①正由以片面维护投资者利益及追求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代协定”向以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为导向的“第二代协定”转变。[1](P103)作为国际投资协定革新的实施路径之一,缔约国联合解释机制日益为各国所重视。继2001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自由贸易委员会出具了该协定下首份解释性文件后,哥伦比亚与新加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缔约国印度、欧盟与加拿大相继以解释性文件的方式,对各自所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部分条款作出澄清或更新。
有关缔约国联合解释机制的功能及优势,学界已多有着墨[2][3][4],但对于国际投资协定的特性——授予除缔约国以外的第三人权益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并未给予充分关照②,就这一特征给缔约国的条约解释与修订权带来的潜在制约,既有研究亦未予以充分阐释。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在缔约国联合解释的可适用性问题上仍莫衷一是:就NAFTA自由贸易委员会所出具的缔约国嗣后解释文件而言,仲裁庭虽对缔约国解释文件的性质不乏疑虑③,但最终仍选择适用该项解释;而在以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下“根本安全利益条款”为争议焦点的数起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认为缔约国嗣后解释有违投资者合理期待利益,进而拒绝适用④。
缔约国联合解释的价值日益彰显,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亦不容忽视。争议的本质在于:倘国际投资协定下的权利义务仅属于缔约国,则缔约国经合意固然可对自身的权利义务重新作出界定,投资者对此并无独立的权利可供主张,所谓的“侵权”亦无从谈起。[2](P151)然国际投资协定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向缔约国以外的第三方——外国投资者授予特定待遇,并允许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仲裁,对自身所受损害向东道国索求赔偿。因缔约国联合解释的内容多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变更,在此背景下,若国际投资协定赋予投资者独立的权利,则缔约国联合解释对协定内容的变更将可能受到第三方权利的制约⑤。
鉴于此,本文围绕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及修订权与投资者权利这一对互动关系,首先梳理学界当前有关投资者权利性质的学说,进而以缔约国联合解释协定为着眼点,分析投资者权利对前者所形成的适用限制的破解之道,以期对我国国际投资协定革新的路径选择有所助益。
二、国际投资协定下投资者权利性质之界定
目前,学界对于投资者权利性质的界定,可分为派生权利说、程序赋权说及实体赋权说三种理论。
(一)派生权利说
派生权利说认为国际投资协定下的权利义务属于缔约国,投资者所享有的仅是以缔约国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派生权利,因缔约国对协定的事实性修订⑥而遭受的损失,投资者不具备相应请求权。该说的分析源自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制度。在外交保护制度下,一国国民因国际不法行为所遭受的侵害,国籍国当以国家名义寻求救济。依据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在1924年“马弗罗马蒂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中对国籍国外交保护权所作的阐释,此时国籍国所主张的是属于该国的权利。[5](P12)派生权利说以此为基础,将国际投资协定视为对传统外交保护制度的延伸与补充,认为缔约国仅出于便利之目的,允许投资者实施属于其母国的权利。回归到国际投资协定的语境中,派生权利说的论据可归纳为:第一,投资者并非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主体,故不应取得缔约方的地位及权利;[6](P889)第二,就形式而言,国际投资协定只表述了对缔约国设置义务,并未直接规定投资者权利;[7](Para233)第三,从协定部分条款的字面含义可推定,投资者仅享有利益,而非权利。如,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拒绝授予利益”(denial of benefits)条款即表述为利益(benefit)而非权利(right)。[4](P170)
笔者认为,上述论据存在如下可商榷之处。
首先,仅从形式而论,国际投资协定中不乏条款直接对投资者“权利”问题作出表述。如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序言部分规定“承认为投资者提供有效渠道以便其提出诉求并实施有关投资之权利的重要性”。又如,中国—以色列《双边投资协定》之《议定书》第1条(a)项对“投资者”的补充定义规定:“以色列的永久居民全面享有与以色列国民在本协定下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为国际投资协定所普遍纳入的“代位权”条款亦就投资者母国或其指定的承保机构代位行使投资者“权利”问题作出规定。
第二,派生权利说在对现状的解释上也不乏困境。该等困境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该说难以为实践中投资者对权利的独立处分行为提供合理解释。如,对于自身所受侵害,投资者是否有权决定放弃仲裁?当投资者母国明确反对仲裁庭对争议事项具备管辖权时,投资者是否仍有权对东道国提出仲裁请求?就GAMI案及Modev案的实践而言,投资者母国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事实上并未影响投资者提起仲裁请求,两案仲裁庭分别认定其对争议事项具有管辖权[8](Para43)[9](Para92);其二,派生权利说难以对投资争议中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及赔偿的归属问题提供合理解释,即,在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上,为何仲裁庭没有考虑投资者母国所受损害?在损害赔偿的归属问题上,为何损害赔偿最终归属于投资者而非其母国?
第三,从与国际贸易法的横向对比来看,派生权利说难以对《世贸组织协定》与国际投资协定在权利救济方式上的差异提供合理解释。有别于国际投资协定,在《世贸组织协定》下,成员国境内的贸易活动参与者对因他国违反《世贸组织协定》义务而遭受的损害,无法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争端解决请求并主张损害赔偿,而必须由其母国将另一成员国诉至争端解决机构。将国际投资协定等同于《世贸组织协定》下的派生权利模式,难以解释两者间的上述差异。[10](P372)
鉴于派生权利说对现状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和整合力,学界有观点主张投资者在国际投资协定下享有独立的权利,其见解又可区分为程序赋权与实体赋权两种理论。
(二)程序赋权说
程序赋权说认为,投资者在国际投资协定下只享有程序性权利而无实体性权利,投资者可因主张其母国之权利,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仲裁请求。[11](P184)原则上,如无实体权利,则当事人缺乏请求权基础,自然更谈不上享有程序性权利。那么,投资者如何在不取得实体性权利的情形下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程序性权利?国内法下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分离的制度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程序赋权说提供支撑。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诉讼担当制度中,当事人可在不取得实体权利义务的情形下,以自己的名义享有诉讼实施权⑦。根据学理定义,诉讼担当制度是指,本来不是民事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具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行使诉讼实施权,所受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12](PP144-149)即,诉讼担当人取得诉权的前提是:诉讼担当人对他人的财产具有管理权,而所有权人又不能行使财产管理权,也不能行使诉权。[13](P145)诉讼担当制度固然可为程序赋权说提供制度依据,为投资者对程序性权利的独立处分行为提供合理解释,然而,这一制度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仍存在适用困境。如认为投资者对系争标的仅享有管理权而非所有权,仍难以对损害赔偿最终归属于投资者而非其母国,以及仲裁庭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未尝考虑投资者母国所受损害等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鉴于程序赋权模式对现状仍难以提供完备的解释,学界进而发展出第三种观点——实体赋权说。
(三)实体赋权说
实体赋权说认为投资者同时享有国际投资协定下的程序性及实体性权利。这一观点主张,判断投资者是否享有独立的权利,关键在于该权利可否由投资者执行(enforce)。国际投资协定经赋予投资者程序性权利,将缔约国间的义务转化为可供投资者独立执行的权利。[10](P372)这一观点承认国际投资协定具有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国际条约的特殊性,认为协定在缔约双方与投资者之间构建了三方法律关系。在实体赋权说下,可进一步区分投资者本位与缔约国本位两种取向。
1.投资者本位取向。以投资者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可基于不同理论范式加以解释:
一种解释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基础。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基于对允诺人给付其利益的允诺产生信赖并改变自身的处境,在其信赖利益受损之时,依据信赖规则,可请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第三人获得请求信赖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损害赔偿的诉权,便是其享有合同权利的体现。[14](P61)据此,投资者作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受益第三人享有协定下的权利。[15](P75)根据《2010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2010)中有关撤销第三方权利的规定,授予第三方的权利仅可在“受益人接受合同为其设定的权利”或“已信赖该权利合理行事”之前,方能修改或撤销。[16]基于此,缔约国间对条约项下权利义务的变更应以不损害投资者的信赖利益为限。
另一种解释将国际投资协定视为一项旨在为外国投资者创设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根据国际法院在1974年“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Nuclear Tests)中对国家单方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所作表述,一国经公开声明,表明其有意受该声明内容所拘束,该国便为自己设置了义务,所涉国家可对其予以信赖并要求表意国信守其承诺。[17](P267-268,Paras44-46)基于此,部分学者将国际投资协定视为缔约国向不特定多数投资者作出的单方法律行为,旨在对缔约国设置义务并授予投资者权利。投资者基于对该条款的信赖并履行投资行为,即形成缔约国对投资者的权利授予[18](P186),而权利一经授予,非因情势变更等法定或约定事由,不应受到任意变更或剥夺。
上述两种解释的共性在于以维护投资者信赖利益为核心,主张以投资者既得权利限制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
2.缔约国本位取向。以缔约国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虽不否认投资者享有实体权利[10](P372-373),但主张该等权利应从属于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及修订权,其原因在于:首先,缔约国与投资者间并非平等主体,两者间的法律关系应适用公法原则进行调整。在公法语境下,国家有权对私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变更。其次,国际投资协定本质上仍属主权国家间订立的条约,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与变更行为应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调整。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7.2条关于授予及变更第三国权利的规定,投资者所享有的权利是否可经缔约国合意而变更或撤销,取决于缔约国的原意。[19]基于此,投资者所享有的权利便成了以缔约国原意为条件的、有限的权利。由此,投资者的权利原则上可经缔约国合意而变更或撤销,除非缔约国已作出明确相反的意思表示。
三、投资者权利对缔约国联合解释适用限制之破解
厘清投资者权利的性质可为评估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限制奠定理论基础。因此,需要对前述有关投资者权利性质的学说进行评价,进而分析投资者权利对缔约国联合解释适用限制的破解之道。
(一)对投资者权利性质的评价
因国际投资协定普遍未就缔约国授予投资者待遇的属性作出规定,故而造成“投资者利益”和“投资者权利”之争。就与现状的相容性及对事实的解释力而言,实体赋权说显然更具优势。实体赋权说下的投资者本位及缔约国本位两种取向均不否认投资者享有独立的实体权利,然而,投资者本位取向主张考察投资者是否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内容形成信赖,进而以此为标准对缔约国的事实性修订行为形成制约;而缔约国本位取向则主张以缔约国原意为基础,评价投资者权利是否得以被变更或撤销。对于上述分歧,笔者认为,投资者本位取向的核心前提存在缺陷。投资者本位取向的适用前提乃是将缔约国与投资者视为平等主体,由此,方可将调整平等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合同法原则推及适用。然而,缔约国与投资者间存在从属关系,而非平等主体。例如,根据合同法理论,非经第三人同意,合同当事人无权为第三人设定义务,而国际投资协定中已不乏对投资者设置义务之实例⑧,这正是缔约国与投资者间从属关系的体现。基于此,笔者认为,对投资者权利性质的界定,当取缔约国本位立场。对于投资者权利可否因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而发生变更,应回归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框架内,比照其中有关授予及变更第三国权利的规定进行分析。
(二)投资者权利对缔约国联合解释适用限制之破解
身处除旧布新的变革浪潮中,我国也同样面临着国际投资协定更新换代的问题。我国早期双边投资协定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本高度简约、表述模糊宽泛以及侧重维护投资者利益等缺陷。相较于条约修订,条约解释具有较高的适用灵活性及较低的谈判成本等诸多比较优势。鉴于此,我国可否考虑以缔约国联合解释为手段,事捷功倍地实现对现存国际投资协定的革新?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厘清投资者权利在何种情形下可对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构成限制。基于前文对投资者权利性质的解构,笔者认为:
第一,从缔约国本位立场出发,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7.2条之规定,授予投资者的权利能否为缔约国联合解释于嗣后变更或撤销,核心在于确认缔约国间是否存在“非经该第三方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之原意。基于此,仅在国际投资协定明确表示“不可撤销”地授予投资者特定权利的情形下,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可受限于投资者的既得权利。就中国所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而言,其中虽不乏条款明确表意为“不可撤销”地授予投资者权利⑨,但当前多数国际投资协定并未作出此项承诺。
第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存续条款规定不应视为缔约国在规定期限内“不可撤销”地授予投资者特定权利。根据存续条款的规定,国际投资协定对投资者提供的待遇和保护普遍可延续至协定终止后五至二十年。实践中,不乏国际投资仲裁庭以存续条款为依据,拒绝适用缔约国联合解释,从而维护投资者的信赖利益。然而,原则上该等条款应仅适用于缔约国单方或联合终止国际投资协定之情形。不仅如此,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条约的终止虽不应影响当事国在条约终止前产生的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但该等规定仍受制于当事国之间的协议约定。[19]在国际投资协定的缔约实践中,不乏国家明示约定,自新协定生效之日起,原双边投资协定下的权利义务即告失效⑩,从而排除了存续条款的适用。
综上,缔约国本位立场将分析框架回归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则体系内,以缔约国间的原意作为判断标准,评价缔约国联合解释的可适用性。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我国一方面应避免在国际投资协定或在与外国投资者所订立的商业合同中作出投资者权利不受变更或撤销的具体承诺;另一方面,在协定更替时应就原协定下权利义务的效力作出明确约定,以避免后续争议。
四、结 论
国际投资协定的特殊性在于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向投资者授予权利,并允许投资者以自己的名义对所受损害寻求救济。基于此,在投资者权利性质的界定上,应肯定国际投资协定赋予投资者独立的程序性及实体性权利。有别于以投资者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以缔约国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主张缔约国与投资者间存在从属关系,投资者权利应从属于缔约国对条约的解释及修订权,故不应将调整平等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合同法原则当然推及适用于缔约国与投资者之间。立足于以缔约国为本位的实体赋权说,当缔约国联合解释协定的内容与投资者的既得权利发生冲突时,应探求缔约国原意,以评价缔约国联合解释的适用性。
注释:
①本文所称“国际投资协定”,包括双边投资协定以及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投资章节。
②Thomas Wälde在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一案的独立意见中曾述及,国际投资法与传统国际公法间存在根本差异。Wälde认为,将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国际公法规则类比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这一作法值得慎思明辨。See 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Corporation 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UNCITRAL,Separate Opinion of Thomas Wälde,December 1,2005,para.13.
③See Pope&Talbot,Inc.v.Government of Canada,UNCITRAL,Award in Respect of Damages,May 31,2002,paras.51-52.
④See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2/16,Award of September 28,2007,para.386;Enron 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1/3,Award of May 22,2007,para.337.
⑤国内学界对投资者权利性质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意见。如有学者认为投资者具有实体权利一说存在先天不足。参见:赵海乐《国际法治视角下的BIT“联合解释”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17年第2期);另有学者则以“投资者实体权利”指代其研究对象。参见:沈伟《中国投资协议实体保护标准的自由化和多边化演进》(《法学研究》2015年4期)。
⑥条约的解释应仅限于澄清条文原有之意,理论上应不涉及减损投资者权利或对其附加义务。然而,实践中条约解释与修订的界限不明,对条约的解释亦可构成“事实性修订”,进而引发减损投资者权利或附加义务的效果。
⑦诉权与实体权利相分离的形态包括:诉讼担当、诉讼代位、诉讼承担及诉讼信托,但仅在诉讼担当制度中,当事人可在不取得实体权利义务的情形下,以自己的名义享有诉讼实施权。参见:肖建华《诉权与实体权利主体相分离的类型化分析》(《法学评论》2002年第1期)。
⑧如印度2015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设专章规定了投资者及其母国的义务。See Chapter Three-Investor,Investment and Home State Obligations,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https://www.mygov.in/sites/default/files/master_image/Model%20Text%20for%20the%20In dian%20Bilateral%20Investment%20Treaty.pdf.
⑨如,中国—马耳他《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第9.4条规定:“为第二款和第三款的目的,缔约各方作出事先的和不可撤销的同意,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lta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Article 9.4,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h/au/201002/20100206785134.shtml.
⑩Se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Peru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Article 10.20,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Download/TreatyFile/2561.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Republic of Peru,Article 9.17,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Download/TreatyFile/2601.
[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2017.
[2]赵海乐.国际法治视角下的BIT“联合解释”问题研究[J].现代法学,2017,(2).
[3]李庆灵.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5).
[4]张生.国际投资法制框架下的缔约国解释研究[J].现代法学,2015,(6).
[5]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Greece v.United Kingdom),Judgment of August 30,1924(Objection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PCIJ Series A.,no.2.
[6]Lavopa,F.M.,Barreiros,L.E.and Bruno,M.V.How to Kill a BIT and not Die Trying:Leg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Denouncing or Renegotiating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Int’l Econ.L,2013,Vol.16,No.4.
[7]The Loewen Group,Inc.and Raymond L.Loewen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CSID Case No.ARB(AF)/98/3,Award of June 26,2003.
[8]GAMI Investments,Inc.v.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UNCITRAL,Final Award of November 15,2004.
[9]Mondev International Ltd.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CSID Case No.ARB(AF)/99/2,Award of October 11,2002.
[10]Roberts,A.Triangular Treaties:The Extent and Limits of Investment Treaty Rights,Harv.Int’l L.J,2015,Vol.56,No.2.
[11]Douglas,Z.The Hybrid Foundation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Vol.74,No.1.
[12]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肖建华.诉权与实体权利主体相分离的类型化分析[J].法学评论,2002,(1).
[14]吴文嫔.论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范式[J].比较法研究,2011(5).
[15]Moloo,R.When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The Relevance of Subsequent Party Conduct to Treaty Interpretation,Berkeley J.Int’l L,2013,Vol.31,No.1.
[16]UNIDROIT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2010,Article5.2.5,https://www.unidroit.org/english/principles/contracts/principles2010/integralversionprinciples2010-e.pdf.
[17]Case Concerning Nuclear Tests(Australia v.France),Judgment of December 20,1974,I.C.J.Reports 1974.
[18]Sourgens,F.G.Supernational Law,Vand.J.Transnat’l L,2017,Vol.50,No.1.
[19]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http://legal.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