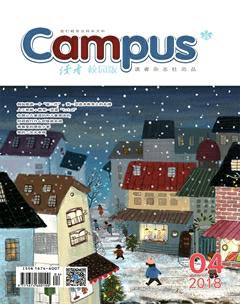三年级往事
路明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妈生病了,先是躺在镇卫生院的病房里挂盐水,后来转院去了上海。上海的医生说,病发现得早,我妈没什么大问题,但要开刀。
我当时懵懵懂懂,并不觉得担忧或者哀伤。我妈不管我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以前都是我妈早起给我做早餐,她去上海后,我爸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一块钱,让我自己买早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肉包子3毛钱一个,菜包子和烧卖两毛钱一个,豆浆1毛5分钱一碗,小笼包8毛钱一笼。要是再多一点,1块5毛钱就可以买一碗加了雪菜的咖喱牛肉面,牛肉切得很薄,铺满整个碗口。只有十字路口的“北方饺子馆”卖这种据说是上海风味的面。
剩下的两顿饭,我去爷爷家吃。放学后,我不用写作业了,牵着爷爷家的土狗到处瞎逛。爷爷有一个邻居是自来水厂的职工,每次看见我都会说:“哎哟,今天又过来骗饭吃。”我“咯咯”地笑,觉得“骗”这个字用得很高级。晚饭后,我爸来接我回家,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上桥时跳下来一路小跑,到了桥顶再跳上车。我爸是高中老师,他上夜自修的时候,我就自己回家,脖子上挂着钥匙,一路晃晃荡荡。回到家,溜到爸妈的房间偷看一会儿电视。我至少要在我爸回来前10分钟关掉电视,否则我爸一摸,电视机壳是热的,我就要挨打了。
周末,我爸去上海陪我妈,我就彻底自由了。爬树打鸟,下河摸虾,跟一帮野孩子玩打仗,折一根竹子当青龙偃月刀。我爸给我的早点钱我通常能省下一半,到游戏厅换3毛钱一个的铜板,打完了站着看别人打。直到我爷爷找到游戏厅,揪着我的耳朵让我回家吃饭。
一天中午,我吃完饭早早到学校。教室里没几个人,我有点百无聊赖。咸菜瓶问我:“你怎么来这么早?”
咸菜瓶大名严彩萍,吴语中“咸”和“严”不分,到后来,连老师都叫她咸菜瓶。咸菜瓶拖着清鼻涕,坐在最后一排,长得比我还高一头,成绩长期在倒数几名徘徊。我平时不怎么跟她说话,有一个老街的纨绔子弟对我说:“我们‘街上囡就跟‘街上囡玩,不要跟‘乡下囡玩。”
我懒洋洋地回答:“我妈去上海了,家里没人啊!”
“你妈干吗去上海?她生病了……你妈死了。”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说出这几个字,我明明白白地看见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咸菜瓶歪着头,挑衅地看着我。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血涌上来。我走到咸菜瓶面前,朝她的脸上用力一拳。
她低头擦了一把鼻子,手上沾满了鼻血,脸上满是疼痛、愤怒的神色,还有不可思议的表情——这个弱不禁风的“街上囡”居然敢先动手。
拳头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发了狂,扑过去拳打脚踢。
几个同学跑过来,连拉带拽地分开了我们。
“猪猡!”我骂道。
“你才是猪猡!”她对我怒目而视。
我抓起她的铅笔盒扔到楼下。她冲过来想抢我的书包,我死死地拽着书包带。课桌掀翻了,两个人滚到地上。在场的同学惊呆了,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见过我打架。
班主任端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里。他说:“据目击者汇报,是你先打的人。”对这一点我供认不讳。
班主任问:“你为什么打人?”
“她骂我。”
“骂你什么?”
我低下头,不说话。
“说呀,”班主任不耐烦了,用圆珠笔敲着桌子,“赶紧说!”
“她骂我妈。”
“骂你妈什么?”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一言不发。哪怕是小孩子,也会有这种说不清的忌讳吧。我不愿重复那几个字,仿佛那是一句可怕的诅咒,说出来就会变成现实。
班主任显然对我的倔头倔脑很不满意:“罚你做一个礼拜的值日生,从今天开始。”然后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出去吧,都出去!”
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了,留下我一个人搬凳子、扫地、倒垃圾……泪水滴到地上,溅起一小团尘埃。
咸菜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一把抢过我的扫帚,要扫地。
我把扫帚抢回来,她又要来抢。我擦擦眼睛,冲她吼道:“滚!”
她愣了一下。我又说了一遍:“滚!”她的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出来。她一跺脚,就转身走了。
晚飯后,我爸来接我,他已经听说了我打架的事情。
“你干吗跟她打?”我爸叹气道,“严彩萍是个没妈的孩子。”
“啊?”我惊诧地抬起头。
“你不知道啊?”我爸说,“听说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她爸经常打她,后来又讨了个媳妇。对了,她骂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