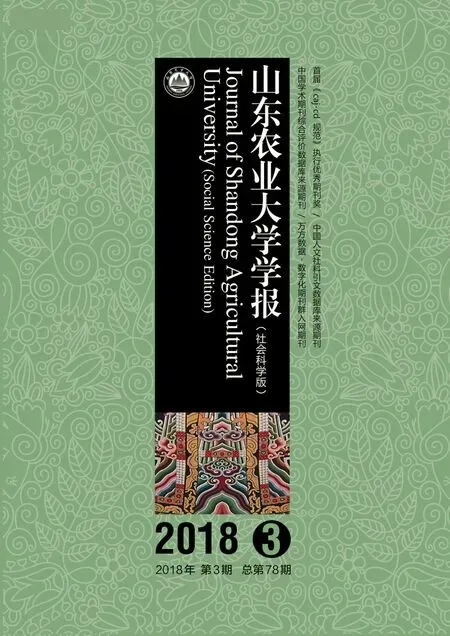《禹贡》篇章艺术及地理思想价值探析
□孙 娟
[内容提要]《禹贡》具有着篇章艺术,其结构严密,以贡赋为中心,九州为经、五服为纬两条脉络,以九州山川、五服制度为两大板块,篇首、过渡、结尾处三次点题。其语言精妙,展现为用词精准严密、句式多变、多用同义词和动词,既有严格书法体例,又富于变化。《禹贡》作为中国系统的地理志,具有丰富的地理学思想,建构了民族地理认知的基本框架,确立起了清晰的华夏地理视阈和大一统思想。
《尚书》是中华上古历史文献汇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功业确立起了民族圣贤政治理想模式和基本内容,以德范位的政治诉求,天命依德的政权更革,圣圣相传的道统谱系,形塑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尚书》还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古奥的文风、精致的结构、朴拙的修辞等对后世文章之学有深远影响,往往成为矫正华丽文风的依据。今以记述“禹身历九州,目营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1]212,被奉为“古今地理志之祖”[2]的《禹贡》为例,剖析其呈现出的高度成熟的艺术技巧和丰富的地理思想,可以管窥经典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形塑功能。
一、谋篇布局:结构严密,体大思精
《禹贡》是中国地理志成熟的标志,全篇条陈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修治,作为贡赋之法,以告成功于上,使君王以此为取民之常例。全篇叙事谨严简练,不到一千二百字便涵括政、教、兵、财等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系列内容,可总结为:分地域、奠山川、修六府、赐土姓、奋武卫、讫声教、明道路及定贡赋等“十二要义”。此文所载事虽不一,实则以任土作贡为主线叙述。
(一)经纬双线
《禹贡》叙大禹“奠高山大川,任土作贡”,而以“贡”名篇,划九州与定贡赋是全篇的核心内容,禹迹九州之“禹”为经线,大禹功绩之“贡”为纬线。“禹”(划九州、平水土、明道路)为“贡”(制五服、制贡赋)奠基,“贡”(五服与贡赋)又是明“禹”中央之尊、天下之序的重要手段,两者皆不可或缺。故《禹贡》有两条发展脉络:以山川为经,以贡赋为纬;一条在明,一条在暗;九州部分经明纬暗,五服部分纬明经暗。明线联系上下的内容,令结构完整严谨;暗线决定文章的基调,喻深层主旨内涵。经纬双线贯串全文,彰显行文的方向性。
(二)两大板块
《禹贡》的架构完整严谨,全篇可分为两大板块:分九州奠山川、制五服讫声教。前为事实基础,后为观念加工。不仅板块间关系紧密,而且各板块内部也有严密的逻辑顺序。
板块一自“禹敷土”至“九州攸同”,以自然地理为径,规划了理想中的华夏地图。首句“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总述禹分别土地以为九州,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此三者:分州、随山、浚川,乃大禹治水之要,故首述之。[4]40)据此可分三部分,即:九州、随山、浚川。自“冀州”至“西戎即叙”为九州部分,以帝都冀州(于此地受命治水)为先,叙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游始,其后依次为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以顺时针顺序历叙九州山川风物。自“导岍及岐”至“至于敷浅原”为随山部分[7]。浚川之功始自随山,故导水次于导山,(且导山之目的是治水)故其后自“导弱水至于合黎”至“导洛自熊耳……入于河”为浚川部分,因山水皆源于西北,故叙述山水皆从西北至东南,导山先岍、歧,则导水先弱水,后依次为黑、逆(河)、漾、岷(江)、沇、淮、渭、洛,叙述九条主要河流的名称、源流以及疏导情形。
板块二可分作两部分,将地理空间由自然秩序转向宗法格局。自“九州攸同”至“不拒朕行”。首句“九州攸同”点明此段要旨。总结九州,平治水土,制定土赋,禹功已成。起衔引之效,使论述由九州至五服,过渡自然。自“五百里甸服”至“告厥成功”。以冀都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辐射,分甸、侯、绥、要、荒五服。继而分甸服为五等,量其地之远近而定贡赋之轻重精粗,依次纳总、铚、秸、粟、米;分侯服为三等,“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分绥服为二等,“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此乃内外之分);分要服为二等,“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分荒服为二等,“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制五服,讫声教,“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4]66。五服制以九州山川为基础,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形成从王都出发笼罩四海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九州与五服互为补充、互相阐发,九州为自然领域则五服为人文图景,九州为根柢而五服为纲维。
裁章贵于顺序,《禹贡》两大板块结构严密,逻辑秩序井然。上古时期洪水横流,不辨区域,禹“相其便宜”,随山浚川,因势利导,治之以为人居之境,终“秩其祭而使国主之”[4]41。两大板块脉络清晰,环环相扣而又相辅相成,于主旨的阐发不无裨补,亦可见《尚书》谋篇布局之大概,各个板块相对独立,或并列或递进而有内在联系,主干突出而中心明确。此外,与两条脉络相互照应,明暗线索互相转化,而更具灵动感。
(三)三次点题
“启行之辞”[5]175,开宗明义。篇首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叙禹以“随山”疏浚之方,“分布治”[11]九州之土,使复其常,再定高山大川以为州境之纪纲,而复新九州贡赋之法。与序言相比,有删略、重复与增补。先言删略:不言作贡,是因《书》文尚简,《序》已言“任土作贡”,故此因前省。犹《仲虺之诰》,上既言“仲虺作诰”,下不言“作仲虺之诰”;《微子》上既言“微子作诰”,下亦不言“作微子”也。次言重复:《序》既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此又复言,盖因《序》、文相对独立。后言增补:一为“刊木”,循山伐木以通蔽障,以望观其所当治,以便规形度功,以明道路而后兴水工,增此“刊木”,以明治水之基础;一为“奠高山大川”[12],定其次序大小,复其祀礼旧制。《周礼·职币》曰:辨其物而奠其禄。奠,定也。“郡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6]19“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能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能迁。”[7]280此不易之秩序,乃天地之“大经”:封国可变,而山川不变;山川不变,则疆域不变;疆域不变,则江山永固。
贯珠之语,(即“板块二”)再次点题。先紧承九州格局及随山浚川,总结禹迹水土平治;次总叙贡法之制;次言“锡土姓”,为下文“制五服”张目。王氏曰:“锡土姓者言建诸侯,赐之土以立国,赐之姓以立宗[8]108”,“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有土则必有氏,而赐姓为难。锡土姓谓始封之君有徳者也”[1]811,而后“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叙禹之功成(修平水土、任土作贡、分封诸侯),时时不忘点题,又与篇尾遥呼。
篇终追媵前旨。篇尾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再言禹之成功。关于“锡”之主客可二分:一为尧锡禹受,一为禹锡尧受。今通观全篇,复查题义,既以“禹贡”名篇,则禹为“锡”之主体,言“以玄圭为贽”告其成功于舜。原因有二:前既于冀州受命治水,此必归于冀州复命述职,应以禹为本体;通观全书,若此句旨在阐扬舜禹君臣谦让互美之大义,则置于虞书之中更为合适。本就作于虞时,若其要旨又合于虞书,岂会编为夏书之首?惟以禹为主,则合题义,且不令其旨逸。把握文本结构,对于理解题旨,不无裨益。
若“经”为分类框架,“纬”则将其系列化,二者所绘之交点,即要旨所在,也即为政治用力之焦点——九州贡赋之所在。若不知九州之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禹贡》便紧扣此要义,它之所以彪炳千古,得益于格局之宏大。
二、炼字琢句:语言精妙,寻理即畅
《尚书》“辞尚体要”,文虽简约,义却宏范,遣词造句也简明严备。正如《禹贡说断》所言:“经文之妙,非后世史官所可跂而望”“犹之行水载、治、修之三字举于冀,而八州惟言其效……经文简严大扺如此,非深求其意莫能知也。”[8]《禹贡》言辞之妙,大抵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书法严密
《禹贡》叙治水土、入帝都之贡道用字精切,有严格的书法体例,推明书法,可明经旨,于读经有纲举目张之效。
《禹贡》用词精准而严密。逾,谈及“荆之贡道”[9]155时云:“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颜师古曰:“浮,以舟渡也。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在冀州南江。汉去洛远而不相通,越陆跨洛,故曰逾。”[10]20此“逾”乃指明“下之所贡”之道路。程氏曰:“不径‘浮江、汉’,兼用沱、潜者,随其贡物所出之便,或由经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4]52。“遡汉之极,无水可浮,则陆行至洛,以期达河”[8]52。此路线由水入陆,再经陆入水,终达于河(南北轴线),人为地规划了进贡的路线,显示了人文地理的向心结构。“逾”字在《尚书》中共现七次,有三次出于《禹贡》,除上条外,有“(梁)浮于潜,逾于沔”及“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可见在此文中,“逾于x”(x为水名)已成相对固定的表达形式。同样是荆贡此条,“浮”字亦应受到重视。“浮”字在《尚书》中出现十一次,八次出于本篇,形成 “浮于x,达于x”,的短语搭配。今以“浮于济、漯,达于河”条为例,详述此字。颜师古曰:“浮,以舟渡也。达,通也,因水入水曰通,又解在导川沇水济水下。”[10]8胡渭在《禹贡锥指》中也曾讨论:“因水入水曰达”,“谓不须舍舟而陆行也”[10]323。“浮”字的阐释中虽有顺流与否之争议,但不用舍舟而陆行这点,为学者公认。此点,“浮”与“逾”恰好构成对立面,但二者仅存在表面的“南辕北辙”,实质仍体现禹治水之大义,即顺应事物自身的“道”和“性”。汉与洛不通,禹没有强改水道使之通,以令贡能舟行至河(冀),而是尊重其固有特征,舍舟陆行再入水,既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又节省改道的人力物力。因势利导,乃禹治水成功之因,是“法先王”之典则所在。
此外,于动词的使用上,在与相似文献的对照中体现出辨洁、明核的审美特征。《职方氏》动词少,《禹贡》动词多。前者言九服,除“辨”、“曰”外,几乎皆为名词。后者则多动词,仅谈九州之水便有浮、达、入、沿、逾、至、乱、汇、迤、溢、流、别、导、被、会、过、同及载、治、修等动词,此类词俯拾即是。动词的精准使用,令主题明确而结构清晰、语言简明而真实可靠。文中还有大量同义词,研究此类语汇于理解文义大有帮助,且对读者日用常行中的运用不无启发。
与同类地理文献相较而言,《职方氏》同义词少,而《禹贡》多。前者不换字,言山称“山镇”,论泽曰“泽薮”,一以贯之,琅琅上口,音乐性与节奏感强,且与其义“使同贯利”相呼应;后者换字多,表义准确、精细、严密:
九州之泽,曰猪、曰泽者:昔焉泛滥,于是乎渟滀而不溢,故彭蠡、荥波皆曰既猪;昔焉漂流,于是乎钟聚而不散,故雷夏曰既泽。九州之土,昔焉沦没,不可种殖,水患既平,其地复治,则曰淮沂其乂、云土梦作乂。九州之山,祭之而水患平则曰蔡蒙旅平;已平而遍祭之则曰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非特水患平而已,又可施种殖之功,则曰蒙羽其艺。总叙众山,始随而刋之,终祭而报之,则曰九山刊旅;叙百川之浚导,则曰九川涤源;叙诸泽之涵浸,则曰九泽既陂。[10]52
言九州治则有泽、土、山、川;叙水土平则有既猪、既泽、其乂、作乂、旅平……深究其效:一,语词多变化,避免行文重复呆板;二,显同中之异,于周密表达大有助补;三,以同义联合,形成排比结构。
(二)句式多变
《禹贡》之句式多变可与同为描述地理的《周礼·职方氏》和《尔雅·释地》对比中看出。三者皆采用总分结构(前二者先总后分再总,《释地》先分后总),先总叙其要义以张目,次分条加以详述;取用递进式结构,先九州后五服(或九服),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以九州为经,以服制为纬;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语义连贯。此为结构上可循之规律。三者之同暂不赘述,就句式之差别而言,《职方氏》较固定,先论九州部分:
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11]431
以九州之整体为主体,依次谈及东南之扬、正南之荆、河南之豫、正东之青、河东之兖、正西之雍、东北之幽、河内之冀、正北之并,不言疆界,仅叙大体方位(九方位),各州下皆依次言其州名、其山镇、其泽薮、其川、其浸、其利、其民、其畜、其谷九项内容。而《禹贡》以山川别州境,多四言句,参差不齐,错落有致,富于变化。各州下“厥土”、“厥田”、“厥赋”、“厥贡”、“厥篚”等句亦具排比之雏形,修辞手法的使用令其文采焕发。再论服制部分: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五百里曰藩服。[11]432
《职方氏》以王畿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服,形成等距的同心圆差序格局,除王畿外,形成以“又其外方五百里曰x服”的单一叙述模式。句式整齐,层次清晰,用排比加强语势、增强节奏感,有益于显示泱泱大国之一统气势,于表达效果大有裨补。而《禹贡》之五服,于整齐划一的“五百里x服”内又有由精到粗的差等秩序交错其中,使文势贯一而不失变化,增添了几分灵动。
三、《禹贡》之地理思想
《禹贡》是地理文献中的典范,使华夏民族的地理观念从混沌走向秩序[3]223,也为后世的地理叙述确立了基本模式,其宏大的地理思想影响深远。
(一)九州的稳定性
《禹贡》所述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顺五行相生之序,其次序先北而东而南而中而西)[12]212,乃“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拥有双重意义的稳定的秩序,既可与九野相配成为天地之大经,也可象征江山社稷的永固长存。“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描述了人文地理的进程与空间观念的发展:其中“禹迹”指经过禹治理的古老神圣的区域,而“九州”由于以禹迹为基础,虽是讲“分”州,却不失“一”统,后成为整个华夏的代称。“九”与五方位关系密切,皆为具有稳定性的传统方位观,秩序不乱则“中”的核心地位不变,这不仅源于九方位的本质属性,还与分州所蕴含的山川崇拜思想有关。“九州”作为区域叙述术语,分州必以山川定界,由于“封国可变,而山川不变,山川不变,则州域不变”,后世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正所谓“人祖在五帝,地祖在九州”,以高山大川定疆界有正史《地理志》以封国或郡县来叙述地理物产的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崇高性与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不仅确立了民族地理界域,也限定了华夏的民族性格不具有对外侵略的扩张性。
(二)五服的文化中心论
自都城向外,以五百里为一层向四方均衡递变,将九州的自然分区整齐划分为甸、侯、绥、要、荒的五服制,蕴含“向心”的文化空间结构。五服是有中有方的空间等级叙述,明确了地域的中心与边缘,代表了中国最典型的天下观念。边疆滞后、中央先进成为空间思维定式,“向心”是华夏文明的动态空间结构,即在追求各领域的最高价值时,表现出价值内求、趋向中央的空间行为模式。“中”具有很强的政教意义,不仅指向由生存环境塑造的虽不乏智慧却稍显保守的文化性格——中庸和平,还指向权力核心的“拱极”、“独尊”地位。这种“天下之中”的观念凸显在了明清紫禁城的平面设计上,也使文化景观显现出权力景观的可视性。
其次为华夷之辨中的文化界限。五服可分为两个层次,绥服介于中原与外域的交界带,“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其内为文明之域,外为蛮夷之地,包含夷夏两分的民族大义。但划分“华夷之限”的根本标准并非政治或地理之限,而是文化界限:主张“四海会同”、“声教讫于四海”,鼓励支持华夏文明向外的传播与弘扬;承认声教感化,鼓励蛮夷吸收华夏文明,为多民族大融合提供可能;夷夏互化,压力与动力兼而有之,弃礼义则变夷狄,行仁义则为华夏。因而,宣称自己居“禹迹”内,为“文明之邦”,是自我、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海”,治理原则大多是恩威并施。
(三)《禹贡》的“大一统”思想
《禹贡》表面上以治水为明线叙述地理疆域,但实质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即以“大一统”思想为精神内核。大地域的政治整合势必会形成新的领土秩序,以“贡”名篇表面上在强调百姓感念禹功而自愿上贡输赋,实质是强调领土整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正所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德”不仅是精神世界的崇拜对象,也是权力正统性的衡量标准。宋人王炎认为:“九州有赋有贡。凡赋,诸侯以供其国用;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挈贡名篇,有大一统之义焉”[1]255。《禹贡》以帝都为中心的叙述和贡道的书写确有“一统”大义,贡道的向心性显示了地理观念的价值取向。“大一统”的实质是讲求疆域、历史和政权等的高度统一与前后传承。地理叙述涵民族“大一统”之观念,禹平治水土所至地域,关系到华夏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认同。
四、结语
“唐虞史官纪载之工简明严备,昭垂万代,灿若日星,后世《书》、《志》虽欲效之,弗可及已。”[10]52《禹贡》虽为地理志,但也具备较成熟的艺术技巧。《五帝本纪》曰:“惟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禹之以贡名篇是也。”文本以事名篇,而结构、语言和思想皆为其篇名服务。依文本线索,可通过对文章诸要素的分析,把《禹贡》的结构完全打开。文本可解构为一个中心、两条脉络、两大版块、三次点题,主旨明确而层次清晰;其语言呈现出用词精密、活用动词、句式多变等特点。“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5]154《禹贡》已具备较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仅《禹贡》单篇精深,《尚书》的大多数篇章都具较高的艺术技巧,其艺术价值应当受到关注。
《禹贡》在自然地理的现实基础上,以圣王禹的名义形成了具有永恒意义的理想空间秩序,将事实转化并上升为观念层面的爱憎标准与价值倾向。禹迹、九州、五服、大一统等观念的形成,是对华夏文明的超越政治区划的观念建构,由此产生的华夏认同力量成为评价后世权力核心正统性与完整性的重要指标,奠定了中华文明与华夏秩序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