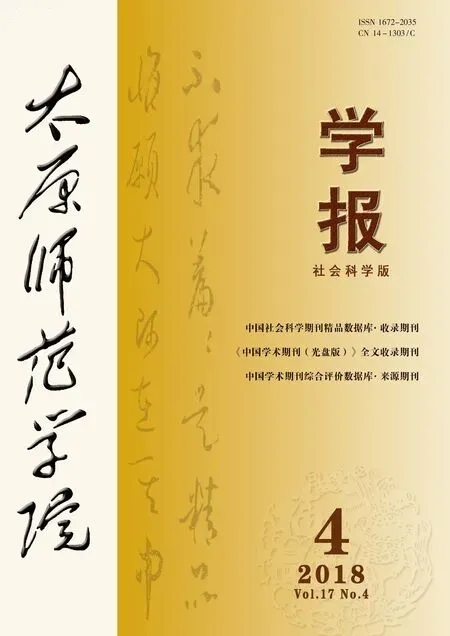小小说的文体创构艺术论
,
(1.辽宁大学 广播影视学院; 2.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小小说作为“热点”似乎已经趋冷,但是作为批评的对象和文体研究则永远不会过时。按理说,小小说不管有多么“小”,既是小说就应该具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共性特征,即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艺术诸元素一样不能缺。但话又说回来,小小说作为小说王国中的一只“小鸟”、一个“精灵”,或称“异端”和“另类”,的确有它自己的“章法”。它不同于长篇可作宏大史诗状,不同于中篇可作文雅中庸状,也不同于短篇可“小大由之”。近三十多年来小小说的繁花似锦、特立独行,为这种文体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经验。实践证明,小小说有其自身的特征和不同于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章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小小说的文体独特,所以小小说的文本创构艺术尤其重要。小小说发展的三十多年里也促生了许多小小说批评言论和小小说批评家。他们或以“微评”的方式推介小小说名篇佳作,或以“点评”的方式为名篇佳作“画龙点睛”,为小小说的推行和发展贡献着批评家的智慧和思想,王晓峰、杨晓敏等就是其中专攻小小说批评的代表。“小小说作为一种时尚读写的文化现象,所形成的一些文化规则与秩序,对文学的大规模普及,在当下缭乱缤纷的快节奏生活中,从表现形式到审美态势都拓宽出另一个生存与发展空间,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1]
“党存青是近期涌现的又一位小小说创作的新锐作家。”[1]笔者由阅读党存青的小小说而引发了对小小说的阅读热情,进而阅读了小小说家族的一些名家名篇,如汪曾祺的《陈小手》《捡烂纸的老头》《尾巴》、林斤澜的《水井在前院》、王蒙的《雄辩症》、冯骥才的《苏七块》、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毕淑敏的《紫色人生》、迟子建的《与周瑜相遇》等;同时也开始接触了一批在笔者的阅读视野里纯属“新人新作”的小小说精品,如许行的《立正》、司玉笙的《书法家》、何立伟的《洗澡》、周海亮的《刀马旦》等等。这些精品经小小说作家、批评家杨晓敏的“点评”,更增加了笔者对小小说的喜好,因此便想对“小小说的文体创构艺术”发表一点拙见,也许对小说理论建设和小小说创作会有一点帮助。
一、虚化背景,简约情节,刻意彰显人性
相比较而言,小小说一般很少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没有那么多笔墨“从猿到人”地讲述历史的沿革,细致地介绍故事情节的缘起、过程、高潮和结局,起承转合,娓娓道来,然后再推出主要事件、主要人物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小说不是一种“线性”思维的产物,它应该是“钻探式”思维的结晶,文体呈现的是一种“标本”或“切片”式的样态。它也可能有“历史”、有“来路”、有“背景”,但这些往往都是隐含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有时是没有文本表层信息显现的潜在因素。
周海亮的小小说《刀马旦》写得简洁、优雅、凄美,意境美妙。杨晓敏点评该作时说:作者“语言用短句,显得动感十足,节奏明快。行文清新绮丽,缠绵悱恻。故事、人物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轻轻一带便又巧妙打下伏笔。”[1]“作品主题拒绝说教式的、图解式的、背景式的设置,而是把人性开掘提升,坚持放在‘自我救赎’的力量上。”[1]整个作品,“疏密有致,境界不凡。”[1]“刀马旦”是传统京剧的一个行当。某剧团饰演“刀马旦”的女演员是一位台上精于专业行当、台下沉默寡言的女性,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女性自然博得了与她演对手戏的男同事“武生”的好感。“武生”多次主动与她接触,还冒死在一次下乡演出时发生的火灾中救了她。“武生”还听说她的婚姻不幸福,丈夫坚持要与她离婚。一个星期天,“武生”被“刀马旦”荣幸地邀请到家做客。当她把房门打开的一瞬间,他惊愕了:“刀马旦”全身披挂,俨然一副正式演出的架势。原来“刀马旦”的丈夫长期卧床不起,没有机会一睹妻子的舞台风采,她特意邀请“武生”前来家中助演,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真相亮给了心仪自己的他,一举两得。“刀马旦”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令武生感动,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等多久都等”的心愿。《刀马旦》篇幅短小,笔墨集中在三个人物(先出场两个人物,另一个最后出场)关系的叙述上,文字表层的信息似乎很单纯,但是整篇作品情感张力极强。《刀马旦》做到了虚化甚至简化背景因素,有故事却并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笔力集中在人物情感的集聚和释放上,“悬念”的设置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更增加了情感的深沉度和震撼力。
党存青的小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背景简化或者模糊的状况,特别是写到“文革时期”、“知青下乡”等敏感问题时,大都采取“隐含背景”的笔法。这不是不尊重历史,而是作家自觉的审慎态度。但是,读者完全可以通过故事的叙述、人物关系的处理、人物言行的设置等方面来体会时代背景,认识作品所指向的社会环境。作家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亮出那个时代的“伤痕”,替人物宣泄愤懑,而是将笔墨主要用在特定时代环境下人性的深层揭示这一主题上。从小小说《打柴》《秦爷》《魏伯》《口粮》《儿媳》《疯女》等篇章,可以隐约读出那个压抑人性正常发展的背景信息。但是,作品更多的是揭示在那种反常的人文环境中人性美好的一面,秦爷不愧为一个顶风冒雪、一腔热忱的“爷儿们”;魏伯的敢于担当,忍辱负重,牺牲自己保护他人的古道热肠;古家和身为村干部,利用有限的“权力”保护村民生存和生活权益的言行等等,都体现了作家对小说人物和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视。但是,党存青的小说没有回避矛盾,有着鲜明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党存青小小说集》中的头题篇章《儿媳》,则是以一种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批判了乡村伦理文化与权力文化扭结变异产生的“怪胎”。党存青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平民关怀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体现,这也同样构成了他小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小小说虽然短小,虽然可以省去一些背景材料,但是思想、文化蕴涵却不可省略。
二、精于剪裁,压缩“闲笔”,凝练意涵
小小说因为篇幅有限,没有条件像中长篇小说那样汪洋恣意、挥挥洒洒、酣畅淋漓、一泻千里,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篇幅可以让作者尽情“挥霍”,所以一般作品都精于剪裁,尽量压缩“闲笔”,凝练意涵,以有限篇幅包容尽可能丰富的内涵。经典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论小说艺术时说过:“简练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须。它要求的是:永远直接地走向事物的重心。”[2]68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小说创作要“直接地走向事物的重心”并非“直奔主题”。这“重心”应该是作家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核心意涵,而只有摈弃那种废话连篇、“言不及义”的弊端,才能做到“直接”。
当然,经典作家作品也有例外。汪曾祺的某些小小说“闲笔”不少,几千字的篇幅照样有“闲笔”,铺排、铺垫、荡开一笔的情形反而构成了他的创作特点。比如,小小说《捡烂纸的老头》起笔竟有一半的文字在叙述那个平民化的小饭店的状况以及“常客”的吃相如何如何,并没有集中笔力述说那个“捡烂纸的老头”,他不过就是“常客”中的“这一个”而已。其实,这正是本文的高明之处:“闲笔”不“闲”。作家是想让读者从众多的吃客中发现那个老者——一个更不起眼的拾荒老头儿。小说前半部分的铺排是在有意营造一种日常化的、平民化的生活氛围,通过这种氛围推出人物,强调的是人物的底层身份及其生存样态。当作品结尾处写到“捡烂纸的老头”死后,人们在他的床铺底下发现八千块钱的时候,才会更为震撼。一个老者每天省吃俭用,甚至每顿饭都喝别人丢下的残羹,身后竟然留下那么多的钱,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态度?小说中蕴含的意味引人思考,令人痛惜。
党存青的小小说特别善于剪裁,用当代著名作家刘兆林的话说就是“一点多余的材料也不要”。有限的篇幅集中写小人物、小环境、小事件,并且“小人物,小环境,小事件,展现的却是大时代的大的精神风貌。”[3]党存青小小说虽然集中写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却不只是活跃在单篇作品中,而是活跃在多个故事中,人物系列化、谱系化构成他的一个创作特点。同一人物可能出现在多个篇章里,每个单篇可以独立成章,单篇阅读,多篇作品串联起来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大的时代场景和一类人物的命运起伏。党存青笔下的“秦爷”“生茂”“柱子”“古家和”等人物都曾出现在多个篇章里,是他们把那些乡村故事、历史命运、文化变异、人物成长构成了一个“线性”的文学景观,从宏观上展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东北文化风貌。这样一来,小小说便以其有限的篇幅延展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信息,容纳了更多的文化审美内涵。从党存青的人物谱系化书写,不难看出他对著名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小说构成“陈奂生系列”,呈现了中国农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也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文体改革的一种范式,从而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的经典。
所以,党存青的小小说写的是乡土,讲的是旧事,塑造的是小人物,但从整体上看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蕴含,张扬着一种鲜明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他在审视普通人生时带有现代意识和哲学意味,通过人间百态来揭示人物命运,挣脱道德判断的藩篱来达到价值判断。他重视描写生活的本色,对自然原生态与精神原生态的双重再现,构成他探索人物心灵的幽暗,在多层面上挖掘生命意义与坚韧精神,擅于发现普通大众中的典型性,进而发掘出中国北方民众的乡土内涵。”[4]
三、“抖包袱”,“爆炸式”结尾,弦外之音
小小说的结尾几乎是全篇的眼睛,一个漂亮的结尾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或耐人寻味百读不厌的魅力。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被称为“典型的以柔克刚的思辨哲理型小说”[1],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主题的多向性。故事就是一桩极为平常的小事:父女俩到访,男主人倒完了茶急忙进了里屋。这时,客厅里的暖瓶却突然爆炸了。当主人端了一盒糖出来的时候,一边招待客人一边说“没关系”,“父亲”却主动说“我把它碰了”。事后,女儿却对此不解:“是你碰的吗?”确实不是父亲碰的,但男主人也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没有放稳暖瓶。父亲无奈的回答告诉人们,世上有些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而且往往越想说清楚越说不清楚,你想要说清楚的结果反而会遭来更多的麻烦。由此可见,小小说结尾最讲究“临床一刀”“临门一脚”,有一个“爆炸式”的响亮的结尾,同时也要留下思考、回味的空间。所以,一篇小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要有精彩的结尾,有了精彩的结尾往往就决定了作品的成功率,因为作品的成功率是由作家—作品—读者共同完成的。大量的小小说篇章揭示了一个“规则”:结尾检验作家的写作才华和超然的智慧;结尾几乎决定作品的全部思想蕴涵;结尾决定能否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和反复阅读的热情。
小小说的结尾不仅要有爆炸效应,还应该有弦外之音,于有限的文字中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余地,不要“一马平川”“一览无余”,要有“嚼头”,有弦外之音。汪曾祺的小小说《尾巴》的结尾确实可谓“弦外之音”。领导点名让人事干部“黄顾问”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审查发表意见。黄顾问没有正面回答领导的问话,也没有直接批判某些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无休止地审查的恶劣做法,而是给与会的人讲了个寓言故事。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个叫“艾子”的人乘船过江,船在水面上过夜。夜晚,忽听得水下一片哭声,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一群水族在哭泣,问它们为什么哭啊?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长尾巴的,所以在这里哭啊。”艾子深表同情。他突然发现一只青蛙也在哭泣,便问:“你又没长尾巴,你哭什么?”青蛙说:“我虽然没长尾巴,可是我怕龙王查我当蝌蚪时候的事啊。”与会者听了这个故事都哑言了。汪曾祺不愧为小说大家,《尾巴》的结尾真的是奇哉妙哉,没有批判的话语,没有讽刺的言辞,却令人感慨系之,其批判的深度、讽刺的力度尽在读者心中。
党存青小小说结尾有自己的特点,设置悬念、抖落包袱、语惊四座等等都是常见的结尾方式。《儿媳》不愧为党存青小小说的头题。仅从文题看起来,这是一篇点赞良家妇女“儿媳”、从正面歌颂乡村“好人好事”的作品,但读后却让人五味杂陈,令人啼笑皆非,原来这是一篇批判乡村权力异化和反思伦理道德的小说。谢队长利用“干部”身份与“村花”秀芝有染,秀芝怀了谢队长的孩子。谢队长的儿子雨竹是个“彪呼呼”的傻小子,偏偏看上了秀芝。队长夫人托媒说亲,秀芝父亲却默认了这桩亲事(实则是对权力的默认)。秀芝虽然不情愿“奉子下嫁”给一个傻小子,但却对谢队长说“反正都是你家的人”,嫁就嫁了。小说结尾写道:“开春种地时,秀芝生了个大胖小子。雨竹乐得合不上嘴,谢大嫂却有些模糊,怎么这么快?谢队长却从不抱这个大‘孙子’,而秀芝整天就知道傻傻地笑了。”这几十个字的结尾把小说中的几个人物一起推出来,而且同时活画了他们各自的表情心态,可见作者的文字功夫更像一支画笔,为我们画了一张具有多向讽刺批判力的漫画。
据追溯小小说源头的批评家透露,阿·托尔斯泰认为,初始时期的小小说就是“笑话”。他说:“小小说产生于中世纪,那些被挤在天主教堂和封建主城堡之间的小城镇狭隘街道上的居民,编造了一些针对宗教和封建主而发的毒辣的笑话。这就是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小鸟,文艺复兴时代的小说家赋予这种笑话以文学形式。”[5]他这段话中两次说道“笑话”这一概念,既为小小说的文体形式作了定义,也指出小小说产生的民间化特征及其“毒辣”的讽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小小说至少在欧洲诞生时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喜剧元素。纵观我们的新小小说,同样具有喜剧元素和刺激读者笑点的作用。会心的笑、含泪的笑、爆发式的笑等等,往往成为小小说家构建一个精彩“结尾”的普遍之道。
四、语感独特,惜字如金,篇幅短小精悍
如果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小小说便是小说王国中的精灵,小小说对语言的要求更为苛刻,需要作家具备语言的天赋,有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使得小小说的语言真正能够像刘震云所说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虽不能字字珠玑,但在用语理念上一定要有惜字如金的思想。当然,这是小小说语言艺术的理想境界,需要千锤百炼,需要学习贾岛“推”乎、“敲”乎精益求精的精神。
“语感是作家对文学语言的独特的敏感性,是语言风格的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我们说一位作家的语感很好,不是说作家擅于遣词造句,辞藻华美,意象独特,而主要是指作者对分寸感和节奏的把握。”[6]98“由于语感的产生因人而异,作家对语言的把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语感通常是不可言说的”。[6]99党存青的小小说语感独特,分寸感强,节奏明快,惜字如金,短小精悍。用李轻松的话说,党存青的小小说没有一句废话,“他做到了惜字如金,也做到了最后的简洁,但都不失为生动。犹如一幅山水画,他先画必是画山是山,画水是水,一山一水都需笔墨堆积;但当功夫到了,他画山不似山,画水也不似水,但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却是山之魂和水之魂。这必是走过千山万水之后,才可以随性地描摹出的心灵山水,是无限的。他写得简洁,在叙述过程中从不拖泥带水,总是能够捕捉到最典型的特征,下笔有神。”[4]
东北作家的语感非常有特点,具有浓重的关东乡土气息,这可能也是近年来东北小品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作家对语言的感受力往往不是刻意学来的,而是具有地缘性的天资天赋。党存青的语言感受力就特别强,他能够从整体上驾驭知识分子语言、民间方言俚语,包括在东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嘎古话”,经过融会贯通,准确应用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便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味的语言特色——党存青式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叙述语言上,民间话语书面化,风趣幽默,简洁明快;“彪乎乎的”“虎凿凿的”“妈吧子”等人物个性化语言直接描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更重要的是党存青所设置的独特“语境”,如《儿媳》的结尾,离开了谢队长、队长夫人、队长儿子、儿媳“四人对谈”的特定语境,自然无法实现作者采用黑色幽默的艺术效果。
小小说的命名和界定,文字多少、篇幅长短是主要依据。字数少、篇幅精短是一个外在的结构框架。小小说最初被认定为篇幅在三千字左右的小说,进而又被定在一千五百字的篇幅。其实在作家笔下有的小小说只有几百字,如何立伟的《洗澡》六百多字、司玉笙的《书法家》包括标点符号一共才179个字。所以,笔者认同小小说为“微小说”的命名。小小说也好,微小说也好,字数少、篇幅小虽然是其定义的关键依据,但是其微小的外壳必须包含着精致的思想、情感、审美的诸多元素,才能无愧于“短小精悍”的文体要求。在仅六百多字的《洗澡》中包含着人们对刻板的、枯燥的生活的无奈,对浪漫的个人生活空间的希冀。公务员“老何”每天生活在早八晚五、三点一线的枯燥乏味的生活中身不由己。某一天,老何下班走到一条僻静的老街时,听到一座被常青藤遮掩的院落里飘出悠扬的钢琴声,老何便沉浸在这种精神享受之中。有一天,妻子下班路过,见丈夫老何站在那里陶醉着,便问了一句:“站在那个鬼地方干什么?”老何从他沉浸的乐境中惊醒过来,答曰:“洗澡!”挣脱乏味刻板的生活,寻找诗意,可谓这篇作品十足的韵味。司玉笙的小小说《“书法家”》,对体制弊端、官僚作风的尖锐讽刺批判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正可谓“一剑封喉”。作者仅用一百多字刻画了一个文牍主义、官僚气十足的“局长”形象。高局长被邀请参加书法展会,办会的人诚邀高局长也一展其书法艺术,局长“挥毫泼墨”熟练地写下“同意”两个大字,“人们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要他再写几个。高局长却回答说:“能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书法家”》虽然不似《洗澡》那么有味道,但似乎更为“毒辣”,“意味”更为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