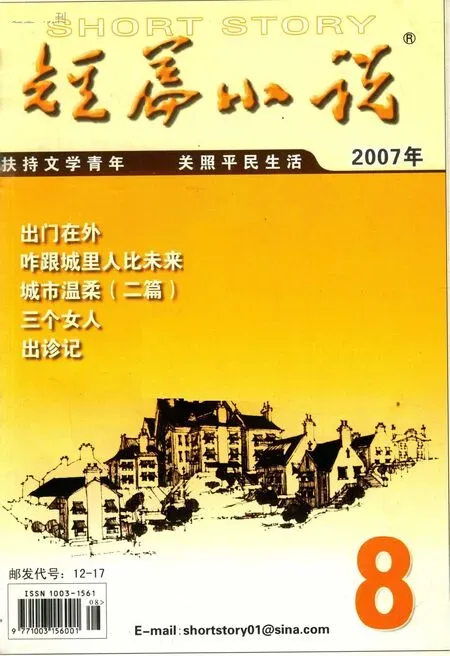生死往返
◎邱 力
1
站在街头,面对步步逼近的夜色,我有点气馁。
这时候,雨水为夜色推波助澜,紧一阵慢一阵的。我的面前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雨伞。我看不清行人的面孔,但每一柄雨伞下面的面孔应该都是从容镇定的,因为他们至少不用为回不了家而担心。晃来晃去的雨伞让我想要回家的念头越发强烈。可该死的出租车要么不来,要么一闪而过。为了躲避汽车经过时溅起的污水,还有越来越密集的雨水,我只好步步后退。我身后不远处是张双喜举办婚礼的丽天酒店。一些客人正陆续走出酒店大门,从人数上猜测,张双喜的婚宴已接近尾声。
看来今晚得留在乌的市了,天意如此。
我想,作为张双喜对外宣称的最好的朋友,张双喜不会不考虑安排住宿吧?何况我连婚宴上的任何一道菜肴都没有吃上一口,现在我已是饥肠辘辘了。就在我打算返回酒店去找张双喜时,我看见张双喜和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女人出现在酒店大门。张双喜殷勤地用左手为女人撑着雨伞,右手环绕在女人的腰部。这只代表着主人意图的右手略显慌张地在女人的腰部游走,二人边走边说话。张双喜西装革履,胸佩一朵写有“新郎”字样的胸花,脸上是一副被酒色和财气浸泡得浮肿的神情。他和那个女人亲密的样子让人浮想联翩。我正犹豫着是否上前打招呼,或者先进入酒店去等候。这时,张双喜看见了我,他向我挥了挥手:“嗨,怎么样,我就猜准了你打不到车。”我还来不及说那今天晚上只好由你安排了,他就接着用右手轻拍身旁那女子的肩头说:“我同学。正准备回家哩。你不是要去火车站吗?你们正好拼车。”
张双喜说这话时,左手仍然高举着雨伞,为那个女同学忠心耿耿地遮风避雨,而我仍然沐浴在风雨中。看来张双喜丝毫就没有考虑要安排我的住宿,倒像是急着要让我赶紧滚蛋。这就是张双喜一贯的行事作风。多年来和他交往的经验证明,从来他都是需要你帮忙时像汉奸一样点头哈腰,一旦帮完忙后他就会变得像个暴发户一样目中无人。他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样的雨夜让我独自赶回瓮中县城,有必要吗?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参加张双喜的婚礼,更不应该答应帮他拍摄婚礼。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留在乌的市。先找个干净的小旅馆,然后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榨菜肉丝面,再洗个热水澡,最后慢腾腾地钻进柔软的被窝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等天光大亮再走。反正像我这种体制外的自由人用不着担心迟到早退。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捷达出租车停在了我们面前。出租车司机不耐烦地说:“快上车,我还得赶回家去补补瞌睡。”听他说这话好像是专门来迎接我们似的。我一直苦苦等候的出租车竟然就这样轻飘飘地从天而降。张双喜那位女同学把黑色风衣紧了紧,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边脸,低头上前一步拉开前排车门,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走吧。记得抓紧时间帮我把婚庆刻录成碟啊。”张双喜朝地上啐了口痰,“兄弟之间,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他妈的,这鬼天气。”我不由自主地被张双喜推进了出租车后排。
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事情可能一开始就错了,知道错了还将错就错,那就真是件不可救药的事情了。
2
张双喜在婚期到来前一个星期,托朋友捎话,要我参加他的婚礼,并顺带将一张大红请柬送到了我的手里,还不由分说地给我安排了摄像的光荣任务。那段时间,一些相识的和似曾相识的朋友仿佛突然间想起了我,他们纷纷以发送请柬或口头邀请的方式,要我务必出席他们各式各样的重要活动,比如结婚、离婚、复婚、满月、升学、乔迁、寿宴、葬礼等等。我的出席总让大家莫名其妙地激动不已,大家一边说着好久不见啊,你这小子光顾自己发财不管朋友死活之类的客套话,一边用好奇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个刚刚刑满出狱的犯人,或者是个刚刚海归的成功人士。频繁的握手和拥抱造成我右手骨节酸痛不止以及持续胸闷,回家后我不得不用正红花油反复揉擦。他们的盛情相邀让我备感温暖,同时又使我囊中越发羞涩。
如果参加张双喜的婚礼,我得乘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换乘汽车亦如此)抵达乌的市,还得协助不相识的婚庆公司人员摄像。这样一想,我立马变得犹豫不决起来。我于是打算托人带份礼金给张双喜,再编个什么理由取消乌的市的行程。
在瓮中县,我经营着一家以策划庆典为主的“良辰吉日”公司。近段时间,来公司洽谈庆典活动的客人越来越少,倒是有些不速之客希望我能为他们刚去世的亲人策划一场风光的葬礼。因为这事晦气,我没有接受,和钱不钱的没关系。每天走进公司,见两三个员工坐在电脑桌前,懒散地上网聊天或者表情亢奋地在网游世界里战斗。他们连看我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他们用这种态度表示对我的失望和抗议。我估计如果再这么走下坡路,不要说再想爬上坡来难上难,恐怕这些正在玩电脑的家伙很快就会炒我这个老板的鱿鱼了。推开窗户透透气的时候,放在黑色写字桌上的一堆杂物被风吹得一阵乱响,张双喜那张大红请柬格外醒目。我在整理桌上杂物时,又翻看了一眼请柬,上面注明的婚礼时间为:9月24日下午5时30分。我发现,眼下距离张双喜的结婚时间正好是半天。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出发的话,那么当天下午5时30分,我就会如期出现在张双喜的婚宴现场。这半天时间,似乎是特意为我出行预留的。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个声音在说,别犹豫了,走吧,张双喜不是说要介绍几位成功人士给我认识吗?还有一单大业务等着我去谈。再说,也可以顺便参观考察其他公司的婚礼庆典是如何策划运作的。
这次出行,兴许能让我真的迎来 “良辰吉日”呢?
9月24日中午,我带着那台松下高清摄像机以及一些零碎物品,坐上了一列开往乌的市的火车,怀着又高兴又惶恐的奇怪心情去参加一个名叫张双喜的朋友的婚礼,这种奇怪的心情类似于我前些日子准备结婚时的心情。
一路上,火车“哐当哐当”响个不停,带着我从一个隧道冲向下一个隧道。
黑暗,吞没,绝望,呼啸……
火车奔驰的样子像一个亡命之徒大声叫喊着慷慨赴死。忽明忽暗的光线让我心生恍惚,我感到喘不过气,窒息。这种状态让我觉得随时会有惨案发生,比如爆炸、塌方、脱轨……
这种状态跟我眼下遇到的糟心事息息相关。
我耳畔仍然回荡着张曼砸门而出时的那声巨响,整栋楼房都在摇晃。我心都碎了。张曼是我相交八年的女友,近段日子我们一直在闹。这次闹得最凶,我现在连吵架都提不起神。我想保留一个男人残余的尊严,还有张曼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份美好,哪怕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吧。房间里面仍然残留着张曼的味道,还有那张我们辗转反侧的双人床上,雄性荷尔蒙与雌性激素的气息仍然纠缠不清。八年了,从厂里出来到自主创业开公司,除了没有那一纸婚约,没有办场像样的婚宴,让张曼像模像样地穿上洁白的婚纱,没有郑重其事地称呼她的父母为爸和妈。其他方面,我们和所有夫妻一样,混迹在同一个屋檐下,为油盐柴米酱醋茶焦头烂额。每当我跃跃欲试的关键时刻,张曼一再叮嘱:“老公,为了我们的小孩能有个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千万注意别让我怀孕啊。”这句话让我至今心疼不已。八年时光,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确保在我们寻欢作乐时,张曼不怀孕。许多夜晚我不无悲哀地发现,面对一丝不挂的张曼,我的小兄弟竟然成了缩头乌龟。乌龟就乌龟吧,最担心的是如果有一天准备就绪了,我的种子却不能在张曼的子宫里开花结果。我们走过了像夜晚那么长的路,如同正在穿越的黑暗的隧道,终点站总会在前方抵达,张曼却毅然决然地砸门而去。我不怪张曼,怪只怪我不能够像张双喜一样,每次从乌的回到瓮中,就召集过去的哥们见面,就咋咋呼呼地喊,聚一聚聚一聚。见了面,就竖起那根伟大的中指,说:“我买单啊,一条龙,谁和我争,别怪我不把他当兄弟。”
丽天酒店是乌的市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通往大门的道路铺上了长长的大红地毯。走在红地毯上,听到美妙的曲子环绕左右,看见“长枪短炮”追随前后,来宾无不感到有如正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盛大仪式上。张双喜和新娘子刘玉玲缤纷亮丽的结婚照充斥于酒店的大门、过道、墙上以及各个目光所及的位置。尤其是楼面的那幅百余平方的巨照让人震撼:蓝天碧海映照衬托下,白色西装的张双喜和白色婚纱的新娘子相依相偎。张双喜左手轻托新娘子的香腮,右手环绕新娘子的细腰。
新娘子刘玉玲看上去真美。即使是卸了妆也美。作为张双喜的第二任妻子,刘玉玲的外貌完全符合张双喜一直宣扬追求的审美观。张双喜总算是找到个值得投资的女人了。刘玉玲偎依在张双喜身边,微笑着为我点燃香烟后,柔声细语地说:“双喜一直都在提起你,还麻烦你亲自来摄像,真的谢谢了。”我嗅到刘玉玲迷人的体香,看到洁白丰满的乳房上沿,浓郁的女人味扑面而来,他妈的张双喜真是艳福不浅。婚宴高潮迭起,主持人大声询问,要不要现场见证张双喜先生刘玉玲小姐纯洁的爱情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大家齐声高呼,吻一个、吻一个。刘玉玲却娇羞得像个处女,左闪右躲不让张双喜得逞。现场一片哄笑。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抓拍了许多精彩镜头。在新郎新娘为来宾敬酒时,刘玉玲换上了一套红色的中式背心,越发显得娇小玲珑。她对每一桌客人解释道:“我们家双喜血压高,这几天又忙得晕头转向的,他喝的是水,原谅他啊。我这杯?绝对是酒。不信你闻。”几桌客人敬下来,刘玉玲两颊粉红,双目顾盼生波,时不时还和熟客开点荤玩笑。神态跟先前那个躲吻的新娘子判若两人。
欢声笑语中,我忽然感到胸闷,便抽身离开了婚礼现场。
3
此刻,雨水正顺着车窗往下流。雨水的走向弯弯曲曲,像一条条虫子在车窗上爬行,爬着爬着,这虫子就不安分地乱窜起来,有些窜到窗外,有些窜到窗内,座位边缘有些湿漉漉的,我只好往中间挪了挪。
“嗨,这破天气,说下就下了啊。”司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我们说话,“哎,二位,坐我的破车,不乐意?你们运气好,要不是我急着往家赶,你们……”
“没有,还多亏你了,师傅。这破天气。”我只得跟着司机骂这破天气。前排那位身穿黑色风衣的张双喜的女同学,仍然不搭腔,不知在想什么。
“只要上车了就别急,早晚总会回得了家的,是不是啊?”
这句话说得太对了,简直就像是我兄弟说的话。我有点喜欢这位司机大哥了。是啊,尽管现在我又冷又饿,但是我总算是坐上了出租车,不久之后我将坐上一列开往瓮中县的火车,早晚总会回得了家的,早晚面包会有的,早晚会钻进热被窝里睡个安稳觉的。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很快在城区内的光明大街遭遇了堵车,而且这一堵就是两个半小时。
雨越来越大,车顶上响起持续不断的敲打声。整个世界成了破铜烂铁,被无数双手使劲敲打。车窗外模糊一片,时间已经不重要,饥饿感使我全身僵硬,蜷缩成一团。这时候下车是不明智的选择,只有等待。
司机抬手扶了一把后视镜,从镜子里看了看我,说:“原先跑车我一天起码跑个头十趟,现在呢,跑个五趟就算是阿弥陀佛了。都是他妈的这交通害人。”
司机说完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来一只乌龟,乌龟呈灰褐色,在司机厚实的手掌中探头探脑,从司机的右手慢慢爬行到左手,它对堵车和下雨视若无睹,神态自若,胜似闲庭信步。
司机从一旁取出个小盒,揭开盖后,夹出肉丝喂手中的乌龟。我在后面看得目瞪口呆。乌龟大口吃着瘦肉丝,全然不顾及我饥寒交迫的感受。我想这家伙吃完瘦肉丝后,下一步会不会喝点可口可乐?接下来又会不会引吭高歌?或者像这位司机一样破口大骂天气和交通?
“师傅,我们来玩‘猜手指’如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伸出只有四根手指的右手,撮成个圆锥形,左手将右手包围,只露出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指尖,“你如果猜得到我的中指,我多开你10块钱。猜不到呢,你给我5块钱。”
出租车司机来了兴趣,掉脸过来,露出稳操胜券的神情,略一观察,就抓住了他自认为是中指的指头。我缓缓松开左手,向他展示他的失误。出租车司机咦了一声:“你这手指奇了怪了,明明我抓住的是中指,怎么会是小指呢?”
他怎么知道,在厂里,凡是跟我玩“猜手指”游戏的人,十有九输。我是个失去右手食指的人,如果想使用食指来表达什么,就会让大拇指代替食指来完成,大拇指点头哈腰的,看上去好像我总是在表扬别人。
“想不想和我来玩‘猜手指’?”我用手轻轻点了下前排那位张双喜的女同学。她摇了摇头,仍然不搭腔,不知在想什么。出租车司机还想再来一次 “猜手指”,前面车流开始蠕动了。大约十分钟后,张双喜的女同学在路口下了车。雨中,我看见她脸色苍白而忧郁,右嘴角边有一颗醒目的黑痣。
4
午夜时分,我登上了一列开往瓮中县的火车。
在火车不停地摇晃和“哐当”声中,我又回到当年类似印刷机的声响和浓烈的机车味里。
张曼和我是瓮中县彩印厂的同事,包括张双喜、李爱民、王守国。我当时负责厂里唯一的一台海德堡彩色胶印机,这机子是厂里的宝贝,厂里揽大业务全靠它。张曼从技校刚毕业就到厂里做了我的学徒。张曼听话乖巧,一教就会。不像张双喜的那个徒弟,学了一个多月烫金机,连内六角的型号都搞不清,还经常将印件烫糊。张双喜忌妒得两眼冒火,好几次想单独约张曼出去耍,都被张曼笑吟吟地婉拒。我们这里把争抢别人的男女朋友称为“端飞碗”,张双喜他们眼睁睁看着我和张曼师徒情深,硬是端不走我的飞碗。出事那天,海德堡机子巨大的力量将我的右手卷进胶轮中,右手食指永远离我而去。张曼掏出手帕将地上的那截食指包裹,招呼正在给厂里送纸的货车司机送我到医院。整整十五天,张曼像我明媒正娶的老婆一样守护在我身边。正是因为这次事故,我和张曼成为正式的恋人。
直到八年之后,我们分手。
我养好手伤后,回到厂里,调到照排车间,兼着帮衬办公室出个墙报、写个总结什么的。张双喜离开了印刷厂,到乌的市混去了。
厂里越来越不景气,陆续有人办理辞职手续,去乌的市,或者去更远的广州、深圳、海南等地挣钱。瓮中县城人心躁动。人人都在往高处走,我呢,属于没有多大雄心壮志的那种人。在瓮中习惯了,发不了财也饿不死。张双喜却发了。据说是承包建筑工程项目、开洗脚城、买卖二手汽车等等。什么生意搞钱快就做什么生意,想不发都不行。
在和张双喜每次的聚会中,少不了的一个游戏就是“猜手指”。
这比划酒拳、斗地主、猜剪刀石头布简单而有趣。每次赢了对方,我都兴奋得大喊:“谁来和我猜手指?咹,谁敢来?”但每次面对张双喜,我都输给他。输的原因,大抵和心理有关。谁让有钱人全都霸气外露呢?最近的一次聚会,张双喜当着张曼的面,用中指指着我说:“杨力,你只配做个小指,连无名指都不配。张曼跟你,真他妈的亏大了。”
夜色中,站着几个若隐若现的人影,他们在瓮中火车站站台走来走去的模样,稀薄而且虚无。风又大又硬。到站已是凌晨。铁轨在夜色中泛着清冷的光芒。
比铁轨还要清冷的是这间曾经属于我和张曼的家。张曼跟我真的是亏大了?当年如果跟张双喜呢?即便她和张双喜离了婚,那笔补偿款也是相当可观的,足以让她在乌的市过上有声有色的生活,在衣锦还乡瓮中小城时风光无限。听说张双喜还要在瓮中县城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我不会再去参加,如今我孑然一身,张曼也许另栖高枝了,也许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公司经营不善亏欠的债务又更加让我无法入眠。
这时,手机响了。
在深夜,铃声显得尖锐粗暴,让人猝不及防。
“喂,你是杨力么?唉……就在一小时前,张双喜突然发病……脑溢血……家属的意思……希望你能为他送送行……多拍点东西……留个纪念吧……”
一个沙哑的女人声音低沉地说完,就挂了。
我竟然没有太大的震惊,仿佛一切都是天注定,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我从床上爬起来,倒了杯白开水。边喝边想,人死为大,婚礼都去了,葬礼就更应该去。何况还是最好的朋友呢?明天吧,我赶最早的一班火车去乌的市,和一个名叫张双喜的死者会面,而之前我所认识的那位张双喜才刚刚举行婚礼。
上了床,一夜无梦。
5
殡仪馆内熙熙攘攘,昨天婚宴上的大多数来宾,今天又见面了。我们相互间点头致意。大家从昨天婚宴上的酒桌改换成了今天葬礼上的牌桌。我打开摄像机,取出先前那盒DV带,在带子上写上“张双喜婚礼”,又取出一盒新的DV带,在带子上写上“张双喜葬礼”,装上带子后我开始拍摄。
大厅内停放着一具冰棺,棺内死者身上穿着得体的新衣,脸上蒙着张纸钱。不用问,这就是那位他们称为张双喜的死者。我感到自己正走在一个真实的梦中。这时候,刚刚晋升为张双喜遗孀的刘玉玲走了过来。遗孀刘玉玲的神情风平浪静,新娘妆仍然固定在头上。浓郁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她的手柔软而温暖,她说:“又麻烦你了,你真是双喜最好的朋友,那些狗日的只会吃他的喝他的,影子都看不见。”我愣了下,没料到她会说粗话。
一会儿,门口响起一阵骚动。张双喜的前妻带着女儿来了。
“老贱货。双喜都给她那么多了,还不满足!”刘玉玲咬牙说道。
前妻拉着女儿,给双喜烧纸、上香、叩头。然后揭开冰棺,为张双喜整理衣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泣着。做完这些,就在两个亲友搀扶下,软软地坐在家属席。刘玉玲作势要冲过去,被自己的几个姐妹拉住。她的头发乱了,妆也有点败。又一会儿,门口再次响起一阵骚动。我掉脸看见昨天夜里和我同乘出租车的那个女人,那个张双喜称为女同学的女人,牵着一个四岁大小的男孩走来。她们的身后紧跟着五六个男女。女同学(姑且还是这样称呼吧)脸色苍白而忧郁,右嘴角边那颗黑痣在殡仪馆白炽灯的照耀下异常明亮刺眼。她身后的男女,神色凶悍,一副来者不善的样子。
女同学摁住小男孩的头,说:“给爸爸磕头。”
小男孩木然地跪下,磕头。女同学冷不防一巴掌抽在小男孩的后脑上,小男孩哇地一声嚎啕大哭。他长得和张双喜真是太像了,简直是张双喜的童年翻版。
刘玉玲和张双喜的前妻几乎同时冲了过去。
“贱货,双喜就是被你害死的,还敢来啊?”刘玉玲、张双喜的前妻以及各自的亲友团,与这位女同学团队,在张双喜的冰棺前形成紧张的对峙,场面剑拔弩张。一阵冷风拂过,张双喜的遗像摇晃了一下。成为遗像中人的张双喜,双眸中仿佛闪过一丝慌乱,冷眼旁观着自己遗留下的这副烂摊子。
在众人的劝说和拉扯中,我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还是举起摄像机,从突发事件的现场慢慢摇拍到冰棺。我拍到张双喜的脸部,被定格的脸部无比清晰巨大。这时,我看见张双喜紧闭的双眼突然动了一下,随即慢吞吞地睁开,直视着我,似乎有话要说。我赶紧从寻像器上移开眼睛,去看冰棺里躺着的张双喜,他还是和原先一样紧闭双眼,只是抿着嘴角露出苦笑。
我浑身战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醒来时,我发现刘玉玲、前妻和女同学们都已不在。一个小型乐队正在悲痛欲绝地演唱《我的老父亲》《送战友》《把悲伤留给自己》。我坐在冰棺旁的小板凳上,为死者守灵。我又冷又饿,我想,如果再这样枯坐下去,即使不发疯,也会很快和棺材里的这位张双喜相会在九泉之下。
回到瓮中,我生了场奇怪的病。忽冷忽热的,输液打针吃药都没用。十多天后,我像一条冬眠的蛇,从昏沉疲软中苏醒。想到那么多天都没弄点好吃的,亏待自己了,就爬起来去超市买东西。床上那蜷缩成一团的被子,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像是我作为一条蛇蜕下的皮。
在狭长的货架边,我看见刘玉玲的细腰被一个比张双喜还要魁梧的男人紧紧搂着,像亲密无间的夫妻面对琳琅满目的货物挑挑捡捡。
我好像大白天撞见了鬼。
从超市出来,我才发现两手空空,什么都没买。看着熙来攘往的行人,再想想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笑了起来。在穿透厚重云层的阳光照耀下,把残缺的右手团拢,左手握住右手。我想对整个世界说:“谁来和我猜手指?”
我看见四个剩余的指头亲密无间地挤靠在一起,像四个青梅竹马的兄弟姐妹。握得久了,那截食指的断茬处逐渐发热、发胀、发痒,继而,这根残废多年的食指开始一毫米一毫米地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