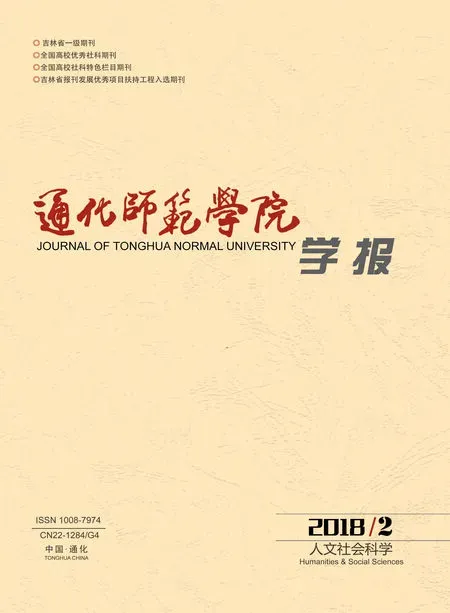民族熔炉与文化高地所锻造的文学巨匠
——论尹湛纳希与辽西地域文化
叶立群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文学的重要开创者,是蒙古文学史上第一位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著名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匠。
文学巨匠和文学高峰的出现,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作家的成长环境为重要因素之一。文学是人学,它是“创作主体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出来的体现着人类感性意识形式特点并实现了象、意体系建构的审美话语方式”[1]48。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率先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2]212,已是现代哲学所反复论证和认定的观点。作为一位生存于特定时空的文学大家,尹湛纳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离不开辽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孕育。
一、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地域文化传统
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是一个地区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域文化这一概念指称了具有特定地理风貌和历史沿革基础的地方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观念、文艺娱乐等诸多层面与诸多因素,是特定地域全部文化的总和”[3]11。尹湛纳希所出生和成长的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北票境内),位于当代学者所论定的“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4]的辽西文化区。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辽西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辽西地域文化传统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并由此铺就了辽西的汉文化底色。远古与上古时代的辽西文化具有显著的先发性特征,在东北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其先进性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明显超越辽南、辽东和辽北地区,较之中原古文化,辽西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也毫不逊色,它“同华北平原联系与交流密切,故农耕文化发展过程中,最早吸取了中原农耕部落的较先进文化因素,且与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保持相近发展水平,有时甚至领先一步。辽西地区较早出现的龙文化、玉文化和与此相关的巫文化,便是鲜明的标志”[5]。在距今1万∼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汉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居于辽西文化的主流地位,并推动着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二,辽西是北方诸多民族的起源和杂居地,有着民族融合的传统和多元性的文化质素。这里既是诸多民族的起源地,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中部分民族迁徙驻足或长期聚居的重要地区。作为辽西核心区域的辽西走廊,既是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6],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媲美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靺鞨、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他们在这里生息、迁徙、争夺,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改变着其中的文化元素,使辽西成为多元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第三,历史上的辽西,处于中原汉文化向东北辐射的过渡地带,长期的吸纳、沉淀、转化与升华,使这里的汉文化土层渐趋丰厚。周武王灭商后,将商太师箕子封于朝鲜,箕子携诗、书、礼、乐、百工经由辽西走廊前往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7]1658。箕子的东行,将当时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特别是殷商治理国家的思想和制度文化,留在了辽西地区。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大批汉人经由辽西进入辽东。其后的一些战事,如曹操经由辽西古道征伐乌丸等,也加速了内地文化在辽西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中原流民进入“三燕”统治的辽东、辽西地区,汉族文化得到进一步扩散。明代,首先在辽西和辽东大力推行儒学,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后推广至东北其他地区。清代,在数量庞大的移民、流人北迁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辽西的汉文化。
辽西地域文化的先天营养充足,文脉绵长,成果显著,特色鲜明。这种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见证着区域精神生活的丰富、兴旺和活跃,以及世代传承、深入人们深层心理结构的文化与文化精神的存在。
二、民族熔炉与文化高地
19世纪的辽西,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开放的地域文化形态,成为融合程度空前的民族熔炉,并构筑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多民族文化共融共存的文化高地。
“熔炉”一词由美国作家赞格威尔于1909年首次提出,描述为多民族融合在一起重构一个新世界[8]1226。“熔炉”的实质是民族同化(аssimilаtiоn),同化是一个民族群体与另一个民族群体趋向于融为一体,分享文化的过程。尽管有部分学者指出过“熔炉”存在的弊端,但通过民族融合、文化共享而催生更为先进的新质文化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自元代起,辽西逐渐成为喀喇沁、兀良哈、土默特、蒙郭勒津、科尔沁部等蒙古人游牧和居住的区域。清初,设立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盟、伊克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包括喀喇沁、土默特两部共5旗399佐,是东三盟中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盟”[9]1411。辽西地区原有少量汉人居住。康熙三十年(1691)后,清政府鼓励汉人移民东北,开垦边塞,大批河北、山东籍汉民陆续来到辽西蒙古族聚居区,与蒙古族共同生活。后政府虽下令禁止汉人进入蒙地,但因关内灾害频发,且人口激增,禁令无法遏止汉人的迁入。至清代中期,在卓索图盟已经形成了蒙汉杂居的局面。
19世纪初,辽西的蒙汉文化交融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期,是当时民族融合最为彻底的蒙古族聚居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熔炉。蒙汉居民长期杂居,必然相互取长补短,实现民族融合。蒙汉民族的融合,始于生产方式的相互渗透和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习俗的交融,以及语言、教育等领域的学习与借鉴。卓索图盟是清代开垦地亩最早、面积最广、农业人口最多的蒙古族地区之一。在生存压力及新的生产方式影响下,一些牧民开始放弃游牧生产,从事农业生产。《钦定热河志》卷75记载,乾隆曾作诗称赞蒙古人农业生产的精细化:“蒙族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乃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虑。”[10]302清末,包括卓索图盟在内的“近边诸旗,渐染汉俗……凡设郡县之区,类皆农重于牧,操作亦如汉人”[11]473。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化习俗的变化。在开发较早的地区,部分蒙古族已“弃蒙古包而改居土屋,语言、饮食、服饰逐步汉化”[12]237。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辽西蒙古人多建“拜兴”(也称“板升”,用土木石建造的房屋)而聚居;饮食上也由肉类、粮食二者为主转变为以粮食为主;部分从事农业劳动者,着装以束以腰带的半长袍、及膝皮衫取代了长袍。随着融合的深入,蒙古族平民开始与汉族通婚,起汉名,学习汉族语言文字,上层蒙族人达到了对汉文的精通。清统治者与地方官员在辽西地区建立了秀塔书院等多家书院,吸纳满、蒙、汉子弟入院读书,加深了蒙古人的汉化程度。在交流过程中,汉人也最大程度地接纳了蒙古族文化习俗,部分汉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13]7。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辽西地区,汉满、满蒙文化同样实现了深度的碰撞与融合。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清代,蒙古族自身文化与文学的积淀达到了一定的厚度,形成了由神话传说、歌谣、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祝词与赞词、历史著作等组成的文学体系。蒙古族对汉族文化典籍的研习,始于元初,对《四书》《孝经》等进行了蒙译,军政要员、士宦开始系统地学习汉文化。元亡后,这种交流处于停滞状态。清政权建立后,在支持和倡导蒙古八旗成员等学习和使用汉语汉文的同时,为推动各民族书面语言的规范化,组织编纂了《满蒙辞典》《五体清文鉴》等各种民族文字对照的辞典,并以满文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自17世纪初到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汉文蒙译著作,包括《大辽史》《金史》《大元史》《诗经》《西游记》《水浒传》《今古奇观》《红楼梦》等。19世纪初,译著活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文人荟萃、文风日盛的卓索图盟,由哈斯宝等蒙古贵族所翻译的文化、文学典籍,在蒙古地区的各阶层中广为流传。此时辽西的蒙古族聚居区,蒙族人的汉文化修养得到了普遍的提升,且得风气之先,不断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文化修养较高的蒙古族文人群体。就如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初序中所说:“我们卓索图盟的蒙古人可说是身居中原地区,不少人致力汉文的学习。正因为如此,对于古代的故事和现代的法典都了如指掌;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秦,以至西汉、东汉、宋、齐、梁、陈、隋唐、北宋、南宋、金、辽等朝代的历史也知道得一清二楚。”[14]5哈斯宝大约活动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他所翻译的《今古奇观》,节译和评论的《红楼梦》,对于蒙古文化的重构和蒙古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尹湛纳希的父亲旺钦巴勒蒙汉兼通,擅长诗文。在当时的漠南、漠北,其所在的“忠信府当属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建有几处藏书楼,分别名为楚宝堂、东坡斋、学古斋。珍藏陈列着数以万计的各种文字、各种版本的珍贵典籍”[15]103。他谙熟民族历史,立志撰写《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写至第八章,因旗务、军务繁忙,抱憾辍笔,后由尹湛纳希续写。尹湛纳希的长兄古拉兰萨深通蒙、汉文,有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卓越的文学才能,曾翻译《水浒传》,并吸收汉族古典诗词精华,开创了蒙古族诗歌的新形式。尹湛纳希的五哥贡纳楚克、六哥嵩威丹精,同样有着较高的蒙汉文化修养,均为在近代蒙古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
民族熔炉与文化高地的形成,会拓展相关的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使文化内蕴得到熔铸与提升。汉、蒙、满等文化的超强度融合,使蒙族、满族在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发展和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汉族文化在接纳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塑形。新质文化的生成,使地域文化更具丰富性与超越性,建构了一个呈现出他律性与自律性、文化共通性与独特地域性并存的崭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尹湛纳希,在精通本族语言文字的同时,掌握了汉、满、藏、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博览和精研各族文史典籍,少时即“亲手抄写《五体合壁》《三体合壁》的清文鉴书”[16]49,并接受父兄言传身教。在文学的路途中,他致力于摆脱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模式,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化的书写方式,经过艰难跋涉,不断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终成一代文学巨匠。
三、地域文化所蕴养的文化人格、价值取向与美学精神
萨仁图娅认为,尹湛纳希创作的重要价值所在,是其作品所蕴涵的精神、气韵、人格与信仰:“尹湛纳希小说的精神,不是小说中实在的故事,而是弥漫在作品中的意蕴和气韵;不是预制或外在的结构框架,权威话语,而是渗透在作品中的心灵与人格;甚至也不是那些抽象与概括出来的主题与思想,而是生长于作品之中的憧憬与信仰。”[15]161尹湛纳希作品的精神与魂魄,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民族高度融合所形成的文化场和成熟的中华文化,对于尹湛纳希文化人格、价值取向和美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和作品的艺术特质。
心理学领域所定义的人格,为“源于个体身上的稳定行为方式和过程”[17]3。文化人格,则为文化环境影响下产生的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人格特质。尹湛纳希的文化人格,是一种厚重且具有多侧面的文化存在,其最为突出之处当为对责任感和崇高感的追求。综观他的成长历程,始终以对民族责任、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的践行为己任,并将其转化为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作品中渗透着强烈的文化重构和理性批判精神。尹湛纳希的为学与为文,以勿忘祖先、破除蒙昧为原初动力,通过以《青史演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最终完成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构。撰写《青史演义》,即有感于很多蒙古人“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却一窍不通”,“台吉尹湛纳希我见他们如此,叹息不已,由来久矣”[14]6。通过写这部大元朝的正史,“让所有的蒙古人都知道本民族的历史和宗姓”[14]7。为此,他“凭着愚钝呕心沥血,靠着老眼博览群书”,“几乎到了两鬓挂霜,满额皱纹,肉掉筋弛的地步”[14]7。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既是尹湛纳希创作的动力,也是丰厚的文化资源和高蹈的文学坐标。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批判精神即生发于此。尹湛纳希对蒙古族衰落、部分蒙古人深陷蒙昧境地原因的反思,对当时民族文化政策和宗教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精神的重构。崇高,既是美学范畴,也具伦理学价值。尹湛纳希对于崇高感的追求,则在更大程度上标示着自身文化人格的高度。他带着对辉煌的民族发展史和成吉思汗的无限敬仰,完成了《青史演义》的创作。对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对其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展现,对其“勇毅”“宽仁”精神特质的开掘,则树立了一种深具理想性的精神标准。这种直抵民族之魂与文化之根的艺术表现力,势必会托举文学艺术走向更高的境界。尹湛纳希文化人格的形成,既源于个人的禀赋,也与辽西地域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对于祖先和民族文化的尊崇,对责任的深刻认知和敢于担当,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因,更多的是受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所树立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8]17的伦理准则,士大夫阶层所秉持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376的责任与使命,经接纳、吸收与转化,成为尹湛纳希文化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他不惧艰险,不畏人言,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重塑民族精神,丰富民族历史,振兴民族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为在辽西的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尹湛纳希的价值取向同样是多元的,其最核心部分体现为进取、开放、平等、理性。虽生于蒙古贵族之家,处于国家、民族、家庭衰颓之际,但由于对地域文化中刚健、包容、纯正等具有进步特质的元素的吸纳,使他完全摆脱了贵族文化中奢靡、享乐之风的影响,并通过对庸碌和日渐下坠的世风的反拨,确立了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他强烈地批判不思进取和贪图安逸,有感于“光阴似箭”“世间无永恒”,认为“谁人不珍惜光阴,谁人不珍惜自己的境遇”,“从身上的器官到一生之荣华富贵,统统毫无可惜之处”[20]65,只有“倾心于这笔墨之乐”,“尽愚笨之心,呕心沥血,朝夕奋笔,不怕苦累,不畏病魔”[14]33-34,努力进取,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尹湛纳希开放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于对多元文化的吸纳和文化自信。他反对故步自封和唯我独尊,批判部分蒙古人的学识短浅,心底狭窄,提倡以开放、宽容的心态接纳他人和异族文化,提出“我本人对谁的学说学不通晓,但是从来不责怪哪一学说是完全错误的”,“既然一切学说都是为教育他人而创立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好或错误的地方呢”[14]40-41。同时,他强调文化自信,反对妄自菲薄和贬低蒙古族文化,痛斥那些不知自己族源的达官贵人无异于“栖息大漠丛林、峭壁岩穴之猿猴”[20]49。尹湛纳希的平等观,主要体现为民族平等论和宗教平等论,并反映出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这种观念的产生,既是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也与萌芽于明代、在清代得到了一定发展的近代民主思想有关。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族即形成了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宗教迫害的传统。在文化高地上成长起来的尹湛纳希,也比其他蒙古族地区的人们更早地接触近代文化思潮,初步接纳了民主思想。针对历史上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和观点,如“只有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中国才算是真正符合人伦的天国,只有这个地区才是日月普照的国家,只有这里才能诞生文人学者”[14]40。他认为,不能贬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习俗,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确保了人类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各民族之间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主张。尽管坚持强烈地批评黄教,但只是针对其扭曲的教义和当时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危害。他反对宗教的精神专制,对于宗教本身是持有平等观的。他指出,儒释两家的学说,“一家主张把人世搞空,而另一家则主张把人世填满。乍看起来,二者是如此的不协调,然而其目的都归结于善的结果”[14]40。甚至道家、基督教、杨朱、墨翟、天主教的学说,“也都劝说黎民百姓修行养德,绝没有暗害疏人、算计近亲的意思”[14]41。尹湛纳希对理性有着特殊的珍视和推崇,主要表现在对人本主义精神的追求,强调读书明理等两个方面。他坚持人是“万物之灵,众生之首”[14]33,生命是一切人类活动的依附,是最终目标。反对任何外物和观念压制、摧残人类。这种理性的认知,是蒙古族文化成熟期的产物,也是尹湛纳希吸纳多元文化后所厘清的价值观念,是其哲学思想、社会理想和文学观的基础。他崇尚知识与智慧,极力倡导读书明理,批评释教,认为其当时的最大问题在于“杜绝求学求知之道,极端错误矣”[20]46。他在《一层楼》《泣红亭》中所塑造的贲璞玉形象,寄寓了鲜明的民族发展观:璞玉喜爱读书,尊重理智,相信藉此会有所作为,对蒙古族传统的畋猎骑射毫无兴趣,是那个时代觉醒的蒙古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具有一定反抗意识的民族新生力量。尹湛纳希的上述观念,主要源于儒家“学而知之”[18]10的主张。他在儒释比较和对儒家经典的研习中,萌生并坚定了通过学习读书而破除蒙昧的理念。他本人遍阅“父亲所藏的四书、五经”,“大元朝所属蒙古各部落的史书、传记、历史故事”以及“汉族的史纪、蒙满典册、藏族经文的译稿和畏吾儿历史译稿”[14]17,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寻求其中的真谛,并耗尽心血,完成了一系列足以明理、启智的传世之作。这些著述,以感性的审美形态和理性的精神不断阐释、强化和传递着尹湛纳希的价值观念,从多维度观照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形塑着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儒家与道家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脉,佛教中国化后所形成的禅宗美学,也成为中国传统心理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以善为美,强调经世致用;道家则“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21]117,以其对功利的超越,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想象力;禅宗同样起到了突破儒家美学观的作用,在深沉中寻求顿悟和升华,追求“飞越地进入佛我同一、物己双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那异常奇妙、美丽、愉快、审美的精神境界”[22]362。作为草原民族的蒙古族,其传统美学的核心是尊崇劲健的阳刚之美,在文学艺术中则呈现出质朴豪放的风貌。在辽西汉、蒙、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环境中成长的尹湛纳希,汲取各家文化之精华,形成了具有多源性、过渡性、超越性特征的美学精神。
第一,尹湛纳希的美学世界,吸纳并融汇了汉蒙等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美学因子。蒙古文化中重史的精神和史诗传统,汉文化中儒、道、禅各家的美学思想,如儒家文化中尚实的精神,道家所追求的圆融与和谐,禅宗美学的明心见性与哲学思辨等,均深刻地影响着他对美学范式的建构。中国文化有重史的传统,蒙古文化则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丝毫未影响他对历史的重视与尊崇:翻译《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供人阅读、品鉴;强调对待和书写历史要直言、客观、公正:创作《青史演义》,充分选用、核实了各类历史资料,使其基本框架完全建构在坚实的史学基础之上。这部巨著的宏大结构,对崇高情感的强烈表现,则是史诗性作品的重要美学特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和诗歌、杂文,则具有较为鲜明的关注现实的精神,充满了批判与抗争的意识。同时,其中所涵纳的对有无虚实的调和,对浮生若梦的感喟,对心灵之愉悦和灵魂之苦痛的体悟,则充满了玄机和辩证法,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见证了审美结构的多源性和丰富性。
第二,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出现在蒙古族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其美学风格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在草原文化传统中,极端崇尚力量与勇气,但缺乏汉文化中那种沉思的精神,刚健有余,深沉不足。清代中后期,在儒家文化和黄教的影响下,“蒙古人已从那种对力的崇拜转向了对善的依赖,追求的是宁静和谐的境界”[23]。与之相应的是,尹湛纳希作品的美学形态,清晰地展现出由雄浑壮丽走向冷静沉思的轨迹,试图在静思与静观中抖落纷扰的红尘,走向理性而澄明的世界。同时,他的作品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刚健之风,并不时涌动着生命的冲动,理性因子与感性元素互动所产生的张力,具有独特的美学效果,产生了更为丰厚的美学价值。
第三,与众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尹湛纳希在入世与出世的冲突中寄情于文字,通过游走于儒道两端,实现了审美上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社会责任,道家则追求对精神的慰藉与解脱。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对于作家本人是不幸的,但对于文学则是幸运的。尹湛纳希的人生是坎坷多艰的,他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曾寄望于仕途,希望在现实中有所作为,在屡遭挫折并走上了文学之路后,始终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表现与干预;另一方面,所具有的浸润了道家和禅宗思想的文化心理结构,又使他试图在超脱现世中追求理想人格,在顿悟中参透人世间的悲欢、有无和生死。他的文学创作,受曹雪芹和苏轼影响最大。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影响体现在多方面,尹湛纳希作品中所渗透的民主思想,《一层楼》《泣红亭》的叙事模式、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虚话三十篇”[24]228“午梦荒唐语”[25]309所传递的人生空幻之感和淡淡的感伤情怀,都与《红楼梦》有着密切关系。苏轼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于文化心理内蕴。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在进与退、入世与出世间,“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22]155,将世间万物“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22]157。与苏轼一样,尹湛纳希虽不时地向道、禅寻求解脱,但人生态度和文化理想,却从未脱离儒家的轨道。他在调节内在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平衡,带着齐物我、超生死的人生态度和妙悟禅意,回归人间情味、人世温暖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8]127的儒家伦理。就在冲突、失衡、平衡与回归中,生成了更为广阔的审美创造空间,生命境界与诗文的艺术价值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尹湛纳希的诗歌和几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在审美上虽未达到苏轼的高度,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汉文学的高峰同样尚有差距,但他所营建的优雅、清丽、婉约的意象,深邃、高远、开阔的意境,最终所达到的空灵、深沉且富有哲理化的美学境界,是同时代其他蒙古族作家甚至多数汉族作家难以企及的。
在民族熔炉和文化高地成长起来的尹湛纳希,在学习和吸纳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认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身精神世界、审美世界的改造与建构,进而使他的文学世界涌动着源自历史、大地与民族的“生命之气”“意识之流”和“理想之光”[15]161。可以说,文学巨匠尹湛纳希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辽西这片古老大地为蒙古族文化、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1]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朱德生,等.西方认识论史纲[М].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3]李少群.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论集[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4]崔向东.论辽西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21-28.
[5]彭定安.论辽海文化[J].文化学刊,2013(3):70-83.
[6]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2-6.
[7]班固.汉书[М].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安国政,等.世界知识大辞典[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9]佟冬.中国东北史(第四卷)[М].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0]金海,等.清代蒙古志[М].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1]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下·纪实业[М].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2]阿岩,乌恩.蒙古族经济发展史[М].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9.
[13]周铁铮,沈鸣诗,等.朝阳县志·卷二十六·种族[М].刻本,1930.
[14]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上)[М].黑勒,丁师浩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5]萨仁图娅.尹湛纳希[М].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16]刘文艳,赖炳文.尹湛纳希传[М].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17][美]伯格.人格心理学[М].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18]四书五经(上)[М].陈戍国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4.
[19]张载.张载集[М].北京:中华书局,1978.
[20]尹湛纳希.韵文杂文及中篇小说[М].赵永铣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М].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22]李泽厚.美的历程[М].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3]葛根高娃.试论清代蒙古族的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4):83-90.
[24]尹湛纳希.一层楼[М].甲乙木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5]尹湛纳希.泣红亭[М].曹都毕力格,陈定宇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