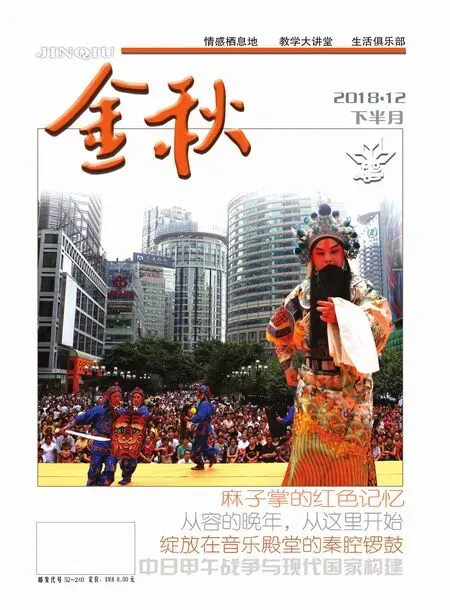在瑞典拔鱼刺
◎文/艾 虎
那天,我到餐厅有些晚,剩下的菜不多,一种有黑色皮的鱼肉还剩不少。在瑞典,这种鱼因为有些细如毛发的小刺,所以不招人待见。午餐接近尾声时,我就感觉喉咙里有鱼刺卡着了,急忙往嘴里塞面包,喝水,吞咽,当时并未太当回事儿。
下班回到家里,继续试试吞咽米饭、面包,没有任何效果,如鲠在喉的感觉依旧。渐渐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于是考虑看医生。由于不是很确定去哪看,就先打电话到1177(瑞典医疗咨询电话)询问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电话接通后,我用英语加瑞典语单词解释鱼刺卡喉这件烦心事。接听电话的女医生大概英语没有过四级,过了很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建议我尝试吃东西、喝水,我告诉她这些办法我都试过没用,可不可以去急诊?她没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还能呼吸吗?当时我高度怀疑听错了,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还能呼吸,在晚上这个时间,急诊是不会接收我这样病例的。很遗憾,我当时还能呼吸,所以应该是没有资格看急诊了。无奈只能洗洗睡,幻想着晚上睡觉使劲打呼噜可以把鱼刺呼出来。
一早醒来发现,鱼刺还是赖着没走。于是决定去社区医院把鱼刺拔了,心想不过是一把镊子几分钟的事儿。不料医生在了解情况后说,社区医院没有设备可以处理这种情况,并建议我去卡罗林斯卡医院急诊。我听他这么说真是一头雾水,这么大的医院难道连把镊子都没有吗?
早上9点30分左右,我到了卡罗林斯卡医院的成人急诊楼,拿号排队,付了挂号费后就等候医生叫我名字。环顾四周,似乎等待的人不多,估计一个小时应该能轮到我了。然而,我错了,一直到下午一点,才听到了亲切的呼唤,我想接下来也就十分钟解决问题吧,结果我又错了。
医生先问诊,然后让我张嘴,伸长舌头,他用手电往喉咙里面照。忙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鱼刺,于是他告诉我决定用喉镜寻找鱼刺。喉镜估计很久不用了,调试和消毒就花了些时间。喉镜是从鼻孔穿入,医生找呀找,终于向我宣布发现了那个困扰我的鱼刺的准确位置。他不厌其烦地用笔画张草图,向我介绍鱼刺卡在喉咙里的位置。说实话,鼻孔插着喉镜的我,对他的这个重大发现实在没有兴趣,只希望他赶快动手把刺儿弄出来。
医生试图用喉镜把鱼刺拨弄走,可鱼刺就是不动。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取走鱼刺:用不锈钢片压住舌根,看到鱼刺后用镊子取出。我一个劲地呕,难受之极,害得医生不停地说对不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鱼刺仍然坚定地占领着我的喉咙。
这时,医生问我什么时候吃的早饭,准备做个手术解决问题。看到我惊惧的样子,医生连向我解释,手术其实很简单,就是完全麻醉喉咙,使它没有呕吐反应,然后再使劲扳开嘴找鱼刺,通过镊子把鱼刺取出来。我理解就是,彻底失去知觉,然后才好下手。
不知道是为了等食物消化还是等手术室有空。我在通道里,又累又饿,颤抖着身躯又等了一个小时,被一根鱼刺折腾成这样,也真是让人醉了。终于,一位陌生的医生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让我进入手术室。进去后才发现满屋子的人,包括最开始的急诊医生在内,一共三位医生在那里等着,还有若干个实习生在旁边围观。看这个阵势,要准备大干一场了。
经过沟通得知,这三位医生准备通过喉镜影像系统的帮助,一起合作,尝试把鱼刺夹出来。麻醉剂生效后,急诊医生开始操作喉镜找鱼刺,另外一位医生左手用吸水纸垫着拉住我的舌头,右手拿着更加细长的鱼骨夹,眼睛瞪着显示器,同时还有一位医生按住我的肩膀。
皇家医学院的顶级医生们,发扬三个臭皮匠精神,向一根卡在中国友人喉咙里的小小鱼刺发起了最后总攻!
夹子终于出来了,大家围拢过来,盯着夹子仔细瞧——除了口水,啥也没有。
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在所有人之间传递。也许为了安慰我,负责按肩膀的医生递过来一杯水示意我喝一口。这一口水喝下去,我差点被呛死,是故意的吗?还觉得我不够惨吗?
操作鱼骨夹医生的瞥了一眼慌乱的按肩膀医生,说了一句我不懂的瑞典语。随后用英文解释说喉咙麻醉后无法控制吞咽动作,所以会被呛到。
这次鱼刺虽然没有拔出,但方法貌似比较靠谱,于是三个医生决定再来一次。可是操作喉镜的医生,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根顽固的鱼刺了!三位医生讨论了一会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要么是之前鱼骨夹掉了,要么是我刚呛水的时候咳掉了。
急诊室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很兴奋,似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手术。鱼骨夹医生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干得好!干得好!我只能泪流满面地回答:应该是你干的好!最后,医生让我在通道里等到麻醉剂的副作用消失后再离开医院,并叮嘱在一周后如果还有异物感,一定要回医院就诊。从进入手术室到最后走出医院,又过了五个多小时。
我被鱼刺折腾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糊里糊涂的它就消失了。但不得不说,这件事儿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不小,之后,我再没有吃过任何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