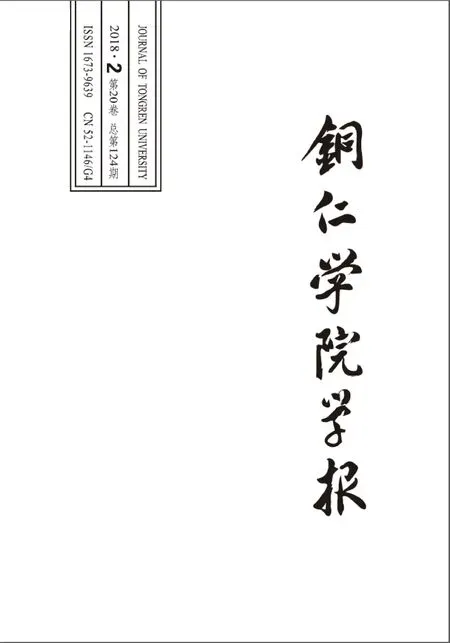回顾与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布朗族”研究综述
冉红芳
( 湖北民族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
布朗族是云南省 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历史上长期分散聚居,是“濮”人的后裔。布朗族研究主要以国内为主,国外少见相关研究。国内古代文献零星记载布朗族先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历史上也少有专门从事布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笔者在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布朗族42部研究著作和389篇论文的基础上,对其历史文献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赵瑛[1]只对20世纪80、90年代有关布朗族的编著和专著做了全面梳理,较少涉及研究论文,也未注重介绍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多数是罗列相关研究书目。笔者对布朗族研究成果的再回顾是进一步对 60年来已取得重要成果的全面梳理和近 10年来研究新动向的特点总结,进而提炼出未来研究应规避的问题,旨在为学界提供一个“人口较少民族”较为全面的学术动态。
一、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研究六十年回顾
(一)历史源流研究
史学界认为布朗族源自古老的濮曼族群,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布朗族源于古代南方濮人一支,在汉文史籍中曾被称为濮、朴子蛮、蒲蛮等。罗大云[2]从周秦时期“百濮”、东汉置永昌郡、三国时“南中”、元明“淮”人追溯至清代,认为清代布朗族分布的区域已和现在大体一致。杨毓骧[3]考证布朗族源流认为,“濮”人汉代之前统称“百濮”,汉晋称“僚”,唐称“葛僚”、“犵僚”,明清称“浓”、“沙”、“土僚”,解放前称“本人”。穆文春主编的《布朗族文化大观》一书,清晰画出源流演进表,描述了商朝到现代布朗族的历史源流。近年来出版的布朗族著作,如《布朗族文化史》《布朗族简史》《变迁与发展——云南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研究》,描述其历史及源流多用此框架,充分展示布朗族的发展程度“形质妆束各殊”[4]的不平衡性。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对源流的追溯仅用史料记载作为一重证据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学者从考古学、田野资料、历史文献三重证据相结合对其族源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布朗族的族源研究还有待深入探讨。
(二)语言与文学研究
布朗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也兼用傣语和汉语,其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布朗语支,无文字。“布朗”意为“住在山上的人”,其语言分为布朗语与阿尔瓦两种方言。李道勇等[5]运用丰富的语言材料,从语音系统统计布朗语共有 43个声母,150个韵母及4个声调,从概况、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文字和词汇等方面对布朗语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王敬骝、陈相木[6]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系统论证了孟高棉语特别是布朗语与侗台语的同源关系。刘岩[7]在分析关双话声调的性质、基本特点、历史来源的基础上,认为布朗语关双话声调正处于发展阶段。周植志与颜其香[8]坚持长期研究布朗语,《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一书成为研究孟高棉语族语言和布朗语的力作。图腾崇拜是布朗族的重要文化,朱净宇、李家泉[9]对布朗族的色彩语言作了全新的阐释。
布朗族文学方面的研究,首推学者王国祥[10]全景式地向人们展示和勾勒了布朗族文学从远古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将布朗族的文学史分期大致划分为远古、古代、近现代和当代,论述了布朗族文学的社会背景、分类及特征,概括了布朗族历史上的各种文学事象。他与郑培庭探讨了布朗族与傣族及其他民族融合汲取文学涵养方面的多边互动。此外,《布朗族民间故事》、《布朗人之歌》和《山茶》杂志刊登的一系列有关布朗族的文学作品也是了解布朗族古代文学的重要资料。从整体上看,对布朗族语言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著述较多,而近10年少有学者涉及,这是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三)所有制形态与社会发展研究
学者们对布朗族社会形态的深度研究已形成一个体系。颜思久[11]论述了布朗族的公社制度,阐明了布朗族母系制的特点,剖析了母子连名制向父子连名制的演变及其实质,证明了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从实行土地公有制、“高戛滚”终身制、“戛滚”间相互扶持、共同祭祀祖先等特点廓清了布朗族在解放前夕已由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转变为农村公社,其社会形态中仍有父系氏族残余,并在专著中构建了一个研究体系。张晓琼、李成武[12]对布朗山乡布朗族传统社会政治研究也持相同观点。此外,宋恩常、杨鹤书等学者也有相关研究。
布朗族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和少英、黄彩文、韩忠太、赵瑛、颜思久等学者以地域为例对布朗族脱贫发展做过深入思考。和少英、黄彩文[13]以临沧市双江县为例,从增强主体意识出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不仅扶贫还要扶志,不仅“输血”更要培育“造血”机制。韩忠太[14]认为布朗族在反贫困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两山”脱贫模式和以村民跨境劳务输出为主的脱贫模式,并将两种行之有效的脱贫模式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整合,有助于尽快改变贫困状况。赵瑛[15]从教育层面思考了布朗山乡的脱贫致富。刘文光[16]认为布朗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共同进步。此观点颜思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着相同的看法和担忧。“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之一,《勐昂村调查(布朗族)》一书从村庄、农户、村民三部分进行细致描述,对勐昂村经济发展中村寨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政策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四)民间音乐艺术研究
结合近十年研究呈现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专门研究布朗族音乐的学者杨民康;二是“布朗族弹唱”成为重点研究个案。杨民康[17]多篇论文涉及了布朗族音乐形态、文化结构、功能、分类等。在“非遗”的背景下不仅学者多关注这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布朗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表达。近年来,随着布朗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布朗族弹唱”保护传承面临着严峻挑战。黄彩文、子志月[18]呼吁对人口较少民族布朗族的“非遗”保护与传承采取有效措施,显得尤为迫切。
从传承体系对“布朗族弹唱”深入研究正是对这种担忧的解决办法。杨民康[19]认为找出传承体系中出现的裂痕才是文化复兴的关键。他以“宰”、“拽”、“索”的基本调式,总结布朗族民歌发展中不同的阶段特征,反思“域内—域外”发生的文化结果,为学界呈现了一个复杂化、精致化的基本衍化模式,并呼吁政府、学界对此给予必要的批判性反思。何华[20]以布朗族联姻活动为个案,从国家在场、族群认同与个体认同三层面阐析了布朗族音乐是从无序性向有序性发展。此观点是对早期学者的对话和回应。此外,杨伟[21]运用文化发生学原理,考察了村寨民歌的三种层次:原生层次、次生层次和再生层次。高蕾、曹贵雄还研究了布朗族的“蜂桶鼓舞”和“赖笼”。
(五)婚姻家庭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家庭生活的剖析,有助于对社会状况的认识。赵瑛[22]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布朗族妇女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罗阳[23]认为傣、哈尼和布朗族妇女的接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差异与生产方式、经济条件、宗教教育的影响有关。张晓琼[24]通过对布朗山乡布朗族女性外嫁个案的分析,探讨了内地青年男女择偶的价值追求为布朗族女性嫁往内地提供了条件,分析了布朗族女性大量嫁往内地这一现象对布朗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希望社会各界对此类现象引起关注。蔡红燕[25]认为施甸布朗族的婚姻习俗与过去相比,已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嬗变。杨竹芬、苏红斌[26]认为这种嬗变实现了传统婚俗的现代适应,体现布朗文化正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李忠斌[27]从布朗族家庭的主要收入分析了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作用的方式依然体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关于生育状况研究,李光灿[28]就1986年布朗山布朗族妇女生育状况、生育原因以及高生育带来的后果进行初步分析。刘小治[29]等以1987年7月1日零时为调查时点的数据,对勐海县的布朗山、巴达和打洛进行了回顾性调查。还有从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进行的研究。
(六)民间信仰研究
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集中于“祭竜”仪式和“拜认干亲”习俗。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重要的民间信仰。黄彩文探讨了民间信仰与当代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认为“祭竜仪式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30]。另外,他从神秘性、功利性、世俗性、自主性、“辈分”的混乱性特点分析了邦协布朗族“拜认干亲”习俗,认为在社会转型中不断争取自我生存的空间,这正是布朗族构建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形式。蔡红燕[31]从亲缘、地缘和愿缘阐释了多神崇拜产生根源。颜思久[32]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信奉“小乘”,解释了长期以来信仰原始宗教的布朗人为何在近代信仰小乘佛教的缘由。王树五[33]研究了布朗族特有的原始宗教信仰。王向群[34]探讨了原始社会末期布朗族宗教的演进。
部分学者探讨了布朗族民间信仰与其他传统文化互动研究。民间信仰与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安静[35]既探讨了布朗族与邻族间建构的差异化族群关系,又揭示了当代民间信仰是如何来维系布朗族社会的正常运转。杨竹芬[36]基于生态伦理道德、婚姻伦理道德和社会伦理道德探讨了布朗族原始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七)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布朗族的文化传承的本质与特征、影响文化传承保护的因素以及文化传承的理论运用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
已消失的“鸡罩笼”是公弄布朗族传统文化中不可逝去的组成部分。陈柳[37]认为公弄布朗族依然称自己居住的模仿汉民居建造的双斜面小平房为“汉家房”,实则渗透着布朗人深深的文化疼痛感,也是布朗人对已逝去建筑文化的追忆和坚守。蔡红燕[38]认为施甸布朗族传统的“一步楼”民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分上下”、“祈吉久”的伦常文化。
郗春嫒以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安全为视角,运用贝瑞文化适应模式检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认为布朗族文化认同正面临严重危机,调适危机的关键是强调主体民族文化认同中“文化自觉”的重建,其路径选择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认同”,最后达到“文化自觉”。[39]她还认为文化生境是影响布朗族文化迷失的主要因素,故适应生境是布朗族重拾文化自信、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杨竹芬[40]则认为布朗族优秀文化传承面临困境的解决,应在尊重布朗族人民意愿中实现民族的文化自觉。李淑娟[41]认为在保护传承上应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和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来探求改进措施,对布朗族民俗进行有选择性、有意识的保护。黄彩文、梁锐[42]在应用信息化手段在保护布朗族民族文化方面有很好的实践。
(八)布朗族教育研究
教育是一种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得以传承及发展的重要途径。赵瑛[43]以布朗山为例分析了影响教育的七个因素。刘雪道[44]认为布朗族传统教育方式具有文化传承、社会控制和生态保护功能。郗春媛[45]从家庭、社区、寺院三个教育场域的调查,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解释了学校场域中不同资本的博弈导致学业成败。还有学者对布朗族的学校教育的退步进行了反思,认为云南勐海布朗族的学校教育处于一种滑坡状态,其原因是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滞后、学校布局不合理、宗教信仰、国家分配政策的改变、教师不安心现状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反思之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对策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归纳多数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对策:更新教育观念、制定相应政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探索教学模式、解决师资来源、抓好基础教育。具体做法有:“教师安居工程”、“教育优先区”和“走出去”与“请进来”。
(九)文化生态与古茶文化研究
文化生态学是当下研究范式,在布朗族研究中得到部分学者关注。杨竹芬[46]探讨了临沧市邦协村的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赵世林[47]运用民族学资料分析茶文化在西南的发源过程,认为古代百濮民族是最早发现茶并引入家培的民族。黄桂枢[48]对布朗族与茶树驯化栽培种植加工进行考证,论证了“普茶”即“濮茶”。蒋会兵[49]等分析古茶园种植的禁忌崇拜,认为布朗族独特的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传统文化知识是从“习惯法”和“头人”规范古茶树的种植系统中演绎出来的。陈红伟比较分析了布朗族和基诺族,认为“两者创造的茶文化,不仅可传承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促进民族的团结与稳定,还可增强民族的影响力和生产力,促进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50]。
从文献梳理来看,布朗族不仅有着几千年的种茶历史,而且对于茶文化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于古茶文化与文化生态研究紧密结合并不多。多数论文是介绍性文章或者是理工科学者从种植和检测方面的研究,真正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撰写的论文较少,多学科交叉运用是亟待关注的问题。
二、布朗族研究新特点与理性思考
通过对布朗族六十年来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其学术研究史有着鲜明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诸如国家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非遗”的申报等机遇下,布朗族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特色和发展趋势。以下笔者就六十年来布朗族研究的特色及其趋势,试作简略分析。
(一)布朗族研究呈现的新特点
1.研究视野由单一化向多维化的转变
考察六十年来布朗族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云南爱国诗人彭桂萼是研究布朗族的先驱,在《双江一瞥》一文中对双江地区布朗族的语言、宗教、衣食住行、婚丧等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组织了一批学者对布朗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调查,积累的珍贵资料为布朗族研究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1963年编印《布朗族简史简志合编》是第一本研究布朗族的专著。从早期研究可以发现,布朗族研究范畴和主题更侧重于民族族源、语言文字、社会形态和历史宗教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布朗族研究才开始复兴并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布朗族研究有了新的景象,研究成果数量倍增,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转向语言文学、音乐艺术、文化生态、古茶文化、学校教育、习惯法、婚育调查、经济发展等多个研究领域,呈现出研究视野多维化的特点。
2.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完善
布朗族早期研究多为描述性的介绍,缺乏历史学的考据和民族学的调查,理论上也局限于某一学科范围。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突破单一的理论视域,将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遗传学、医学、人口学、文化生态学、宗教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渐渐引入布朗族研究中。研究方法也融入了多学科的结合,出现跨学科整合研究、团体合作研究等。从侧重社会形态和原始宗教的考证向教育学、文化生态学以及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运用等方面的发展。
3.研究范式呈现多学科交叉的取向
文献梳理过程中,学者研究队伍逐渐兼顾多学科的交叉和研究团队的合作,跨学科的有机结合研究,各取所长,相得益彰。近十年来跨学科研究某一文化事项和学术背景交叉研究的研究队伍逐渐增多,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主流趋势。如从社会历史研究范式逐步转向文化生态研究范式也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二)布朗族研究的理性思考
布朗族研究始于对风土人情的文学描述,再到族群的社会历史调查,直至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其从无到有,再到创建体系,足以见出上涨势头。回顾六十年来布朗族学术研究史,取得的成果可圈可点者众多,但是诸多的问题和缺憾需要有深度、高度的理性思考与探索。
1.关注传统的重建多于现实的发展
从收集的著书42部和389篇论文来看,当前学者们对布朗族的社会形态、民族音乐、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方面研究关注较多,对社区弱势群体、农村贫困与扶贫问题、女童失学、非遗传承与保护困境以及旅游发展等现实的问题还关注不够,有待学界重视。
2.研究“客位”表述盛于“主位”话语
近十年布朗族研究的学术队伍逐步扩展,前期研究者多是在国家行动中参与的“他族”学者,如颜思久、王树五、杨民康、王国祥、杨鹤书等,后期大量的学者为布朗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和少英、黄彩文、张晓琼、赵瑛、郗春媛、蔡红燕、杨竹芬等。但是从当下的研究队伍来看,本地本民族的学者是“缺位”的,这也是回顾60年布朗族学术发展中一个凸显的问题。可见,布朗族本土知识分子急需培养和成长起来,尽快成为学术研究队伍的生力军正是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本民族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勃兴,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很好地将人类学强调的‘自观’和‘他观’即主位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51]
3.运用多学科的交叉少于单一学科的研究
由于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专业取向以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因素影响,布朗族研究还欠缺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来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已有成果来看,有少量成果涉及跨学科的结合,如用遗传学方法研究族群、将文化人类学理论引用于生物科学、民间宗教融入民族文学等,这些多倾向于某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某个领域,局限了布朗族研究整体性、系统化的推进。
综上所述,六十年来布朗族研究还存在诸多缺憾。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进一步整合团队力量,提升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如何深化研究议题,加强多学科交叉互补等都是布朗族关注的重点。同时,在国家“人口较少数民族”政策支持下,以跨境民族布朗族的国内外发展案例比较研究来彰显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优越性的问题无人问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存在“双刃剑”把握上的困惑,西双版纳少数民族自身“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建构“小康社会”建设还很滞后等相关问题,需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赵瑛.20世纪80年代以来布朗族研究综述[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
[2] 罗大云.布朗族[J].思想战线,1977(6).
[3] 杨毓骧.布朗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4] 《布朗族简史》编写组,《布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布朗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 李道勇,聂锡珍,邱锷锋.布朗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6] 王敬骝,陈相木.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J].民族语文,1982(3).
[7] 刘岩.布朗语关双话声调初探[J].民族语文,1997(2).
[8] 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9] 朱净宇,李家泉.从图腾符号到社会符号——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0] 王国祥.布朗族文学简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5.
[11] 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2] 张晓琼,李成武.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云南布朗山布朗族为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2).
[13] 和少英,黄彩文.增强主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以临沧市双江县布朗族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6).
[14] 韩忠太.西双版纳布朗族两种脱贫模式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3).
[15] 赵瑛.布朗族脱贫致富的思考——以勐海县布朗山乡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16] 刘文光.布朗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17] 杨民康.布朗族音乐文化的结构、功能及分类[J].民族艺术研究,1991(6).
[18] 黄彩文,子志月.布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践与思考——以“布朗族弹唱”为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1).
[19] 杨民康.论西双版纳布朗族民歌的复叙体结构特征[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4).
[20] 何华.从布朗族联姻及民歌活动看其当代音乐文化认同[J].民族艺术研究,2014(4).
[21] 杨民康,陈颖,布朗族民歌新世纪初发展变异状况的调查研究[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3).
[22] 赵瑛.从婚姻家庭看布朗族妇女的社会地位[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4).
[23] 罗阳.西双版纳傣、哈尼、布朗族妇女的教育比较[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4).
[24] 张晓琼.布朗族女性婚恋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J].民族研究,2006(1).
[25] 蔡红燕.对哀牢后裔施甸县布朗族婚俗传承现在性的思考[J].保山师专学报,2006(3).
[26] 杨竹芬,苏红斌.嬗变中的邦协布朗族婚恋习俗[J].民族论坛,2011(22).
[27] 李忠斌.云南布朗族农村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4).
[28] 李光灿,吕昭河.云南省布朗山区布朗族生育状况的剖析[J].民族研究,1988(3).
[29] 刘小治,刘惠华,侯泽英.云南省勐海县布朗族妇女的婚姻、生育和节育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88(4).
[30] 黄彩文.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4).
[31] 蔡红燕.施甸布朗族多神崇拜中的家园文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
[32] 颜思久. 布朗族宗教信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2).
[33] 王树五.布朗山布朗族的原始宗教[J].中国社会科学,1981(6).
[34] 王向群.布朗族宗教的演进及其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1998(4).
[35] 安静.布朗族民间信仰的功能研究——以西双版纳老曼峨村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36] 杨竹芬.论布朗族原始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J].黑河学刊,2010(6).
[37] 陈柳.公弄布朗族的传统居住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
[38] 蔡红燕.施甸布朗族传统聚落与“一步楼”民居文化[J].大理学院学报,2009(11).
[39] 郗春嫒.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迁与社会发展——以云南布朗族为个案[J].民族学刊,2014(1).
[40] 杨竹芬.布朗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策略探究[J].黑龙江史志,2014(9).
[41] 李淑娟.布朗族民俗价值解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4).
[42] 黄彩文,梁锐.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信息化初探[J].民族学刊,2014(1).
[43] 赵瑛.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8(1).
[44] 刘雪道.关于布朗族传统教育方式及其功能的初步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5] 郗春媛.人口较少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云南布朗族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46] 杨竹芬.布朗族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探析——以临沧市邦协村为例[J].黑河学刊,2013(1).
[47] 赵世林.西南茶文化起源的民族学考察[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11).
[48] 黄桂枢.论普洱茶与布朗族的历史文化渊源[J].农业考古,2011(5).
[49] 蒋会兵,梁名志,何春元,等.西双版纳布朗族古茶园传统知识调查[J].西南农业学报,2011(2).
[50] 陈红伟,王平盛,陈政,等.布朗族与基诺族茶文化比较研究[J].西南农业学报,2010(2).
[51] 祁进玉.土族研究一百年——土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述评[J].西北民族研究,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