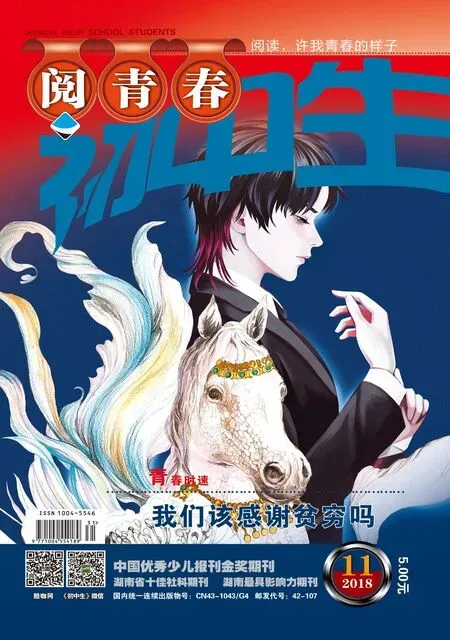最是情浓处,一阕纳兰词
《初中生》编辑部“尘衣之约”公众号
尘衣:
惠特曼说,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标准,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
中国向来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从远古民歌到先秦名篇,到晚清诗界革命,一大批能够站上群山之巅的作品相继产生,其势绵延不绝,而创造它们的诗人,群星闪耀。
词则由诗衍化而来。其用韵、平仄、字数、句数与近体诗一样,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词是歌唱的文学,因而词有词调,词牌即词调的名称。
少年时,我便以“温婉、文静”被人形容甚至称羡。一个人的气质,与其所读诗书不无关联。那时,我对词极度喜爱,或许正是受其浸染的缘故吧。
不久前,又翻到了初中时的整本宋词摘抄,字色未褪。
我喜欢婉约、灵动、深情的词作,豪放倒在其次。这些特征,宋词自不必说,清代纳兰性德的作品,更是突出。
人称“清词三大家”之一的纳兰性德,原名纳兰成德,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更名,字容若,号楞伽山人,1655年1月19日出生,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系大学士明珠长子,其母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爱新觉罗氏。
检索可知,这位清初词人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17岁入国子监,18岁考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因病错过殿试,后补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他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康熙赏识,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康熙十三年(1674年),纳兰与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成婚。康熙十六年,卢氏难产不幸去世,纳兰的悼亡之音由此破空而起,《饮水词》成为拔地而起的高峰,连他自己也再难超越。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后人将《侧帽集》和《饮水词》增遗补缺,共349首,合为《纳兰词》)。其词以“真”取胜,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在当时即享有盛誉,影响力之大,从评价可见:“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以说,不独清代,在整个中国文坛,纳兰性德亦拥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纳兰性德溘然而逝,年仅30岁。个人觉得,失去夫人后,其词尤为悲切,心理状况似乎不佳。这,是影响其身体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吗?
纳兰性德交友,“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为江南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词品与人品合一,也是纳兰性德受人喜爱的原因。他对朋友极为真诚,敬重他们的品格与才华。
爱家人,爱友人,爱山水,爱世界……纳兰其词其人,无处不深情。
灿烂流星,光芒闪耀
天妒英才,才30岁的纳兰性德就去世了,如光芒划过天际的流星,为中国文坛的天空增添一片绚烂。
后人无从得知其形貌,若据其作品度测,大略是翩翩公子,温文尔雅。
纳兰性德的词作,友谊爱情、边塞江南、咏物咏史都有涉及,虽然不见得有多么宽阔的眼界,但多见真性情,佳品不少。在《蕙风词话》中,清代词人况周颐称他为“国初第一词手”,身后,他更是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
从词风来看,纳兰性德受李煜、晏几道和《花间集》影响较大。不过,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可见,他本人更欣赏李煜之作。
纳兰词中,水与荷深得其宠。水多代表柔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水是有生命的物质,是有德的“君子”。水既滋润万物,川流不息,又以柔克刚,力透河山。纳兰性德尤为看重水,水被其从物质性理的角度赋予哲学的内涵。上善若水,纳兰又何尝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荷,出污泥而不染,文人雅士们崇尚的境界就在于此。纳兰心性甚高,也似荷般超凡脱俗。纳兰号楞伽山人,当有禅缘。荷的高洁,跟佛亦有关联。凡此种种,都造就了纳兰的品性与精神,水与荷共生,成为其内心图腾,与其精神同在。
纳兰的作品中,美无处不在。“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既可见跃然纸上的唯美画面,又可见直面生活的坚强力量;“夜深千丈灯”,“故园无此声”,既描述壮美意境,又反映委婉心地……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纳兰深得当时及后世的推崇与喜爱,是不无道理的。
(彭新华)
温润而惊艳——说说我心中的纳兰性德
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遇见“纳兰容若”这个温润的名字了,正奇怪他和“纳兰性德”的关系,心中却隐隐有了一种悲剧意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没错,当他因“成德”避讳改名“性德”时,似乎就已埋下了悲剧的种子。终其一生,他都得为他所生活的时代兴观群怨,不能自已。
当初《红楼梦》赚取了多少观众的泪水,几曲《红楼》插曲,缠绵悱恻,令人动了无限愁思。纳兰,可是那多愁善感的宝玉的化身?
出身高贵,才情横溢,感情真挚,在缪斯的国度里,他就是一代君王。
长亭更短亭,情深意绵绵。多少佳词美句,令多少人神摇意动。作为少年郎,隔着时空,从字里行间感受他当时的种种心情,无由地心生伤感:心中有梦,却不能实现,是何等的悲伤!他仿佛告诉我们:不要说你生于富贵,不要说你饱含才华,当你心中的梦想追逐不到时,你会发现,人生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终其一生,纳兰都在功名与文艺之中摇摆,在遵父命与求己心之中摇摆,在对美好的无限向往和现实如琉璃被打碎的伤感中摇摆……如此种种,导致积郁成疾。最终,年仅30岁,他便去往另一个世界,只留下诸多美妙的诗句和动人的故事于世间,供后人不断吟咏、思索、感慨!
(曹立志)
我读《长相思》
纳兰性德的词,清丽婉约,哀感顽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简朴至极、浑然天成而毫无雕琢之处的《长相思》。
初读《长相思》,觉得颇似唐朝的“边塞诗”,境界开阔,雄浑壮丽。赴榆关途中的山水,正如那孤城外的万仞山、落日下的长河;而那夜中点亮的千帐灯火,是否也映照着“大雪满弓刀”及“美人帐下犹歌舞”?
但纳兰性德终究不是唐朝那些万里觅封侯的意气书生。他出身高贵,年少成名,很早就身居高位,常伴康熙皇帝左右。他仕途的起点,是很多文人骚客穷其一生也不能达到的终点。然而,纳兰性德内心深处,早已厌倦官场和皇帝侍从的生活,他向往的是诗酒相伴,儿女情长。
纳兰性德18岁与大家闺秀卢氏成婚,琴瑟和谐,不幸的是,三年后爱妻难产离世。有考证认为,纳兰性德是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也许纳兰府中,也有这么一座“大观园”,怡红快绿,春色满园,他沉醉其中,过着“富贵闲人”般的生活。但对家族的责任和帝王对其才华的欣赏,却使他不得不违背初心,成为一名宦游人。他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直至而立之年英年早逝,他再也没能回归故园。
也许在《长相思》诞生的风雪之夜,那个在帐篷中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青年贵族无心再推敲华丽的辞藻,他想到的,只是故园春色和那个举案齐眉的知己红颜。
(学 理)
尘衣:
“人生若只如初见”“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然诺重,君须记”……性情之人才写得出这般打动人心的句子。它们,放到今时,仍然流行。
纳兰性德词作十首
木兰花·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蝶恋花·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
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秣陵怀古
山色江声共寂寥,十三陵树晚萧萧。
中原事业如江左,芳草何须怨六朝。
长相思·山一程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
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如梦令·正是辘轳金井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
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
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
谒金门·风丝袅
风丝袅,水浸碧天清晓。一镜湿云青未了,雨晴春草草。
梦里轻螺谁扫,帘外落花红小。独睡起来情悄悄,寄愁何处好。
南海子
相风微动九门开,南陌离宫万柳栽。
草色横粘下马泊,水光平占晾鹰台。
锦鞯欲射波间去,玉辇疑从岛上回。
自是软红惊十丈,天教到此洗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