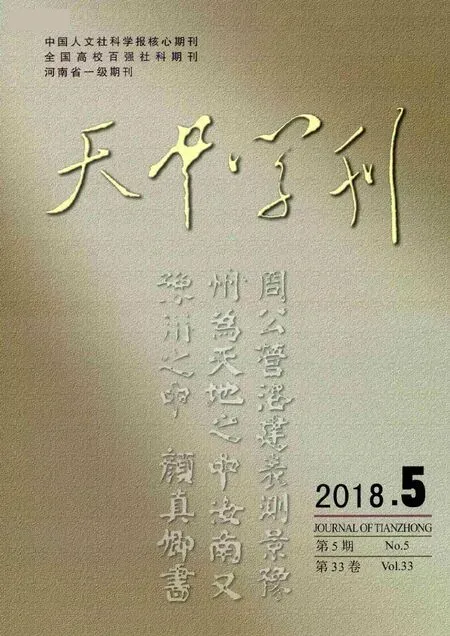词乐研究的第一部力作——论刘尧民《词与音乐》及其音乐文学研究法
张建华
词乐研究的第一部力作——论刘尧民《词与音乐》及其音乐文学研究法
张建华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刘尧民作为第一位对词与音乐关系开展专门研究的学者,其《词与音乐》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刘尧民运用发生学的原理、进化论的观念和系统概念构建的方法,对燕乐与词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形式、原因等都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刘尧民;《词与音乐》;音乐文学;研究方法
一
作为第一部专门研究词与音乐关系的力作,刘尧民《词与音乐》的研究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刘尧民(1898~1968年),字治雍,笔名伯厚、林不肯,云南会泽人。其父刘盛堂是会泽有名的教育家和实业家。刘尧民11岁入父亲创办的“爱国小学堂”读书,13岁入昆明中学,仅读一年即返乡自学,22岁被聘为昆明几所中学的教员,1937年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其间曾回到家乡会泽中学任教三载,1941年之后,主要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从事教研工作。刘尧民研究词学的代表作主要有《词与音乐》《晚晴楼词话》和《唐乐词史》(手稿)。其中《晚晴楼词话》生前并未发表,刘尧民先生去世后,由刘荣平先生校点刊布,始为人知。
刘尧民对音乐文学的研究,当始于其撰写《晚晴楼词话》期间。这部仅3万言的词话之作,前后所论的议题却迥然不同,前半部分主要继承中国传统词话的特色,以摘句的形式对作家、作品以及作品体式、风格等进行品评,后半部分则转而专门讨论词与音乐之关系。可以推测,这是刘尧民开始转向思考词与音乐关系的分水岭。在《晚晴楼词话》中,刘尧民已经对他撰写《词与音乐》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基本框架、论证思路等做了初步探讨,或者可以说,这些正是他日后撰写《词与音乐》的必要准备。从他致徐嘉瑞的一封书信还可知,刘尧民与徐嘉瑞在1923年以前即已开始关注音乐文学的相关话题,比朱谦之与杨没累在一起讨论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还要略早,这是何等的先知先觉!他在信中说:“我看中国的诗歌,彻始彻终都是和音乐不相离的;音乐一有变动,诗歌也随之而转移;有一种新音乐发生,即有一种新诗歌发生。”他还说:“从古代的《三百篇》歌诗,一直数到近代的词曲,彻始彻终都是受音乐的影响而变迁,这是确有证据的。所以研究中国的诗歌,一定要研究中国的音乐才对。”在信中,他还罗列了研究音乐文学的三大发现:“(1) 有一种新音乐产生,即有一种新诗歌发现;诗歌的变迁,视音乐为转移。(2) 音乐的系统,即是诗歌的系统。在音乐系统内的诗歌,即是诗歌的正宗。其不入音乐系统的诗歌,是诗的旁支。(3) 合音乐的诗歌都是极有价值的,不合音乐的诗歌其价值则逊。”[1]11–13以此而观,其时他已对音乐文学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体悟。
刘尧民原打算作一部《词史》,而“词之起源”部分,已经占去全书之大半,遂割裂出来,单独作为《词与音乐》。因此,也可以推断,刘尧民研究词与音乐关系的重要原因是为撰写《词史》服务的,故而,他早期的研究(如《晚晴楼词话》)也就自然仅将目光聚焦在解决词之起源上,这大概是他为什么没有再向前跨出一步提出“音乐文学”概念的原因。正是受刘尧民的影响,徐嘉瑞在初版于1923年的《中古文学概论》之“绪论”中,第一次使用了“音乐的文学”这一概念。他说:“从《三百篇》起,一直到了词曲,都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音乐系统,即是文学系统。此种‘音乐的文学史’从来编文学史的,都没有注意。”[1]10我们将这句话同刘尧民《致徐嘉瑞信》里的话做一番比较,便可以很容易知道,徐嘉瑞是受了刘尧民的影响而创造性地发明一个新的学术概念,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意义。嗣后不久,朱谦之又受《中古文学概论》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标举“音乐文学”的口号,并成为第一个大力倡导音乐文学研究的学者。当然,徐嘉瑞、朱谦之对音乐文学的热情鼓动反过来又深深地刺激和启迪了刘尧民,进一步坚定了他研究音乐文学的初衷和决心。因此,待到他撰写《词与音乐》时,也开始大量融入“音乐文学”的概念和研究视角。
二
刘尧民的《词史》并未撰成,仅留下一部《词与音乐》,现在的通行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这部书里,刘尧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音乐文学观。
首先是对音乐文学含义的界定。刘尧民对音乐文学的界定,经历了从一般到狭义的发展过程。从其早期致徐嘉瑞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起初对音乐文学是取一般之理解。他强调,中国的诗歌史是同中国的音乐具有紧密联系的,音乐一变动,诗歌也变动;从《三百篇》到近古的词曲,都彻始彻终受音乐的影响而变迁。这就不难看出,其所谓音乐文学,是以中国古代的诗歌为主线,自《三百篇》而下,直至近古的词曲,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无不赅备。这与后来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所论议题,几乎正相吻合。不过,待其撰写《晚晴楼词话》和《词与音乐》时,他对音乐文学的界定却骤然紧收,只承认“词曲”。例如,他在《词与音乐》第一编说:“在一般所谓的音乐文学,只要可以合乐的东西,便谥之为音乐的文学。这么一来音乐文学的范围便模棱广泛,因为什么诗歌都可以‘削足适履’的去合乐(像乐府时代的办法),什么诗歌都可以被以音乐文学的名义,这样未免糟蹋了‘音乐的文学’的美名了。这样不但把音乐文学的范围弄坏,而且把一段诗歌进化的痕迹也抹杀了。所以,我的‘音乐的文学’的定义,不但要诗歌与音乐的系统相合,而且要诗歌的形式与音乐的形式相合,才给它这个定义。”[2]21他的这一观点,还可在其《晚晴楼词话》中得到印证:“乐府诗有两类,一为纯粹为文人制作之诗,与音乐毫无关系……另一种即音乐的文学,声辞合写,长短不齐,可解不可解,如铙歌之类是。此二种诗,一适于音乐而不适于文学,一适于文学而不适于音乐,必二者均衡发展,始可言音乐的文学,如词是也。”[3]266所以,刘尧民所谓的“音乐文学”,实是以词为开端的。在他看来,只有词曲才算得上真正的音乐文学,词以前的诗歌或韵文都不能纳入音乐文学的范围,这显然有失狭隘。刘尧民对音乐文学含义的探讨,其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能够给出一种准确的界定,而在于他推进了学术界对音乐文学内部特征的探究和认识。
其次是对词之起源的考察。词的起源是词学研究的第一大命题,也是词学界历来争论纷纭的议题。关于词的起源主要有风格说、形体说和音乐说,其中后两说影响较大。形体说主要着眼于词为“长短句”的外部特征,从隋唐以前参差不齐之诗篇寻找词的萌芽,如古谣谚、《诗经》、楚辞、乐府诗等皆有长短错落之句,从这些诗体中寻找词的起源,方向虽然不错,但也不免大而化之,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音乐说则是从词之合乐可歌的内在特点出发,就词与音乐相结合的原因和方式探讨词之萌芽,这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刘尧民主音乐说,他认为词的产生不是“突变”,而是伴随着燕乐的兴起而逐渐产生的。他的词之起源观可概括为三:其一,词是循着古诗到乐府诗再到近体诗的方向一路走来的,其进化的动力在于诗歌是循着趋向音乐的状态发展的。他说:“自古诗以至于近体诗,以至于词,便是一贯的趋向着音乐的状态。古诗和音乐的距离相差得远,到近体诗已经渐近于音乐的状态,到了词便完全成为音乐的状态,所以词才够得上称为‘音乐的文学’。”[2]21其二,刘尧民对词的起源虽主音乐说,但他并未绝弃形体说,而是以音乐说为主线,以形体说为副线,综合考察词的起源。如他说:“所以词和过去的诗歌,以及后来的南北曲,是一个有机的连系着的诗歌的整体……现在研究词的起源,假如不把握着这个趋向,不从过去的诗歌史里,寻找它进化的渊源,单把这个变形的长短句拿来研究,说明它之所以形成,就不免认为词是一种‘突变’的诗歌。”[2]15他强调词是整个诗歌发展链中的一环,是由古诗到近体诗进化而来的。词之为词,首当其冲的是它有别于既往诗歌的形式,而音乐只是促成这一形式的内在根源。所以他认为,诗歌进化的历史,就是诗歌与音乐由冲突到接近再到融合的历史,“一部乐府的历史,就是诗歌与音乐冲突的历史”。他重视词之形体的另一表现是注重考察词的声韵系统,他称其为“内在音乐”,这也是词合乐可歌的自身特性。只有“内在音乐”与“外在音乐”都成熟以后,词才能与音乐相融合,辞与乐才能两不相碍,反而相得益彰。其三,刘尧民将词之起源的内因定在音乐上,但他并不认为词的起源可以划定在某个“时间点”上,而是酝酿于某个“时间段”内,是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过程中长期冲突与调适的结果。例如,他对王灼的“乐府变为曲子”说、朱熹的“填实泛声”说并不全盘否定,但又不同意词之成功仅仅是这种“偶然的尝试”。“但是要问他,何以那泛声里要填成实字?何以文人要去偶然的尝试?为什么不早尝试,不早填实字而把词成功,一定要到唐末五代时才成功?……它的背后,一定潜伏着一段深长的诗歌进化的历史。”[2]16这就将词的起源放在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既符合生命发生学的一般原理,也符合诗歌进化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的论述和结论也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再次是对燕乐系统的考察。刘尧民认为,词的起源是诗歌与音乐相互融合的结果,而能与词这一文体融合无间的音乐正是燕乐。关于燕乐研究的专书现已有“燕乐三书”①、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刘崇德《燕乐新说》等多部著述,刘尧民《词与音乐》则是继凌廷堪、林谦三之后,又一部以较大篇幅研究燕乐的著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燕乐与词的关系:其一,燕乐的律调与词的关系。燕乐可以推演八十四调之多,但用于词之律调又不过二十八调。正如夏敬观《词调溯源 · 二十八调的词牌名》所说:“(总上列)各‘词牌名’所属‘律调’,皆不出于苏祗婆琵琶法的‘二十八调’以外。”[4]227此外,因犯调犯曲的变化,又可以翻出若干新的曲调。刘尧民因此得出结论:“因为燕乐的声调繁多,所以词的新形式便源源不绝的创造出来。”[2]255–256词是“由乐定辞”或“依调填辞”,填词即是一个“择腔”和“择律”的问题。古人择腔择律多以月节时序为准,比如杨守斋《作词五要》曰:“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如十一月调需用正宫,元宵词必用仙侣宫为宜也。”[5]424张炎《词源 · 序》曰:“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6]刘尧民认为古人将乐律视为神秘之物,以月节应律虽不可取,但把它一笔抹杀亦殊觉可惜。他还提出词要合于曲,曲要谐于调,不可不从乐律的起调毕曲和声韵的疏密缓促入手,可谓抓住了词与乐相结合的根本。其二,燕乐的情调与词的关系。刘尧民强调“诗与乐的结合,一定要性质相同”。他认为,一种音乐之所以动人,系有各种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律调为最重要的因素。燕乐二十八调较旧有的清商三调,变化既多,音域遂广,更适宜抒发细腻的感情。而词之为长短句较五七言近体诗尤为婉转,可以说词的婉约的抒情调子,正是燕乐的染色,是燕乐的灵魂。其三,燕乐的形式与词的关系。刘尧民认为词体分为令、引、近、慢等,皆是由燕乐所决定的。如他说:“词是乐曲之词,乐曲的种类不止一种,所以词便有小令之词,慢曲之词,大曲之词,法曲之词,转踏之词,琴曲之词等等。”[2]283燕乐之曲实可分为两种,一为包含若干遍数的大曲,一为没有遍数的令曲。小令配合令曲演唱,以抒情为主;大曲结构较大、遍数较多,故以叙事性歌曲为主。刘尧民还指出,大曲用于抒情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摘取大曲中的一遍为一曲者,也称“摘遍”,如《伊州摘遍》《薄媚摘遍》;另一种是在各大曲的本宫调里制作抒情小令,如《碧鸡漫志》卷三“甘州”条云:“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7]其四,燕乐的配器与词的关系。燕乐之律调出于琵琶,即所谓“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故琵琶当之无愧为隋唐北宋燕乐的主要乐器。唐五代北宋间,琵琶是当时流行乐器,可谓家弦户诵,江陵一带有“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的谚语。琵琶可以奏出繁音促节之乐,且音域极广,便于转调,流利活泼,声情自在,最宜合抒情小曲之演奏。时至南宋,燕乐势力渐敛,管色觱篥渐次风行,曲奏也趋向啴缓,词坛遂以慢曲长调为主。这即是为何唐五代北宋多以小令之词为主,南渡以后长调慢词厥为词坛常态的原因。刘尧民从燕乐的律调、情调、形式、配器与词的关系,深入探讨了词伴随燕乐产生的内在原因,发前人所未发,颇具说服力。可以说,刘尧民对词与燕乐关系的探讨,实际已不仅仅停留在词的起源上,而是放眼词在唐宋的一个发展流变阶段上阐明燕乐对词的影响,即使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有一定价值。
三
《词与音乐》在音乐文学的研究方法或思路上,也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既然这部书是探讨“词之起源”的,所以刘尧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发生学的研究视角。发生学的研究视角,就是要探究事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由果求因,循着一个一个的问题,层层深入,追根究底,逐步展开逻辑推理。这一研究视角,与一般意义上的考据并不相同,而是更多地关注事物发生的内在文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刘尧民的这部著作中,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他在“导言”中说:“词的长短句,是一种音乐的形式,何以这种诗歌会成为音乐的形式?这是因为从古诗乐府以来,经过唐人的律诗,这一系的诗歌是循着一个趋向走,到词来完成这个趋向。什么趋向?即是诗歌音乐化的趋向。在这一部分里便说明了从古诗到律诗和音乐的关系。如何冲突?如何接近?”[2]2刘尧民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层层递进地发问,如剥笋子一般来探究词之起源的。在《词与音乐》中,不但在具体的篇章里可以体现其发生学的研究视角,从整部书的谋篇布局也可以略窥一斑。《词与音乐》共分四编,依次是《长短句之形成》《词之旋律》《从以乐从诗到以诗从乐》《燕乐与词》,刘尧民最终的目的是要论证词的起源是由燕乐所决定的,但他并未直接切入论述词与燕乐的关系,而是采用倒推法,由结论推求其原因。在整部著作的结构安排上,却又是由因到果地正序论述,既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又显得条理清晰,引领读者不知不觉信服其结论。刘尧民对词的起源采取发生学的视角展开研究,他认为词是渐变产生的,而不是突变产生的,词是在某一段时期内孕育而成的,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偶然尝试而成的,这些观点也都符合发生学的一般原理。
《词与音乐》所体现的第二种研究思路,则是采用进化的观点来考察词之起源。例如在第一编第一章“诗歌之进化与词之产生”中,刘尧民总结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四库提要 · 词曲类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王灼《碧鸡漫志》、王昶《国朝词综序》、竹西词客《词源跋》、王世贞《艺苑卮言》、汪森《词综序》等诸家观点,将中古以来诗歌的进化过程归为三个系统:古诗至近体诗的系统、乐府诗的系统、长短句诗歌的系统。刘尧民并未对以上三个系统确信不疑,而是对其假说逐一清理,考其渊源,辨其真伪,最后他认为“三个系统”的假说均不能成立。他认为中古以来诗歌进化的系统只能有一个,即古诗以至于近体诗的系统。他列出一个简明公式:古诗—近体—词—曲。刘尧民采用进化的观点,梳理中古诗歌发展的过程,是较为令人信服的。这种将诗歌的发生发展看作同有机生物一样具有进化的阶梯性、层递性,也是科学可取的。又比如他在一编五章“绝句成为词的三种方式”里一开始便讲:“我们既由文学进化趋势上,认识了近体诗是比古诗为接近音乐,词是更比近体诗进一步的趋向于音乐,与音乐融合;而且肯定了词是由近体诗逐渐蜕化成功,现在是要由音数的蜕变上来看它是如何成功的。”[2]49再比如,他在第一编第七章“由声多词少的绝句成为词”中说:“从隋唐之际,绝句的歌法便开始了,一直到唐末五代时,长短句的词才正式成立,可见其间的经过不是单纯的。总是经多少的歌者,尝尽了歌曲上的种种甘苦,慢慢的由绝句的基础上,逐渐蜕变,逐渐尝试,这种长短句的词才正式成功。”[2]70类似的论述还见于第二编第四章、第三编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等。这些足以说明,刘尧民在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时,是在自觉地运用进化的观念。如果要进一步追问,刘尧民的进化观念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想至少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说的影响。有学者研究称,刘尧民对王国维及其学说十分服膺[8]。第二是受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等近代音乐史和音乐文学史著述的影响。刘尧民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不可不关注中国较早的几部音乐史或音乐文学史,王光祈和朱谦之的这两部史著,均具有浓厚的进化观念,何况刘尧民也在其论述中多次称引王光祈的著述。第三是受从西方译介而来的域外著述之影响,例如严复所译《天演论》等。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学东渐的维新思潮开始日益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国的传统音乐也逐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刘尧民生逢其时,毫无疑问会受到维新思潮的洗礼。总之,运用进化的观念研究词之起源,在当时仍不失为先进的方法或观念。
从《词与音乐》里,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刘尧民研究音乐文学的第三种路径,即建立系统的概念和逻辑的分类。刘尧民的《词与音乐》可算是朱谦之以后,又一部音乐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在这部书里,他筚路蓝缕,对音乐文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都做出了初步的界定和划分。他除表明自己对音乐文学的理解外,又对朱光潜提出的“内在音乐”和“外在音乐”的概念予以阐发,并指出音乐和文学结合的特点、辞乐结合的形式和表现、燕乐与词的四种内在关系等,其论述明显较朱谦之更为深刻。如其论内外音乐:“这里所谓‘谐畅’,应该分作两种意味看,第一是诗歌本身的声韵平仄的谐畅,第二是和外面音乐的谐畅。前者可名为‘内在音乐’,后者可名为‘外在音乐’。”[2]99这就在词的字句、声韵与乐的拍板、旋律之间找到了对应关系,为探讨词与音乐的结合方式找到了落脚点。这较之当代学者侧重于从社会风习、文人社交、歌妓制度、仕人心态等外部因素寻找燕乐与词的关系,更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实质。刘尧民之前的学者论及音乐文学,都未深入探讨辞乐结合的特点和形式,只是含糊地认为,只要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文体皆可视之为音乐文学,唯有刘尧民首先提出只有辞乐结合谐畅,辞与乐必须性质相同,才算得上真正的音乐文学。任中敏对音乐文学的辞乐结合也有类似的论断,他说:“所谓‘结合’之义则甚重要,乃词章之字句、平仄、叶韵、感情等,与音乐之抑扬、曲折、节拍、感情等,契合为一体,构成一曲调,共戴一名称。”[9]6虽然辞与乐的结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刘尧民这种认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辞乐结合的初步研究,刘尧民堪当第一功。刘尧民认为,诗乐结合的方式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古以至于汉代是‘以乐从诗’,先作好诗,然后跟着诗歌的节拍来制曲。汉以后至唐是‘采诗入乐’,因为汉后诗乐分途,不能不采诗以合乐。从唐以来是‘依声填词’,先制好曲,然后跟着音乐的节拍来作诗。”[2]202这是对中国古代诗体音乐文学之辞乐结合方式的重要概括,也基本符合中国古代诗体音乐文学的辞乐结合方式。另外,刘尧民论燕乐与词的关系,则从律调、情调、形式、配器四个方面展开,已论如上文。就整部著作的谋篇布局而言,他也是有所统系的,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是依照元微之(元稹)的一条原理将书写成四部分的。所谓元微之的原理,即其《乐府古题序》所云:“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10]这句话便是刘尧民整部书的纲领,纲举则目张,结构自然就十分严谨。“句度长短之数”对应第一编《长短句之形成》,“声韵平上之差”对应第二编《词之旋律》,“莫不由之准度”对应第三编《从以乐从诗到以诗从乐》,“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对应第四编《燕乐与词》。这样看来,无论是从整部书的谋篇布局,还是从各章所涉重要概念、分类看,刘尧民都做了深入的思考、准备和研究,这也成为此书的一大研究特色,颇具借鉴意义。
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词与音乐关系的力作,对词乐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刘著作为开创之作,自然也有不足之处。如其第一编第一章谓:“近体诗已经渐近于音乐的状态,到了词便完全成为音乐的状态。”[2]21这显然把“诗律”与“乐律”混为一谈了,甚至是把诗歌律化的内在动力归功于音乐了,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又其第一编第五章指出,绝句生成词有三种方式,盖必用之以证词是由绝句而来。绝句填实泛声、和声而为词,实为词产生之极其微小的途径,因词之大宗产生皆由燕乐而定,即所谓“依调填词”,故其说亦需加以甄别。诸如此类,不得不予以明辨。
注释:
①“燕乐三书”指凌廷堪《燕乐考原》、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丘琼荪《燕乐探微》。
[1] 徐嘉瑞全集:第1卷[M].昆明:晨光出版社,2008.
[2] 刘尧民.词与音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3] 刘尧民.晚晴楼词话[G]//词学:第1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66.
[4] 夏敬观.词调溯源[M]//“民国丛书”:第5编:第54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6:227.
[5] 杨守斋.作词五要[M]//丛书集成续编:第163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4:424.
[6] 夏承焘.词源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9.
[7] 岳珍.碧鸡漫志校正[M].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69.
[8] 曾大兴.刘尧民先生的词学研究[G]//词学:第1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3–241.
[9] 任中敏.唐代“音乐文艺”发凡[M]//任中敏文集:第5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6.
[10] 唐元稹.元稹集:卷23[M].冀勤,点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编辑 杨宁〕
The First Research Book on——Review on LIU Yaomin'sand His Research Methods on Musical Literature
ZHANG Jianhua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s the first scholar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i and Music, LIU Yaomin'shas the certain create meaning in academia. LIU Yaomin use concept, the principle of 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and system building, the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Yan music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 and the form and reason has made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still has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LIU Yaomin;; mu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2018-01-28
张建华(1984―),男,河南方城人,博士研究生。
I207.23; J609
A
1006–5261(2018)05–008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