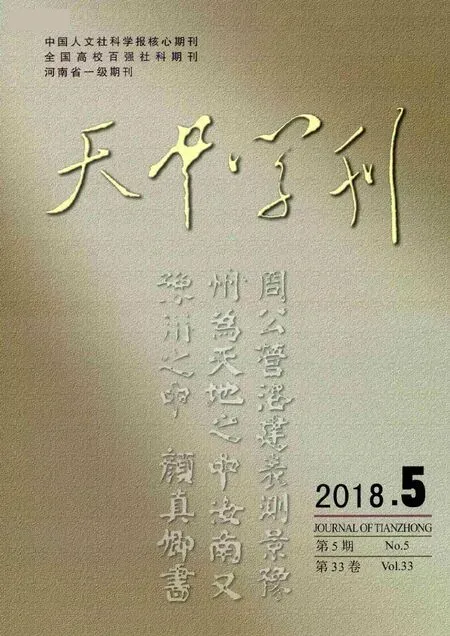人类自我意识视角下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
杜晓丛
人类自我意识视角下环境问题的若干思考
杜晓丛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在21世纪的今天,环境问题已经愈发严峻和不容忽视。环境问题是个历史性问题,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展而逐渐产生,并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时,环境问题也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也是个普遍性问题。而这个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根本成因还在于人类自身,在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对自然环境的无度破坏。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人类自身入手,从完善人类的本性、约束人类的实践活动入手。
环境问题;自我意识;人类本性;实践活动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因为我国人民对于优质生态产品以及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还在于生态环境破坏已经成为关乎人民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其实,环境问题已然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既然这是一个关涉人类自身命运的亟待解决的实存问题,就必须拿出积极的态度来研究环境问题的成因,努力寻找环境问题的出路。
一、环境问题的出现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 · 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然而,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只是一个开端,环境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化学农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今天所谓的环境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生存现实问题——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1]1。我们必须对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环境问题的历史性
在早期原始社会,人类主要是以采集狩猎、打鱼捕捞的方式来进行生存活动的。这一时期的人类从自然界中采集果实、捕获猎物来维持自身的生命,从而对自然存在物施加了人力作用,虽然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一定的人为影响,但是这种索取还是在自然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因而在这一时期,人类和动物一样,没有对自然界造成太大的、可见的破坏。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不再像原始社会那样追随着生存资源的所在地而进行流动性生活,而是转为在某块土地上开始定居式的生活。人类通过刀耕火种进行作物种植,通过驯化一些动物圈养食物。但是人类的种植活动,必定要以毁坏林地、烧除植被、降低土壤肥力、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为代价;人类的圈养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动物的本性,人为地造成了动物的习性转向、本质异化。并且由于人类定居方式而增加的人口数量,也给局部地区的环境造成了更大压力,这一时期也曾出现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崩溃的情况。
在工业社会时期,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活动时,人类大量砍伐森林,大肆开采矿产,从而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开发、物种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的不稳定。人类进行工业生产之后,又开始向自然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废渣,从而使自然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肉眼可见的,也是深藏不露的;是立竿见影的,也是影响深远的。
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依次推进,在人类谋求生存的活动中,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且程度也不断加深。
(二)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这里提出环境问题的普遍性,拟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领域,以人类谋求生活发展的活动为线索考察环境问题的存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环境问题出现绝非个别现象,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本文着重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加以分析。
从经济领域看,自然界被视为一个资源宝库,人类所要考虑的就是所得利益的多少。什么样的投入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什么样的地方能产出最大的经济利益,人类的经济活动就会导向这些投入和地方。在古典经济学中,作为经济活动原材料“产地”的自然界并不被纳入成本计算中,这导致人类为了发展经济而肆无忌惮地消耗地球上的资源。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界的破坏不仅表现在资源的消耗上,经济生产活动的副产品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何东出的这档子事儿,让本来就心不甘情不愿去相亲的何西更有理了,他去找老爸商量,希望能找个理由把明天的相亲给推了,没想到老爸不买这帐。何西只好试着以理服爸:“爸,咱能与时俱进吗,二十一世纪都过去十年了,咱能不包办吗?”
从政治领域看,政治政策也是导致许多环境问题产生和加剧的原因。一些环境问题主要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发达国家凭借着经济和政治优势在双方的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产生环境问题的方面,发达国家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方面,发达国家往往不愿意认同那些能保护环境但却会损失自身利益的政策。这些都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产生和加剧。
从科技文化领域看,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既可以上九天揽月,也可以下深海捉鳖;既能使山低头,也能使水倒流。人类可以充分展示对自然界的威力和强权,从而充分享受征服自然的快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环境被打上了人类行迹的烙印,自然变得再也不自然,甚至面目全非。
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不同领域中,环境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的。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链条中,我们考察的是人类的生存活动;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科技文化领域的普遍性链条中,我们考察的是人类的发展活动。毫无疑问,无论是谋求生存的生存活动,还是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发展活动,人类都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然而,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远远大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尤其在人类把自然环境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当作需要被征服和改造的存在时,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由此,环境问题的出现和存在也就成了必然。
二、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
环境问题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展开,是在人类的作用之下才逐渐出现的。自然环境是种客观的存在,它本身没有所谓的危机。自然环境危机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相对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的。虽然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也曾出现过剧烈的环境变动,也曾表现出自身内部系统的紊乱。但是这种变化是自然界自发产生的,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自我调整,是保持在自然界自身的恢复能力的范围内的。然而,人类产生之后,在人类生存活动方式的不断影响下,自然界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才真正有了自然环境危机。因此,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从人类活动的历史性和普遍性来看,环境问题程度的加深、范围的扩展,都在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
(一)从历史性来看人类自我意识对环境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的人类虽然也要为了生存而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的能力比较弱小,人类的自我意识和动物本能是融合在一起的,人服从于大自然的强权。这时人类像动物一样与自然界是种依附关系,拜伏在自然的脚下。无论是对生存所需食物的积极接受,还是对自然生存考验的逆来顺受,人类都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的给予。
在农业社会时期,由于合力作用的提升,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在意识和行动上,人类都不甘于屈从自然界,努力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向自然界主动求变。即使力量还远未达到与自然界相抗衡的水平,人类也企图借助简单粗陋的工具表达控制自然的愿望。在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不再屈从,开始自主地对自然界改造,以使其能够为人类自身的生存提供便利的条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活动就是在这种自我意识的主导下开始迈出了试探性的步伐。
在工业社会时期,在理性以及工具的推波助澜下,人类的主体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不仅深化了控制自然的想法,而且也发展出了控制自然的强大能力。人类在主体意识的鼓动下,打着不断提升生活水平的旗号,对触目可及的一切事物进行掠夺和改造,把对自然的控制发挥到了极致。“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的进步可以从人类征服自然的节节胜利中看出来。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功是这样巨大,人类可以战胜自然一事已经毋庸置疑了:自然虽然尚未被最后击败,但显然已经无可逆转地做了撤退。即使在自然还坚持着的地方,人类也认为,最终取得控制权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2]。人类对于自己能成功地改造自然是如此的自信。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的自我意识也经历了由被压抑到开始凸显再到大肆张扬的不同阶段,由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
(二)从普遍性来看人类自我意识对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中,个人主义观念盛行,每一个人想要追寻的都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一切都要为人类的自我满足、自我利益服务。因此在经济活动之中,人类把自然界当成经济活动的物质资源载体,把消费当作生产活动的动力,把利益当作生产活动的目的。当一个人消费的东西越多,所占有的物质越多,他就越感觉幸福。物质财富便成了幸福的象征。为了追求财富,人类就必须用最小的成本来生产最多的利润。而自然界不像人类,自然界没有自己的意识,自然资源不会因为向人类提供了什么而索取报酬,也不会因为被伤害而向人类索要赔偿。这样,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界、开采自然界,因而自然环境所遭到的破坏不可谓不大。
在政治领域,环境问题的出现也与国家政策的偏向有关。在政治政策的决策中,每个国家优先考虑的都是本国的利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为了生存不得不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对环境有消极的影响,即使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发达国家来说,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这也关系到其本国的经济发展,因而发达国家往往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通过转嫁危机来暂时保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一切都使环境破坏的程度不减反增。
在科学文化领域中,人类理性思想的高扬,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人类愈发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完全摆脱自然的束缚,已经可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这种意识作用下,人类随心所欲地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进行支配,人类要把自然界改造成人类想要的模样,让自然环境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种种物质。即使给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人类膨胀的自我意识也会认为人类的技术是乐观的,人类总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无论是历史性链条中人类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抑或是普遍性链条中人类的个人利己主义、国家本位主义、自我意识的膨胀,究其实质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类本性的狭隘、人类本性的不完善。
三、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
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以高于其他存在物的优势地位而存在,就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人类获得优越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同样,人类之于动物的悲哀之处也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度性。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力图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因而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既然自然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人类自我本性的不完善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度性造成的,那么,就应当从这两方面入手思考环境问题的对策。
(一)思想上:完善人类的本性
理论是行为的先导,要想真正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必须首先在思想上进行革命,破除错误的意识。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几经转变,主要有敬畏的态度、征服的态度、共生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对应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定位,因而在这些不同的意识和态度的指导下,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也不同。这三种态度可以分别对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论述的人类历史生成过程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
敬畏的态度是“人对自然的依赖”的形态,人类把自然界当成至高无上的存在,强调自然界的威严性,夸大人的自然属性,把人降格成自然界中如同动物一般的普通自然存在物,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事活动要以自然界为榜样和楷模。这实质上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类以消解人自身的主体性原则、消融自身的自我意识来换取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征服的态度是“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态,是把对物的获取当作目的的。它要求人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把人类自身当作万物的尺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只强调自身的利益,不关心其他任何存在物的利益,不关心自然的存在状态,人为自身立法、为其他存在物立法、为自然界立法。
敬畏的态度、征服的态度都不是人类对待自然界应该采取的态度,主体性的消解、自我意识的膨胀都是人类本性不完善的表现。尤其是征服的态度和自我意识的膨胀不仅给自然界带来了灾难,也终将危及人类自身。
对自然环境的大肆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浪费、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都是过分张扬自我意识、错误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界必须是共生的,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161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不是超脱于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人类是生活在自然界之中的,人类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应对环境危机,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人类是时候完善人类自身的本性了,是时候转向与自然共生的态度了。
共生的态度要求人类抛弃敬畏和征服的态度这两个极端,要求人类自我本性的完善、自我的全面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共生的态度对应着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只有全面地认识自己、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才有可能是自由的,才有可能全面地认识自然、全面地占有自然。当然,这里所说的“占有”自然并不是指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万物,而是指人类通过对自身本性的认识就能够达到对自然本性的认识,能够找到适合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定位。这样,人类就不是要去主宰自然,而是能够找到一条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的道路。
只有深入挖掘人类内在的善,看到人类的命运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把人类自身的“度”和自然界的物的“度”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也只有真正认识到环境问题产生的思想上的原因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张扬,是源于人类对待自然的心态上的错误,并以此来纠正人类不合时宜的观念,全面发展人类的本性,凸显人类内在的善,才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二)实践上:约束人类自身的行动
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来说,转变人类的思想还只是第一步,理论最终还是要导向实践。从实际的行动出发,一切思想才具有现实意义。
在早期生存论阶段上,自然界对待人类和动物一视同仁,给所有自然存在物的生存设下了种种限制,人类也只能依靠着本能在自然界规定的条件和划定的领域内开展生命实践活动。但是人类毕竟不同于其他存在物,实践活动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动物是本性先于存在的存在物,其后天的种种活动都是其本性预先规定好的。而人类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物,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性特征,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塑造着自身。正是在展现其本质的超越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自我意识,逐渐开始超越自身的自然性,发挥自身的超自然能力,并由此力图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和控制,把自然界当作自身生存发展的资料,进入掌握自身命运的历史。同样,在沉浸于自身的超自然性的过程中,在挣脱自然掌控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人类萌生了控制自然的想法,开始认为自然界应当有求必应。因此,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实践活动上便是人类忽视了自身实践活动的超越性与自然环境的有限度性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自然环境的有限度性,并不要求人类停止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发展资料的实践活动,自然的本性也并非是自在的自然,自然只有在与人类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人类实践活动的超越性,也不等同于人类可以任意地超越自然的承受能力,从事不加节制的开发干预实践活动。“超越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既是人类理想性、精神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活动过程。”[1]66既然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活动,那就会被加以条件性和有限性的限制。
人类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实践活动的“极限性”进行反思。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是离不开自然界的,人类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与自然界及其内部事物发生具体的联系。然而,人类不能只将自然作为无意识的客体的存在,自然环境是有其自身的系统性、结构性、功能性的,自然界也是一种“活的”存在,具有“活的”性质,它具有自身的规律性。自然环境危机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人类证明:一种实践活动如果只注重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体的客观规律性,必然要走向极端,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危害。
因此,即使是出于“生存论”的关怀和要求,人类也应该自觉地约束自身的实践活动,把握好自身实践活动的无限性与自然环境的有限度性之间的平衡,使其既符合自然界潜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规律,又达到人类健康永续发展的目的。对于人类来说,生存和发展是永恒的话题,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因而把严峻的环境问题纳入人类的视野中也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完善人的本性、约束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健康永续发展的目的。
[1] 林兵.环境伦理学的人性基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 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M].梅艳,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87:11–12.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叶厚隽〕
2018-03-22
杜晓丛(1993―),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
B82-058
A
1006–5261(2018)05–0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