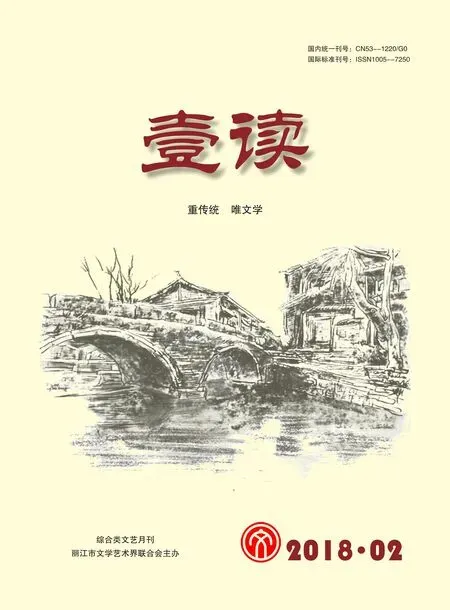木祥小说里的“乡愁”
尹晓燕
我是学习写小说的,阅读的小说相对比较多,并且,比较关注云南、特别是丽江作家的小说写作。木祥是云南比较有实力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丽江为数不多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集《束河啊束河》和长篇小说《红灯记外传》,我都认真拜读过,受益匪浅。
在阅读过程中,我觉得,木祥的大部分小说都流露出浓厚的乡愁,他的小说总是让人读到怀乡的情感,眷念故土的思乡情绪。
其实,对童年的回忆,对故土的眷念,一直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或源泉,是我们铭记历史的精神蕴藉。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乡愁或对故土的眷念一直是漫长的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我们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就常常读到许多优秀的表达乡愁的作品。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就已经有不少表达乡愁的作品(如《君子于役》《采薇》等),唐诗宋词就更不用说了,表现乡愁主题的诗篇更是不可胜数。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范中淹的《塞下秋来》等等,思乡情感,乡愁情节在诗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20世纪,我喜欢的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作家,他们书写乡村记忆的作品,让我们读到了乡愁乡情的同时,还让我读到了对乡村陷入现代困境的深切关怀。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同时造就了一大批以乡村乡愁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炜、阿来等,他们或者以乡土叙事为主导,或者以个人亲历的角度书写乡村,使读者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进步与转折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挚的记忆。
当然,以乡村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记录乡村,塑造新型农民形象,表达乡愁的作品,肯定会有作家的乡村生活经历,有他们独自的情感世界。木祥小说的乡愁,可能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素养有关。木祥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过农民,当过民工,在西藏当过兵,退伍后当过汽车驾驶员,然后走上了创作道路。他丰富的生活阅历,见证了新中国六十多年翻天覆地的变迁,可以说,这是一个小说家的重要财富。人生的阅历对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十分重要,丰富的经历,难免产生不少人生的磨难,悲欢离合,这些,往往会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深度,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决定着作家的写作方向。所以,我们阅读木祥的乡愁小说,可以从题材的选择,故事的编织,语言的表达和情感的倾诉等方面找到亮点。
一、题材选择决定了木祥小说的乡愁情节
写小说的作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写作方向,即题材选择的时候,都得明白自己的长处在哪里,自己的局限在哪里。比如,昭通的夏天敏就没有尝试写丽江东巴文化情死题材,丽江的和晓梅也不会轻易选择写西藏,同样,五十年代出生的木祥,也不可能选择写现代青春校园文学。他们都知道自己写作的优势在哪里,同时也明白自己的盲区在哪里。他们在写作技巧上作大胆的尝试,但在素材的选择上都尽量避开局限,选择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题材。木祥的小说,大多都以滇西北一个叫“妃子村”的村庄为地理坐标,他的长篇小说《红灯记外传》,中短篇小说《束河啊束河》等一大批乡土小说,都是以自己经历和生活过的时代故事为背景,表达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乡愁。
到了近几年,木祥的小说也没有走出乡村乡情这个主题,他的《童年三题》《走阴》《洪水中的村长》《村长也用苹果5》等中短篇小说,依然与乡村有关,与故乡有关,其故事情节,都来自他的体验和感悟。木祥的小说题材,来自他自己生活的原型,也来自于他对大量乡村素材的采访记录,用心捕捉,严格筛选。通过多年的实践,木祥似乎明白了,小说不是照搬生活,他总是能通过细致的观察,体验,分析素材在小说中对主题和人物性格有何作用,然后才作出最后的选择。
比如短篇小说《走阴》,讲述的是一个巫师通过走到“阴间”,与去世后的人对话的老故事,充满迷信色彩。如果就事写事,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木祥通过思考,把“走阴”的故事嫁接到爷爷奶奶身上。小说中,奶奶一直怀疑爷爷与“风摆柳”有染,然而,生前从来没有得到印证。爷爷死后,奶奶去为 “风摆柳”家“走阴”。“走阴”到最后时刻,奶奶说有一个“身穿绿缎子长衫,头戴红顶瓜皮帽的人”进了“疯摆柳”家。“疯摆柳”家的人,谁也猜不出这个人是谁,“疯摆柳”却是泪流满面了。因为奶奶“走阴”时设置的这个人,就是“爷爷”的“阴魂”。 木祥就是用这种隐喻,通过爷爷的灵魂回到“风摆柳”家的过程,表达生死之爱的真挚情感,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让我们从老故事里读到新的观念,浓烈的乡愁扑面而来。
类似这样对故事巧妙设置的例子还很多,这样的小说,不但让我们读到现代情感,同时能让我们在老故事中读到浓烈的乡愁情绪。
二、在现代乡村故事叙述中植入古老的乡村情节,增加小说怀旧情绪
木祥近两年的小说,以现代乡村故事为主,但他在写好现代乡村故事的同时,融入乡村故事和人物的怀旧情节,表达乡村变迁和乡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让人感到温暖。写现代题材的小说,要深入生活,撷取具有新的生命力的故事和人物。木祥不断地深入生活,寻找到反映新农村的新变化的题材后,不是盲目地写作,而是观察,体验,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情感在哪里,他明白自己想表达的,最能让读者和他自己心动的,是乡村人物的感情,还有在现代生活中的怀旧情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乡村,是生产关系、思想观念都变化了的乡村,乡村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物质突飞猛进,精神生活却往往处于游离状态,如何通过小说反映这一命题,木祥作了一些尝试。他最近两年的乡村题材小说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如何写出现代村民的历史与现实交融,从而达到对乡村、农民的多重解读,使小说具有思想力度。
我们读到的《洪水中的村长》,是2017年他发表在《民族文学》“建党九十周年专辑”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滇西北乡村的一个洪水抢险故事。小说中的杨大武和杨大才,是两个出生不同阶级成份的兄弟,他们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奋斗事业有成,又回乡为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特别是杨大才,为了赚钱,在发展自己的砖厂时因不小心生殖器被皮带轮绞掉,而在关系到自己的村庄被洪水淹没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决堤把多年艰辛创建起来的葡萄园冲毁了,一种乡愁,通过理想中的人物,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读来让人感动。
在同一篇小说中,主要人物杨大武是新时期乡村干部的典型,他是在通过艰难的创业发家致富以后才回乡当村长的。杨大武回乡当村长,为村民服务是大方向,但他也不是高、大、全的典型,其中,也包含着他复杂的情感。杨大武是地主子女,小时候受了许多凌辱,回乡当村长,也是想争气,回杨家村去证明自己。但木祥塑造的杨大武,回乡当村长也不完全是私心,最终还是被服务村民这个大局所征服。比如杨大武当村长时五保户的安葬,抢险救灾,美化村庄,拒绝回扣等等,都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村干部形象。
这些乡村人物的塑造,来源于木祥对现代乡村的正确解读。乡村农民,在经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以后,他们在赚钱的时候想尽千方百计,这也符合客观规律,杨家村的人穷怕了,没有钱的滋味他们尝够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钱所打倒,通过勤劳富裕起来以后,他们依然怀念家乡,他们觉得,保住自己的村庄,人生价值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这与近年来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回乡建房,富裕起来的村民回乡发展产业等等情形是多么的相同。
木祥就是通过深入了解新农村,再通过对自己的乡愁情感进行梳理,写出乡村农民的多面性,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正因为如此,才能立体地反映乡村,表达自己的乡愁,让主题多元和模糊,让小说不再是单一的故事,单一的人,而是具有了生活的多重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容量。
三、乡愁情节让小说具有浓厚的个人情绪
读木祥的乡愁小说,我们总是能读到一种复杂的情绪,一种淡淡的纯朴的韵味。我在谈自己的小说创作的时候说到过,我的小说是有自己的情绪的。我的小说里,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我始终觉得,小说里有了自己的情绪,才可能读出一点儿韵味。后来发现,作者的情绪是会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基调、韵味的,是明快还是缠绵,是悲壮还是诙谐,都产生于作者对材料的把握,然后决定了作者的情绪,韵味。同时,这种情绪或韵味,又决定了作者的叙述方式,语言的运用。
仔细读木祥的小说,小说里的情绪和韵味不是生硬的,而是从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中自然地体现出来的,读他的小说后,有时会会心一笑,感同身受。
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小说中的情绪与韵味,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它关系到小说的可读性,感染力和作者的态度。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能很好地控制小说的情绪,调动情感。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深度,但是,我们更期待思想性与作者的精神气质融和在一起,让作品有瑰丽的想象,诙谐,机智,生动,妙趣横生的情节。
木祥的小说在人物故事中自然地融进自己的情感或情绪上,作了很大的努力。读他的小说,总是能让我们读到他的感情,有时候,我们会猜他作品里的哪个人物是他。连他自己都说,他写的小说,差不多要用现实中的人名才过瘾。我不知道对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放入了太多的感情好不好,但是,没有作者情绪的小说,我难以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木祥的许多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这样更能表达出他的情感世界。如《妃子村片断》《童年三题》中类似自叙的表达方式。当然,小说故事不可能全部是作者的,但是,都是注入了作者情感的,是经过他思考,筛选过的,这样的书写,小说就有了韵味,就容易产生共鸣。
如此的表达方式,使木祥的小说具有浓厚乡愁情绪的同时,也让他的小说具有散文韵味。他的小说,我们有时候无法分辨是小说还是散文。从文学理论上说,散文是自我的,小说是客观的。但在他的小说里,既是自我的,又是客观的。如果认真分析,里面小说元素是主体。比如他在《走阴》里这样写道:
“大门老旧了,头上盖着的瓦越发黑了,松木的门板和门墩、门槛都成了棕黑的颜色。两旁的土坯墙也斑斑驳驳。门头上的瓦沟里长了一些石帘花。
每到有人开门,“吱呀”声庸懒沉重。门里的巷道只有二三米宽,比较深,都铺了瓦砖。开门声在深深的巷子里缓慢的流淌。
巷道里有一口老井,井槛上写着“龙泉清”三个字。”(木祥:《走阴》)
这样的表达,散文味道扑面而来。但是,后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的戏剧效果,依然让我们感觉到小说构架的存在。比如在《走阴》的结尾处,木祥这样写道:
“纸钱烧得差不多了,奶奶的脸色好像回转了一些。然而,时间不长,奶奶马上又抖动起来,嘶哑着声音问道:怎么了,这个时辰了,又进来了个瘦高个的,穿蓝色缎长衫的,头戴瓜皮帽的?
“风摆柳”家的人都吃惊,想站起来的又跪下了。然而,都猜不出这个人,想不起自家有这么个人。
奶奶说:想不起来啊,真没有啊?但真是进来了啊,瓜皮帽上,还有个红顶子的——有点像个秀才呢。
“风摆柳”眼里却是噙着泪花了。他知道是我爷爷的灵魂去她家了。
“风摆柳”只是什么也不说。
奶奶说:是不是我家那老鬼走火入魔走错了门,我把他赶出去!
然后摇了一会磬铃,说道:出去出去,回家去,我给你烧油茶。
说着说着奶奶就醒了。奶奶醒了,用枯瘦的手指揉了揉眼睛,然后对“风摆柳”家的人说,这个人回去了,可能是走错门了……”
在小说中表达自我情绪,难免使用散文语言。有人说,小说要用客观性的语言来写,作者有什么思想感情,作者并不站出来说,而是让人物、让情节代作者说;而散文则运用主观性的语言,作者不站出来说,还不行,作者可以直抒胸意。我觉得,木祥是善于用散文语言写小说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他是在场的,又能客观地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的,并且能让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意境。
由于是真诚的情绪,木祥的小说是聊天式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这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生活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上,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作家对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充满了自信,才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如果没有对事物的把握,没有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我们是不可能在小说叙述中感受到作者情绪的。
总之,木祥的小说对乡愁小说作了难能可贵的探讨,他小说里的乡愁是真诚的,表达着他的灵魂。我们期待着木祥有更多更好的反映乡情乡愁的小说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