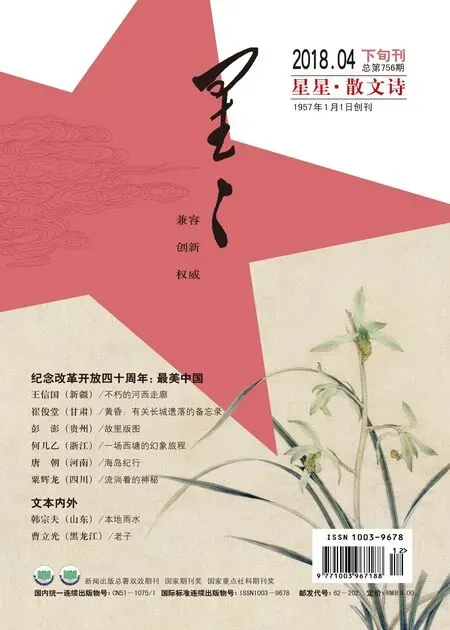书写眉山的几种方式(组章选三)
张晓润(陕西)
散文眉山
在眉山,我因它而生义,觉出它额头高挑,或舒或蹙,无论身靠何处,都早有自己的方圆。
凡事有眉目之道,此时的眉山,恰是一种引领,像春风领着低头的马匹,只顾向前。
眉山如眉,偶有翘首,神思常为之而往。有陕人常年蜗居北塞,终日开门见山,一日忽念起眉山之媚,忍不住要急着拨云而见蔚。
相思间,眉山,如同一粉黛女子,叫人如鹿撞怀。
于宽处见,它丰乳、肥臀、蜂腰,一如盛唐女子。
于窄处寻,它桃面、樱口、莲步,恰似楚国宫妃。
宽窄恰当处,自是咸淡得宜时。
女子二八,当是眉山最好的春光。
春光眯缝,在眉山,我见证过两棵树,一棵是银杏树,另一棵还是银杏树。
银杏树下,苏东坡曾提宽袖饮茶,风吹过,落花点点,误入杯池,他却不与浮沉之物论急缓。
茶毕,他逃出庭院,离开泥塑之身,在诗和远方之间,备手移步。
于月下,他提明月为灯,举酒肆为幡,错愕处,几问青天。
他遍食美物如悟世间诸事,在口舌之间推移聚散。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他目尽总有慧光叠出。
他胸中多有块垒,却常常能大隐隐于坐。眉山因他而富足,因他而分送流水。
在眉山,又怎能遗珠三苏,他们以相同的姓氏,贯通起一代骄子江山。
古人的辉煌福及今人,写、读、尚、爱,让眉山,一浪惊鸥,一浪又起。
在时间的光点上,眉山,翩翩成为形神皆备的散文的故乡。
诗歌眉山
在眉山,一朝踏进,便会被诗书裹身。
一方文脉,绕梁趋巷,香染耳目与衣襟。
它静卧成都平原腹地,有岷江穿谷而过,带来钟毓灵秀。它含灵吐玉,俊贤层出,盖以书城氤氲聚才。
在眉山,诗魂不是一件外在的衣裳,它藏于骨缝,行于精髓。
在这里,城是尚诗之城,在这里,人是尚诗之人。在这里,有风吹过,遍地都是诗歌的种子。
公元1037年1月8日,来过一场年轻的雪,它在三苏古宅呱呱落地。
从此,一轮月亮从眉州诞生,从中国诞生,从世界诞生。一口古井,托起了月亮诗意的脸庞。
它垂挂梢头,一照经年。它明亮、长久,如城市的一颗饱满的诗心。
染疾之时,抬头望月,如同治病、疗伤。
虚妄之时,身披月色,一如养神、安魂。
在眉山,要把自己当做它隔墙而在的邻居,拾柴火而不一定添火焰,居简室而不一定抱虫眠。
在眉山,我要束草绳而富为诗人,我要一谈起天府就要就着芙蓉花和银杏树品茗。
我向下低望,向上远眺,每一次经过或驻足,都逃不过一花一树的楼阁和镜台。
在两者之间,或多者之间,当我偶然谈论起岷江之水,我都会继而谈论起一朵浪花起于江河的意义。
而我终将会被这一朝过度的山水惹了醉意和倦意,那么,选择在眉山做好一介看客和过客,该是多么美妙的选择。
醒着时,我克制白天的繁华,睡着时,我放纵夜晚的黑洞。
而我也终将因诗经附身而浑身闪亮,眉山密集的光斑擂我一如鼓点——
木末芙蓉花,我又怎能不被这灿烂的繁花所惊?
桂冠银杏树,又如何能不被这耀人的辉煌所撼?
在这些沉静的激流中勇退吧,那么,趋步彭祖山吧——
让我借用它老者的形象,靠近和回探眉山年轻的模样、成熟的经验,以及佛前那些深陷眉山的草木。
以此来写下眉山旧的储物与新的燃料。
小说眉山
眉山,是要用针头和线脑来铺陈的,需要用竹编的笸箩来收纳的。
它有热气腾腾的日常,素朴的需要用粗布缠裹,纷繁的需要用金边绣烫。
它有软的纹路,硬的棱角,我不可以用花拳潜入它的内里,更无法用绣腿踢开它的外部。
小说般的眉山,我要定下它的核心,我要找到它的骨架和环境。
在眉山,三苏是千年不倒的人物,如果时间是一场关于奥秘的探险和跋涉,这便已足够。
如果借古思今,从古人的身上,推拿生命的光辉,那么眉山,就是一部关于中国文人的心灵史。
当谈论起它的外貌,我们会如此述说:它集产城一体、景城一体、文城一体。
当谈论起它的动作,我们会如此描绘:它正跨江东进、拥江发展,抽松老城、繁荣新城。
当谈论起它的语言,我们会如此表达:它要步步见绿、500米入园、1000米见水。
当谈论起它的神态,我们会如此铺陈:它须共享现代服务,回归田园生活。
当谈论起它的心理,我们会如此揣度:它举现代工业新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活品质之城。
眉山的故事情节已拉开序幕,这是古典的眉山、生态的眉山、诗书的眉山。
它已从细节走向海量,从骨架走向血肉,从灵魂走向灵魂。
从乡村叙事到城市合围,它的发展,已步入高潮。
眉山,这一部乡村结合史的大戏,留下了它永无止尽的悬念。
有趣一点,再有趣一点,不要让阻挡的伞挡住了披挂前进的水珠。
新鲜一点,再新鲜一点,不要把爱过的事物再爱一遍,而是把恨过的接过来去爱。
眉山的胸怀只有大了,才能用葡萄交换美酒,用人心囤积粮草,用石头置换星星。
只有这样,当我们用力合上眉山这本小说体,我们就会拈花微笑、起身致意。
像立在水边的陶罐,丰盈而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