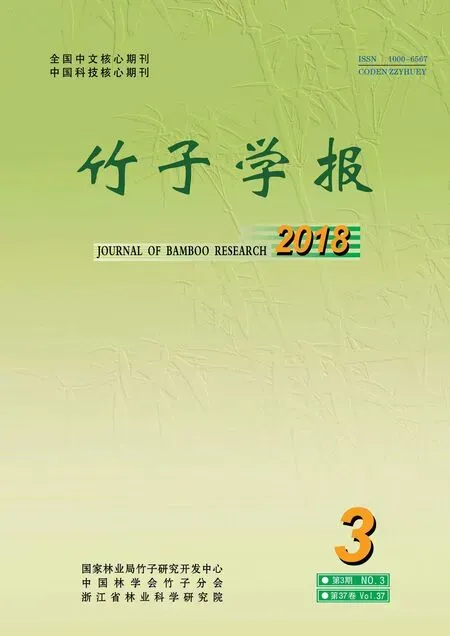竹简考竹
蓝晓光
(浙江省林业厅,浙江 杭州310020)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东亚往往被称为‘竹子’文明,有证据表明,商代已经知道竹子的多种用途,其中一种用途就是用作书简”。同样,与竹简相关的毛笔和竹纸等书写工具,也在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一起构成了中国竹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利用出土竹简,结合有关典籍记载,研究竹简以及竹笔、竹纸等书写材料或工具背后的竹子,无疑对探究“竹子文明”曾经的辉煌具有重要意义。
1 简之脉络
时间上看,中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竹简大都是战国时期,其中最古老的为战国早期曾简和信阳楚简,约为公元前400年。曾侯乙墓竹简出土于1978年,共240枚竹简,整简长度70~75 cm、宽1 cm,总计6 696字,记载的主要是车马兵器和木俑等[1];信阳楚简出土于1957年,148枚竹简,每简简长45~70 cm,宽0.7~0.8 cm,厚0.1~0.15 cm,残存1 530余字,内容主要是思孟学派、书籍和遗册[2]。现存年代最晚的简牍为甘肃凉州区和高台县古墓出土的“升平十三年”木牍,而最晚的竹简为长沙走马楼吴简,分别在公元369年和237年。其中走马楼吴简总数高达14万余枚,超过近代以来出土简牍的总和,被列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出土竹简中,上至春秋晚期,经战国、秦、汉至三国两晋,其时代是连续的,整整延续了近800 a。
关于竹简起源,不少专家也有推测。《战国楚竹简概述》一文说:“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字就象将若干条竹(木)简用两道组绳编缀成一页书之状;典字则象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陈炜湛根据商初“有册有典”、周初书祷文于简册、西周书王命于竹简、春秋普遍使用竹简、笔削更书之证和战国时人尚可见“先王”遗册等史料,指出“商周之际除甲骨文、金文之类刻或铸的文字外,当同时有竹简之类手写体的文字存在,其时之有简册,亦可论定。”至于为什么至今不见春秋之前一简?陈炜湛认为原因在于初时不知“汗简”故易朽蠢、秦始皇焚书和盗墓者不识竹简等,并相信在地下还沉睡着大量包括商周时期在内的简册[3]。陈梦家判断,西周的册命之制是先将王命写在简册上,当庭宣读后再铸到铜器上。王的左右有两史,一执简册、一读册命之文。所以,铜器上的王命就是预先写在简册上的册命的迻录。可见,西周铜器上文字的由上到下、从左向右,是据简册而来[4]。陈炜湛先生也推测,甲骨文中的大字是先书后刻,小字才直接刻上,所以甲骨文中,字越大刀笔味越小,而字越小,刀笔味越重[5]。
这里,不妨再从制作工艺上分析。相较于竹编,竹简的制作工艺更简单,仅有截筒、剖竹、刮削等工序,甚至无需启篾即可获得厚竹片,更不用编织。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代先民们就已开始用竹子制作竹器。湖南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已有7 400多年历史的炭化竹篾垫子,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陶器底部有竹编织物的印痕,杭州良渚文化遗址发掘了大量竹器纹饰的印纹陶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有200余件竹器实物,浙江诸暨沙塔村出土了保存尚好、花样繁多、工艺熟练、四五千年前的竹片编织物。由此可推测,在夏商周时期,以竹简作为书写材料从制作工艺来讲完全没有问题,可与甲骨、金文和石刻等书写材料同时并用;而且从不少出土竹编的完好性来看,理论上讲中华大地上应该保存着可考的夏商周竹简。
空间上看,王国维先生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2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前者为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发现了《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孔壁中经”;后者为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在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竹书纪年》等“汲冢竹书”。这些记载中出土的竹简,如今皆已无存。1952年,最早的竹简在长沙五里牌出土,共37件,形制大小不一,所载文字是殉葬物品的清单。此后不时有重大发现,总数量超过30万件。湖南、湖北、甘肃、内蒙、河南、江西、山东、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等16个省市自治区均有竹简出土,以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内蒙等省出土最多。一些没有出土竹简的省份并不一定就没有,如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中就出土了整治竹简用的刀和削,编组简册用的线锤等工具[6]。其中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除了上述的曾侯乙墓竹简、信阳楚简、走马楼吴简和长沙五里牌竹简外,还有中国首次发现秦代竹简的睡虎地秦简,一次性出土3.74万枚的里耶古城秦简,有《老子》和《子思子》等道家儒家著作的郭店楚墓竹简,再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涉及西汉早期律令、司法诉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内容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已经出土最早书籍的长台关竹简等。
功能上看,竹简涉及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的古书籍,也有早已佚失的古文献,涉及屯戍文档,也涉及法律、法规条文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书,为众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首先,书籍制度始于竹简。中国古代书籍制度一般分为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等3大类。由于甲骨刻辞、铜器铭文或者石刻碑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籍,简牍当之无愧成为最早的书籍,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的书籍制度。汉代,竹简作为书写材料达到了顶峰,集中体现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与竹简密切相关的文字就有册、篇、籍、页、篆、符、札、传、笏、等、策等10多个。其次,书写格式源自竹简。钱存训认为:毛笔书写的笔划大多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只能容单行书写的狭窄的简策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7]。再次,重大发现频出竹简。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年代,孔子的“韦编三绝”、《竹书纪年》等编年通史和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古代经典,正是因竹简得以保存和和传播。近100多a来,随着出土竹简的不断增多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批新的史料和作品被发现,不少历史疑案和悬案得到解决,大量传世文献得以考证,今后还会让世人惊喜不断。
2 书简之笔
这里讲的笔,是指以竹子为材料制作,用于书写的工具,包括竹质硬笔和竹管毛笔。提到笔的起源,自然会想到蒙恬造笔的故事。但是,考古发现表明,早在秦代之前竹管毛笔就已存在,蒙恬充其量只是改良罢了。不少学者根据出土商、周金文和甲骨文以及陶片上的书写款识,结合《尔雅·释器》《札记·曲礼》等记载,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笔”字显示右手握着一管饱濡墨汁或笔毛分散的笔,推断毛笔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中国发现最早,存世最古的实物毛笔,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与小竹筒、竹片等一起藏在竹笥内。笔全长21 cm,带套23.5 cm,直径0.4 cm,毛长2.5 cm,笔管与套均系竹制,笔头传系兔毫。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汉一尺约合23 cm,与出土发现的实物大致吻合。如包山楚墓内发现有一支放在竹筒中的毛笔,长22.3 cm,笔杆为竹质,上端用丝线捆扎,插入笔杆下端的孔眼内;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毛笔3支,长21.5 cm,径0.5 cm,竹竿上尖下粗,有笔套作插笔用,中间及两侧镂空;放马滩秦墓中发现毛笔及笔套共4件,笔套用2根竹管粘连而成,呈双筒套,毛笔插人套内,杆用竹制,锋长2.5 cm、入腔0.7 cm、杆长23 cm;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现竹管毛笔1支,笔长24.9 cm,笔杆上尖下粗,笔管制作精细;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出土毛笔1件,竹制,笔尾削尖,通长19.6 cm、直径0.4 cm,笔毛长1.2 cm;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毛笔4支,杆竹质,其中2支保存较好,通长24.5 cm,杆长22.3 cm、锋长2.2 cm;磨咀子东汉墓中出土毛笔2支,长21.9 cm,径0.6 cm,笔尖长1.6 cm,外覆褐色狼毫,笔杆竹制,前端扎丝线并髹漆。也就是说,从春秋战国到两汉的竹简时代,毛笔的大小、形制和材料等基本保持不变,细笔的特性与狭窄的竹简相适应。
两晋以后,竹简逐渐被纸张代替,毛笔也明显增粗,醮墨更多。日本正仓院就有10多支唐代毛笔,其长度与秦汉笔相仿,但笔杆和笔头都显著增粗,杆粗甚至达到了2 cm。制作笔杆的竹种也趋多样化和艺术化,如宣笔就有鸡毛竹管、湘妃竹管、水竹管等。梁元帝还对“文章赡丽者,以斑竹管书之”[8]。19世纪钢笔的普及,毛笔的功能也转向书法和绘画,成为“文房四宝”的首位。如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毛笔,仍然因为书画艺术的繁荣而光彩夺目,型制更趋多样。
与毛笔相对应的是硬笔。中国古代也有过硬笔,它的起源应该早于毛笔。在历代书论及文献中,常出现“竹梃”等说法,是区别于毛笔的一种竹质硬笔。宋人赵希鸽就曾说:“上古以竹梃点漆而书。”元·吾丘衍《三十五举》也说“上古无笔墨,以竹梃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古谓筆为聿,仓颉书从手持半竹,加畫为聿,秦谓不律”。不少学者也研究发现,一些史前陶器上的花纹,是用竹木所制的硬笔蘸以墨汁所画,而非毛笔。事实上,钱山漾出土的竹编已经告诉世人,早在4 400 a前,中国的剖篾和竹编技术就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试想,古人们在编织过程中,用竹条粘上颜料,在竹篾上做个记号,顺理成章。尽管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笔,却直接启发了竹质硬笔的诞生。接着,硬笔写多了容易软化起毛,人们发现这样反而能醮墨更多,进而为竹管毛笔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91年在敦煌的汉代高望燧遗址就出土了竹笔,敦煌市博物馆馆藏品介绍:该笔“通长11 cm、宽0.8 cm、厚0.3 cm……器物质料为竹质,人工制成扁平状,一端削平齐,一端刀削为尖状。器物表面打磨光滑。刀削尖状一端,有似漆非墨之迹,一面无迹。状似竹签”。李正宇称它为“汉代竹锥笔”,是目前中国已发现最早的古代硬笔。可喜的是,这种笔并未完全消失,傣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书写文字都是靠竹笔,纳西族的东巴经也以尖头竹笔书写而成,藏族不仅使用竹笔还称其为“拍牛”[9]。著名的《坡芽歌书》也是壮族人民用竹签蘸上仙人掌,用方块壮字来书写的,经久不变色。
3 简与竹纸
从纸张发明到完全替代竹简,两者伴随着长期的共生、互补和碰撞。纸张以其携带和书写方便流行于民间,而竹简以其传统和规范仍在官方使用。魏晋以后,竹简虽然逐步退出了书写历史舞台,却在碰撞中催生出了新的书写形式——竹纸。竹纸始于何时,学术界尚有争论,主要有晋、唐二说。本人持起源于晋代之说,并认为竹纸一定迟于以麻等为原料的纸。理由有三:其一是竹子原材料不足。自古以来,竹子始终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原材料。因气候等影响,竹子分布逐渐南移,北方竹林逐步减少,不可能再用竹子作原料造纸;其二官方缺乏动力。春秋以来,竹简始终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史料记载两汉还设有“司竹监”。官方也需要大量竹子用于制简,很难想象会再将竹子用于造纸;其三是技术不成熟。古代造纸是以相对较嫩的树皮等为原料,而成年竹子过于刚硬,嫩竹又要成竹孕笋繁衍后代,均难以应用。
竹简与竹纸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没有竹简,没有制简等竹产业的发达,特别是民众与官方对竹简的感情和熟知,竹子用于造纸并迅速占据半壁江山,也是无法想象的。纸始于何时,目前说法不一,有西汉前说、西汉说和东汉说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东汉到魏晋,竹简和纸并用。纸虽然以其廉价、便捷等优势迅速传播,在社会下层广泛使用。但,简帛也因受众的情感和心理,以及权威、经典和正统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特别受到官方的宠爱。以至于到了21世纪,仍有竹简和竹纸的踪迹。如道教法器中的笏、道情中的简板和宫观寺庙或民间用的签符等,仍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着竹简,而书画艺术用纸和民间迷信纸等则依然坚守着竹纸。“签”符,一种书写签语之签,用以占卜未来;“笏”,古时为臣属在帝王前奏对之用,其形体略曲而两端稍窄,以竹为材料制成;简板,由两根长竹片组成,用左手夹击发声,以伴奏“道情”。
首先,它促进了造纸技术和竹林培育的突破。竹纸起源于晋,却到宋代才有大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竹材质地坚硬,细胞组织紧密,化学组成复杂,纤维分离困难。宋代是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竹材的处理技术也取得突破,通过采伐嫩竹、长期浸漂、加工捶洗以及长时间高温蒸煮等造出了优质的竹纸,并以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为标志,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操作生产技术。同时,纸桨竹林经营也取得突破。嫩竹是造纸原料,更承担着孕笋和育竹的重任,经营不当,无异于杀鸡取卵。必须在嫩竹采伐与竹林培育上寻找到平衡点,竹林既可自然更新,又确保经济效益。
其次,它促进了竹纸的广泛使用。南宋以后,造纸工艺的突破,竹纸便以其低成本、高品质和种类多等优势得以蓬勃发展。一是种类多。宋代,福建的玉扣纸就用于印书,曾是上号的书法、族谱、寺庙用纸;富春竹纸名品竟出,有元书纸、京放纸、高白、海放、花笺等近20种;四川的夹江纸是清朝考场专用文闱卷纸,国画大师张大千赞其为"国之二宝"。二是用途广。无论朝廷、书画、印刷甚至民间,竹纸无所不在。明代朝廷大量用纸,司礼监设专造纸坊于南方山区生产竹纸,还搜派地方纸张入贡。明中叶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就是以竹纸为主要依托而繁荣兴盛。今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干道七年《史记集解索隐》、绍兴戊辰《毗庐大藏》,都是使用竹纸刻印而保存至今。《绵竹县志》也载:“竹纸之利,仰给者数万家犹不足,则印为书籍,制为桃符”。
再次,它促进了竹纸与书法的结合。《说文》:“篆,引书也。”《段注》:“引书者,引笔而着于竹帛也。因之李斯所作曰篆书,而谓史籀所作曰大籀,既又谓篆书曰小篆。”同时,隶书走向成熟,草隶也发展成了草书。“竹简书法”是近年兴起的一支流派,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别有一番古朴雅致。竹纸具有“滑,发墨,宣笔峰,舒之虽久,墨终不渝”的特点,是书画家练字作画和拓帖的佳纸。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明代的竹纸,长56.7 cm,宽42.1 cm,柔软,单薄,呈现半透明状。据鉴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米芾行书《珊瑚帖》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用竹纸书写的作品之,而王羲之《雨后帖》和王献之《中秋帖》用的也全都是竹纸。
4 制简之竹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王充《论衡·量知》),这是竹简制作最早最经典的论述。寥寥数语,却蕴含着大量信息:将竹子截断成竹筒,再把竹筒剖成竹条;根据不同用途,竹简有宽窄长短之别;竹简未经启篾而是直接用原条,竹青和竹黄的硬度使得竹简更加坚硬;不在乎竹简是否有竹节,加以刮削后即可书写,竹节结构的致密可防止竹简开裂。
制作竹简,首先是竹种。从上述信息看,竹简与竹子节间长短无关,而与竹子的胸径和壁厚有关。出土竹简的相关数据表明,竹简长度因其用途和重要性而异,竹简的宽度和厚度似乎并无规律可循。经典著作的竹简,长度常为80 cm、40 cm和27 cm;《南齐书》卷21曾记载,479年发现的简牍为“简广数分”;斯坦因发现的简牍,其宽度为0.8~4.6 cm不等,其中大多数是1 cm;居延出土之“兵物册”,每简宽1.3 cm;长沙出土的竹简,宽0.6~1.2 cm;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宽约0.6 cm、厚0.1~0.14 cm不等。大致说来,简宽不超过2 cm[10]。秦汉简牍一般长23 cm、宽1 cm、厚0.2~0.3 cm,秦汉制,一尺约相当于23 cm,因此,称之为“尺牍”,这是最为常见的形制,每简约写30~50个字,现在人们称书信为“尺牍”即由此而来[11]。
那么,假设竹简宽1.5 cm、厚0.15 cm,则竹子壁厚0.3 cm、需要多粗的竹子才能用于加工竹简呢?根据勾股定理,2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设内圆半径为x,外圆半径则为x+0.3,其等式为(x+0.15)2+(0.75)2=(x+0.3)2。解方程得出x=1.675,则竹子直径为(0.3+1.675)×2=3.95 cm。也就是说,理论上壁厚大于0.3 cm,该竹种的胸径应大于3.95 cm,才能用于制作竹简,竹壁越薄,所需竹子越粗。
遗憾的是,古代典籍中均未有竹简制作原料的记载。南北朝刘宋人戴凯之的《竹谱》,不仅为中国竹类第一部专谱,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专谱。书中记载的30多个竹种,均没有提及竹简,或许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竹简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原著遗失的另外30多个竹种里有记载,因为留存的竹种中有关竹编的记载也很少,而竹简与竹编制作方法相近,对竹种要求相同。
其次是竹林。《庄子·天下》有“其书五车”,史书记载孔子学问“汗牛充栋”、读《周易》“韦编三绝”,《汉书·刑法志》中秦始皇“日县石之一”,都说明当时竹简用量之大。那么,如此重要的基础性物资,其原料林又是怎样的呢?
在出土竹简的区域内,有关竹简时代竹林的记载不少,其中最完整的有3处:一是竹林规模。《史记·地理志》云,“秦地有鄠杜竹林”。“鄠”即鄠县(今户县),“杜”为原杜县。《史记·货殖列传》记:“渭川千亩竹……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西安府志》卷十八中引述《图书编》记曰“竹出咸宁、蓝田、鄠县、益侄渭南”。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司竹园在今(盩厔)县东一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元池,乃植之竹,是此故《史记》曰‘渭川千亩竹’,汉谓鄠杜竹林,故有司竹都尉。其圆周回百里,以供国用”,可见官方竹林在渭川分布之广。二是竹林用途。《唐六典》载,司竹监的职责是“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须帘笼筐荚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供尚食”。魏晋以后竹简退出了历史舞台,竹简用竹大幅减少,官办竹林大幅度缩减,监管职位降低,我认为这恰恰说明该竹林主要用于制作竹简。《旧唐书·李密传》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之说,说用尽陕西终南山的竹子制作竹简,也写不完隋炀帝的罪行。《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斩淇园之竹木塞决河”,《后汉书·邓寇列传》也有:寇恂“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三是竹林管理。《穆天子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乃树之竹,是曰竹林”。南朝《述异记》记载:“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诗‘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是也”。淇园位于太行山东南麓淇水两岸(今淇县),是春秋时卫国的官方竹木园[12]。据《魏书·官氏志》《新唐书·地理志和百官志》和《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司竹监》等记载,几乎历代都设有“司竹监”或“承”等官员,掌管着“在官竹林”。因此,我的判断是:至少在战国到两汉的800 a里,竹林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官方掌控着大片竹林,主要用于竹简等官方用竹所需,遇战争、洪水等灾难时用于制作弓箭和救灾等。
值得一提的是斑竹林。在竹简时代,斑竹(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 f.lacrima-deae)是典籍中有记载,名称沿用至今并且可考的竹种。斑竹亦称湘妃竹,《山海经》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门,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又《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晋代张华《博物志》:“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从此,斑竹成为湘妃神话的象征。目前,斑竹主要有桂竹(Ph.bambusoides)和淡竹(Ph.glauca)的2个竹种的变型,除了竹杆上有紫褐色斑点外,其它性状与原种几乎一样。桂竹与淡竹同为刚竹属,很多性状也相近,如竿高5~12 m、胸径2~5 cm,分布广、篾性好、材坚硬、笋可食,是优良的竹编、制箭、作楗等用材竹种,当然也是制简的理想原材料。前者以九嶷山斑竹林为代表,为桂竹的变型,是湘妃竹神话的直接发祥地。在我看来,与其说斑竹是湘夫人洒泪而成,不如说是含泪书写竹简更可信。目前已建立了九嶷山斑竹自然保护区,残存斑竹林面积仅有几百亩。后者则以河南博爱斑竹林为代表,为淡竹的变型。淇园残碑记载光武帝时期,安(今安阳,实即淇园)竹西移,这是淇园之竹移栽覃怀地域最早的记载,但未见于史书[13]。看来目前黄河流域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北半球纬度最高的博爱竹园,或许是淇园之竹的延伸和发展。
第三是“汗简”。战国前“何以至今不见一简?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初时制作不精,不知‘汗简’,故易朽蠢,不若钟鼎盘盂之可长留于世,此其一”[14]。诚然,竹材的最大缺陷是易腐易蛀,竹简防腐防蛀就显得尤为重要。“汗简”,竹简制作中的重要一环。《后汉书·吴裕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蠢,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也就是说,通过“汗简”可以将竹的水分烤干,以免蠢蚀。除此之外,从竹子采伐看,《礼记·月令》提到:“仲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汉代《崔宴》亦指出:“自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蠢”。说明在汉以前人们已认识到冬季采伐的竹材较为干燥坚实,不易腐蠢。而从涂漆技术看,生漆氧化结膜有很强的隔绝空气和水分的性能,楚墓中大量出土的竹胎漆器表明,涂饰竹材表面后具有防腐作用。当然,上漆后竹简不易书写且容易褪色,但是否可以对书写好的竹简进行涂漆呢?至少,在理论上是行之有效的。再从储藏技术看,春秋战国时期,白膏泥和炭是常用的防腐材料。马王堆出土的竹简、竹器,以及混杂在白膏泥中发现的嫩绿色的竹叶、青绿色的竹片、竹管和竹棍等,之所以2 000 a不腐,棺椁以木炭保护,并用白膏泥封固。同样,该技术也可用于竹简书籍的储藏。
- 竹子学报的其它文章
- 竹类植物开花生理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