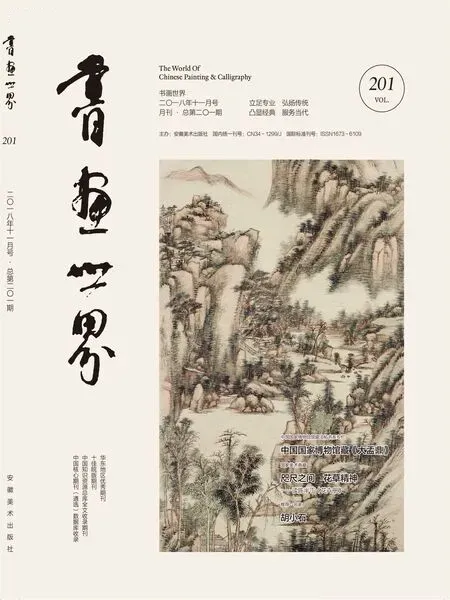连林人不觉 独树众乃奇—陈师曾书法研究
文_张孝玉
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内容提要:本文从陈师曾各体书法入手,以作品为实例,通过对陈师曾书法作品的分析,推导出他书法的师承与渊源,最后联系时代背景总结出陈师曾书法的成因,重新确认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陈师曾是近现代书画史上的一位全才,诗、书、画、印无不擅长,只不过他在绘画和治印上的成就更高,使得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陈师曾独擅此二艺。事实上,就书法而言,他也称得上是个中高手。本文将从陈师曾不受人重视的书法入手,以各体书迹为例,切实分析陈师曾的师学渊源和个性特征。
一、篆书
在陈师曾学习书法的历程中,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当推老师吴昌硕。陈师曾的学书路径与吴昌硕大体相似,两人在书法上的审美追求也颇为近似,只不过与吴昌硕以石鼓文打通各路书体不同,陈师曾书法的取法路径显然更广一些。
在诸多书体中,陈师曾于篆书用力最勤,这和他本身就是篆刻大家不无关系。陈师曾对待篆刻主张先练好篆书,认为“学刻印须先学篆书,书能佳,刻印自易”[1],因此他自身对篆书的学习和研究自然更加深入一些。陈师曾篆书取法颇广,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秦篆、汉篆,甚至秦诏版和权量文字,他都曾下过功夫。陈师曾认为篆书首推石鼓文,其次是《泰山》《琅琊》两处摩崖石刻,其他篆书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秦篆的法度。因此,陈师曾的篆书没有囿于秦篆固有的程式法度,而是由秦篆和石鼓文上溯到两周金文,以求深度寻求篆书中的“古意”,在“古意”中加以变化,力求“翻新”。他写石鼓文,与吴昌硕不同,陈师曾笔下的石鼓文,没有走吴昌硕苍劲老辣、精雄老丑的路子,而是以高古脱俗、肃穆严谨的面貌示人。[2]
篆书节临《毛公鼎》铭文四条屏共书篆字224字,文末自题“辛酉初秋陈师曾陈衡恪于安阳石室”,由此可以推断出这幅作品书于1921年,正是陈师曾去世前两年。从年龄以及书法风格来看,这幅作品是人书俱老的一件典型作品,不仅字形、章法等趋于稳定,整体气局也偏向于平稳,退去了年轻的火气,显得沉稳老辣。从体势上来看,《毛公鼎》铭文因为是随着鼎内的弧面展开的,因此其章法布局宽松疏朗,错落有致,相对更加灵活一些。在陈师曾的临本中,因为是在规整的乌丝格中,所以章法相对原作更加整饬,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布局都偏于平正。《毛公鼎》原文字形修长,陈师曾的临本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字形特征。在运笔方面,陈师曾纯用中锋,藏锋入纸,因此笔画起首处尤其浑圆饱满。如“女”“子”“孙”“命”等字,起首处几乎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墨点,而后转中锋裹毫运笔,刚劲挺拔。如“又”“方”等字的处理就充分体现出了线条的质感与张力,凡到了圆转处,并没有顺势而下,而是有意识地向反方向运笔,形成了一个自然的方折式运行轨迹,看似是一笔圆弧顺势而下,实际方正的细微转折已经蕴含在圆弧之间了。收笔处如“光”“不”“命”等字,虽然也并非是笔笔中锋,却能明显感觉到笔锋的停顿。这个停顿不是重落,而是毛笔写到收笔处时,笔上的墨色自然减少,呈现出些许干涸浅淡的墨色来,在这个基础上有一次轻微的驻笔。这种带有细微飞白效果的收笔,也就是所谓的“平出之法”,尽管不是以中锋收笔,却自然有一股雄浑老辣之感。
篆书五言对联《好学近乎知 即事多所次》,有自题款署“修直学兄雅鉴,弟衡恪”,钤盖“衡恪私印”白文印。与节临《毛公鼎》不同,虽然同是大篆,这副对联出自《石鼓文》。因此,从字形来看,较之《毛公鼎》的修长更趋于方正,下笔也更加雄浑、老辣,如“乎”“事”“所”等字的飞白已经相当明显了。而在运笔方面,这副对联“方折”的意味更强,笔画转折时尤其有意识地强调一种方折。比如“事”字最后一笔横画,以及“次”字的最后一撇一捺两笔,可以明显感受毛笔在运行到转折处时候的停顿,陈师曾是在有意识地刻画出这种方折的感觉。
二、隶书
陈师曾的隶书没有走一般书家标准汉隶的路子。他的隶书不求优美婉转,走的是清奇纵逸、高古脱俗的路子。与保存完好的汉碑相比,陈师曾更偏爱风雨侵蚀的摩崖刻石,《杨淮表记》《石门颂》《开通褒斜道》等,他都曾用功临摹过。这也自然形成了陈师曾隶书运笔饱满、下笔含敛、书风质朴雄强的特点。[3]
隶书七言联《暇豫威仪汉博士 原流礼乐鲁诸生》上款题“逸志仁兄大雅”,下款题“陈衡恪集刘熊碑”,钤盖“陈衡之印”白文印。《刘熊碑》,即《汉酸枣令刘熊碑》,相传为蔡邕所书,书风近似《史晨碑》《曹全碑》偏婉约遒丽的一路。原碑虽然在气局上稍嫌促狭,但字形结构端方,规矩整饬,笔画淳古秀逸,疏密相间,波挑明显,章法布局也属清爽疏朗一路。陈师曾此副对联虽然自称是集字联,但基本已经脱离了原碑的束缚,显现出明显的个人风格来。此副对联在保留原碑字形端庄方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突出了一个“雄”字,这是原碑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的一大特点。在书写过程中,陈师曾有意识地减弱了原碑中跌宕的波挑,使笔画更加凝重含敛。如“乐”“汉”“生”“博”“士”等字的横画,如果按照一般的写法,应该特地强调一下笔画的弹性,将波挑突出,但陈师曾反其道而行之,藏锋切笔入纸,调锋转中锋平稳运行,中间不做波动,至需要收笔处回锋,微微向上一挑,而后出锋收笔。这样的运笔方法,能最大限度地让线条平稳运行,线条会更加浑厚有力,与波挑明显的笔画相比,虽然飘逸略有不足,但凝重浑厚远胜。
原碑中的捺画尤其铦利,如“武”“进”“陵”“之”“欣”等字,笔画随着收笔的上挑,进而生发出一个更加锐利的出锋来,颇具装饰意味。但陈师曾处理得更加含敛。如“暇”“豫”“威”“仪”“流”等字的捺画,基本上多有意识地弱化了收笔处的出锋。“暇”字的捺画类似楷书写法,收笔处只做微微上提,“豫”字收笔稍有出锋,这种写法已经脱离了传统隶书的用笔,开始向颜体楷书靠拢。而“流”字则更为夸张,藏锋入笔,藏锋收笔,无论是起首还是收笔处,都以圆笔表现,绝不见笔锋。陈师曾这种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作品整体效果的考虑,这些字基本上处于对联靠上的位置,如果过分强调铦利的笔锋,则会显得更加跳脱,而对联上部跳脱所容易形成的问题就是整副对联重心不稳。相反,陈师曾故意让对联下部的横画出锋更加明显一些,这一部分势必会更加突出,整副对联在视觉上自然也就会更加稳定端庄。除了在笔画上一改原碑风格之外,陈师曾还在字形上下了一番功夫。《刘熊碑》原碑偏方正一路,横平竖直。如“日”“君”等字的“口”部,几乎都使用了内的用笔,使得单字字形在视觉上更加端方。而原碑中的“鲁”字,“田”部一笔横折画,几乎已经夸张成为一个内切的折笔,与后来楷书的笔画写法更为接近。但在陈师曾的集字中,他刻意将这些内的运笔转化成为外拓的运笔,使得单字在视觉上更加开张。同样是“鲁”字,陈师曾首先弱化了起首长撇画的收笔一挑,圆笔入,圆笔出,将原本可以夸张强调的一笔圆弧撇画,变成了刚劲挺直的一笔斜画,这就为整个字奠定了一个基调。后来无论是“田”部还是“日”部,笔画都趋于方正。而且与原碑带有楷书意味的转折相比,陈师曾在处理“田”部、“日”部时,有意识地将转折的笔画拆分成横画竖画两笔来写,使其首尾自然衔接,避免了原碑中出现的凸出圭角,单字也自然更显平直方正。
通览整副对联,可以发现字势起首含敛紧收,愈向下字势愈见开张,整副对联呈现出正梯形的章法布局。这样设计的目的,主要是在视觉上营造出稳定的效果来。如果起首几个字就自由伸展,到最后反倒紧缩,这样在视觉上对联就会向前倾斜,从而失去了稳定性。陈师曾这样设计,巧妙地规避了这一问题,使得七字对联在视觉上从容有度,端庄稳定。
三、楷书
陈师曾的楷书不落俗套,没有走传统观念中“尊唐抑魏”或是“尊魏抑唐”的路子,他的楷书自魏碑起步,先学隶书意味较重的《张黑女墓志》,再学隶书、楷书参半的《爨宝子碑》,至于《泰山经石峪摩崖》这类摩崖刻石作品也有所涉猎。他的楷书虽然以六朝碑版为主,但也兼取唐法,可以说陈师曾的楷书自初学时便已不俗。
《临泰山金刚经摩崖四条屏》是陈师曾一件楷书作品,节临《金刚经》部分内容,有个别缺字的情况,且前后段落也并非连贯,应该是有意安排所致。款署自题“君庇仁兄学长雅正,弟陈衡恪”,显然是赠送给友人精心书写的作品。《泰山金刚经》是南北朝时期的摩崖刻石,属于魏碑中相当优秀的一件书法作品。原迹单字一尺见方,笔法并非成熟楷书的标准形制,而是隶书楷书参半,且颇具篆书笔意。而在陈师曾的临本中,他保留了原作中浑圆运笔,几乎每个字每一笔都是藏锋入纸,收笔处也能明显感觉到有意识的停顿。这种驻笔实际上是一种首尾呼应。而在原作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纸上书写这种载体形式,以及方格条屏所应具有的矩度,陈师曾有意识地对原作进行了“楷书化”的改良。
所谓“楷书化”,是指在陈师曾的临本中,实际上有意识地突出强调了原作中的楷书意味,原作字形偏方扁,更接近隶书。但陈师曾的临本因为有乌丝方格,所以他将字形进一步拉长,变方扁为方正,甚至如“义”“三”“多”等字的字形已经偏于颀长,这种纵长的字形,实际上已经是成熟楷书的结体方法了。字形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笔画的变化。以原作中“持”“时”两字为例,因为字形偏于方扁,所以部分笔画就需要压缩长度。比如这两个字的“寸”部,原本半包围结构的偏旁,被转化成了左右结构,“寸”部的点画已经被安排到了结构之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笔画,而横画也因为偏旁结构的变化而缩短,为的是给点画让步,留出空间。但陈师曾的临本因为字形发生了变化,笔画结构自然也随之变化,如“应”“得”等字的横画,如果按照原作的写法应该缩短,但陈师曾有意识地将这几笔横画拉长,甚至故意谋求一种长度的统一。这种改变离不开方正字形的支持,只有当笔画不需要为方扁的字形服务时,才有延展的可能。再比如起首的“是”字,原作中的“是”字不仅趋于方扁,而且笔画结构也较为简单,“日”部偏圆,最后一笔捺画直接顺势下弧,收笔圆浑。但陈师曾的“是”字更强调了笔画的质量,也更向楷书靠拢,原本偏圆的“日”部被他改写为方折写法,转折处虽然不见圭角,却能明显感觉到笔画更加硬朗。
最后一笔捺画显然也是顺势而下,但捺画的起笔明显借助了前一笔短撇画,似乎是撇画写完后顺着毛笔自身的弹性直接生发出了一笔捺画。这笔捺画并不像原作那样下弧,而是由一笔上弧翻转而来,这种笔画结构已经是楷书的写法了。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捺画的收笔,原作中的藏锋收笔被转变为尖锋出笔,这种出笔不同于隶书的“雁尾”,而是顺势而为。因此,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陈师曾虽然临的是魏碑,但并不为原碑所束缚。他对于原碑进行的“楷书化”改良,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
四、行书
陈师曾的行书取法王铎,进而能上溯到“大王”体系之中。此外,他也能兼收并蓄,除王铎外还学李邕、黄庭坚等人。只不过陈师曾深厚的篆书功底,决定了他无法走轻灵飘逸一路的行书风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黄庭坚那种长枪大戟式的笔画结构自然也停留在了取神而遗貌的阶段。
行书《黄山谷诗》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根据“癸亥夏日,陈衡恪”的自题可以推断出这幅作品书于陈师曾去世的那一年夏天。也就是说,这幅作品完成后的两三个月内,陈师曾就去世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相对完整的“绝笔”行书。从整体气局来看,或许是由于已近暮年,整幅作品于豪放的外观下更见内在的含敛,高堂大轴自然气脉贯通。但这幅作品并没有像其他学王铎的作品那样行轴心线剧烈摆动,而是通过单字简单的位移来调整单字的重心,使得每一行以几个字为一个小的单位进行摆动。如第一行“市”字之后的“人”字明显向左偏移重心,“只菜蔬”三字皆顺势而下,而“水”字又因为“蔬”字最后一笔的牵丝连线而再次向右偏移重心,此后四字再次顺势而下。这就自然形成了三组不同位置的位移,一行字由于单字重心的偏移而被分成了三组,通过小组的位移而形成了行的位移,也自然就生成了行轴心线的轻微摆动。
此幅作品单字在外形上有“大王”的痕迹,但笔画较为硬朗,起笔偏方,字与字之间较为独立,没有明显的连缀关系。而如“水”“远”“仰”“间”等字,虽然有侧锋运笔,但线条缺少细微的变化,且运笔过程轨迹更加平直。因此这幅作品在用笔上应该更接近李邕。虽然在字形结构上有黄庭坚中宫收敛的痕迹,但总体来看,单字字形修长,稍有欹侧的痕迹,甚至有如第三行“临”字那样明显摇摆的字形结构。因此可以初步断定,陈师曾的行书应该更向王字一路靠拢。
此外,陈师曾也有草书作品和章草作品存世,只不过数量不多,他的草书取法黄慎,章草用笔有时也能融入今草或行草书之中,但总体而论,此两者的成就不及其他书体。
总结
陈师曾的书法,真行草隶无所不能,取法高古深远,不落一般的窠臼。篆书从石鼓文出,隶书学摩崖石刻更多,楷书、行书则多有六朝碑版的痕迹。陈师曾的学生俞剑华曾将陈师曾与吴昌硕对比,从对于毛笔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二人的差异。吴昌硕惯用羊毫笔,用笔软中见硬,绵里藏针;而陈师曾惯用狼毫笔,多用中锋,擅长寓柔于刚,运笔如折钗股。[4]
遗憾的是,后世学者提起陈师曾多会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而非一个出色的书法家。殊不知,在名家高手林立的时代,陈师曾以其独有的书法风格、高古的书法品位,仍可称得上是一代书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