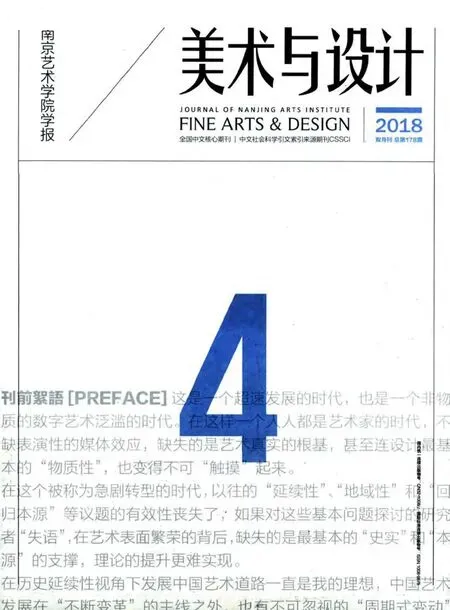“第四基座”
——公共艺术的当代样本
季 峰(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第四基座”位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西北角,原计划安放国王威廉四世的骑马雕像。1841年,基座完工后因为经费问题及高层意见不统一导致雕塑计划搁浅,闲置了150年。1994年,时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RSA)主席普鲁利斯写信给《伦敦标准晚报》,建议对这一基座进行改造。1998年,皇家艺术协会开始策划。1999年,皇家艺术协会委托卡斯雕塑协会(Cass Sculpture Foundation)在基座上展示雕塑作品。1999年至2001年,卡斯雕塑协会选择的三件当代雕塑作品在基座上次第展出并获得了正面的评价,使得第四基座正式成为一个项目得以继续。RSA为此通过了第四基座“临时艺术作品滚动”方案,确定了基座作品的展示内容和形式。①2003年,时任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司通斯(Antony Stones)在南京大学举办讲座,向国内艺术界介绍了“第四基座”的项目情况。近年,国内也陆续有相关的文章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具体项目内容可登陆伦敦市政府网站“第四基座”项目栏网址查询:https://www.london.gov.uk/what-we-do/arts-and-culture/current-culture-projects/whats-fourth-plinth-now2003年,特拉法加广场及第四基座的所有权转交给伦敦市政府。2005年,伦敦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十位专家组成的“第四基座委员会”(The Fourth Plinth Board)对“第四基座”项目的运营进行指导和监督。1999年至2017年近二十年间,一共有11件当代艺术作品在第四基座上得到了展示。未来数年的作品也已经通过遴选、公示,即将逐年呈现。
“第四基座”作为一件正在进行中的公共艺术形式,在特拉法加广场这样一个世界性窗口的位置,越来越吸引了艺术理论界的目光。在对公共艺术的研究热潮中,公共艺术所呈现出的精英艺术与大众文化、艺术与社会、当代与传统、民主与专制的矛盾统一是艺术学界乃至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第四基座”项目的存在为公共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份当代样本。
一
当代艺术艺术家们的作品大多处于需要解读的非对话状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与公共场域所应具备的亲民特征都存在着矛盾。当代艺术对于艺术和社会的反思、批判甚至是颠覆和嘲弄也使得当代艺术在公众群体的话语中被小心处置。眼花缭乱的原创性特征取代了时代先锋性特征,公众对于当代艺术的批判性接受往往停留于博物馆、美术馆的界限内。而公共艺术不同,公共艺术从诞生之初就具备服务性特征②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规模服务于市政建设的“百分比计划”被公认为公共艺术兴起的源头。,用理性机制消减了当代艺术的批判性;用场域限制了艺术呈现的方式。当代艺术所需要的各种自由创作姿态以及主题内容的无禁忌很难通过遴选方和建设方的审核。权力成了艺术品诞生的砝码,许多当代艺术家对审核制的公共艺术体系望而却步。
“第四基座”同样不具备宽泛的创作条件,遴选机制及专家委员会的约束注定了其入选作品的不自由形态。这种不自由与个体创作的自由方式格格不入,这使得也正是公共艺术不同于个体艺术创作的重要分水岭。
查看艺术家的身份时我们不难发现,入选“第四基座”的艺术家大多是获得广泛承认的成功艺术家:如第一位获得“透纳奖”的女性艺术家蕾切尔·怀特里德(Rechel Whiteread)(1993年),她为第四基座创作了作品《纪念碑》(2001年);托马斯·舒特(Thomas Schutte),曾在2005年获得过威尼斯双年展“最佳艺术家金狮奖”,是第一位为第四基座创作作品的非英国籍(德国)艺术家,他创作了2007年的基座作品《酒店模型》。2009年作品《一个和其他》的作者安东尼·格姆雷(Antony Gormler)也是“透纳奖”的得主(1994年)。2016年作品《非常好》作者大卫·舍里利(David Shrigley)曾获得过2013年“透纳奖”提名。
第四基座的委员会由来自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的专业领域涵盖设计、当代艺术、城市规划、博物馆等。群策的结果保证了艺术的品位,当然也排除了激进的作品。第四基座创立的遴选和公示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乌合之众”的一种妥协。成功艺术家可以保证作品的品位,在没有既定价值评价的约束前提下,身份无疑是最好的鉴定标准。
另一方面,第四基座的平台向公众的推荐能力获得了凸显,马克·沃林格(Mark Wallinger)即通过“第四基座”的作品展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瞧!这个人》是第四基座的第一件展示作品(1999年),描绘了基督被判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和政治共鸣,成为马克·沃林格代表作品,并一举获得2007年“透纳奖”。
从“第四基座”作品涉及的命题来看,作品内容涵盖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种族主义的态度、对商品社会的批判、对战争的批判、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等方面,体现了艺术工作者对多样化社会命题以及地域文化的普遍关切,也代表性地说明了公共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共生关系。泰瑞·史密斯在2005年11月第45届卡内基国际双年展的一场名为“现代性和当代性:20世纪后艺术和文化的二律背反”的会上指出,当代艺术的三种潮流:一、现代主义的当代延续;二、后殖民的批评视角,探索本土与全球化的种种问题;三、探索时间、空间、社群和情感的多变性,探索人类与特殊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关系。[1]第四基座上的11件作品都可以印证这三种潮流的存在。如2009年的作品《一个又一个》,作者对于这一作品有如下的解读:
《一个又一个》(2009年)有幸将这长4.3米、宽l.5米的特权平台(第四基座)变得更加大众化。普通百姓被邀清作为活人雕像登上第四基座进行自我展示,每个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24小时不管刮风下雨、阳光明媚或是白昼黑夜从不间断,共持续了100天。这样,共有2400个参与者在2400个小时内成为“活着的”雕塑——一座纪念碑。恐怖之处在于,参与的人被分布在广场的不同地方,作为物体与空间、自然世界的关系,暴露在公众面前。这对观众来说同样也是一场庆祝。这种被分享的空间上的自我展示替代了艺术客体,更展出当代社会的某种群体。他们通过自我展示,颠覆了传统的艺术对象,引导人类思考自身价值、希望以及恐惧。[2]72
从上文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广场客体的利用,将基座上的表演者与观察者之间的状态影射到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而另一件作品《瓶中的纳尔逊战舰》,直接与特拉法加广场的历史相对,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所试图表达的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于本土文化以及曾经的战争行为的反思。
第四基座限制了作品的呈现方式,英格兰人舍弃了曾经崇拜的偶像,空荡荡的底座更像是一个托盘。没有神明(其他三个底座上矗立的是人类的精英、民族的英雄),被选中的作品更像是为观众呈上的视觉大餐。“第四基座委员会”的专家们希望的是轻逸、幽默的方案,“为伦敦营造丰富的视觉文化,更重要的为了让大众参与到对于公共空间内的当代艺术作品的讨论中来。”[3]已呈现的11件作品中,除了第一件作品《瞧!这个人》描绘了耶稣受难的悲苦场景外,其他作品几乎都能验证委员会的企图。2016年9月至2017年的作品《非常好》,是一个高达7米的翘着的大拇指。伦敦市长在其揭幕式上说:“《非常好》的积极性和幽默性真正蕴藏了伦敦的精神,也代表了积极性和‘我们是最棒的’这层自信”[4]。
第四基座的艺术家们在有限的场域限制里,作品的形式呈现了尽可能的多样化。当然,除了《一个又一个》是行为表演外,其他作品大多是架上雕塑的形式。第四基座的底座属性从另一个角度提醒,这是一场有限定的游戏,形式上同样是不自由的。
二
公共领域诞生的初期便具有批判性的特征,与政府公平形成了对立,从文艺和艺术作品的批评扩大为政治和经济的讨论。安东尼·格姆雷曾说:“冬宫博物馆是权力物品的汇聚地”[2],“艺术需要人人参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人类的创造力将怎样发展,以及人类的智力、感受力和意志力将如何影响地球生命的进化,我们能否做到,又将如何做到。”[2]41
“第四基座”是对非永久性公共艺术的一种尝试,一种平台,产生了规范化的遴选机制。基座本身与宣传媒体共同构造了一种公共艺术的样本,从另一个层面上这种结构模式是当下西方社会对当代艺术及公共艺术的一个“绥靖政策”的写照。有选择性的推送是一种官方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第四基座不仅仅是场域的限定、价值的界定同时也包含对于形式的限定。很多非架上的当代艺术形式无法在这个小小的基座上获得展示的机会,而这些艺术的表现形式可能更为激进,更富有挑战性。在公共艺术的产生过程中,文化精英与官方体制空前的合作。通过艺术介入的空间,当代艺术完成了从精英艺术到大众艺术,从文化参与到文化策略的转变。这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符号学的换框。
在当代艺术介入公共艺术时,公共艺术以公众的名义将其拉入囚笼,两者从本质上是对抗的。由于道德法律、社会公约甚至传统审美认知的底线所制约,当代艺术在公共艺术的形式上无法表现出它的无约束的自由状态,这是公共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无法僭越的鸿沟。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直接形成了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现代艺术家不再为委托人服务,由一种艺术品的委托定制的消费模式向艺术品商品属性模式转化。艺术家可以成为商品,可以完全为自己心中所愿创作作品。这种艺术品交易模式的转换背后是形成单一群体趣味的资本促成的。资本消费阶层故意花高价消费的艺术品,认定自己的品位所在,以拉开非此类艺术品的距离,构成低一层次的另一群体欣赏品位。丹托在《艺术界》一文中指出,“艺术界”不是艺术作品中的审美世界,而是环绕在艺术作品之外的理论氛围。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构成了对艺术作品的解释。葛瑞斯伍德的“文化菱形理论”指出了艺术界构成的重要四个元素:艺术产品、艺术创作者、艺术消费者和更广阔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增加了艺术分配者的角色,艺术分配者即菱形四元素之间的中介。①关于艺术概念的这部分表述转引自:从“艺术”到“艺术界”——艺术的赋魅与祛魅,彭锋,文艺研究,2016年第5期,第5-13页当当代性的合法性得到质疑,这种危机被公共意识形态所媾和重生,艺术家从一开始被遴选,被重新分配,被纳入公共事业。艺术家的态度上升为一种公众态度,被政府所认可,政府与公众达到空前的一致性,公共艺术也可以呈现出一种“被许可的批判性”。
哈贝马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听命于任何一方,保持不偏不倚。如果把公共艺术的创作者艺术家转换成知识分子,就会发现,艺术家在公共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在各级艺术成为公共艺术的过程中,处处会受到掣肘。在获得暂时的权力能够影响他人的过程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正在消解,往往成为政府的“帮凶”、代言人或者资助者的宠物。哈贝马斯呼吁知识分子不能犬儒,而公共艺术家们却命中注定了犬儒的属性。公共艺术被选择被利用,进入政府话语权的范围,获得被消减来的自由权利。当最终呈现的作品与公众目光相遇时,公共艺术作品需要立场正确、向善且积极,代表着群体的共同愿望和祈求,符合审美经验。然而这些并不能表达个性艺术家的全部思想性内涵,最终的作品也往往会被富有批判精神的独立艺术家横眉冷对。
哈贝马斯曾经对于语言的属性有精彩的描述,他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媒介,人们关注的是表达客体与事实的命题的逻辑形式。语言被遮蔽在意义之后,是打开表象世界的大门。对于公共艺术而言,形式是对话的媒介,是公众与艺术家之间的交往。但是相比较于语言的直白和使用频率,艺术形式往往就是内容或者形式太过于激烈导致内容的被忽视。就像哲学家将研究对象转向语言和符号,当代艺术评论家有时也在作品语言构成的方式上纠缠不休。
资助制度注定了公共艺术需要对群体意见,甚至是与政府长官意志的妥协,公共艺术的生死取决于权力社会的权力属性。但无论是经济的或是政治的霸权,都会导致公共艺术的犬儒姿态。公共艺术必须是和颜悦色的、谦恭的聆听者,任由全体在自己的作品前指手画脚。公共艺术被从特定的领域撤销,意味着对抗的失败,塞纳的《倾斜的弧》足以说明这种对抗的惨烈下场。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换言之,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从欧洲古典公共领域,经历了中世纪的贵族阶层的代表性公共领域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开放程度,是伴随着交往权利和文化权利的发展而发展的。普通大众逐渐获得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但在19世纪后,公共领域又逐渐沦为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公共场所虽然被操控,但仍然表现出通过交往理性注入公民情感的人文情怀,以及对审美经验的共鸣。个人的审美的经验往往被全体的集体的审美经验所取代。公共艺术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的代表,不如说是一种群体的消费,体现的共性的文化需求、地域的文化特质以及个体的创造能力。每个社会的参与者都能获得消费的快感和文化的认同感。
批判性应该是公共文化所具有的属性,有学者因为中国古代缺乏个人权利和批判精神,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不具有公共文化领域的特征。公共艺术存在的场域是广泛参与的开放性平台,与当代艺术的独立性不同。公共艺术之所以称为公共艺术,除了公共开放的公共领域,更多地表现为艺术的非精英语态。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认为以资本为统治的社会机制,造成了对真理的遮蔽与阻碍。对话而不是单向诉说,参与创作而非简单的艺术创作的排他性,这些都证明公共艺术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方式。孙振华在谈及公共艺术概念时认为,城雕与公共艺术是两个概念,公共艺术更侧重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与公众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系。
三
当代美学家在追问艺术的创作是为哲学的意义还是社会学的意义。当代艺术的焦虑表现为艺术本体的被消解,架上艺术技法被放弃,艺术被玄学所打动,艺术不再是一幅画或一件雕塑,对象更不是艺术创作的主旨。当杜尚把小便池搬进展厅,观念便彻底摆脱了艺术本体的束缚成为当代艺术的主要内容。观点等于艺术本身,观念的原创意识把艺术家逼得走投无路,反身投入到哲学的怀抱。黑格尔声称的艺术的消亡正基于此。从另一方面,博伊斯的出现把艺术家引向另外一个征途,从杜尚的出世姿态转向入世。“社会雕塑”或者“雕塑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借用艺术改造社会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沿着这条路奋力前行。
当代艺术家们从艺术家的身份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参与到对于真理的判断和时代趣味的审定这样的全球性的话语中来。但是,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艺术与生活以及大众媒介的喧嚣,机械复制时代的全面胜利,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性冲突从来没停止过。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主体的焦虑,韵味的没落,以及文化上的冲突。
我相信艺术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冶炼场,不受任何控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检测自身和我们的需求、欲望以及梦想。它把我们从博物馆制度化和市场商业化的双重影响中释放出来,同时也能认识到这两者的重要性,前者提供了一个评估的基础,而后者则作为补给和滋养。[2]77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艺术是在顺从的艺术和反艺术之间进行的第三条路。艺术的终结,代表着个体艺术的即将终结,当代艺术家们呈现出明确的反艺术姿态。此间,精英艺术与群体意识的交媾、肇生,使艺术个体又有了可言说的状态。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组合,先锋派的冒险与乌合之众的妥协。当代艺术拒绝商品化,拒绝庸俗,拒绝与社会的同谋,转换为被限定在体制内的自由。一切都在理性的框架里运行。从第四基座我们也不难看出,某些形式上的小自由是“披着韵味的薄纱”,掩饰的题材和内容的不自由,艺术家选择了意识形态的话语,表面上成了大众的代言人,骨子里是被政府利用使用这种小自由整合了社会。
公共艺术诞生之初由于服务性的宗旨及服务性的成果,也曾被意识形态的争执搅得痛苦不堪。艺术家应该服务于整个社会,应该继续为有教养的人和眼光独到的赞助者服务,或者应该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一起对抗资本主义。肯尼迪说,因为艺术建立了基本的人类真理,这真理必然要被用作我们判断的试金石。但是,当艺术遇到普遍性危机的时候,真理仍在被追问的状态。我们无法利用这样的试金石。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呈现为公共艺术,让它被追问、被质疑、被思考、被探求,这也许就是第四基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