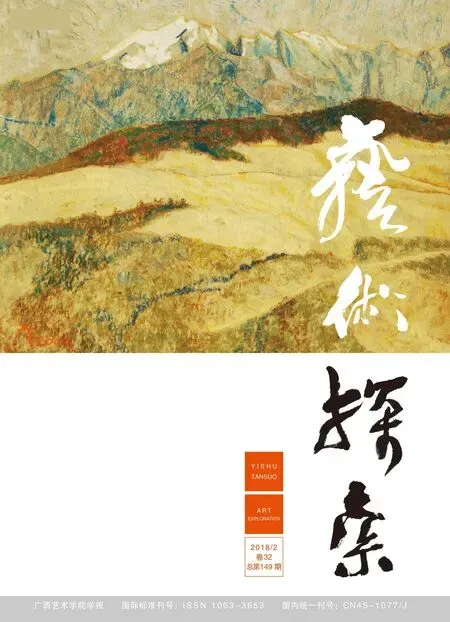流徙缅甸:跨文化视域中的赵德胤电影
陈 晓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缅甸的电影事业起步较早,曾跻身整个东南亚电影前列,20世纪60年代以后,缅甸的电影业每况愈下,政治把控和时局动荡成为其电影业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在大动乱的1988年,(缅甸)国内一部电影也没有生产,1989年也只拍了17部,1990年代前期,平均每年仅能生产15部左右”[1]57。进入21世纪,尤其在缅甸国内形势相对缓和之后,缅甸的电影业趋于回暖,但整体观之,缅甸电影在人才技术、影片产量及国际声誉等方面均已落后于同时期的泰国、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然而,导演赵德胤拍摄的缅甸题材电影,为缅甸电影业的枯水期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让国际观众的视线重新聚焦于缅甸这块神秘的土地上。
赵德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缅甸导演,①根据赵德胤的自述,赵德胤1982年出生于缅甸,16岁前往中国台湾,于2011年取得台湾户籍身份。他的电影也并非纯粹的缅甸本土电影,而在他的缅甸题材作品中,观众看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缅甸平民社会,她既不是二战时期湿热且毫无生命力的战场,也不是民主政治斗争的戏剧化舞台,而是作为一块流徙之地,沉默不语地旁观着平凡庶民的流离与迁徙。赵德胤本身作为缅甸华人以及跨文化电影实践的亲历者,他在电影中呈现了怎样的缅甸世情?他为何选用此种表达方式?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因素是什么?这一整套电影语法又将给东南亚(题材)电影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底层叙事:缅甸题材的跨地想象
赵德胤出生于缅甸底层社会,浸染于多元文化背景之中,因此他对缅甸题材的表述始终带有跨地想象的成分。这种“跨地性”在其电影叙事的表达中直接指向了缅甸底层民众在地理空间中的流转和迁移,空间环境的转变进而引发了人物心理不同面向的变化,从而引导人物走向对未来道路的不同选择。此外,在资金及设备有限的情况下,用固定镜头和长镜头等电影修辞方式,营造出逼真的“纪实感”,成为赵德胤表现完整空间和人物状态的最佳手段。
除处女作《白鸽》之外,赵德胤的“归乡三部曲”(《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冰毒》)、新作《再见瓦城》、两部纪录片(《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及一系列短片,①赵德胤的短片包括《猜猜我是谁》《摩托车夫》《家乡来的人》《家书》《华新街纪事》《南方来信》《海上皇宫》等。均没有离开缅甸题材,影片所聚焦的对象也主要以身处异地的缅甸人(腊戌地区的缅甸华人)为主。电影中缅甸华人流转的空间主要包括缅甸与中国(含中国台湾)、缅甸与泰国等,同时提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越南。其中,语言和饮食成为缅甸华人异地流转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语言来说,缅甸华人多使用汉语,包括普通话(国语)及方言(腊戌地区华人的口语接近中国云南省方言),夹杂使用缅语和英语词汇。语言是异乡人与源生地的根本连结,甚至被当成身份选择和认证的标志。短片《猜猜我是谁》讲述了一对身处台湾的缅甸青年男女,在抢劫他人的过程中,就是否回缅甸的问题产生了分歧,这一桥段可以视为赵德胤后作《再见瓦城》的先导。男人让女人跟他回缅甸,女人却想留在台湾,男人在对话过程中始终使用缅语,甚至逼迫女人用缅语回话,女人却一再坚持使用汉语。画面中的一道门框分隔了这对男女,疏远的距离感来自两人使用语言的差异,同时又来自两人对未来的不同向往。语言作用于人的听觉感官,食物则作用于味觉感官,短片《家书》中的主人公提到“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跑到华新街吃稀豆粉”,继而又出现了一整段关于稀豆粉和缅式奶茶的语言描述。除此之外,影片中与缅甸相关的视觉元素,如摩托车、隆基(传统服饰)、特纳卡(用来涂面的粉末)等也随处可见。劳拉·马科斯(Laura U.Marks)在《电影皮肤:跨文化、涉身和感官》一书提到视觉、器物、触觉和各类感官都牵涉到深层次的文化记忆问题,她认为:“对于跨文化的艺术家而言,电影不仅作为一块银幕,而是作为一层带给观众接触记忆的物质形式的薄膜”[2]243。赵德胤也正是通过电影这层薄膜,相对准确地传递出其本身对于出生地缅甸的独特文化记忆,这份记忆不仅包含着这片土地的空间地理景观,同时也包含着深入生活各个侧面的点滴细节。
与作为中产阶级观光客的猎奇心态不同,赵德胤电影中的人物在地域迁徙过程中,时刻伴随着文化心理上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的复杂性不仅来自于异域符号、日常语言、饮食习惯、文化风俗的普遍冲击,还关联到对于个体归属以及身份认同的再思考。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缅甸底层民众的心理转变涵盖了两个方面:一是处于全球化商品经济之下的选择;二是对于安身立命之所的选择。安土重迁思想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亚洲地区的传统文化心理,然而商品经济却迫使以务农为生的民众流向异地,以争取“生存”的权利。《冰毒》的叙事起点恰恰在于小农经济破产后,男主角不得不用家里的黄牛作为抵押,借钱做起了摩托车接客的生意。女主角三妹则为了远在中国四川的孩子,铤而走险开始了贩毒的买卖。影片末尾那只被宰杀的黄牛,似乎寓意了底层民众如黄牛般沉默失语,始终无法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都以挖玉矿的工人为刻画对象,矿工们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靠着微薄的收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尽管同处缅甸,但矿区并不是工人们的家,高强度的劳作和精神上的空虚让他们更容易沾染毒品。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生存权至上的底层社会,道德感和法律意识几乎成为奢侈品,生存的原始本能压倒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规则。相比之下,偷渡出国的缅甸人不仅面临着急迫的生存问题,更要直面身份归属问题。《再见瓦城》以一对相爱的男女为视角,他们皆是偷渡到曼谷打工的缅甸华人,女主角莲青的梦想是以泰国为跳板,最终前往台湾生活;男主角阿国的愿望则是赚够一百万泰铢后就带着莲青回到缅甸生活。对梦想朴素的坚持,让莲青为了泰国的身份证件,不惜与阿国决裂,甚至出卖肉体、冒领身份,也让阿国最终杀死莲青,随后又葬送了自身。麦克卢汉(Mcluhan)认为“地球村”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任何新的媒介,由于它的加速作用,都会扰乱整个社区的生活和投资”[3]141。然而,在电子媒介引导的“重新部落化”的趋势下,赵德胤的电影彰显了东南亚地区存在的断裂、不平衡与非连续性。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摩托车、汽车、船只等交通工具与不断延伸的道路相映成趣,人物面无表情地坐在运输工具上,被动地接受着被运输被转移的命运,流动与迁移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这种流动性并非全然指向光明的未来,反而潜藏着深重的危机感和悲剧性。
同是表现迁移人群的生存状态,香港电影《踏血寻梅》选择了极具形式感的蒙太奇表现手法,而赵德胤则选择了朴拙的长镜头表达方式。赵德胤对于长镜头的偏爱早在《摩托车夫》里就有所体现,到了“归乡三部曲”,基于长镜头和固定镜头的电影修辞特色更加突出。《再见瓦城》在保留了长镜头的基础上,其影片整体的流畅度和完成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影片中阿国在与莲青发生争执之后,赤裸着上身,将木材扔进熊熊燃烧的窑炉,镜头慢慢拉远,他机械般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内心的创伤通过这种方式宣泄而出。有台湾学者以“数位写实主义”(DV Realism)和“声音写实主义”来定位赵德胤的“归乡三部曲”[4]147-184,然而“写实主义”的论断或许适用于“归乡三部曲”,却无法笼统概括赵德胤的全部作品。另有学者认为:“赵的这部处女长片(《归来的人》)既存在于发端于21世纪初东亚以及东南亚以数码摄像机即DV推动的独立电影运动之中,却又因为导演独特的离散背景而游离在任何浪潮之外。”[5]67在某种层面上,赵德胤的电影已经超越了纯粹写实的范畴,《再见瓦城》里买走莲青初夜的嫖客以蜥蜴的形象现身,吐着舌头贪婪地舔舐莲青的肉体。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尝试显然难以归入写实主义的框架,写实主义或许仅仅是赵德胤在经费有限、技术贫乏状态下的必然选择。如果将超现实与写实分别置于两个极点,只能说赵德胤的电影偏向于写实,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等同于写实或将持续写实。与此相对,赵德胤的电影审美倾向需要被关联到最质朴的电影独立表达本质之上,其影片所关注的题材和群体使得“纪实感”始终作为一种电影风格,长镜头和固定镜头的运用,其一为了表达时空的完整性;其二为了连续记录人物在完整时空中的生存状态;其三则是用以将人物置于被动情态之下,表达等待的漫长及时间的纵深感。总体观之,赵德胤的电影创作目前而言处于平稳上升的状态,从“归乡三部曲”到《再见瓦城》,赵德胤在保持纪实基调的前提下,对电影语言的掌控愈发自如,对缅甸题材的运用愈发成熟,其电影本身的观赏性也逐步提高。
二、异乡人:跨文化作者身份的建构
赵德胤作为“异乡人”的特殊身份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电影题材和创作方式的选择,其特殊身份的建构一方面来自赵德胤本人的缅甸生活经验,这一经验同时带有原生的表达冲动和强烈的私人叙事意味;另一方面来自于侯孝贤等台湾导演对赵德胤电影思维的塑造,这种塑造还涉及世界电影语言的习得与内化。赵德胤的创作实践为跨文化导演身份的建立提供了鲜活的范例,对于电影的“作者理论”而言,可谓是一次新的尝试与补充。
“据估计,1999年华人占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即瓦城)人口的30%”[6]28,缅甸的华人群体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始终没能得到与原住民平等的权利,政治上的失语难以保障华人经济事业的持续发展,于是华人在缅甸包括整个东南亚区域的地位都显得尴尬且失衡。赵德胤本人隐秘的家族史,似乎正是缅甸普通华人家庭变迁的一个缩影。赵德胤家族的历史首先是迁徙的历史,他祖籍南京,祖辈从南京迁徙到云南之后,又因战乱而进入缅甸。在赵德胤这一代年轻人身上,这种流徙的状态也未发生改变,赵德胤的大哥在缅甸矿区工作,大姐和二哥在泰国打工,而他自己则辗转于缅甸和中国台湾两地。家庭成员分散多地,各自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彼此之间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这一细节深刻地体现在赵德胤的电影表达之中。《挖玉石的人》中工人们讨论着山顶的通话讯号最好;《冰毒》里三妹从中国来到缅甸,为自己的爷爷送终后,又与身在中国台湾打工的哥哥通话;《再见瓦城》中莲青在曼谷寄钱过后,又往缅甸家中打电话再次确认汇款金额。更有意味的是短片《家乡来的人》中的一幕,四个缅甸年轻人都站在阳台上与亲人通电话,这种形态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而这种离散的状态正是缅甸华人的生存常态。因此,离散并非赵德胤刻意选取的主题,只是因为他生长于类似的环境,又经历着相似的故事。赵德胤将《翡翠之城》称为“贴近我私人情感的家庭录音带”[7]85,父母及兄弟姐妹的亲身经历都成为他的叙事来源,也成为电影表达中不断上演的相似情节。这套叙事既是赵德胤私人体验和个人情感的投射,又是华人群体离散状态的具体表征,而透过个人和家庭的“小叙事”,观众才得以窥见整个时代的“大叙事”。
赵德胤在十六岁之前所接触的跨文化经历来自于近旁的亲友,十六岁之后他便真正成为跨文化身份的亲历者。从缅甸到台湾,赵德胤既是一名学生,也是一名打工者,随后作为首届金马电影学院的学员,他直言从剧本结构到拍摄手法都受到了李安和侯孝贤的指导。由此,赵德胤的电影形式从无意识的原生表达,变为了一种有技巧的、自觉运用电影语言的表达,而这种转变又直接来源于他自身的跨文化体验。《摩托车夫》里的长镜头显得生涩而粗糙,《猜猜我是谁》里的长镜头开始出现一些有意为之的调度,“归乡三部曲”虽然存在着声画错位、场景不统一等瑕疵,但赵德胤对于镜头的掌控,已经足够表达相应的意义。到了《再见瓦城》,赵德胤的电影语言进一步精简,开头第一幕是莲青坐船漂流在河水之上,远处飘着缅甸国旗,而当她上岸之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摩托车夫却说了一句:“一千泰铢,不要缅币。”这个长镜头直白精当地道出了莲青从缅甸偷渡到泰国的全过程,其手法的确颇有侯孝贤的风范。赵德胤在世界电影节上所受到的关注,也证明他的电影语言能够被囊括进入世界电影的系统当中,《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在评论《再见瓦城》时认为:“赵德胤继承了其导师侯孝贤的场面调度和杨德昌的电影哲学,证明了台湾新电影的精神仍在。”[8]然而,与自幼移居台湾的侯孝贤不同,赵德胤的跨文化身份更为显著,这也让他为台湾新电影的精神注入了新的异质元素。电影理论家哈密德·纳菲斯
(Hamid Naficy)在《方言电影:流亡与离散导演》一书中将流亡与离散导演(exilic and diasporic filmmakers)的共同点界定为“处在社会及电影工业之中,且具备主观性和间隙性”,而在流徙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和矛盾“催生了伟大文艺作品的张力和复杂性”[9]11。在后殖民和后现代的语境之下,流亡和离散只是空间迁移形态下的不同体现。离散与流亡相比,具备了更显著的集体性、多样性与混杂性,他们不仅需要处理与原乡的关系,还要处理与散居同胞社群的关系。正如赵德胤电影中所反映的那样,缅甸华人作为离散群体,在离开故乡之后并非处于流亡状态,而是与其他具有共同文化记忆的人组成新的群体,群体内部既互相帮助又互相影响。例如《再见瓦城》中,除了少数泰国官员之外,莲青所接触到的人,包括同屋的室友、餐厅的老板、工厂的工人均是来自缅甸的华人。离散电影作者所生产的跨文化电影打破了静态的电影分类形式,难以捉摸、漂浮移动成为这种电影现象和文化生产活动的特殊样态,而这样的特征又与全球范围内的散居及文化流动相互映照。
尽管我们可以用流亡或离散来概括跨文化作者,但其个体之间仍存在着巨大差异。换言之,赵德胤的跨文化经历难以被旁人复制,他的作品为缅甸和台湾电影带去了新的视角,但是又不同于缅甸及台湾的本土电影,不同于借用他国元素强化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且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对照中西方迥异之处的跨文化电影。同样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李安的《喜宴》和《推手》表现了强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而赵德胤的作品在整体上仍处于亚洲语境之下,这使得他的叙事手法,包括他对于爱情的描绘以及对于残酷现实的描述,带有一份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的冷峻、克制与隐忍。《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里工人们面对矿难时的无动于衷,《冰毒》里摩托车夫与三妹之间朦胧的好感,《再见瓦城》里莲青和阿国点到为止的爱情,都在传递着赵德胤本人对于周遭事物的诊断和观点,而这种思维方式又产生于其受到多元文化熏陶的过程之中。由此,或许可以沿用“作者电影”的术语来进一步说明赵德胤对于自我电影身份的判断。这个法国新浪潮时期诞生的电影理论概念之所以适用于此,正是因为赵德胤的电影本身烙上了太多导演个人的特色。这种特色包含了赵德胤所有的生命体验,包括其亲属的经历,他本人作为缅甸华人的经历,作为台湾电影人的经历,以及作为跨文化作者的经历。赵德胤的文化身份与其生命体验越是复杂暧昧,其作品也将透露出更多文化符码,如《冰毒》里涉及到的妇女买卖、毒品交易,《再见瓦城》里涉及到的色情行业、证件伪造、官员贪腐等,都在倾诉着隐藏于光明世界之下的灰色地带。赵德胤曾盛赞台湾的电影环境,他认为:“台湾电影的优势就是纯粹,台湾电影人有独到的电影方法和电影态度,做一部电影要有情感、有兴趣,不管商业、非商业,去按部就班地研究电影、剧本,准备拍摄。”[10]77可见,赵德胤没有将自己框定在缅甸题材,也没有将自己限制在非商业片领域,他更倾向于使用现有资源对电影进行最大程度地加工和提炼,这也表明了他所坚持的“作者写作”直接关联着导演个人的直观表达,不为商业制作、集体创作和类型电影所取代。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其他跨文化作者身上,他们一方面更容易生成一种坚持甚至信仰以抵抗无根和游离的现状,另一方面又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忍耐力。
三、回不去的原乡与生命的离散
原乡与离散是跨文化作者的永恒主题,包括赵德胤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导演均表现出对于离散主题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一主题从流徙的大背景中浮出历史地表,又流向不同的侧面。相比之下,赵德胤作品中的原乡更加漂浮不定,他对于离散的看法也上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从而汇聚成一份深切的关怀。从浅层的表象来看,赵德胤片中的离散者对于原乡的幻想,构成了一组支离破碎的图景,他们对于故土的复杂情感,让原乡变成了一块内心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驻足的土地。从生命离散的角度看,离散承载着时间和空间的疏离,这种疏离打破或是重构了人际关系,并将个体置于更广阔的生命向度之中,这种深重的危机感不仅来自于流散与跨境本身,更来自于个体生命本身。
“凤凰视频”曾邀请六位东南亚华人导演,以“原乡与离散”为主题分别拍摄短片。①“原乡与离散”主题下的六部短片分别是蔡明亮(马来西亚)的《行在水上》、陈翠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夜话》、阿狄·阿萨拉(泰国)的《此时此刻》、陈子谦(新加坡)的《薄饼》、许纹鸾(新加坡)的《新新熊猫》及赵德胤的《安老衣》(《冰毒》是以此扩展而来的长篇作品)。详见:http://v.ifeng.com/program/yingshi/yxyls/。从这个微小的窗口可以透视出东南亚华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复杂的文化心态,这批作品的共同特点在于都透露出一种潜藏的无力感,他们所描绘的原乡均代表了个体特殊的情感与记忆。《行在水上》中的那名僧侣在导演曾经居住的楼房中一步一步地、极其缓慢地前行,虽然不知来处亦不知归处,但这栋小楼总体上仍算是一处宁静祥和的故地。《马六甲夜话》用意识流的剪辑和黑屏字幕的方式表现了散乱且无序的意象,陌生人的言语“你是一个异乡人,到哪里都是”刺痛了漂泊者的心,不被认同、无处容身的不稳定感充斥了整部短片。《薄饼》涉及对父辈传统的反拨与继承,薄饼作为一种原乡意识的物质载体,体现的是迁徙者对原乡的共同想象。《新新熊猫》则完全是一篇关于海外移民的寓言,南下的“熊猫”对于中国既有思念又有敬畏,对于新加坡既想亲近又无法完全融入。诚如学者所言,赵德胤作品的特点在于其“离散叙事始终根植于个人经验视域下母国的底层,它割裂了经滤镜加工的他者想象,而径直抵达缅甸华人日常化的离散状态”[11]78。赵德胤对于“母国”(原乡)的展现总是多层次、多视角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原乡想象对他而言是个体化、私人化、差异化的存在。
原乡(Homeland)在中文语境下有很多相似的表达,如家乡、故乡、家园、母国等,这个概念首先根植于地理区域及文化习俗,当个体发生空间位移且感知到变化的前提下,对于原乡的想象便会突显出来,这种想象又会随着认知体验的增加而产生异化、扭曲和增生。因此,原乡并不指向具体的某时某地,而是指向对于时间和记忆的知觉,它可能是私密的个人体验,也可能是集体的“想象共同体”,亦可能是多种情感体验的结合。每一个经历过迁徙的个体,都有可能产生对原乡的不同想象,个体的归属情结正是在处理自我与原乡关系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冰毒》里三妹一家人实际上就展现了一个家族对于原乡的多维度想象,三妹出生在缅甸,被骗去中国四川嫁为人妇,她带着从云南拿到的“安老衣”②“安老衣”是一种风俗,从云南迁徙而来的缅甸人,会在生前做好安老衣,他们相信死后穿上安老衣,灵魂会回到故乡并得以安息。回到缅甸给爷爷送终,而临终的爷爷嘴里不断念叨着家乡的名字,直到安老衣盖上身之后才离开人世。对于三妹的爷爷来说,原乡是云南,并物化为一件安老衣,简单却又深刻。三妹的母亲劝三妹回到四川,因为在中国的生活更加稳定,三妹却想留在缅甸赚钱,再将孩子接回缅甸生活。对于三妹来说,祖辈的原乡已经消散,甚至从未出现在她的记忆里,而她的原乡变成了其出生地缅甸。在这个家族内部体现了纵向上的原乡想象差异,这种差异又因为时间的流逝和不间断的流徙而变得更加盘根错节。就横向而言,《猜猜我是谁》和《再见瓦城》中两对情侣的分裂本就体现了“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两种选择的对立。在同辈之中,除了这两种普遍的选择,更有处于矛盾、震荡和摇摆之中的“多栖人”。《海上皇宫》里的三妹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台湾的街道上,一直喃喃地说着要回家,却又不说她具体要回到何处,又将如何回家,影片末尾的一段倒放镜头,让三妹归于来处,她嘴里的“家”因此指向虚幻的精神上的慰藉。有美国学者认为赵德胤的电影是处于庞大的中国文化外部的文化生产,普遍的跨媒介性(intermediality)和全球资本的融通让中国性/中国化(Chineseness)的概念不断漂浮,“中国性的概念通过‘归乡三部曲’中人物的关系和民族身份进行不断谈判,并伴随着对于中国性这一共同身份的再理解”[12]11。这里的中国性是赵德胤原乡想象中的重要一环,而在他的电影世界里,个体对于原乡的想象千差万别且不断变化,原乡更像是海市蜃楼一般,虽能够感知,却无从触及。
离散(diaspora)这个与原乡并置的主题,原指离开家园、漂泊不定的散居状态,现在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普遍适用于全球范围内人口流动与迁移的现象解释。有论者在梳理“离散”概念的历史演变时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之下,diaspora越来越远离某一既定的群体及其特质,更多强调体现于空间散布中的联系、制度与话语”[13]19。因此,从“联系”的角度去思考赵德胤电影中的“离散”主题,能够超越这一概念本身流动的定义,回归赵德胤书写离散主题的本质之上,即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赵德胤曾在访谈中明言《归来的人》以其自身的经历为原型,当他从台湾回到缅甸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与缅甸格格不入,他与亲人之间的亲密感之所以消失,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①访谈来源于台湾《文人政事》节目“缅甸侨生导演赵德胤,拍出异乡家乡真性情”,详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DBEX8SKnXI。时间上的疏离相对而言更为普遍,生命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会经历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变化。空间上的疏离则是离散群体所面临的特殊困境,这种疏离一方面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生命流徙所带来的深重危机感。随着空间的移动,人际关系首先面临着疏远,即使是父母与兄弟姐妹也不例外。《冰毒》里的三妹在爷爷死后,本想给身在台湾打工的哥哥报丧,却在听到哥哥对爷爷的关心之后,改变了话锋,说家乡一切都好。这种“报喜不报忧”的通话情节在赵德胤的电影中重复上演,这自然是一种亲情流露的方式,但从另一方面看,空间的距离让原本无话不说的家人缺少了信息共享的平台,由此打破了由血缘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与此相对,正是由于空间移动,人际关系又得以重构和组合。《再见瓦城》中的男女主角因为偷渡而结识,继而相爱,这里所体现的叙事张力表现在,原乡作为离散的向心力,将人物关联起来,同在异乡漂泊的共同命运,让两人的情感显得更为真挚可贵。然而,在赵德胤的电影中,离散所带来的危机一直存在,漂泊的人始终没能得到现世的安稳与宁静,即便是影片中的小角色身上都饱含着悲剧色彩。例如《再见瓦城》里的福安,同是偷渡来泰国打工的缅甸华人,他在工厂做工时被机器轧断了腿,最后只拿到四万泰铢(约合八千人民币)的赔款。离散所带来的这种深重的危机感潜藏在全球化商品贸易的流动之下,仿佛形成一股暗流,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及其演变。赵德胤对于离散人群的关注和描写似乎沾染了亚洲语境下佛教文化的气息,尽管赵德胤没有直接回应其作品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但是他影片中掺杂着太多诸如僧侣、佛像等佛教元素。可以说,赵德胤描绘的这一幅众生皆苦的“爱离别”(佛教“人生八苦”之一)景象,既是缅甸社会流徙状态的一隅,又是世界族群流散的一个典型片断。
结语
“流徙”的概念囊括了缅甸底层的社会图景、跨文化作者的生命体验以及全球化离散族群的生存现状。赵德胤的缅甸题材电影聚焦底层民众,在“跨地性”的表述中,以纪实的长镜头语言展现了边缘群体在多地流徙背景下的生存状态。赵德胤本人作为“异乡人”的跨文化作者,构建了以私人叙事为基底的电影叙事,通过世界电影语言传递了复杂暧昧的文化符码。赵德胤的电影主题始终围绕着“原乡与离散”,在展现原乡差异化想象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离散背后生命悲剧的深切关注。
从严格意义上说,赵德胤的电影不属于缅甸电影,不属于台湾电影,却又无疑将在缅甸电影和台湾电影的历史上留下一笔,他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运用电影语言来表达生命状态的亚洲电影乃至世界电影。赵德胤的电影实践为包括缅甸电影在内的东南亚电影提供了未来电影言说的一种可能性,即跨越国界,突破地域电影的界限,从他者(文化上的异质者)的镜头中观照自身,以敞开的胸襟和开放的视野反思自我。就理论角度而言,以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包括赵德胤在内的亚洲跨文化作者和跨文化文本,不仅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纵向挖掘电影的文化生产过程,还将有利于进行横向的文化参照与文化比较,进一步拓宽电影研究的理论视域。
参考文献:
[1]贺圣达.电影在东南亚:发展、问题和前景[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5(3).
[2]Laura U.Marks.The skin of the film:intercultural cinema,embodiment,and the Sense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3]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王万睿.少无可归:数位写实主义、流行歌曲与赵德胤的“归乡三部曲”[J].中外文学(中国台湾),2017(46).
[5]马然.论·谈:归去归来不得——华裔导演赵德胤及其越境电影[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4).
[6]范宏伟.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2).
[7]柳莺.赵德胤柏林专访:电影不需要我,是我需要电影[J].电影世界,2016(2).
[8]Clarence Tsui.The road to Mandalay:Venice review[EB/OL].(2016-09-01)[2017-10-18].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review/road-mandalayzai-jian-wa-924196.
[9]Hamid Naficy.An accented cinema:exilic and diasporic filmmaking[M].In the United Kingdo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0]赵德胤,黄钟军,赵文婷.赵德胤:我遵循着自己的情感去拍每一部影片[J].当代电影,2007(11).
[11]黄钟军.离散与聚合:缅甸华人导演赵德胤电影研究[J].当代电影,2017(11).
[12]Melissa Mei-Lin Chan.Mail-Order Brides and Methamphetamines:Sinophone Burmeseness in Midi Z’s Burma Trilogy[J].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2017(43).
[13]段颖.diaspora(离散):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J].民族研究,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