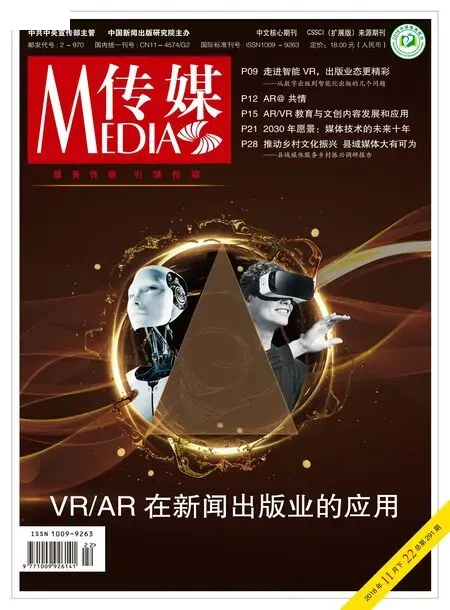真实事件电影改编的侵权风险及其规避
文/王军峰
近年来,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发展迅速,这类题材注重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照,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色彩,能够引起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诸如电影《亲爱的》《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等,都引发了收视狂潮,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这类电影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事件,通过艺术加工的方式对其进行戏剧化改编,因而更具有独特魅力。但其在实现商业和艺术上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侵权问题,无论是《亲爱的》上映后,故事原型人物高永侠对电影侵权的不满,还是《我不是药神》中故事原型陆勇发布声明进行澄清并欲起诉制片方等,都说明了这类电影改编过程中存在的侵权风险。因此,需要分析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过程中侵权风险产生的原因,寻找事件真实性和电影艺术性之间的平衡,在充分尊重故事原型人物心理感受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
一、真实性与艺术性:事实与艺术的不同追求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绝非还原真实事件,而是通过对真实事件的改编与想象,表达出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热点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这类真实事件在当时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媒体报道,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从事实层面来看,这些发生的事件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成为事件的核心特征。例如,电影《亲爱的》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事件。2008年3月25日,在公明营生的彭高峰发现4岁的儿子乐乐不见了,怀疑是被人拐跑了,他马上报警,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旅,一直到2011年春节,才终于找回自己的儿子。而电影《红海行动》则取材于2015年我国“也门撤侨”事件的真实故事。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取材于2015年的陆勇案件,陆勇是江苏无锡的一名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了减缓病情,他需要坚持不断地服用一种叫“格列卫”的瑞士进口药,但这种药价格昂贵,一盒23500元,开支巨大。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发现了一种印度生产的仿制药,疗效一样,然而价格却相当便宜,一盒只要4000元。后来,他因为代购仿制药,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抓。2015年1月27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陆勇最终获释。可以看出,这类基于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都选择了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电影和新闻事件属于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新闻要求真实,电影追求艺术性,更加注重对故事冲突性、戏剧性的呈现,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与描写,追求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魅力,改编时如何拿捏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尺度是新闻事件电影改编存在的一个问题。在电影《亲爱的》中,为了呈现李红琴的个人命运际遇,在创作中放大了不幸,无论是虚构情节如给别人下跪,受到殴打和辱骂,为了找证人作证自己的女儿是捡来的和别人睡觉等,都是从艺术角度进行的二度创作。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了凸显主人公程勇在赚钱和道义之间的情感转化和价值观转变,将其设置为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从非法贩卖印度药品中赚了大钱,抱着一大堆钱睡觉的人。正是起初将其设置为这样的“小人物”,才能通过后期程勇在看到自己的兄弟因病死亡后良心难安,到印度再次高价买药低价卖药救助白血病人这一事实,呈现了主人公的价值观转变的历程。由此,这部电影不再是小人物的电影,而凸显了普通人对生命的追求与尊重,呈现了小人物的大情怀,从而实现了电影主题的升华。因而,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故事细节的重新设置,还是对电影主人公角色的展示,以及在故事发展中对电影情节的推动等,都是基于电影叙事和电影主题呈现的需要,而这些细节和情节的展示能够凸显电影的戏剧性转变和冲突性存在,增强故事叙事张力,给观众更强的代入感。
可以说,正是基于事实的真实性特征和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的电影创作追求的艺术性特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不仅仅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还是对真实事件的艺术加工与再创作。因而,这也决定了它们绝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对现实事件的镜子式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突破真实事件中的细节,实现对细节的改写、重设和虚构,就成为创作的重要途径,而正是在此间,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侵权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二、真实事件电影改编侵权现象产生的现实动因
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受到观众关注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效益。电影《亲爱的》上映后,最终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于2015年上线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我不是药神》则在上映后引发了各界对我国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讨论和对仿制药、进口药的高度关注。对此,李克强总理专门就该片反映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由此可见,这类现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具有较好的社会效应,但这类电影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对一些故事情节的虚构和再创作,引发了故事原型人物的不满,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和名誉权。
一是电影播出后导致当事人的情感受到伤害,如受到周围人的质疑,导致周围人对其社会评价降低。在电影《亲爱的》播出后,其中关于故事主人公下跪、遭到打骂和陪睡的情节,就引起了故事人物原型高永侠的不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她说道:“(电影)我没看完,受不了。里面说我和别人睡觉,又生了孩子,还给记者下跪。实际上这些都没发生过。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别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
二是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制片方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偏差,导致对某些虚构情节的认定存在歧义。如制片方认为基于真实事件的电影改编对情节的再创作是基于艺术的需要,而影片结尾中通常标注“故事部分情节纯属虚构”就可以避免当事人的指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我国电影相关管理办法并没有对普通人形象的规制,如根据原广电总局第52号令《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曲解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严重违背历史史实”“贬损革命领袖、英雄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形象;篡改中外名著及名著中重要人物形象”的电影片,应删剪修改。根据原广电总局发布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第八条,“凡影片……,涉及历史和文化名人的,还需出具本人或亲属拍摄的书面意见”。从中可知,电影审查制度主要保护的是革命领袖、英雄人物、重要历史形象和名著人物等 “大人物”形象,而对电影塑造的普通人形象并无规制。针对由真实故事改编成影视剧,只谈及了需要历史和文化名人的授权,也未涉及利用普通人物形象需获授权的管理规定。但如果电影存在那些足以影响当事人形象和名誉的问题时,还是需要慎重。如电影《手机》中对崔永元的映射和《手机2》开拍过程中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已经引发了影视圈的震荡。
三是从行业规范来看,当前真实事件电影改编发展快、影响力大,但这类电影依然处于成长期,和文学改编电影、纯虚构创作电影相比,在涉及版权问题、肖像权和名誉权问题方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行业规则。其中,如何在虚构情节追求艺术性的同时,将对当事人的伤害降低到最小,依然是这类电影创作需要解决的难题。在真实事件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如何与故事原型进行沟通、协调,就成为关键,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事件中的当事人或基于自身名誉的考虑或者基于其他方面的衡量,难以有效与制片方进行合作。如电影《亲爱的》剧组曾多次联系高永侠,但实际上被她拒绝了,在一则采访中,她说到:“第一次对方和我说要拍一部《爱心妈妈》的电影,想采访我,被我拒绝了。”后来,她又接到剧组的电话,在通话中剧组再次提出想来见见她,都被拒绝了,原因在于“过去几年了,我不想再翻出来,想一想就心里难过。”这也成为制片方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而电影《我不是药神》播出后,也引起了当事人陆勇的关注,他说到:“该电影的预告片和花絮在网上发布以来,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主要原因是电影取材自真人真事,却并没有经过他的授权,并且在片中主角程勇“从非法贩卖印度药品中赚了大钱”,抱着一大堆钱睡觉的场景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名誉。为此,他发布声明进行维权,明确指出自己并未授权制片方拍摄电影,而只于2015年授权韩家女女士根据自己的故事原型创作剧本。但在和制片方进行沟通协调,要求“要求在片尾加一小段我的说明,以澄清事实”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制片方并未满足其诉求。由此可见,这类电影创作过程中和现实故事中原型人物的沟通与协调对于电影上映后规避当事人指控具有重要作用。
三、真实事件电影改编侵权现象的规避措施
从电影改编的角度看,《亲爱的》和《我不是药神》引发故事原型人物侵犯名誉权的控诉在于虚构故事情节,而这种基于真实事件的虚构创作是事实转向艺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由此引发的当事人的指控和质疑,依然是电影改编过程中的重大风险,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如果电影中不恰当的虚构情节和过度的隐私信息披露,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身心受到二次伤害,则为该类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因此,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需要和当事人密切沟通,阐述电影创作主旨和意图,争取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积极动员当事人参与到整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心理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在影片中也需要明确标识虚构的情节有哪些,避免因电影自身的叙事逻辑而导致观众的误读与误解。
1.要在拍摄初期争取当事人的授权,提供豁免书。在《我不是药神》中,原型陆勇的纠结之处在于电影的剧本成型以及拍摄过程当中,始终未有人联系他,这是他认为自己被侵权的主要原因。尽管原广电总局第52号令《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第八条的规定都没有涉及普通人作为原型的电影改编和拍摄,但制片方仍需要以此为参考,充分争取事件当事人或其亲属的同意。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如在美国拍摄真人真事影片,首先要拿到当事人或其后人的“豁免书”(Release Form)就是一个普遍惯例。再比如,纪录片拍摄中,制片方明确告知“正在拍摄影片,入镜将作为电影片段”,当事人获悉后并不反对,同意继续拍摄进入镜头的,视为当事人通过默示方式给予制片方豁免。我国在拍摄这类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这种“豁免书”的方式,规避后期存在的侵权风险。
2.不能过多地暴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尽管这类事件改编电影在片尾都会提示“本片根据XXX事件改编”,以规避风险,但如果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过多暴露,就容易引发当事人的指控。如《亲爱的》电影中的原型人物高永侠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对其解释电影是虚构的,不等同于现实生活时候,她说到:“可是在片尾,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份信息都暴露了?”“里面很多情节我没法接受,比如李红琴给别人下跪,受到殴打和辱骂,为了找证人作证,和别人睡了一觉,最后又生了孩子。”这些都是没有的事,但在影片最后却播放了我的真实画面镜头,“这会让别人觉得,这些事都是我真实经历的。由此可见,对当事人信息的过多暴露,会导致走向艺术的电影中的人物角色被“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当事人的诸多不便。因此,需要在影片中提示观众哪些故事情节是虚拟的,哪些故事情节是真实发生的,引导观众在观看和认知电影过程中形成对当事人的正确评价。
3.要进一步规范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行业规则。要形成电影创作全链条的职业规范,保证电影创作与事件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如果创作不当,会给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我不是药神》中,陆勇的质疑就在于电影中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设定,将自己设定为以金钱为追求,“抱着一大堆钱睡觉”的人,而电影预告片和其他的拍摄花絮中的搞笑行为,也成为引发陆勇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在他看来“这种‘爆笑’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这种消费病人的行为,不值得称道。”因此,需要制片方遵循电影创作的伦理规范,尊重当事人的内心感受,以更多的人文关怀指导电影创作的全过程。
四、结语
毫无疑问,真实事件电影改编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其关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够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真实事件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形态,前者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后者则追求艺术性,突出呈现故事的冲突性和戏剧性并以此为电影故事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真实走向艺术的过程中对于一些情节的虚构和再创作就成为必然,但由此而引发的侵权风险也值得创作者关注。在未来的创作中,还需要平衡真实与艺术、商业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推动真实事件与电影艺术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