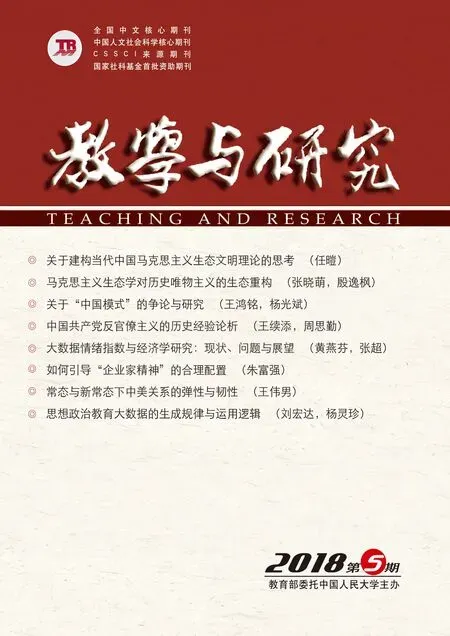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与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无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发现中国崛起已经不再是单纯依靠外部反应而寻求的改变,更多地需要从中国自身出发寻找内在原因,“以中国为方法”探求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理论依据。不少海内外学者从宏观入手加以整体概述,提炼出属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概念性质。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道路的表述引发新一轮的关注,指出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官方表述的“中国方案”必将引发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本文主要目的是述评海内外政治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以助推“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
一、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早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就开始了,不过当时更多地以“中国特色”的名词形式作为国内外关注的理论热点话题,这不仅反映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对于国外学者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让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原有的理论范式尚无法完全解释中国成功崛起的内在因素,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以“中国为方法”,具有“中国眼光”,来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模式的概念成为国际上瞩目的焦点,还是在雷默发表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之后,这使得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与日益走向没落的“华盛顿共识”相比,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有可能成为其替代者*参见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2004.“华盛顿共识”源自撒切尔和里根在上台后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做出的一定程度的重整,从而影响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思维革命,通过实行“大市场、小政府、轻赋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举解决了西方国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滞胀”局面。这种“新自由主义”路线最后被升华为“华盛顿共识”,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世界推销,一时间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的典范。。“北京共识”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显然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浓郁的政治背景,站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视角上,潜意识地显露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造成了巨大挑战。
丁学良就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概括出了中国模式是“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的联结体,并认为中国模式应该定位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内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1](P11)但丁学良对于中国模式的概述割裂了改革前后三十年的关系,也割裂了革命历史演化的逻辑,显然这样的历史观是值得商榷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也指出,在中共十六大顺利召开之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权力交接过程、干部晋升改进、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渠道拓宽等四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并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改革全面地使政权得以稳固和加强,因此他把这一套政治模式称为“有韧性的威权主义”。[2]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相当重视中国改革以来的发展经验,也承认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而且这样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对于亚洲地区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了市场经济、一党执政的威权政府、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对有能力的国家,据此福山指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开放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他最近设计的衡量各国治理状况的坐标系中,中国就处于国家能力强而程序约束弱的一端,而美国则正好相反。但福山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核心理念: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着民主化的压力。他进而强调,这样的中国模式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出口导向实现经济发展,二是在政治体制上缺乏对下负责的责任体制导致政府无法始终保持高质量的治理能力,所以福山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可持续,也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3]
在西方学者找不到更好的概念描述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找不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弊病时,他们发现他们给中国扣的所谓概念帽子根本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无法指明中国面临的现实矛盾,于是转而从对中国体制机制的“病理学分析”转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运行的“生理学分析”,把目光的焦点对准中国的改革经验,对其进行经验性研究和高度的理论概念概括。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共识”一经雷默提出就引起了海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西方学者们把“北京共识”等同于中国模式,认为搞明白了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就能摸清楚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这头大“象”。
二、中国模式的研究主题
(一)改革开放与经济腾飞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首先是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展开的。许成钢和魏兹曼曾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悖论:按照一种形式标准的主流产权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种引起经济灾难的、极端不现实的方案,在现有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应该是没有效率和无人负责的。[4]这两位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这一悖论,事实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经济方面对于“中国模式”为何能够取得成功的普遍困惑。
对于中国的经济腾飞,不少学者们认为中央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利用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下,形成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林毅夫就把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成就定义为中国的奇迹,并认为中国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背后源自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通过选择“比较优势战略”,走出了一条不同时段内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了竞争优势,能够使得后发国家迅速赶上发达国家。[5](序言P18、19)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地方竞争的角度入手,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权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财政分权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锦标赛”式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钱颖一等就认为,地方分权一党体制通过引入地方政府间竞争提高了中国体制内的创新能力,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所以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主体与其说是一个个企业,倒不如说是一个个地方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地区间的竞争推动的;同时,地方分权的一党制体制还鼓励各省在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展开竞争,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6]
以上这几种主流的解释,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一致认可,但是并不能充分回答西方学者们对于“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困惑,因为它们的不同解释都是从政策实施角度出发而没有从宏观制度入手对于体制模式进行制度演化层面的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全面地提升并归纳“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大致框架。
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制度性总结,郑永年教授首先批驳了“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西方学者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和称呼,也不赞同部分学者简单地把国有部门发展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起来的片面看法。他认为“大家说中国的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秩序的本质,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秩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因此从概念上来说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而美国是‘市场内政府’(state in market)”。[7](P137)胡鞍钢也认为,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差异性、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混合型的经济结构最符合中国国情,而这样的混合经济体制对于世界也具有巨大的外溢性,通过在国际大舞台上“两条腿走路”,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有着巨大的机遇和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混合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征。[8](P141-161)可以说,正是采取了混合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统一,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经济绩效的推动下,中央政府有强烈的意愿进行自上而下、从整体到局部的改革发展,不断克服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大力鼓励地方创新,探索适合本地发展模式的独特路径,从而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积极性,这样在混合经济模式的宏观架构上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省一起联动,使得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一党执政与政治发展
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良好政治制度所提供的稳定政治秩序,尤其在2008年全球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因素成为海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不再单纯地只是归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而更希望从政治层面探讨中国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
郑永年教授不赞同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认为对于中国模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讨论显然不能帮助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为此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从历史演化的逻辑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经验脉络。他把政党对于国家的主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比喻成“组织化皇权”,认为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和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也是贤能政治的制度承载,而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被中国的政治精英所认同,并且有着更为广泛的组织基础和更为强大的渗透能力。[9]通过梳理现代党权的发展脉络,郑永年教授进而对于中国模式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模式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政治上是开放的一党制下形成的“内部多元主义”,而经济上是混合经济模式。但历史没有终结,这样的中国模式是开放的,也需要不断进行渐进性地改革,为此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经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步走”的改革过程。正是因为这样的模式还有尚待改进的弊端,他认为或许采用中国经验这样去政治化的描述更为恰当,对于中国模式过分道德化的审美趣味解读下无异于进行“捧杀”了。[10]
王绍光教授则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不同角度对于中国模式有一个很好地总结。他首先指出了本体论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形,在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人类发展指数的成就是巨大的,所以他在本体论意义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更愿意把中国模式称作为中国道路,进而他在价值论上认为中国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是值得被推广的,特别是中国在公共政策、社会领域方面的改革经验是完全有资格向外推介的。在认识论意义上,王绍光教授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对于中国式发展道路的理论性解释,在宏观上解释清楚这样存在着的中国模式。他批评了一些对于中国模式持保留意见的学者观点,指出他们只把关注点放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总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就能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王绍光把这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称之为“政体思维”,并指出这种“政体决定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拿来分析中国政治模式显得方枘圆凿。为此,王绍光教授对于分析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政道思维”观点,强调要把着眼点放在政治秩序的实质和治国的理念方式上,强调不要一味地盲从西方理论家的“政体思维”,从而只关注政治体制的形式而不关注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和途径,或许用“政道思维”来观察中国政治,会有不同的感受。[11]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把视角放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上,结果却发现新兴企业主们伴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谋求与执政党和政府相对抗,相反他们被中国共产党吸纳进入到政治体制之中,形成了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狄忠蒲考察了中共在吸收民营资本家入党方面所作的努力,他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扩大了中共执政的基础,显示出了中共极强的调适能力,企业家们也愿意加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全新的政策创新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2]蔡欣怡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度田野考察也印证了狄忠蒲的观点,她在结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私营企业家不太可能要求政权变革,即便民主化在中国发生,也不可能是由一群私营企业主主导的,他们改变政府议程设置的方式不是通过民主而是通过一种“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来产生影响的。[13]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发展模式颠覆了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关于“资产阶级带来民主”、“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等论断,也与李普塞特、派伊等现代化理论家逻辑下的经济发展带来政治自由的观点南辕北辙,在用西方传统理论模式解释不清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经验的情况下,部分海外学者不得不把这样的实践经验称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
可以说,实践经验证明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没有犯所谓的“颠覆性错误”,实现了在不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达到高速经济增长的目的。黄宗良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符合了中国国情,契合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程度,并一直具有开放性的特征。[14]可以看到,如果简单地把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私有化”加“自由化”的产物,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何世界上推行私有制和市场制的国家那么多,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度发展。“中国模式”通过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经济发展先于公民权利与民主化的发展,强调有选择地学习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兼顾了制度创新与制度延续,从而展现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
(三)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
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形态孕育了独特的中华文明,“百代犹行秦法政”,自秦汉以来儒法合一的官僚制政治体系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而如今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体系又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保证。不少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在“以中国为方法”的身份意识和问题意识下,更加重视基于中国自身文明性和历史经验出发所进行的高度经验概括,从而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实践价值。
张维为把中国模式的成就看作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归纳了“文明型国家”的八大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广阔的疆域领土、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独特的政治),尝试性地描绘出中国模式的文明价值内涵。[15]潘维同样指出,中国模式的基础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必须横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去研究这样一个模式的内涵意义,而“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是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亘古不变的传统,正是对于“人民性”的强调构成了中国模式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位一体组成的结构。[16](序言)
在文化方面,学者们通过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考察,探寻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因素,他们首先发掘了民本主义贯穿在中国模式中的重要价值。朱云汉教授在研究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兴起的时候就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一向重视“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而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力求“民享”。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特别看重“民享”,而不采取有碍“民享”的“选举民主”或“民粹导向”的“民治”。[17]贝淡宁从“民本主义——贤能治理”的角度思考了中国模式形成内在因素,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贤能政治、中层的实验和基层的民主制”三者的有效结合,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巨大潜力和经济增长活力蕴藏在伟大的中国儒法哲学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主贤能制模式”。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式民主,“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的治理模式将选举(election)与选拔(selection)相结合,有助于中国在传统基础上建立强大而有力的政治体制,并不断回应人民的诉求。[18]姚洋则对民本主义下的精英治理有着很好地总结,他认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发展的成就得益于一个中性的政府,这个中性政府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因为组成中性政府的政治精英们更加关心人民整体的利益,从“民本主义→贤能治理→中性政府”,民本主义的关怀最终推动了中性政府的形成,而中性政府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政治优势。[19]
在另外一个角度,也有许多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将民本主义与天下观结合起来,并嫁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意在寻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现出中国模式在文化方面的内在意涵。“天下观”或者说是“天下体系”理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是王道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华古代农耕文明直至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一直延续的民族精神精髓。王赓武就指出,正是“天下”的概念让中国人可以将这些要素编织成一种单一的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文化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文明,并将之转化为中国人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对强政府、国家地位、天下一统等行为的认可。[20]赵汀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有一个很好地总结,在赵汀阳看来“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21]
文化主义是理解中国模式必不可少的视角。二战之后的比较政治学先后研究公民文化(阿尔蒙德等)、价值观表达(英格尔哈特)以及社会资本(普特南),所有这些都是围绕“民主化”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问题是,即使形成了有助于民主化的政治文化,很多国家因此而发生了民主化转型,但为什么依然是无效的民主和无效的治理?说到底是文化和社会结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沿着托克维尔—韦伯式的文明研究,杨光斌教授提出了“中华文明基体论”,中华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不变的语言文字与华夏民族;国家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行政体制的郡县制、官僚制和选贤任能;文化上的包容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22]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强大文明世界,由此可见其生命力以及其对现时代中国的影响。
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并又被抽象化的产物,作为话语概念,理论又是被有意识地建构或塑造的意识形态;实践则常常是不符合逻辑而相对具体的产物,作为悖论性的模糊对象,实践既带有扎实可信的经验证据也可以被理论所高度概括。不可否认,无论是主流的既有西方理论还是希冀建构出的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它们都存在一个共识,都是希望能够认清中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但实际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二战后所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取得了成功。在改革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在经济模式中为世界提供了快速崛起的基本经验,同样在政治模式中展现了大国有效治理的典型范本,还在文化模式上贡献了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白人优越论不同的文明内涵。中国改革实际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悖论性”决定了在研究中国自身方面,只有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实践经验出发,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共的革命资源和当代中国的改革经验与既有理论连接起来,才能看到中国实践的独特意涵,由此总结出属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体系,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与西方理论对话。
三、中国模式是一种神话吗?
尽管自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被提出之后有相当多的学者肯定这样概念的存在,但是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被神话的概念,与20世纪70年代曾经提出的日本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一样,是经济高速增长下意识形态的产物,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社会矛盾的凸显以及“威权主义政体”未向民主化转型,中国模式将不可能持续。
一部分学者从政治方面的角度对于中国模式提出自己的思考。裴敏欣认为中国执政党存在着“党组织渗透能力匮乏、在群众的威信减弱、党内纪律遭到破坏”等主要问题,由此带来的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下降,进而她认为不亚于苏联体制的腐败和庇护现象将成为困扰中国执政党的顽疾,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显示出了苏联勃涅日列夫时代政治停滞和印尼苏哈托时代权贵资本主义的双重病症。[23]“历史终结论”者福山指出,中国模式是威权主义体制主导下的高速增长,相比于阿拉伯等独裁国家,无疑这样的政治体制显得高效有程序,并且已经取得了将近三十年9%的年均GDP增长率,还成功地应对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但福山认为,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具有其强大的优越性,政治制度更应该看重其长期的治理绩效或者说观其长远能否经受住考验,但显然在福山看来缺乏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中国从长远来看仍然将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24]福山的观点与谢淑丽等不谋而合,谢淑丽认为,尽管现在“中国崛起”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中国仍是一个存在种种问题的“脆弱的超级大国”,其表面看起来“睡醒的巨龙”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保障下正准备展翅高飞,但实际上中国内部社会问题十分复杂,而这样国内政治带来的后果就是影响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她为此提醒美国政治界和学界要注意中国内部问题发生的变化,很可能中国的脆弱会带来对于美国的威胁。[25]沈大伟也同样强调,共产党单纯的调适并不能拯救一个正在收缩的政权,要想给这个政治制度提供无限的生命力,执政党必须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民主空间”。[26]而黎安友也认为“韧性威权主义”尽管是具有韧性的,但其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政治体制,威权统治是有时间限制的,强健的法治和异议的公开化是这样的体制不可避免地转型方向,旨在潜意识地强调中国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尽管现在看起来健康良好,但民主转型是迟早的过程,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27]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经济方面的角度对于中国模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许小年提出,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分为两个阶段。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退民进”,国家把计划经济年代占有的资源交还给市场,小政府模式下资源的快速流动和自由配置使得市场的效率大为提高,但这样的巨大成就在许小年看来并不是中国模式所独创的,而这样的发展思路早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有体现,或许叫做亚当·斯密模式更为恰当。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源于“国进民退”,国家重新占有较大规模的财政、土地等资源,大政府模式下由政府主导进行经济发展,而这样的发展思路在许小年看来早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就已经采用了,是典型的凯恩斯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许小年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中国模式照搬的要么是亚当·斯密模式,要么是东亚模式或者说是凯恩斯模式,而没有自己的独创性。[28]陈志武也指出,单纯靠投资带动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只能带来短期的繁荣,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扭曲了市场经济理念,无法释放出个人创新的活力、增加个人的自由,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福祉的倒退。陈志武进而认为,缺乏政治制衡机制的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并不一样,日本、中国台湾的民主制衡模式会抑制政府权力的快速膨胀,而不受限制的中国政府权力很可能将把中国带回到改革前的状态,因此陈志武同样认为,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推动中国崩溃论的学者才是真正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人。[29]黄亚生同样很支持陈志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所谓的东亚模式,而是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在黄亚生看来,东亚模式是成功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模式,拉美模式则以最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而告终。为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拉美化说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发展方式,中国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国进民退”导致的民营经济萎靡、土地财政的暴利已经证明了这一套经济模式的短期性和脆弱性。所以黄亚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模式是拉美化失败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即使存在也是不可持续的,远远落后于他所看好的印度模式。[30]
梳理对于中国模式持保留态度的观点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中国是否能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他们用“民主—非民主”两分法概述着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行模式,用多党制、三权分立、选举民主这些西方的制度表现形式来管窥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政体思维的影响下,这些学者们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民主集中制不属于传统民主理论的概念范畴,但极权体制又无法描绘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体制甚至执政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2002年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后强人时代”完成了第一次权力和平交接之后,善于造概念的西方学者把“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上,在民主和极权中间制造一个概念——“威权主义”,并在概念前面通过添加各种不同的形容词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加以描述,“韧性威权主义”、“碎片化威权主义”、“协商性威权主义”、“争议性威权主义”,“审议性威权主义”,不同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概念虽然修正了冷战结束后海外学者们对中国执政党和民主化改革的悲观主义态度和批判观点,认为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改革巩固了政权的统治能力,中国的体制还有韧性空间,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是收缩与调适两者互动的动态作用过程。但无论是“威权主义”还是“体制调适”,西方学者们囿于“转型学”范式仍然认为这个体制还是会走向从所谓威权到民主化的历程,调适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适应体制内外不断要求的变革诉求,倘若体制转型止步不前,或许又将会陷入机制僵化,国家面临崩溃。
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则更是斩钉截铁地认为中国模式并无独特之处可言。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不少学者们要么认为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2.0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按图索骥依葫芦画瓢的形式走日本等“东亚四小龙”曾经走过的路,而且在未来也将面临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的困境,那时才是执政党真正遇到挑战的地方,因此不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更为悲观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但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截然不同,而更具有拉美化色彩,在他们看来东亚模式至少在二战后期到20世纪末取得过较大的成就,而拉美模式则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发展止步不前,中国模式只会在不可持续发展下面临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深渊,而那就是中国模式神话破灭之时,所以中国模式即便存在也不会成功。
很显然,这些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的判断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政治化或者说理论模式化的思维路径下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显然无法能够深刻赘述中国模式的独特经验,没有历史观和缺乏大空间视野的比较前提下,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比如唱衰中国模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违背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有违主流理论的发展模式注定不可持久,因此他们更为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中国模式持根本性地否定态度。石之瑜对于“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下衡量中国模式对与错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好地总结,他认为英美知识界所界定的中国模式大多聚焦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中政府发挥了如何的作用,相反很少论及政治经济现象以外的层面,所以明显将这一模式“简单化”了,这样只会把中国模式看作是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威胁,而影响到对于中国模式正确的价值判断。[31]可以看到,尽管在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研究上,不少学者针对中国独特模式的归纳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就中国模式整体研究而言,仍然没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主导型话语体系,而不少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内在愿景还是希望中国能走向西式民主的道路,接受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成为“西化”国家的一员。
所以,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整体性和系统性仍需提升,否则这些研究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法指明中国模式的真正实质,只会让一些并不太靠谱的观点占据了关于中国模式探讨的主流市场,却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与内在经验视而不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从集中权威到发展经济,再到社会建设最后到政治民主,一系列理性、有序的渐进民主化过程显得极为有生命力,而且配合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与社会发展,也为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文化条件,这样的民主发展历程在最近十几年里已经被证明极为有效,中国的民主实践模式却被中国模式“唱衰论”者选择性忽视,只能说这些学者一方面太局限于某个领域的具体政策层面,另一方面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也有问题,因而造成了无法从整体上真正了解中国模式。
四、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模式的内核
事实上,在中国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讨论一种政治模式,如果不能够从中国根本的政治体制入手,把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解中国模式的钥匙,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作为理解中国政治模式的关键词,并从革命年代以来历史演化的脉络理解中国模式的发展逻辑,是很难辨清中国模式的内涵实质,也很难形成关于中国模式的完整理论框架,更不用说归纳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的改革经验。而这样的政治模式在杨光斌教授看来必须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并适用于国家的组织原则问题的模式机制,这种模式机制就是民主集中制。[32]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运行中,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它既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基础,又是党内部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基本制度机构的组织原则,形成了以执政党为核心,将党和国家有效组织起来基础性制度原则。如果要谈中国模式,必须要把执政党作为理解这个模式的核心关键,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为理解这个模式的切入点,而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历史内生演化性的产物,也是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政治逻辑,[33]因此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优势,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制度的奠基者,针对革命实际和群众意志,将革命的背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中共的独特政治组织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模式,不仅调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革命的积极性,同时也塑造了党的核心权威,有力地保障了党内政令畅通。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者,同样也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34](P312)在改革年代,如果没有民主,就无法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最大活力,为改革事业的发展增添动力,但如果失去了权威,则更可能在改革中迷失了方向,无法抵御外部势力“和平演变”的诱惑。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制度的定型者,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0周年讲话上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可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并用了八个能否来衡量这个国家制度是否民主有效,强调“既要加强党的领导,避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又要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法保障人民权利”。[35]
政体是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的根本性制度或手段,在中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政体,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关系原则,民主集中制同时也是一个政策过程,在“国家—社会、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各个维度上把不同领域组织起来,展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组织力和国家能力。民主集中制作为革命年代形成的中共政治组织原则,有效地强化了群众路线下的政治参与,奠定了中共的组织基础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既实现了国家权力,又保障了人民权利,最大程度地展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使得社会在增强活力与创造力和重建能力与秩序之间保持高度的稳定。人民意志的统一与意愿的反映得到了充分结合,保证了国家机关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协调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了集中领导与广泛参与的统一、充满效率与富有活力的统一。
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将权力行使的集中性、权力分享的民主性和权力来源的民本性有机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自身的政治模式,所以如果说要谈论中国模式的话,民主集中制及其中介机制群众路线就是最根本的中国模式。对比西式民主制度如今遇到的困境,先发国家制度僵化,产生不了强势的能够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政府决策被利益集团裹挟,政策制定否决点过多,导致否决型体制、弱政府的出现。后发国家只学到了西式民主的表象,而没有学到其内在实质,缺乏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只能导致后发国家面临着民主潮回流和劣质化民主的双重窘境,一人一票选举民主和多党竞争的盲目推行要么被寡头政治取代,要么陷入民粹主义政治困境,民主化大大超前于国家制度建设,只能使得这些后发民主化国家陷入权力危机之中。所以说,民主集中制这种从革命历史中而来、在改革发展中管用、在现实治理中有效的制度,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法宝,其优势在当今国家治理比较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1]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3] Francis Fukuyama. What is Governance[J]. Governace, Vol. 26, No. 3, July 2013.
[4] M. Weitzman, Xu. 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4,18(2).
[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6] Qian Yingyi,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1, No. 4, Autumn 1997.
[7] 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8] 胡鞍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9] 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0.
[10]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 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 Bruce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3] [美]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M].黄涛,何大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4] 黄宗良.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5]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6] 潘维.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2010.
[17]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8] Danie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19] 姚洋.中国模式及其前景[J].中国市场,2010,(24).
[20]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M].黄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2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2] 杨光斌.中华文明基体论[J].人民论坛,2016,(5).
[23] Pei Minxin.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4] [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N].读卖新闻(日本),2011-09-25.
[25]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27]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28] 许小年.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J].上海企业,2013,(1).
[29] 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J].南方人物周刊,2011,(8).
[30] 黄亚生.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EB/OL].http://www.guancha.cn/HuangYaSheng/2014_10_15_276253.shtml.
[31] 石之瑜,李梅玲.“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模式[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3).
[32] 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J].政治学研究,2015,(6).
[33] 杨光斌.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在[N].光明日报,2014-09-30.
[34] 邓小平文选[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5]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