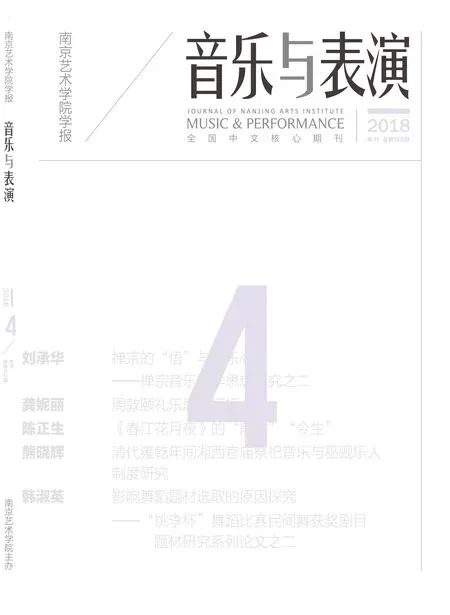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国乐”建构①
—— 对郑觐文和大同乐会的考察
叶洁纯(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北京 100031)
郑觐文与其领导下的大同乐会以“保存国粹、中兴国乐”[1]为职志,通常被人视为“复古”而贴上保守派的标签。过于简单标签化解读的危险是,人们会轻而易举地落入中国/落后、西方/进步的二元对立当中,将郑觐文与大同乐会视为社会进步和音乐发展的绊脚石,从而难以客观、全面理解和认识他们重建国乐的努力及其思想世界。事实上,“国乐”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的提出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密切相关。在郑觐文看来,国乐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塑造民族认同的一项符号。因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阐释郑觐文与其领导下的大同乐会的“国乐”建构事业,分析其“国乐”观念的基本内涵、“国乐”与民族国家建设之关系,以及“国乐”建构的路径,探寻郑觐文如何运用中西方的音乐思想和知识资源,从中寻找国家想象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什么才是真正的“国乐”,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性,并对其“音乐大同”理想重新做出思考。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下的“国乐”建构
1928年7月22日,在大同乐会暑期班开幕发表演讲时,郑觐文扼要概括了他提倡的“国乐”的性质:“国乐是国家音乐的性质”[2],明确肯定了国乐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鸦片战争以后,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促使民族主义思潮急剧高涨,冲破传统的“华夷”观念,摆脱落后的天朝帝国,进而建立起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诉求。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流行起来的“国乐”一词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正如陈洪所言:“‘国乐’这个名词还是很新的,以前大都称为‘中乐’。‘中乐’也不是一个顶旧的名称,在闭关自守的时代,乐便是乐,无所谓中西;海禁开,‘西乐’来,才有人给它起个称号,叫做‘中乐’,借以区别于‘西乐’;和用‘中文’‘中画’‘中医’等名词用以区别于‘西文’‘西画’‘西医’等一样。但‘中’‘西’是地方形容词,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不足以表示尊崇之意,所以现今的爱国之士们,便又把中字改成国字,于是‘国画’‘国医’‘国术’等名称相继出现,‘中乐’也改成了‘国乐’。”[3]可见,从“中乐”到“国乐”概念的转变正反映了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渐清晰,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在形成。
实际上,“国乐”一词古来有之,古代诗文和史料中就有关于“国乐”的记载。唐代诗人李讷《命妓盛小丛歌饯崔侍御还阙》中有“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辽史·乐志》记载:“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4]显然,这里的“国乐”,指的是由天朝帝国制定的代表国家权威的音乐,或是某些地域、民族风格的音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古代的“国乐”包含了国家的内涵,但是,它所代表的是传统的“天朝帝国”,而民国时期的国乐力求代表的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相较于古代的“国乐”,民国时期的“国乐”拥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具有了“现代性”的属性,可称为“新国乐”。近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是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基于对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强调,以及塑造国民性的现实需要,国人呼吁创造一种能够激发国民爱国情感、表达时代声音的“新音乐”。然而,当国人在感叹“雅乐沦废”“淫乐俗陋”的同时,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却因能够鼓舞国民进取之精神、增进国民合群之思想,而备受国人推崇,进而被纳入近代中国国家教育体系之中,开始在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当音乐被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之一有效手段和工具的时候,人们集中关注的是它在政治教化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国家、民族之文化的存在价值。1904年,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发出“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吾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5]的宏愿,中国音乐的民族意识初露头角。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音乐逐渐被视为塑造现代国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利器,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文化之一种,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关系到唤起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政治建设。
郑觐文曾明确指出:“国内学者,咸惧自己文化之灭亡,国民性将不可传,乃急起直追,提倡国乐之声渐盛,学校时有发起,团体亦日渐其多。”[6]在他看来,一种文化是一个国家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涌动,它是与民族或国家同步发展的生命有机体,文化不亡则国不灭,文化亡则国必随之。因此,“国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是与民族意识的盛替,与国家的成败互为因果,所以国乐救亡就是民族救亡的根本。郑觐文敏锐地认识到:自近代以来,受“西乐”风潮的强劲冲击,中国音乐“在世界乐坛上已经没有它的地位,是人所公认的”[7],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自西乐入中国,其风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慨”,“西乐风行于中国不过二十年,势力之增进可惊可骇”。[8]他和多数中国音乐人一样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音乐向何处去?重建中国“国乐”成为最紧迫的任务。对于郑觐文来说,“国乐”不只是表达国人情感和思想的工具和载体,更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与国家认同的大问题,它是彰显中国民族特性的象征和符号,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为了建设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更为现代中国创造一种进步的音乐文化,从而改善中国音乐在世界乐坛上的地位,郑觐文殚精竭虑,领导着大同乐会共同开启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建设与音乐文化建设的志业。
二、“国乐”建构的路径
(一)诉诸传统
这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典型特征,也是郑觐文建构国乐的基本路径。他认为“国乐”即为“制乐”,是“在一切杂乐之上,规模宏大,学理完备,自古相传”。按照其性质可分为三大类:一是“雅乐”,历史最为久远,“是中国音乐的根本”,不但有“五音十二律、旋宫起调诸法”等理论,乐器种类繁多,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而且“在上古时代立过许多很大的功劳,后来成为郊天祀圣永远国教的音乐”。二是“大乐”,“用于朝会大节”,与万古不变的雅乐相较,大乐则“是因事业而成,历朝不同的”,亦可称之为“功业的音乐”。三是“国乐”,它的性质是“专司对外”,“在中国春秋时代最风行,现在西洋各国也特别注重,前清名燕乐”。在编制方面,“以中和清乐作基本,以番部、高丽、缅甸、回子、安南等国乐作合奏”,规模宏大。[2]由此可见,郑觐文的“国乐”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即包含了古代中国宫廷用于郊庙祭祀的“雅乐”、国家礼仪的“大乐”(属于“雅乐”范畴)以及外交宴飨的“燕乐”。从皇族宫廷生活方面来看,它们是一种礼仪的规范;从国家政治生活来看,它们更是华夏文明的象征,代表了国家政治的权威。因此,它们自不免成为自幼便熟识传统音乐的郑觐文亟欲攀附的思想资源,而视其为“中华民国”“国乐”的核心内容和民族精神的真正代表。
郑觐文将古代宫廷音乐中的“雅乐”和“燕乐”作为“国乐”的内容,原因还在于,他看到它们在民族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认为它们是“立功于开国者”“效用于感怀者”“建树于国本者”“效用于革命者”,“能倡导和平,消弭战祸,造福人类,巩固国基”。[9]①在郑觐文的音乐言论中,“国乐”与“制乐”“礼乐”“声教”等词同义。在《中国音乐史》的“制乐类”中论及“制乐”的源流时,郑觐文指出:“制乐者,关于国家制度之乐也,现时可以收集者尚有二十八体,其体多大规模之合奏,其作用为祭祀会同而设,即古之所谓礼乐也”。可见,郑觐文所说的“制乐”即是“礼乐”。在《辟中国无文化可言之谰言》一文中,他又指出“中国真正之文化”正是四千年前已有专词名为声教,(一曰礼乐)上自国家大典,下而社会交际……”,这里,“声教”又等同于“礼乐”。由此可见,“国乐”“制乐”“礼乐”和“声教”在郑觐文看来是一个概念。他曾反复批判丝竹乐是为了娱乐的个体情感的宣泄,于国家、民族之振兴并无益处。国乐既作为代表国家的音乐,它自然不能是一种娱乐的音乐,更不能是“郑声”“淫乐”,而必须是一种能够象征民族的伟大与崇高、促进国家的富强与进步,融真、善、美等因素为一体的音乐。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郑觐文发现古代宫廷音乐中“雅乐”和“燕乐”对于建构现代中国“国乐”的价值,并将它们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以此重塑民族认同,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问题。郑觐文认为真正的国乐必须被寻找到,必须被发现和保存,并在挽救民族危亡、致力民族振兴的背景为国家和国民而重新创造,于是提出重建“国乐”的方案:“一面宣传上述的制乐、一面将北京前清剩余的乐器运之南来,联合沪上及外埠名音乐团体内的中坚因时制宜,编成中华民国新制乐,作大规模的组织。凡属音乐界中人,不分中乐西乐,大家共同负责,一致提倡以制作为前提,不要单讲娱乐做号召,求真正的国乐”[2]。
(二)以“西乐”重构“国乐”
“世界音乐,中国发明为最早,四千年前已极美备。其理则五音十二律,其器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远而走飞草木,近而性情形体,无所不赅。”[10]对本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是民族主义的必然选择,郑觐文对中国音乐的赞美是其思想底色中民族主义的充分表现。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他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寻得雅乐、大乐与燕乐来重建国乐,以抵抗西方音乐的威胁时,参照的却是西方音乐这一权威,他与其领导的大同乐会从始至终其事业都未能摆脱这一困境。
首先,以西方音乐中的十二平均律重构“国乐”。郑觐文尖锐地批判中国国乐衰微的原因是“宫调混淆”,认为中国在唐宋以前无论是雅乐还是俗乐均是采用十二律,而“现行之九宫七调法实胡乐之遗传,本非雅制”。[11]在他看来,若要振兴国乐,就必须废除属于胡乐的九宫七调法,用回十二律音阶,重新确立华夏正统。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历史上“夷夏”观念的表现。但是,仔细分析发现,郑觐文坚持采用十二律是因为看到西洋各国音乐也是采用十二律,而并不在于顾及“夷夏”之别与确立华夏文化精粹的特征。他从音乐的起源进一步阐释,认为:“音乐之产生,由于造化大法,纯全天然性质,与他种学术不同,非人力所能改造。是故中西律体皆止于十二相生之法,亦完全相同。”[8]在他看来,中西音乐的本源是相同的,皆因天然而产生,并无中西之别,其律体都是十二律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西乐优而中乐劣的说法。如今西洋各国音乐都是十二律制,那么,也只有将国乐重新建立在十二律制的基础上,其价值才能再次得以彰显。通过研读中国音乐史,他发现古代雅乐不仅于国家功业有所助益,而且它以五音十二律为基本原理,这与西乐之十二律完全相符,因此,将其作为国乐的内容名副其实。为此,他极力主张:“欲振兴国乐,当先订正宫调始”。[12]
然而,中国古代的十二律与西乐的十二平均律是不能等同的,西乐的十二平均律,全音是200音分,半音是100音分,而古代的十二律是在三分损益率的基础上产生的,运用五度相生法,大全音是204音分,小半音则为90音分,因此是不平均的。郑觐文却并没有看到二者的差异。实际上,当他将西方音乐之十二律视为进步的标准,并用它来重估自身的音乐传统时,已经在心中树立起西乐权威的地位。郑觐文认为中国传统乐器,“笙、箫、管、笛,粗、细、厚、薄,皆无定率,而京腔丝竹社会等所用宫调之主旨,亦多随便,高低不知律准,如水无源,如木无本,实为音乐前途之大碍,若不急求订一正确之音度以为基础,将永无发展之希望。”[11]大同乐会复制和改良古乐器就有意识地采用了十二平均律律制,或将六孔的笛、箫扩大为十孔,以便能够吹奏出12个半音,或将传统的4相12品的琵琶改为6相18品的“葫芦琵琶”,按十二平均律排品,目的是能够自由转调。这样就能够加强各种乐器间音高的统一与协和,增强乐器合奏时的音响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个如西方管弦乐队一般的现代大型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就成为可能。
其次,以西方管弦乐体系为样板,追求“多、大、宽、厚”[13]的音乐音响表现力,创建“伟大雄阔之气象”的中国国乐。无论是乐队规模和形式,还是乐器配置、音效和表现力等方面,郑觐文都致力于效法西方管弦乐队,追求如西方管弦乐队那样的音乐音响表现力。在他看来,这些审美特质在中国古代的“大乐”中均已具备,“大乐”为数十百人合奏的形式,乐器高低中各声部俱全,有洪大周密的曲体,接近西方管弦乐的音乐表现力,能够创造“伟大雄阔之气象”,“达到声响最高最速之希望”。因此,郑觐文在《国乐正轨》中为“国乐”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风向标:即“国乐”“欲上正轨,尤非从大乐做起不可”,因为“大乐之规模,是可容数十百人合奏,非若普通丝竹,人多则烦生;大乐之乐器,是高低各部俱全,非若普通丝竹止用中音一部;笙箫弦笛数种大乐之曲体,是洪大周密,非若普通丝竹平弱单薄;大乐之用度,是有关国家之大事大典,非若普通丝竹仅供私人娱乐者可比。”[14]为达到“多、大、宽、厚”的音响效果,创建大型的现代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大同乐会采取“稽古与改造”的方式,“尤当以改良旧式乐器为急务”。[15]一是增加乐器和乐队人数,“大乐”演奏员有二十人,所用乐器有四五十种,在人数和乐器数量方面已经与单管制西方管弦乐队不相上下。二是增加乐队音域的“宽”度和各种乐器组合后乐队频响的“厚”度,从扩大音域、增大音量、注重高中音区的配置等方面对古乐器进行改良,如用双层桐面制成的七弦琴,音量“宏可震耳”,[16]后又制五弦仿古琴,声响“宏亮异常”,[17]三十六弦大瑟,音响“洪大时如风雨骤至,幽静时如鸟语花香,有一弹经过二十多弦者,有四五弦合一音者”,且有复音性质,指法甚多,可弹三级音大曲,音响有如钢琴,[18]还有五十弦大瑟音域更宽,加装增音器,音域可达一百八十四个音。[19]此外,为适应大乐队演奏需要,加强乐队的高、低音声部,将因腰部太宽而缺乏高音的传统琵琶改为葫芦琵琶,增加高音四品,将传统月琴改为瓶琴,增加四个高音;考虑到原本的低四管只有中高两个音域,缺乏低音,故新制了倍四大管,使其音比原先低四倍。[20]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在当时“复音性质”被视为西方音乐进步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音乐落后的表现,“复音”成为评判音乐进步与否的标准。[21]为了证明中国古乐的价值,郑觐文等人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记载中搜寻出来数十种具有“复音性质”的乐器,[1]还力图将它们用于“交响性质”国乐的创作。
除此之外,国乐作品的形式、结构和表现力也应该具备西方交响乐特征,即合奏形式,多乐段、章结构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从郑觐文领导的大同乐会的古曲改编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努力,《申报》上报道过的有:改编古曲广陵散原曲节目六十段,更名为《犹在人间》曲。[18]改编琵琶独奏曲《浔阳夜月》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共十段,“有起有伏、有分有合、有整有散、有缓有急”,并模仿西方管弦乐总谱方法,将记谱由直行改为横行,为每件乐器编配成十二行总谱。[22]改编古琴谱《昭君怨》为合奏曲《明妃泪》,共九节五百余字,句法有长有短,有三十余字一句,一二字一句,颇有抑扬疾徐之妙。[23]改编古《霓裳羽衣》曲,由柳尧章演奏主器琵琶,用筝、琶、洞箫、阮、提琴、弦各种乐器合组按和声法新编为《难得人间》。[24]翻编古琴曲《海水天风》,共十二段,作大规模之合乐,定名为《冰花雪月之章》,仍用其原名《海天乐》。[25]详细研究得到名为“鼓吹饶歌乐”的古乐,称为“中国之交响乐”,能与“西乐之交响乐”相媲美,一改中国音乐“单调”的现状。[26]
综上所述,郑觐文的“国乐”建构,参照的标准是来自西方,即中国国乐需要借助西方的承认才能确立自身的地位和价值。《申报》上关于大同乐会相关活动的报道中不厌其烦地展现西方人对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景仰之情,即可视为此一悖论的又一具体表现。譬如,西人卫西琴氏醉心我国之《乐记》,认为中乐胜于西乐之处在于,中乐是“皆自中出”,而西乐则“皆自外作”[27];德国远东会代表林台博士参观中国古乐器,并购置一副带回德国,向德国民众宣传中国音乐[28];林台博士听过大同乐会的古乐舞演奏后,称赞为“乐而不淫”[29]。但必须强调,郑觐文借用西乐的权威来重构国乐,并非要西化,而是要“世界化”,即将国乐提升到世界先进的水平,一言以蔽之,西方音乐既由乐谱、复音、乐律、音乐音响表现力等方面的惊人发展而处于世界先进地位,那么,中国国乐为了获得同样的发展以求生存和成长,就必须根据成功文明所提供的范式,在技术层面和审美观念等方面进行重新建构。这是郑觐文的国乐建构思想的内在思路,而他的根本目标在于重新确立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相应地改变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这种理想抱负在“音乐大同”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国乐的未来:“音乐大同”的乌托邦理想
有学者认为郑觐文的“音乐大同”思想,“使无比丰富之世界音乐咸归于大同,这样一种惊人的理想,要么是一种无比美好的乌托邦愿望,要么是痴人说梦般的奇思妙想”。[30]但是,仅从思想的内容和世界音乐的丰富性价值观来看待这一思想,还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笔者看来,这种思想的价值在于它预先提出了一种新的时空感,为的是解决中国音乐如何在现代世界音乐中定位这一危机。
“大同”一词源于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寄托理想社会愿望的精神家园,在面对列强入侵、国家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大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近代中国知识人批判现实、谋求民族独立和自由、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郑觐文熟悉儒家经典,自易获致大同的理想,他要用“大同音乐”助益世界文化运动,促使世界走向统一。他说“今也,世界大通,一切事业胥归大同,音乐为直接自然体,当为一切事业之先导。”[8]1920年(民国八年),郑觐文将“琴瑟学社”改名为“大同乐会”。[2]
为了构建大同音乐,郑觐文首先为音乐的起源作了“世界化”的解释:“音乐之产生,由于造化大法,纯全天然性质,与他种学术不同,非人力所能改造。”[8]既然音乐是天然产生,与人的创造无关,则自然泯灭了国界之别和中西文化界限。如此一来,中国音乐的存在价值变得理所当然,同时也推导出“音乐大同”蓝图里,中国音乐自然也有一席之地。其次,郑觐文批评否定中国音乐价值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雅颂清燕诸乐体与西方音乐一样都是自然地产生,而不是古人一时冲动之创造,以音乐起源的“世界性”取消了音乐的时代性,从而消解了中国音乐落后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音乐具有自然的独特性,应成为大同音乐的一个积极的因素,它不应该也不会在发展中被淘汰,若无中国音乐,世界音乐将不完全。再次,他承认西乐的科学性质,但不认为这是一种“至善尽美”之乐体,只有将西乐与自然性质的中乐融会贯通才能创造出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家的为全世界所公认的音乐样式。正如他所说:“本会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挈其精华,提其纲领,为世界音乐开一新纪元,以完本会大同二字之目的。”[15]可见,“大同音乐”是经由中西两文明中最进步的因子结合而成,它代替世界各民族、国家的音乐而具有了“万国语”的性质,由此,“大同音乐”不再被当作中国、或西方所特有的,而成为整个人类所共有的财富,为全人类所共享,而这正是中国“国乐”的未来。
从表面上看,“大同音乐”似乎带有超越民族之上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具有世界主义的特征。但是,实质上,这是一种以世界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其所表达的是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新的时空语境,从而有可能把中国“国乐”重新界定为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个完整部分。正如阿里夫·德里克在讨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同”思想时所提出的那样,在近代中国,“大同社会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前是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阶段。这个乌托邦的名称和种种优点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乌托邦传统,但其动力则在将来——而且是一个超越了中国自己的世界并且把中国刚刚成为其中内在一部分的世界社会作为自己的范围的将来。”[31]这也是郑觐文构建大同音乐的根本意图。对于郑觐文来说,他要把中国“国乐”“世界化”,从而在这个以改变全世界和世界文化的人为最终目标的“大同音乐”中,使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主体,中国“国乐”也将成为现代世界音乐体系中有地位的成员。由此可见,“大同音乐”是郑觐文为中国“国乐”立足世界、走向世界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结 语
在构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下,郑觐文与其领导的大同乐会将国乐视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国乐的国家性质及其对民族、国家的建设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中寻找到了代表天朝帝国的“雅乐”和“燕乐”,将之奉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乐,认为这种国乐是继承了中国音乐文化的道统,是真正的“中国性”之体现,希望以此建筑其合法性基础。然而,在重建国乐抵抗西方音乐威胁的同时,郑觐文却以西方音乐为权威和依据,通过设定大同音乐的新的时空图景,试图借此引领国乐走向世界、重新确立中国音乐在现代世界音乐中的地位。郑觐文的“国乐”建构其实并不切实际,还具有一定的保守性。首先,随着清王朝的颠覆,代表天朝帝国的最高水平的雅乐和燕乐也一起被留在了历史中,在没有样本、没有参照的情况下,单凭想象显然是难以恢复和还原的。其次,近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音乐代表进步和科学,是世界音乐发展的方向,日益成为音乐界的共识。郑觐文对这一思想文化变动趋向虽有足够的认识,且积极地学习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以重建国乐,然而,激进而盲目的改革,最终忽视了中国音乐自身的特性,而粗制滥造的乐器改革缺乏科学性,简单拼凑的乐曲改编也被批评为单调而无和声。而将那些改编的古乐曲作为新国乐和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在那些经西方音乐熏陶成长起来的音乐人看来显然是保守和落后的,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音乐的前途不在于整理和保存,成为供世人瞻仰的“博物馆”,而在于全新的创造。1931年,萧友梅在《对于大同乐会仿造旧乐器的我见》一文中表明:“整理国乐”并不能单靠仿造旧乐器,而是包括了考订旧曲、改良记谱法、改良旧乐器、编制旧曲等内容和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创作有民族特性的新国乐。他在1939年《复兴国乐我见》一文中再次强调,从旧乐及民乐中所搜集的材料,是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础,而他在上海国立音乐院开设“旧乐沿革”课程,以及发动整理旧乐工作,目的正在于让学生能充分利用中国音乐文化遗产,以创造新的中国国乐。[32]与大同乐会的根本区别是,刘天华把研究传统音乐和输入西方音乐作为两种手段,而将新国乐的创造视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改进国乐,创造新的乐谱,给国乐一种新生命”,“我们想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的艺术。”[33]由此可见,在当时大多数音乐精英看来,中国国乐的进步和出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国乐,而对传统音乐的改造和利用则是创造新国乐的基础和途径。在这种“国乐”观念的支持下,创造新国乐就成为了“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评判标准,大同乐会是以复兴和改造传统音乐为目的,自然被视为“复古”“守旧”的代表而屡遭批判。
最后,在关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上,从国乐的内容看,古代雅乐和燕乐显然不适合作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因为,雅乐和燕乐作为古代宫廷音乐,满足的是传统帝国官方政治的实用需要,其受众对象仅限于统治阶层,而对下层百姓的影响甚微,它们只能是作为官方阶层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并非是中国国民这一社会群体普遍认同的音乐传统,选择一种没有下层百姓基础的音乐作为国乐的内容,将很难在国民的思想意识中建立起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事实证明,嗷嗷待哺的老百姓并未对既陌生、又不能解决温饱的大同乐会的国乐演奏感兴趣,他们对于国乐的态度仅仅是出于一种“好奇心”[34]①贺绿汀在《听了祀孔典礼中大同乐会的古乐演奏以后》中这样描述国人在祀孔典礼上聆听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的情景:“在这繁嚣而单调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四周的人摇扇声及细语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有些人在那里讨论那些乐器的怪形状,渐渐有喧宾夺主之势;大多数人都在那里期待着这‘中和韶乐’的结束”;“这样的管演乐终止之后,接着就是殿上的报告与演讲,这是殿前的群众所听不见的,所以大家都为好奇心所驱使,一齐围上来请教这些演奏员:‘这是什么?’”。。因此,要完成对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必须重新创造一种面向全体国民的共同的音乐语言,使之在意识层面融成一个活跃而自觉的大众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以此来构筑全体国民对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才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