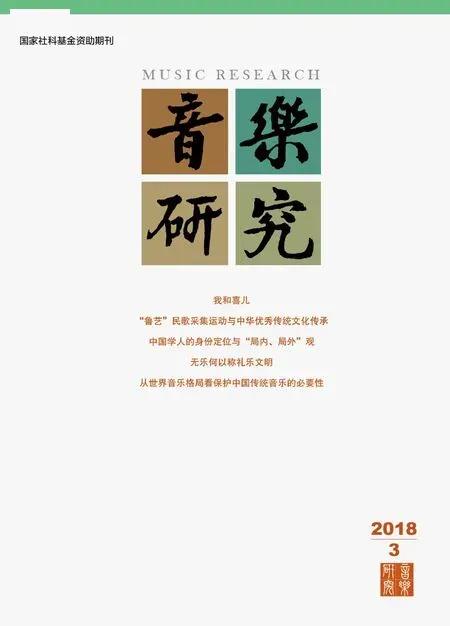中国学人的身份定位与“局内、局外”观
文◎张振涛
民族音乐学有一对基本概念:“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或“主位、客位”(emic/etic)。这对术语进入中国音乐学界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事,但学术脉络却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的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对待超布连岛人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相沿成俗的做事方式,基本做法就是让其自我呈现,不加干涉,以此立场概括出两个“关键词”。这对概念的大面积传播,自然是田野考察在人类学主体地位的确定和操作规范中采访与被访两种关系的逐渐确立。中国学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西方学术界处理与“在地”关系的预设立场,也是因为处理城乡关系时遇到了大体相似的情况,特别是21世纪以来对“干部”身份的质疑和对居高临下态度的克制以及摆正平视位置的调整。概念虽然建立在西方二元认识论基础上,但的确让中国学者保持了适度清醒,使之尽量不干预“文化持有人”的“日常”,避免“改造民间陋习”“封杀封建迷信”“创造新传统”等“善意”的动手动脚。
但是,作为传统文化培养起来具有“文化宣示者”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像研究“他文化”的局外人(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不干涉局内人的“日常”?能否像《锁麟囊》唱的那样“袖手旁观在壁上瞧”?现以“冀中学案”为例,观察学界的惯常做法。
一、反思身份定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不但没有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采访中袖手旁观民间乐社的恢复,而且积极主动“集体”参与了“文化复兴”的一系列活动。乔建中、薛艺兵等作为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急切表达了渴望民间恢复传统的态度,不但对前路未明的会员晓以大义,而且对无动于衷的地方政府苦口婆心,更有对懵懵懂懂的媒体介绍引领。联手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国家媒体报道宣传,引荐乐社到中央音乐学院、“国际音理会”等重要机构举办音乐会,介绍吕骥、赵沨、高占祥等领导前往参观以及提交政协议案等,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实际功效。联手媒体,游说政府,呼吁社会,演变为局内人、局外人不分彼此的抢救遗产运动。“起向高楼撞晓钟,不信人间耳尽聋”(王守仁)。高调干预,颇为奏效。学者官员,媒体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冀中,给自“文革”以来完全丧失自信的民间乐社注入了生机。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行为,不会让学术界惊讶,换了另外的单位也差不多,只不过以研究传统音乐为己任的学术机构的专业定位而意识得较早、行动得较快而已。无论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当时的行为确实起到了学术界不加干预的“自然状态”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到的效果。
问题来了:此类行动中我们到底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我们日趋日深地走入“文化复兴”运动成了一身兼具双重身份、采取两种行为方式的“人”——既是为研究而探索的“局外人”,又是为乐社找寻生路共谋大局的“局内人”。为什么我们不会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袖手旁观、提醒自己不加干预并以此自戒?
儒家传统有种超越学术的强烈实践性和政治化倾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衍生出的政治理念和国家体制下的学术模式,使学者面对民间疾苦,绝不会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保持局外人的客观冷静。帮助农民是文人天职。儒家文化的“国家化”决定了知识分子对待本土文化的扶持和庇护态度。当时的反应及接下来持续三十余年的后续行为,不仅是出于对“文革”的反驳和有意而为,而且是传统教育的自然结果。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政治高度”或“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如说是来自儒家话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伦理信条。理念不仅是20世纪的精神遗产,而且是历史遗产。诸如“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等众多历史的思想资源,都成为谨记于心的“集体无意识”。在职则“为官一方”,退耕则“教化乡里”,退居二线、三线还要“化作春泥更护花”。无论身处庙堂还是远居江湖,都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文人。骨子里脱不掉的脾性让所有了解民间疾苦的人,毫无顾忌“身份”而情不自禁伸手相助。一代代、一茬茬学者,深度参与乡村变革,自我牺牲在所不辞。中国书生的本色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身处其中的历史景深。
我们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学者的头衔有:研究民间音乐的学者、复兴传统的斗士、官员面前的讲解员、民间乐社的代言人、大众的吹鼓手、鼓动社会赞助的活动家、帮农民找活路的经纪人……“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令一身尝尽矣”①袁宏道《锦帆集·丘长孺》,转自陶慕宁《晚明文人的真情与矫情》,《读书》2016年第2期,第81页。。头衔与其说是别人给我们戴上的,不如说是自己头上长出来的,是文人这个“物种”自然兼备的!如同巴尔扎克《幻灭》形容的:“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好了出世的。我们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这个“脑袋”,耐人寻味。
把自己的行为作为一个思量与拷问的学术话题予以讨论,探究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自身问题,是反思问题的扶手。“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等历史信条滋养的群体,能否做到抱臂旁观、隔岸观火、无动于衷、拿着笔记本和照相机站在心急火燎的农民乐师旁边不置一言?能否看着“农夫心内如汤煮”而优哉游哉“把扇摇”?能否看着薪传无望的乐社嗷嗷待哺、饥肠辘辘、手握话语权却不动嘴、不动手、不挽袖子添柴助燃并呼吁众人拾柴火焰高?纯粹西方式的“局外人、局内人”二分法能否定位我们?或者说,这对影响世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对“本土化实践”到底合不合适?
回想冀中学案一场场包含“正剧”“悲剧”甚至“闹剧”(帮助发展经济之类)的“剧情”,不能不说,学者们控制不了帮扶民间的冲动,被访者也控制不了拉我们下水的冲动。舞台上不单有观看的剧情,还有自己跑上台去的表演。乐社复兴,风生水起,除了乐社的风声、媒体的雨声以及政府的风雨交织声,就是音乐学家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嗓门有时最大,至少不比别人小。身处中国田野,每位学人都多多少少干预了采访点的“日常”和“自然”,与民间艺人一同经历复兴过程中病魔般的苦痛,体会只有“入道”才能感受的纠结和困惑,这些恰恰是学术界之所以写出那么多考察报告并且笔力日深的原因。
因其如此,每位音乐学家在深入采访时都会自问: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难免不充当“运动员加裁判员”“演员加导演”“乐手加指挥”,乃至给了一个连自己都吃惊的定位:既不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也不是安分守持的“局内人”,而是抱着知识分子良心参与其中,甚至难免越俎代庖,更难免“好心办坏事”的“文化参与者”。
将自身视为一个“客体”加以考量,自然要对西方“二元对立”模式进行反思,回答中国文人无法与本土分开、无法与传统分开的行为方式,进而考虑是否要另立一种“身份模式”。民俗学家高丙中解析道:
从传统认识论来看,民俗学的知识群体是认识的主体,民俗现象是认识的客体。但是,中国民俗学的当代发展恰恰不是基于这种截然二分的认识论可以理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民俗复兴的过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民俗现象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如此呈现的,而是逐渐恢复、生成的。而且,这个由恢复与生成的机制所得到的“复兴”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公共部门(政府、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不断介入的过程。其中,民俗学人发挥了专业性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在村庄(社区)层面还是全国层面,民俗学人都以自己的专业努力参与了民俗复兴,今日的民俗复兴状态或局面毫无疑问是民俗学人参与造就的……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评估把对象限定在学科内还是把对象定位在时代中,会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果。②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
如高丙中所说,以往的定位模式是把“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政府”分而视之。民俗(复兴)与时代(变迁)、民俗之民与政府机构的关系,被解释为“反映论”的单向被动模式,而不是“共生论”的多向主动模式。
两种理念,一个是反映论的,一个是共生论的……以共生论来看,这四组概念所指的实体都可以是主体,都可以是主动者,而任何结果都应该被看作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政府等等,都不是一个被决定的消极的方面,恰恰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反映论的认识论指导我们看见单向关系和结果,共生论的实践论引导我们关注动因和复杂互动的过程。③同注②。
中国学者的田野,不是国外学者的“异国他乡”,而是本乡本土。我们兼具“观察文化事项”与“参与文化事项”双重身份。乡情抑制不住。音乐学家一开始就面临两难,既是西方定义中的“客位”,又是本土文化中的“主位”,而且是心甘情愿行动起来改变旧貌的“主位”。这个行为主体与西方二分法中的截然对立,无法无缝对接。引进概念,进退失据,面临严峻挑战。换句话说:外国概念与中国实践,严重脱榫!
高丙中从认识论层面反思“民俗之民”与学者关系,是现实层面,而历史景深则是“学优登仕、涉职从政”的强大传统。这重景深让我们看到自己沿袭的自20世纪50年代“保护扶持民间文化”的“历史语境”和“预设立场”。
“非遗”时代(2005年后),学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工作,投身其间是历史文化的“习得”,未加思索。评选“冀中笙管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的决定,既符合学术标准,也符合政府要求。我们的“学术身份”是教授、研究员,“行政身份”是国家干部,智库谏言者。决定既是“政府行为”也是“学术行为”。20世纪50年代以吕骥、周巍峙等为代表的兼具官、学于一身的传统,沿袭旧制,因此“国家级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全部由学者构成。一方面说明知识分子得到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文化部门基于本土实践的中国经验。从长远来看,此类行为是“帮了大忙”还是“帮了倒忙”都非一天半天所能看清,民间文化也绝不是什么基金、“非遗”保护拨款所能扶持和培养的,但无论如何,学人的行动至少起到了一点作用,就是再也没人把“文化遗产”视为“封建糟粕”了。至少在纠缠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封建糟粕”还是“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全社会达成了共识。
二、适度干预
干预或不干预,对民间乐社命运攸关,其中学者的行为到底是应该现实地看还是应该学术地看?到底是应该以现实的目的为判断还是以学术的目的为判断?为避免离题太远,暂不列举太多文化层面的事,只看几则技术性较强的事,以此探讨学者的干预到底合不合适以及干预到什么程度更合适?怎样达到有分寸而不至于把自己与“在地人”混为一谈。
事例一:涞水县南高洛的单明、单伶兄弟,是音乐会里最聪明的乐师。因为懂简谱,所以把工尺谱翻译成简谱,觉得做了一件谁也做不来、能够与“现代”沟通的大事,并带着自豪向我们展示,当然是希望得到专业音乐家的鼓励。看到这份真是下了一番功夫、辛辛苦苦的“成果”,我们当头泼了一瓢凉水,毫不客气地批判“破坏传统”。话一脱口,他们大为惊讶,疑惑地看着我们,也不解地相互观看。我们的话很实在:“如果音乐会用简谱、五线谱,城里人还来干什么?你们俩会把英国学者钟思第气跑!”单明、单伶始而眉头紧锁,继而笑逐颜开。劈头盖脸的一席话,非但没惹他们生气,反而觉得不再生分了,讲心里话了。农民乐师太聪明,一听就明白,马上懂了“现代”理念:只有传统才吸引人!无论如何,兄弟俩是听进去了,这类行为再未发生。从技术层面上提倡一些事,叫停一些事,及时纠正跟着城里人跑的习惯,把新理念告诉人家,此个案让人沉思:我们的干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事例二:南高洛音乐会有部演说民间故事的“善书”,属于笙管乐伴奏的坐唱形式。这让我们想到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鼓吹曲辞”。也就是说,鼓吹乐这个品种历史上也是唱的,而非以前所认识的那样仅仅是吹的。这个传统很少见了。听到会员们叙述原来“文坛”(专门唱的人)在葬礼上伴着亲人战栗的哭声,翻着木板夹线装书,念唱“泰山韵”,并于20世纪60年代收束为最后一点音量时,我们禁不住为没赶上那个时代收录其音响而叹息。这引发了他们的警觉和重视。起先,也没想到自己的话有多重。但这无疑发出了信号:这是一种渊源深厚的传统!在“会头”蔡安带领下,经过一年多努力,“文坛”四位乐师(蔡安、蔡然、蔡海增、单明奎)竟然把中断了十几年的“前韵”“后韵”以及间插其间数支“曲牌”一点点衔接起来。乐社延续着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合奏方式,当整个社会不再以此为荣并视其为多此一举时,也丢弃了稀少的传统。遇到我们,他们又一次对拥有过独一无二的“对口”(吹韵同步)而自豪并燃起恢复热情。隔了小半年,回到南高洛,他们竟然齐声高唱“泰山韵”!那场景令人难忘。看到“费尽移山心力”的结果,我们无比震惊。看着我们胀满红晕的脸,他们也胀满红晕;看着我们无比兴奋的表情,他们也无比兴奋。终于把鼓吹乐的古老传统恢复了,让“唱”的鼓吹乐声势复振。老百姓相信音乐家,以专家标准为标准,在没有要求这样做的情况下,却因我们的“身份”点燃了“自觉”,催活了一个几近淹没的坐唱形式。这个结果既体现了乐师恢复传统的坚韧,也体现了学者介入的效应。这也让人沉思:我们的干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事例三:2015年正月十五,我们参加南高洛音乐会、南乐会、北高洛音乐会、南乐会四会的“穿插”仪式。拜会踩街,例年仪式。按规矩,南高洛音乐会“会头”蔡玉润,带领乐社从“官房子”(乐社中心)出发,逐个到各乐社拜会。第一是本村南乐会,在“官房子”演奏一曲,以示敬意。“穿插”持续一上午,一路下来很辛苦。乐师偷懒省略,节省气力,为了四家乐社汇聚一堂时,在有点竞技意思的最后放开气力吹。所以,到了南乐会“官房子”,就想省略不吹了。我示意蔡玉润按规矩来,面对人家的盛情一走了之,不合适呀!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知道我的提示是对的。于是带领乐社吹奏一曲,仪式完整无缺。这种提示也让人沉思,我们的干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事例四:钟思第抱持的态度与我们不同。他是西方人,作为局外观察者,尽量不介入,不影响南高洛音乐会的自然发展,更不鼓励像屈家营音乐会那样到北京演出,尤其厌恶到国外演出的请求,这反映了西方学者的态度。他希望看到“原生态”,不希望看到“被创造的传统”。对于太多被文化馆“创造的传统”,他像中国学者一样痛心。这一点说明了学者对上辈人在民间造成的“恶果”保持的警醒。然而,不能不说,恰恰是因为钟思第的英国身份,让视外国学者为“国际标准”的农民获得难得的身份自信。这还是让人沉思:我们的干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上举荦荦细端者有四,我们愿意说:比起政府干预,我们宁愿学者干预;比起文化馆干部干预,我们宁愿院校教授干预;比起法规政策干预,我们宁愿技术层面干预;比起大事干预,我们宁愿细节干预。“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吕思诚《戏作》)。
三、核心概念本土化
“局内、局外”是民族音乐学区别于系统音乐学的关键之“核”。本土实践已有几十年,积累了诸多“中国经验”,这使得当代学者有条件对核心概念做出学理层面的反思。学科依赖的“工具”性概念及隐含的技术危境,使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工具”本身。我们应该成为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思辨者。
我们是什么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这重要吗?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中国文化的“当事人”!这是我们与西方学者的根本差异。
诚如高丙中对当代民俗现状分析的那样,冀中乐社起死回生,上百家音乐会大面积恢复,不是“自然”结果,而是学术界言说、正名、推介、扶持的“人为”结果。没有音乐学人的参与干预、投书献文、驱走奔竞、上达天听,就没有当前现状。眼瞅着民间生生不息、捂都捂不住的复兴愿望,“冀京津音乐会普查小组”与当地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否是以造福乡里为己任的读书人的“自然”?冀中音乐会从被定位为封建迷信到陡然变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与学人从1986年开始的积极参与和发挥出巨大建设性作用密不可分。若依主客二分法的原则做袖手壁上观,不会产生这种局面。所以,西方二分法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持。
“局内人、局外人”的设定是个没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属性的概念,是种把不同于西方的“局外人”假定为与西方学者相同并采取相应态度的界定。四海异俗,任何概念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区分作为本民族一分子的中国学者与作为“他者”一分子的“局外人”之间的区别,两种局外人因教育背景不同而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上有天壤之别。二分法在形式逻辑和理论推定模式上,显然忽略了中国学者的历史背景和由此养成的做事习性。认识行为主体是谁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中国学人是在国学语境下与国家行为融为一体甚至本身就属于其中一分子的群体。我们愿意“卸除”身份,当然不是完全出于对西方学理的遵循,而是出于不愿意再像前代人那样“改造民间”的自我检束。困难的是,我们常常出自本心,不自觉地“出手”。之所以重新检讨工具性概念,就在于要给自己的行为范式提供理论依据并据以探讨应该于什么范围内“出手”,在什么范围内“住手”。中国学者遇到的实际问题,既不能囿于西方定义而缩手缩脚,又不能无所顾忌而指手画脚。所以,就要运用学术智慧挑战定义,而非轻信戒律教条。
从“共生性”立场反思的意义还在于,“正方反方”并非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而是既有此亦有彼,既彼此交叉又彼此对立。身份跳跃两域,中国学人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与研究对象对立的另一客体,而是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很强认同和连带的“文化实践者”。
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可否修改一下用到此处?既是“参与式观察者”也是“参与式实践者”。“参与式观察者”或“参与式实践者”并没有取代“局外人、局内人”成为“法定语言”的意思。学术界提出过多种“中间层次”,既不同于局外的不干预态度,也不同于局内的干预。这或许能够使人摆正自己的做事方式。如此定位,我们是否就能迈出非常不同而后果深远的一步,如果学术界既能深触现实又有足够思力超越既有定义的话。
20世纪,人类学创造了整套表述体系,即使不喜欢的人也会从内心服膺其冰冷的“理性”。人类学家用手术刀一样冷酷的工具,解剖研究对象并发明了成套概念,把从理念分析到操作层面的步骤做到极致。19世纪以来涌现了大批极富创造力且极具说服力的著作,创造出社会科学的新天地。音乐学领域亦复如此。民族音乐学家梦寐以求的“工具”似乎都摆到面前了。然而,越是深入家乡,越感到中西差异。新奇感过后,带着反思目光解读本土事项,越来越觉得全盘接受碍手碍脚。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确是个关键认定。不仅因为中国与西方研究对象不同,而且做事方式不同。原有界定无助于中国学者施展手脚,难免产生不接地气的隔阂以及不能回馈乡村的伦理自责。中国音乐家逐渐学会了从比西方秩序更庞大的传统秩序中寻求自我定位的方式。这既是对现有学术体系的反思,也是对摆脱此前种种肤浅操作的认知。今日中国之民族音乐学已非原有之西方民族音乐学,今日之语境也非他者语境的翻版。“拿来”“采借”“融入跳出”,创造性地开拓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学术范式,摈弃其中包含的自我束缚甚至自我摧毁的悖论,当然是中国音乐学的责任。鞋子合不合脚,概念适不适合,都需要“时间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