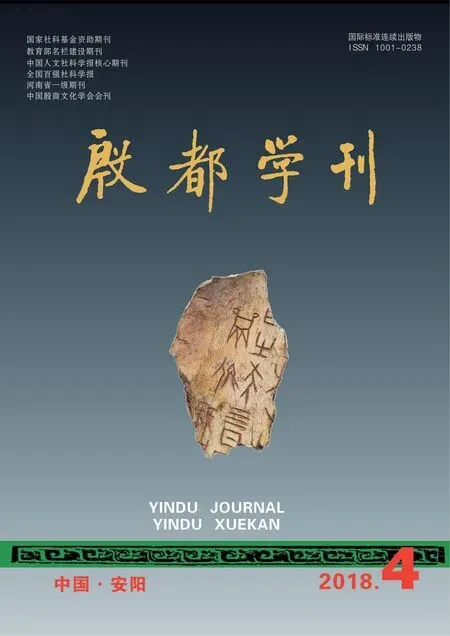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折光
——刘壎古文理论探析
崔花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刘壎为宋末元初的江西诗人和评论家。刘壎的《隐居通议》卷十三至卷十九有文章评论七卷,多摘录前贤的文章并加以品评。从他所选录的文章和他对所选录的文章的品评中可见其文论思想。作为宋元易代之际的文人,他的思想既体现出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元初文学尚新求变的影响。他主张文章要关乎世教,根据性理;有诗文尚新之论,却反对刻意求新;崇“简古”,尚“风骨”,重“自然”,这些都体现出宋元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一、关乎世教,根据性理
刘壎比较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因而推崇关乎世教之作;又因为受宋代以来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文章要根据性理,内外兼修,从而非常推崇曾巩之文。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刘壎比较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注重文章的教化作用。在《隐居通议》卷十一《答谌桂舟论铭文书》中,他说:“天地无全功,能生人,不能使斯人之有传。传者,以文章耳。”[1](卷十一)认为文章之功甚至可以与天地并论。天地可以生人,而文章可以使人名传后世。这其实也就是曹植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由于刘壎身处易代之际,他所选录的文章多为忠义奋发之作以及论及人物出处进退的文章。比如,他非常赞赏谢枋得为文中的忠愤之意。谢枋得为宋末忠臣义士的一个典范。在宋亡之际,他毅然担任江东制置使一职,组织当地的军民奋力抗元。在宋亡之后,他易服变姓,隐居乡里。为拒绝元廷的征聘,他以死殉节。《隐居通议》卷十六选录了谢枋得的《程汉翁诗序》,刘壎评论道:“叠山翁,信州贵溪人,素有文名,笔力奇劲。此序不尽其所长,而忠愤之意见于言外。”[1](卷十六)《隐居通议》卷二十还收录了谢枋得的《江东运司策问》:“景定中,江东转运司行贡举,引试北方士人一科。时叠山先生谢公枋得为考试官,发策以中原为问,问目笔力甚伟,当时远近传诵。”[1](卷二十)也反映出谢枋得的忠义之心。
刘壎所选录的许多文章还关系到人物的出处进退问题。比如,刘壎在《隐居通议》卷十五选录苏辙所作《管幼安画赞》,称赞其“有为而发”。此文是苏辙晚年对自己一生宦海浮沉的总结,表现出他对管宁在乱世中隐居求志、明哲保身的生活方式的赞赏。苏辙认为管宁在战乱之际,既能够布衣蔬食,饮水而乐,又能够躬亲祭祀先人,超脱于时代和战乱之外,而为天之逸民,令人钦慕不已!清人张伯行说:“颍滨晚年连遭贬斥,故慕幼安之见几远患,而为之赞,犹东坡之慕渊明也。”[2] (P198)而综观刘壎之一生,他虽然有用世之志,在晚年出任儒学教授一职,但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他所录苏辙此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他自己对易代之际出处进退问题的思考。
刘壎所选录的这些文章,关乎忠孝节义、出处进退,通过对这些文章的选录和品评,透露出传统儒家思想对刘壎的影响之深。同时,由于受到理学的影响,他还主张文章要根据性理。以此为标准,他对欧、苏之文一洗昆体之弊,表示赞赏,但对其文不及理学则表示惋惜。他在《南丰先生问学》中说:“濂洛诸儒未出之先,杨、刘昆体固不足道,欧、苏一变,文始趋古。其论君道、国政、民情、兵略,无不造妙,然以理学或未之及也。”[1](卷十四)而对曾巩之文,他推崇备至:“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1](卷十四)刘壎认为曾巩之文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欧阳修的文风,而且因为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1](卷十四),在理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刘壎还认为,对曾巩之文要静心探玩,才能得其深意:“公之文自经出,深醇雅澹,故非静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1](卷十三)(《涪县学记》)由于刘壎主张文章发自性理,因此他以“内外齐观”为作文的最高境界。他在《隐居通议》卷十八文章六《象山小简》中选录陆九渊《与张伯信》(《象山集》卷十七),其文曰:“风露凄清,星河错落。月在林杪,泉鸣石间。薫垆前引,茶鼎后殿。方塘为鉴,回溪为佩。冰玉明莹,霜雪腾耀。则喷玉新亭,真蓬壶瀛州也。”此文用寥寥数语,不仅描绘出了一幅清静幽深的夜景,其中还蕴含着对自然景物的静观体察和对生命意蕴的体会。刘壎对此评论道:“余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语清俊如此,真可为法。但他人当此境界,惟供风云月露之姿,先生则内外齐观,即鸢飞鱼跃之妙矣。”[1](卷十八)认为文章不能仅仅停留在“描摹风云月露之姿”,而要做到“内外齐观”,这样才有“鸢飞鱼跃之妙”。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不仅仅对自然景物做浅层的、形貌的欣赏,更重要的是要将自我的生命融入自然,达到物我浑一的人生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在创作不失情趣的同时做到观物体道。[3](P48-49)从中也可见理学对刘壎文论思想的影响。
从刘壎所录文章及其评论可以看出,刘壎虽然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不像南宋理学家那样认为“作文害道”,但他认为道学高于文学,文学为道学之余事。比如,他称赞其朋友傅自得“深明《春秋》之学,而余事尤工古赋”[1](卷四)(《总评》)。在所录《涪县学记》中,他也说“夫知道者于文必知,文固学之余事也。”[1](卷十三)他称曾巩“余事文章,信意翰墨”[1](卷十八《象山小简》)。而刘壎于去世之前所作之《一斋记》则表现出对自己没有一心于道学的深切悔恨之情,并让其孙刘深以此为戒。这些足见理学在刘壎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文统与道统的分合是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自韩、柳古文运动标举“文以明道”以来,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认为文章仅仅是载道之具而已,程颐则有“作文害道”之论,直接把文学放在理学的对立面。而与朱熹和张栻齐名的吕祖谦则主张融合文道。吴子良在《筼窗集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学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而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4](卷首)而融合文道也是元代许多文人的自觉追求,如由金入元的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载王郁之语曰:“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元初的南方作家刘将孙也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5](卷二十九)(《赵青山先生墓表》)。刘壎这种重视文学,但主张文章要根据性理的主张,正是元代社会文道并重的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二、主张语意不陈,反对刻意求新
由于受到理学和科举时文的影响,南宋后期,文风卑陋。元朝立国后,废除科举制度。如此一来,一方面,读书人失去了进身之阶,但另一方面,许多读书人也开始理性地反思科举时文的弊端,而提倡求新求变。刘壎也批判科举时文,有诗文尚新之论,但又反对诗文创作刻意求新而走向怪奇。
关于科举时文的弊端,刘壎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科举程文束缚读书人之身心,埋没人才,为害甚巨。而元代科目之废,是为读书人卸下重担,是天赐读书岁月,可以放意为文,体会古代圣贤之自得之乐。[6](卷十一)宋濂在《剡源集序》中也历述宋季文章之弊:一为四六俳谐之应用文;二为穿凿经义、隐括声律之科场文,三为空言明道,喋喋不休的语录文,四为徒称宏博,不可以句的伪古文。[7](P193)元初的南方文人一方面承袭了宋代的文风,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从而开始反思宋季文风,于是在文坛上出现了求新求变的倾向。如戴表元的“清深雅洁,化腐朽为神奇。”[8](P1424)而程钜夫“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9](卷四十)江西文风本来就有尚奇、尚险的特点,例如刘辰翁在《不平鸣诗序》中说:“凡歌行曲引,大篇小章,皆所以自鸣其不平也。而其险哀,有甚于雷风星变、山海潮汐者矣,豫章杨氏所为诗是也。”[10](卷六)他认为奇险之作才可以表达内心之激烈的情感。刘辰翁还推崇并评点李贺诗,使读长吉诗、效昌谷体,成为元初的一时风气。程钜夫在《严元德诗序》中也说:“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余习时有存者。无他,李变眩,观者莫敢议;陈清俊,览者无不悦。此学者急于人知之弊也。”[11](P72)而诗文一脉,这种尚奇险的风气在文章写作上也比较明显。徐明善在《学古文会规约序》中说:“至元庚寅至大德乙巳,予于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异乎昔之士也?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12](卷上)其中“钩棘以为文”也指刘辰翁一派“諔诡变化”的文章风格。由此可见,刘辰翁诗法李贺、陈师道,而为文尚奇险,在当时影响颇大。
在元初这种反思前代文风,力求新变的文坛风气下,刘壎论文也主张要尚新,这里的新,包括立论之新,如其《隐居通议》卷十录苏轼《序晁君成诗》曰“达贤者与有其实而辞其名者皆有后”,刘壎称赞“此论甚新,可以为世戒。”[1](卷十)在《青山文集序》中评论赵文之作品曰:“盖君所著,体裁丰茂,新意川赴,抚事感怆,时有千古之愤。”[6](卷五)但刘壎又不主张刻意求新而走向怪奇,这在其文论中多有表现。唐代樊宗师之文艰涩怪僻,刘壎在《隐居通议》卷十五《唐樊宗师文》中选录其文《绛守居园池记》称其“硗戞磊块,类不可读”,并对其文进行逐句批驳,刘壎认为“凡文章必有枢纽、有脉络、开阖起伏、抑扬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诡异险涩难读为工,其于六经简严易直之旨合乎?否也。”刘壎认为如果为文无所统纪,即便一味以奇险相高,也不能称之为文章。在《隐居通议》卷十五文章三《龙川宗欧文》中,他也说:“欧、曾、王、苏四家为宋文宗,然皆未尝用怪文奇字,刻琢取新,而趣味深沈,自不可及。”[1](卷十五)尚新而反对怪奇,刘壎对于诗文陈腐之疾,提出了自己救治之法。他在《隐居通议》卷十八文章六《诗文取新》中说:“语意不尘,诗文之一妙也……熟复《庄》、《骚》即不尘矣。夫《南华经》与《楚辞》二书经千有余年,然一展读,则焕烂如新。学文者能取《庄》、《骚》玩味之,又取《世说新语》佐之,则尘腐之疾去矣。”[1](卷十八)刘壎所举三书或是雄奇险怪,或瑰丽奇特,或用语清峻,作文者如能对其熟读妙悟,得其神理,自然不落尘腐。
三、崇 “简古”,尚“风骨”,重“自然”
刘壎论文以“简古”为最高审美标准。与崇尚“简古”相联系,他也强调文章要有“风骨”。刘壎论文虽有尚古的倾向,但是他反对刻意仿古,也反对尚奇求险,而是主张自然为文。
刘壎论文崇尚“简古”,而所谓“简古”就是“简严有古意”。他以“简古”为衡文的最高标准,并不轻易许之于人。《隐居通议》卷十八文章六《平园文体》摘录刘克庄《跋周益公亲书艾轩林公光朝神道碑后》曰:“平园晩作,益自摩厉,然散语终是洗涤词科气习不尽,惟艾轩志铭极简严有古意。”[1](卷十八)刘壎认为刘克庄评周必大的评语并不确切,称“平顺典雅则有之,谓之简古则未也”,认为周必大此文虽算得上平顺典雅,但尚未达到简古之境界。《隐居通议》卷十七文章五《魏鹤山文集序》称刘玉渊“其笔端透彻处,痛醒人意。第腴赡之过,反伤泛滥,若加揫敛之工,以造简古之味,足可名世矣”[1](卷十七)。也以 “简古”为衡量名世之文的标准。他还以“简古”之文与今世之文对比而突出今文的弊端。如在《张才叔义》中,他说:“南渡前,经义简实典古,有补世教,岂若近世浮虚磔裂者所为?宜为先儒之所深取也。”[1](卷十五)可见,刘壎认为“简古”有补于世教,是衡文的标准之一。
因为崇尚简古,刘壎论文从而注重语言的精炼,反对语言泛滥无归。对于“辞简意足”之作,他非常推赏。如在《半山总评》中,他对“抑扬有味,简古而蔚”的王安石散文表示赞赏。他还往往以“简洁”作为衡文的标准。其评《玉堂闲话》中所载《耶律德光灭晋事迹》曰:“此论词简而意足,非苟作者,殊不似五代卑陋之文。”[1](卷十五)他在《序乐全文》中,评诸葛亮《出师表》则曰:“简而尽,直而不肆。”[1](卷十五)他对于包恢的《范去非墓志铭》也推赏有加,称其“平生为人作丰碑巨刻,每下笔辄汪洋放肆,根据义理,娓娓不穷。盖其学力深厚,不可涯涘。独于予故人范君去非一墓志,简洁清静,足以写去非之平生。”[1](卷十七)刘壎所谓的“简洁”,虽然有平易之意,但也反对语言过于俚俗。如他对《东牟揽秀亭记》的评价曰:“亦简洁可观,但诗末句俚拙耳。虽缁流有此风调,然终非大雅也。”[1](卷十七)
“简古”的另外一层意思,则是主张文章有古意。这就牵涉到作文的师古问题。在元代,古文的写作一直有宗唐、宗宋之论,也有主张超越唐宋而直追秦汉者。刘壎论文便有崇古的倾向。他在《樊宗师文》中说:“夫六经之文,无不可读,而不害其为古。”[1](卷十五)称赞六经之文既简洁可读又不失古意。他论文以《左传》、《庄子》、《史记》为典范,尤其对司马迁、班固多有称赞。如在《文法》中,他说:“春秋以后文章之妙者世推《左传》、《史记》,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盖古人作文俱有间架、有枢纽、有脉络、有眼目”。以此为标准,他对于作文能学《左传》、《史记》之作者也非常推崇。他称赞其友傅自得之《大觉寺长明灯记》曰:“简严温润,自成一家。盖其学本于左氏,故无冗长之病。”[1](卷十七)在《曾文宗西汉》中,他还认为曾巩文章实宗西汉,有超越唐宋,而直追秦汉的趋向。他以曾巩所作序文与刘向《战国策序》相比,认为“向之序文冗赘,而先生之文谨严”[1](卷十四)。表现出他对曾巩之文的推崇。在《隐居通议》卷十四中,刘壎还选录了曾巩所作墓记《秃秃记》,称此文当时远近传诵,又称赞曾巩此文“笔力高”、“文有法度”、“实自史汉中来”[1](卷十四),表现出对曾巩作文能得《史记》、《汉书》文法的赞赏。元初文坛有宗唐、宗宋之论,宗唐者以韩愈为师,宗宋者以苏轼为准。刘壎则认为,不管是韩愈之文还是苏轼之文都是学习秦汉散文的结果。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崇古的立场。南朝宋袁淑作俳谐文《庐山公九锡》,而韩愈效仿此体作《毛颖传》。刘壎以为袁淑之文为六朝之体,而韩愈之文则祖《史记》,所以高妙。[1](卷十五)在《隐居通议》卷十八文章六《昌黎文法》中,他说:“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迁、固。”[1](卷十八)并以韩愈本人之语为证:“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1](卷十八)从而得出韩愈文宗班、马的结论。刘壎认为,苏轼为韩愈所作《韩文公庙碑》中之语:“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使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1](卷十八)为学《史记·龟策列传》中语,二者文法有相似之处。
刘壎论文重“风骨”,《隐居通议》卷二十二《拾遗》中,录他与赵必岊论诗文之语:“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1](卷二十二)他所谓的“风骨”多用来指代诗文创作所体现的生动凝炼、雄健有力的风格,其中也包含着语言文字的简洁凝炼之意。刘壎论文非常注重文气和骨力。如他在《欧公文体》中,称赞欧阳修之文时说:“欧公文体温润和平,虽无豪健劲峭之气,而于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长,则非他人所及也。”[1](卷十三)虽然他对欧文的温润和平、深婉至到表示赞成,但由此亦可看出,他主张作文亦需要有“豪健劲峭之气”。他还评论李华的《政事堂记》,认为此记“峻洁严健,足称名笔。”“与其《吊古战场文》俱可传诵。”[1](卷十三)《隐居通议》卷二十录谢枋得所作《江东运司策问》,有人对此策问提出了疑问:“策问当设疑问难,今一笔说去,似非问目。”[1](卷二十)刘壎则认为此文“文气振发,终是一篇好文字”[1](卷二十)。从中可见,刘壎认为文章要以表意为主,只要具备了文气和骨力,即便突破了文体规范,亦不失为佳作。
宋末元初的文坛之弊,不管是刻意仿古,还是尚奇险,实质上都在于刻意为文。因此,刘壎还主张自然为文。刘壎虽然崇古,但他反对刻意仿古,主张自然而得。他在《经文妙出自然》中说:“经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为也。”[1](卷十八)他还盛赞陶渊明之文“所以独步千古者,以其浑然天成”。他摘录林光朝《韩柳苏黄集》中语,论苏、黄之别曰:“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论韩柳之别曰:“则犹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他对林光朝此论深表赞同,称“此譬亦可人意”[1](卷十七),而他之所以赞同林光朝此论,在于林光朝此论是以自然与否作为评文的标准。《隐居通议》卷十三文章一选录欧阳修之文《跋晋帖》论古人法帖与今法帖之别曰:“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侯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欧阳修认为前人所作法帖皆无所用意,逸兴所至,挥洒淋漓,不过数行,而今人则殚精竭虑去学书,乃至终老而穷年,所作反不及古人高致。欧阳修于此论古今书帖之别,也在自然与作意之别。刘壎对欧阳修此论也深表赞同,说:“此论亦黎然当于人心。”[1](卷十三)
综而论之,刘壎的文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又由于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他主张为文要根据性理。针对受科举时文影响所导致的文章尘腐和刻板之风,刘壎主张为文要语意不陈。但是对于当时江西文坛上刻意求新而尚奇险之风,刘壎也提出了批评。元初在师古的问题上有宗宋、宗唐之论,也有少数文论家主张超越唐宋而直达秦汉。刘壎论文也有这种倾向。他论文以“简古”为最高的审美境界,推崇《左传》、《庄子》、《史记》之文,并且崇尚“风骨”,最后则以“自然”为旨归。刘壎文论既具有宋代文论的特点,又反映了宋元之际文论要寻求新变的趋势,是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一种折光。因此,刘壎文论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宋元之际文学思潮的流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