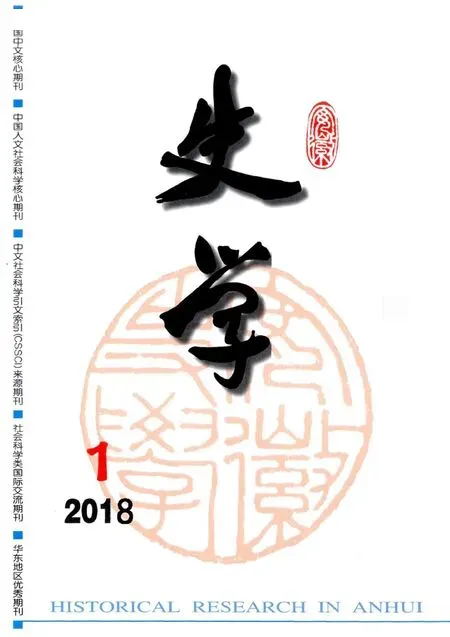刘秉璋学术活动述论
——兼论湘、淮军精神气质之异
吴怀东 尚丽姝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程晋芳、周永年语)桐城派风格之散文是清嘉庆朝至民国初白话文运动兴起前散文发展之主脉。1929年梓行的刘声木(1876—1959年)《桐城文学渊源考》《桐城文学撰述考》,发心于乡梓情结,是桐城派作为散文创作主流终结后对桐城派进行初步总结的两部重要著作,也是桐城派研究的奠基之作,其确认了桐城派作家范围及桐城派研究的大致轮廓。学术界对这两部著作研究比较充分,虽然对刘声木其人及其著述背景亦有所研究,不过并不深入。刘声木在刘秉璋诸子中排行第三,在《苌楚斋随笔》中对乃父刘秉璋读书、著述活动情况记录甚详,以显示自身学术其来有自且渊源深厚,惜乎学术界并未据此深究。本文即着墨于此,讨论刘秉璋的学术活动及其特点。
刘秉璋乃晚清淮军著名将领,其军政活动已受到当今史学界的关注,而其学术活动则尚待清理。
刘秉璋(1826—1905年),字仲良,安徽庐江人,《清史稿》有传。刘秉璋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刘秉璋与潘鼎新早年赴京应考即拜入李鸿章门下。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占据江宁,刘秉璋随钦差大臣张芾至皖南。李鸿章受曾国藩派遣组建淮军进入上海镇压太平军,即奏调刘秉璋于麾下。刘秉璋遂入淮军,逐步成长为李鸿章所器重之大将,是淮军十一大支中庆字军的主要领导者。刘秉璋一生经历了淮军兴起、发展、转型等主要阶段,在淮军主要将领转型为地方军政领导后,其才能得到彰显,地位更加显赫。据王尔敏先生考察,与湘军不同,“淮系将领,官至督抚者人数很少,早期只有张树声、刘秉璋,稍晚又有潘鼎新、刘铭传两人,一共四人。”*王尔敏:《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其中刘秉璋转任封疆大吏后积极作为,政声卓著:任浙江巡抚,精心组织并取得了近代史上难得的浙江抗法胜利;后官至四川总督并主政长达8年之久(1886—1894年),保持了藏区以及西南地区的基本稳定,终因坚决抵制西方势力在四川的传教、开矿等行为而遭罢免还乡。刘秉璋亦武亦文、文武兼备的身份在淮军将领中异常醒目,在他的军政活动中也显示了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担任四川总督期间,身为李鸿章一手栽培的地方大员,处理四川教案时能自觉坚持爱国立场,敢于顶撞李鸿章。本文则根据今所见刘秉璋之著述文字考察刘秉璋的学术活动情况——学术正是其处理军政事务的思想方法、智慧之来源,并结合此个案,一窥淮军文化及精神特征。
一、刘秉璋尚文性格及著述
刘秉璋在淮军中带兵打仗虽不及刘铭传等人,论文化水准却是淮军中佼佼者,他和李鸿章是淮军高级将领中仅有的两名进士。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载,刘秉璋在戎马倥偬之际依然手不释卷,尚学好读,学有根柢,甚至对烦难的小学亦深感兴趣。他还建有藏书楼,名曰“远碧楼”,藏书颇丰。*《苌楚斋四笔》卷5《远碧楼藏书》,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4页。刘秉璋不仅喜好读书,还勤于笔耕,同时代人多有记载。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刘秉璋致张鸣珂(1829—1908年)、薛时雨(1818—1885年)函札各一通,亦可见他与同时期著名文士颇有交往,如致薛时雨函云:“道路太远,送文不便,抽暇自为删阅而已。”其身故后清廷谥号“文庄”。*《苌楚斋三笔》卷5《先文庄公撰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第566页。关于刘秉璋著述情况,刘声木有如下载录:
先文庄公亦自少好学,老而不倦,撰有《奏稿》八卷、《未刻稿》□卷、《强恕斋文集》二卷、《诗集》六卷、《方舆辑要》廿卷、《政典》十卷、《礼典》十卷、《读书笔录》十二卷、《汉书古字考》一卷、《喻言》二卷、《澹园小品》一卷、《古文钞》十六卷、《古诗钞》四卷、《今体诗钞》四卷、《唐人绝句》一卷、《强恕斋日记》十六卷、《尺牍》八卷、《批牍》二卷、《朋僚函稿》廿卷、《外部函稿》十卷、《三省电稿汇存》十卷、《锦鳞集》十卷、《前集》廿卷、《后集》四卷,都廿四种,共壹百玖拾余卷。遗稿高至数尺,惟《奏议》选刊八卷。刊板及遗稿四笈,某甲攘为己有。宣统辛亥国事之变,更弃之惟恐不速,去之必欲其尽,以致先文庄公生平遗稿只字无存。后虽经声木竭力搜罗,仅购得《奏议》八卷刊本,复编辑《强恕斋文集》二卷、《诗集》一卷、《澹园尺牍》四卷,拟编为《刘文庄公遗书》,惟尚须商酌,一时未能即付排印,鲜民实深愧怍。”。*《苌楚斋三笔》卷5《先文庄公撰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第566页。
另据刘秉璋第四子、刘声木弟刘体智为刘秉璋《静轩笔记》所撰序言可知,刘体智曾据刘秉璋读书日记整理成书有《静轩笔记》及其他著述“不啻六七种”。不过,目前看来,梓行的只有《刘文庄公奏议》和《静轩笔记》。幸运的是刘秉璋部分手稿《澹园琐录》收藏于今安徽省博物院。
《刘文庄公奏议》由朱孔彰所编,收其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议205通,都是日常政府公文,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为光绪戊申(1908年)刊本,8卷,流传甚广。
安徽省博物院所存刘秉璋手稿本《澹园琐录》,考其来源,应是刘体智所捐刘家旧物。此稿卷首载“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十(按:原写作为“己亥七”,被涂抹修改为“辛丑十”)月既望”“仲良自记”云:
资性素钝又善忘,每日读书随手摘录,解组后家居无事,戊戌春粗分门类,以便检查,类之中又有类焉。凡三易稿,皆手自誊写,都为十二卷,天部一卷为类四,地部一卷为类八,人部五卷为类八,物部二卷为类八,通计四十余万字,名之曰《澹园琐录》。
稿中有大量涂抹批改痕迹,甚至还有纸条夹注,没有编制目录,可见是刘秉璋本人对往日随手记录的读书笔记进行了简单分类誊抄而成。全稿采用类书体例,共计16册(包括“人部补”与“物部补”各二册)、40余万字(据《澹园琐录》刘秉璋自撰序言),正文以“天”、“地”、“人”、“物”为题分为12卷28类。手稿内容涵盖范围甚广,主要内容是抄检已有知识:“天”部1卷4类,内容主要涉及天文历法、自然现象、阴阳五行;“地”部4卷8类,包括对国内行政区划、地理沿革、名山大川以及“四夷”风貌的介绍;“人”部5卷8类,此部分内容较为庞杂,然大体不出礼乐人伦儒典、武备政令官职、宗教方技杂谈的范围。经学所占比例不多,但刘秉璋的《诗经》学观点在此部分也多少有所体现;“物”部2卷8类,分别为“法物”、“珍物”、“用物”、“食物”、“动物”五个方面,旨在释物。从序言及内容看,《澹园琐录》确实属于家用启蒙教材或是普及基本知识见闻的“百科全书”。《澹园琐录》并未采取逐篇阐释的形式,也未通过考据的手段深入阐发,而是以独立著作为单位对章节进行划分,涵盖范围以儒家经典为主,对著作的体例、流传过程、主旨思想作大体介绍,间或涉及儒家学说的传承问题,内容驳杂而浅显。刘秉璋因处理教案不当于光绪二十年(1895年)被免官还乡,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病逝,一直乡居读书写作,时间甚长。《澹园琐录》序中所提到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己亥”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澹园琐录》应是刘秉璋乡居期间所撰写或整理,并经过其反复修改、润饰而成。
刘秉璋勤于笔耕,从刘声木所述可见其著述文字甚多,内容广泛,涵盖学术研究、文学欣赏等,“琐录”应该不止于我们今天之所见。遗憾的是,由于他是遭贬身退,又不幸赶上清末民国之交政治与社会动荡,家族地位下降,其手稿没有得到及时系统整理、刊刻。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云,散佚甚多,所以,现存清人著述书志中除了《刘文庄公奏议》外并没有刘秉璋其他著述出版之记载。今发现国家图书馆藏刘秉璋参与撰写的碑帖《庐郡会馆记》,实在属吉光片羽之珍。*今著名书画家、《荣宝斋》杂志执行主编徐鼎一先生介绍,其收藏有《刘文庄公文集》部分手稿本,线装,纸本墨笔,共52页,104单页,收有杂著、考论、跋记、奏牍、诗文共78篇。见其2007年10月24日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0a299f01000b67.html 。刘秉璋尚文好学的性格爱好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代,其三子刘体信(声木)、四子刘体智均是近现代不涉政治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详论参见宋路霞:《细说刘秉璋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另参见郑玲:《收藏世家:庐江刘氏的藏弆述略》,《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1年第6期。特别是刘秉璋和刘体智两代人的藏书积累对民国时期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郑振铎的藏书活动起到了不可或缺之作用,这正体现了诗书传家古训的正确性,尤其在改朝换代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
保存完整的《刘文庄公奏议》没有直接涉及学术问题,亦看不出明显的学术思想倾向,而《澹园琐录》所述也属于基本常识,内容浅显,不属于学术研究,皆可存而不论。刘秉璋的学术思考可依据《静轩笔记》加以考察。
二、刘秉璋的学术思考及其特点
《静轩笔记》刘体智序载,刘秉璋“每日读书,凡有所见及所经之事,悉录于日记”,此书即是刘体智从刘秉璋日记中整理成相对系统的文章。《澹园琐录》是刘秉璋本人的读书笔记,而从内容上看,《静轩笔记》不少内容乃至文字与《澹园琐录》大致相同,可见刘体智所整理、编辑的《静轩笔记》内容即来自《澹园琐录》以及其他后来散佚的笔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提及刘秉璋的不少著述,估计也是对《澹园琐录》内容的分专题编辑。《澹园琐录》的著述目的,据刘秉璋自序,是“为子侄辈馈贫粮”,而刘体智《静轩笔记》序中也提到此书是因“当时科举未废,殆为场屋之用”,显然,刘体智注意到《澹园琐录》这一特定性质。粗看起来,虽经刘体智整理、加工,《静轩笔记》稍显专深,不过,仍显驳杂、浅显。《静轩笔记》既非刘秉璋手编,亦非专门学术著述,内容只是刘秉璋日常读书与思考之随手所记,且是为子侄辈应考之用,主要是对已有经书和先秦两汉子史著作研究中有关问题的介绍及其择善而从乃至解读、发挥,不过,既然是刘体智刻意选定并芟汰,内容比《澹园琐录》专深,具有一定的学术性,我们则可据此考察刘秉璋读书范围、学术思考及其特点。
《静轩笔记》准确刊刻时间、过程尚待考察。据刘体智序是由其于民国初年组织刊印,且《静轩笔记》的刊印非一气呵成,而是边辑边印。由于刘秉璋原笔记比较复杂,整理时刘体智还“间参己意”,因此“每成一册,即先付印,不容稍缓”。今存民国刻本《静轩笔记》卷首目录标为120卷,实存第1至第4册共19卷,极有可能是仅印刷4册后即停止。今台湾文听阁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晚清四部丛刊》丛书本即据此重印。
从《静轩笔记》120卷目录看,涉及72种典籍,经、史、子、集皆有涉猎,其中论经学著作有54卷(其中小学著述18卷),分别是:《周易》3卷,《尚书》2卷,《毛诗》2卷,《周礼》6卷,《仪礼》6卷,《礼记》4卷,《大戴礼记》2卷,《春秋左传》4卷,《春秋公羊传》1卷,《春秋谷梁传》1卷,《论语》3卷,《孟子》2卷,《大学》《中庸》《孝经》1卷,《说文》6卷,《六书音韵表》5卷,《尔雅》2卷,《小尔雅》1卷,《方言》1卷,《释名》1卷,《广雅》1卷;史学著述:《史记》5卷,《前汉书》3卷,《后汉书》1卷,《三国志》1卷,《国语》2卷,《战国策》3卷,《竹书纪年》1卷,《山海经》1卷,《穆天子传》1卷,《孔子家语》1卷,《晏子春秋》1卷,《越绝书》1卷,《吴越春秋》1卷,《列女传》1卷,《新序》《说苑》1卷,合计24卷;子部所论包括《荀子》2卷,《孔丛子》1卷,《新语》1卷,《新书》1卷,《盐铁论》1卷,《法言》1卷,《太玄》1卷,《潜夫论》1卷,《申鉴》《中论》1卷,《孙子》《吴子》《司马法》1卷,《管子》3卷,《慎子》《邓析子》《商子》1卷,《韩非子》4卷,《墨子》2卷,《尹文子》《尸子》1卷,《鬼谷子》《公孙龙子》1卷,《鹖冠子》1卷,《吕氏春秋》3卷,《淮南子》3卷,《白虎通》1卷,《独断》1卷,《论衡》1卷,《风俗通》1卷,《老子》《列子》1卷,《庄子》3卷,合计38卷;集部,论《楚辞》4卷。范围限定于先秦两汉文献,不及两汉以后著述;数量上论经学著作最多,分量最重,而论集部只讨论《楚辞》,不及其他诗文。偏重经史,正是科举考试的范围,而不论诗文;偏重思想,正是体现政治家尚用的阅读特点,不同于一般文人学士之兴趣。今存4册,第1册讨论《周易》3卷,第2册讨论《尚书》2卷、《毛诗》2卷,第3册讨论《周礼》6卷,第4册讨论《仪礼》6卷。以下即以其《诗经》学论述为主、兼顾其他内容论述(《澹园琐录》对《诗经》问题也有所涉及,只是更为浅显),以考察刘秉璋学术思考的主要内容。
刘秉璋论《诗经》(《毛诗》)的内容集中于《静轩笔记》第2册第6、7卷,计有57篇。前3篇《诗书之别》、《诗本事》、《诗教》,分别阐释《诗经》与《尚书》之区别、《诗序》的存废以及孔、孟诗教观念三个命题。其后54篇讨论《诗经》单篇内容,基本还是立足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解说《诗经》中的字词内涵、名物礼仪、地理民俗、历史典故等。
刘秉璋重视《诗经》学史的积累,可见他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符合清代科举应考者的知识结构特点。清代《诗经》研究甚热,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别,而刘秉璋的取舍并不清晰,只不过于宋代学者观点吸收较多,从以下三端可以见出:
第一,论《诗经》与其他经典异同、《诗》今古文经传承、《诗经》大小序及其作者等问题,刘秉璋主要参考宋代欧阳修、苏辙、朱熹等人的观点。
《静轩笔记》卷6首篇为《诗书之别》,刘秉璋在此文中将“十三经”分为六大类:《诗》、《书》一类,《论语》、《孟子》、《孝经》一类,《易》一类,“三礼”一类,“春秋三传”一类,《尔雅》一类。又提出“《诗》、《书》同异之处凡十端”,分别是:“《书》无韵文,《诗》有韵文;《书》纪国政,《诗》观民风;《书》以成周止,《诗》以成周始;《书》无可纪而后《诗》传,《诗》亡而后《春秋》作;《书》末附有《费誓》、《泰誓》,《诗》末附有《鲁颂》、《商颂》。”此论平平无奇,但它透露了刘秉璋对《诗经》地位的评价,亦即刘秉璋之《诗经》学观念。“《诗》、《书》为一类”、“《诗》观民风”、“《书》无可纪而后《诗》传”,在刘秉璋看来,《诗》、《书》并举意味着《诗经》地位堪与《尚书》并列,皆属对周朝社会真实面貌之记录,非《诗大序》中强调的“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朱熹:《诗序辨说》卷上,《四库全书》第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之政治功用。这一观点与朱熹“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论断相似,可视作刘秉璋对朱熹《诗经》学说认可之证。
关于《诗序》存废之争的理解。《诗本事》一篇,主要就《诗经》学史上有名的《诗序》存废之争抒发己见。北宋欧阳修作《诗本义》,辩正《诗序》中记载失当之处多达114则,否定“子夏作序”一说,认为《序》当出自后人之手。苏辙采取折衷观点,未像欧阳修一般全盘推翻,但也否定《诗大序》,只承认系于每篇篇末的《诗小序》之首句是孔子所作,其余内容因申说过于详细有流于琐碎之嫌,断非古人所为:“其诚出于孔氏也,则不若是详矣。”*苏辙:《苏氏诗集传》卷1,《四库全书》第70册,第315页。二程针锋相对,虽然认同孔子的《诗大序》作者身份,但又认定《诗小序》应是史官的作品,学《诗》必先从学《序》起:“问《诗》如何求?曰:只在大序中求。诗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后人往往不知是圣人作,自仲尼后更无人理会得”*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18,《四库全书》第698册,第184页。;“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程颐:《程氏经说》卷3,《四库全书》第183册,第62页。到南宋,朱熹通过《诗集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诗经》解释学体系,他除批评郑玄“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朱熹:《诗序辨说》卷上,《四库全书》第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的解读方式外,还彻底否定《诗序》,进而立足《毛诗》本身重新阐发诗旨。刘秉璋称其“学宗二程子,《诗序》独不然”。刘秉璋对这桩公案的评判更接近苏辙的观点。他认为“《序》首句实与《诗》偕作”,首先肯定苏辙《诗小序》首句可存的观点,他的证据有二:一是“《南陔》六诗有义无辞,诗亡,序存”,二是“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相类,而但有首句是‘三家诗’遗说不同,而首句之序则一”。若想求得《诗》之本来面貌,仅仅依靠《诗小序》不够,还要“参之以《尚书》、《左传》暨古传记、周秦诸子所述”。这段论述,不盲信古人,不拘泥一家,虽其证明过程难说无懈可击(亦受笔记体裁因素影响),但治学态度却堪称严谨。在《澹园琐录》第9册《诗经》篇里,刘秉璋还提到了有些学者认为《诗小序》的作者是卫宏的观点(此说源出《后汉书·儒林列传》),但只陈述却不下断语,态度暧昧,可视为不弃不取。同时,批评朱熹将《序》全盘推翻的做法,直言“驳之过甚”。《澹园琐录》第九册讨论《诗经》,主要是借助前人论述辨析、梳理《诗经》先秦传承问题以及大、小序作者问题,没有阐发新见。关于《诗序》存废问题,刘秉璋旗帜鲜明主张存《诗小序》。
第二,关于传世《诗经》收诗范围的认识,也近于宋学。
刘秉璋推崇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2、208页。以及《诗》可以“兴观群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2、208页。的观点,仍有意拉开《诗经》与政治之间距离。在其看来,所谓“教”即教化,从大处讲是教化万民,从小处讲乃人的自我教育,故而《诗经》“涵泳性情,千古不易之理也”。孟子论《诗经》:“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5页。南宋王应麟有“学《诗》必自孟子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3,《四库全书》第854册,第208页。的感叹,刘秉璋极为认同,赞美曰“诚哉是言也”。论《溱洧》主旨:“《溱洧》二章描写男女之情,各尽其致,六朝‘子夜之歌’、唐人‘香奁之集’,于此开其先。”可见,刘秉璋治《诗经》主张就诗论诗,从诗歌本身出发,以文本为本位加以理解,强调《诗经》的情感成分与教化作用,反对过分解读《诗经》的主旨思想,尤其是夸大《诗经》的政治功能。
第三,刘秉璋论《诗经》学,在方法上重视金石考据与书面文献的互证、互补关系,亦是继承宋儒学术传统。
宋代欧阳修撰《集古录》,有意识地利用金石原物、拓片作为经学研究的佐证,开金石考据之先声,后经好友刘敞等人践行鼓呼,逐渐蔚为大观,如清郭嵩焘所言:“宋儒考古之勤,信非唐贤所能及也。”*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卷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清道光年间西周虢季子白盘的出土面世轰动一时,因铭文字词、句式、史实不乏与《诗经》相类甚至重合之处,有人将其视为《诗经》之补充材料。巧合的是,到了清末,淮军另一位将领刘铭传收藏了虢季子白盘,刘秉璋极有可能亲见了这份珍贵的文物,他在《诗本事》中称“诗之原文传世可供参考者,惟虢季子白盘”,肯定了虢季子白盘铭文对解读《诗经》原文的重要参考价值。
重视金石考据与书面文献的互证、互补,这在刘秉璋的“三礼”研究中也有实践。今存《静轩笔记》述《周礼》和《仪礼》的各6卷(第8—13卷和第14—19卷)内容里,器文互证、以器释文者近30处。典型的如:
郑注:敦盘类,珠玉以为饰。按:传世铜器敦盘甚多,敦为盛谷食器,盘为承物器,合乎古训。敦非盘类也。近年玉器出土亦有敦盘之属,较铜器为小,其为盟会盛牛耳盛血之备,不作他用,明矣。(《静轩笔记》卷8《珠盘玉敦》)
郑注:抉,挟矢时所以持弦,饰也。著右手巨指。郑于乡射《礼注》云:决,犹闿也。以象骨为之,著右大擘指,以钩弦闿体也。按:近人金坛段氏、绩溪胡氏佥谓决如今之扳指,皆似是而非。决以象骨为之,验诸古时器物品质,有用象则必有用玉者。今出土玉中有形似扳指而一面高几及寸一面高不及一寸五分之一者,以之钩弦良为适用,殆即此物无疑。(《静轩笔记》卷10《决拾》)
铏即出土之齐侯罍,或曰齐侯壶者是也。本是菜和羹之器,后人误为酒器,遂生异议。(《静轩笔记》卷17《铏》)
然而,尽管刘秉璋吸收了宋学《诗经》学的成果,但是,我们又很难将其划入宋学的阵营里,换言之,汉学传统在其研究思考中也有明显表现。
《静轩笔记》专论《毛诗》的57篇文章里,专门阐发刘秉璋《诗经》学观点或者发挥诗旨的内容甚少,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考据的范围,对《诗经》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几乎没有发挥,看不出他与晚清今文经学的联系。清代考据方法相较前代愈加精良,例如桐城学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常常利用古音古义或是双声叠韵的原理来订正前人注疏中的讹误,这些方法也在刘秉璋的考据中有所反映,刘秉璋有时是直接引用其说法。如,释《诗经·陈风·月出》:
“舒窈纠兮”,《传》:“舒,迟也。窈纠,舒之姿也。”瑞辰按:“窈纠”犹“窈窕”,皆叠韵,与下“忧受”、“夭绍”同为形容美好之词,非舒迟之义。(《毛诗传笺通释》卷13《月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7页。
《毛传》:“‘窈纠’,舒之姿。”按毛说是也。此类双声叠韵形况字,古文无一定意义,观其用处而已。言女子则用“娇娆”,《汉乐府》之“娇娆”即《关雎》之“窈窕”也。(《静轩笔记》卷7《窈纠忧受夭绍》)
马瑞辰(1777—1853年),桐城人,其著《毛诗传笺通释》被视为桐城学术的重要著作,“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马瑞辰对出生于与桐城交界的庐江刘秉璋而言属于乡党,刘秉璋多所引用,自是理之必然。此外,刘秉璋释《周易》、《尚书》、“三礼”,亦综合采用了古音、古字、通假、双声叠韵等多种考据方法:
仁者,人也,取爱之意。从二,从人,则博爱之道也。义者,利也,取利己意。以利为训,盖人情趋利避害亦无有不宜焉。古韵义利同音同字。利,和也,亦同韵通用。而台予余盖别体也,《易》彖辞中之“元亨利贞”,《彖》传辄言大亨以正以利通用,而又与我字义字同训,以字殆即台字,于此益见古义利二字不分。(《静轩笔记》卷2《利》)
《注》引郑司农云:菑读为不菑畬之菑,栗读为榛栗之栗。玄谓栗读为裂繻之裂。按:菑斯声近,菑栗即撕裂之古字。(《静轩笔记》卷13《菑栗》)
执假借作謺,《说文》“謺”下云“讘也”,“讘”下云“多言也”,谓邻国猎取鸟兽便于多言以致讨有词可措,不患无名矣。(《静轩笔记》卷2《六五田有禽利执言》)
“契”与“怯”同韵,与“需”双声,以状马行之不倦,古文中形况字也。《诗·邺风》之《北风》章,其虚其邪,当如是解。若求其字,反失之矣。(《静轩笔记》卷13《契需》)
刘秉璋《诗经》学考据之范围,虽以字词、篇名、主旨为重点(比例约占62%),但并不单单局限于此,还包括礼仪、典制、职官(13%)、名物(11%)、地理(9%)、历史(5%)等诸多方面,这一点不似马瑞辰,却有焦循之风。
显然,刘秉璋的研究、思考,无涉于汉、宋以及今、古文经学之辩,貌似融通,个人见解不多,其实是其非严格学者的表现。这种非专业性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第一,刘秉璋治《诗经》不像一般学者那样追求严格的系统性,未采用通行的逐篇逐句释法,而是随机选取感兴趣的内容加以阐述,篇目主要集中在“风”、“雅”两部分。涉及《国风》数量最多,有34篇,其次是“雅”17篇(包含《小雅》12篇、《大雅》5篇),“颂”数量最少,仅有4篇,三者在各自整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1%、16%和10%,看不出系统性。《国风》中,与《周南》、《召南》有关的篇目数量相对而言更占优势,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可见刘秉璋的《诗经》学趣味比较集中,他不太关注内容更为庄重严肃的“雅”、“颂”,而更关注《诗经》中反映西周社会风土人情、内容比较具有民间性的《国风》部分。
第二,《静轩笔记》引用材料来源较为集中,均以阮元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对版本异文不甚关注;在观点上兼取前人学说,辨析前说失当之处,所做学术史引用并不全面,有时甚至以个人日常生活感受代替征引文献的严肃、深入考证。《周易》部分引用多出自《困学纪闻》、《周易集解》,《诗经》部分引用来源集中在《说文解字》、《玉篇》、《左传》、《礼记》、《经传释词》等等。但《周礼》、《仪礼》部分是个例外。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转折——从推崇敖氏(继公)到回归郑玄,这种学术风气变化在《静轩笔记》中的最典型之反映恰在其征引来源的选择性。刘秉璋不但将郑注作为研究之底本,而且征引了郑注推崇者吴廷华(《仪礼章句》)、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等人的观点。相比之下,对敖继公《仪礼集说》一书内容的引用次数明显要少得多,而且每次出现必伴随着批评。但需强调的是,对郑注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无所甄别,刘秉璋对郑玄及其追随者观点的广泛征引,其前提是对郑注失误的体察与纠正:
《天官》之九嫔、世妇、女御数阙,《春官》之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为下文之内宗,即阍人职之内命妇是也。外宗即外命妇是也。内命妇,王后宫官也;外命妇,卿、大夫、士之妻也。九嫔比于天子之三公六卿世妇;每宫卿二人,王后六宫,共十二人,比于天子之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内外宗隶于大宗伯之下。《白虎通义》:宗者,尊也。郑注以王同姓之女谓之内宗,王诸姑姊妹之女谓之外宗,以宗为祖宗之宗,失之。(《静轩笔记》卷10《内宗外宗》)
郑注“聚所获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郑于《月令》注引“司马职,罗弊致禽以祀祊”。贾疏证彼“祭禽于四郊”与此“馌兽于郊”为一物,其实彼一解以为是仲秋祭禽,以祀祊为一也。按:郑注此书引《月令》以证为冬狩,“祭四方神”其注《月令》又引此书以证为秋狝祀祊,未免互相矛盾,贾疏纠正是也。拘于郑学者,虽单词片义之偶误,必为之掩饰,弥加尊重。此则两处互相矛盾无可掩饰者,特表而出之,以见千虑容有一失,未可株守一家之说也。(《静轩笔记》卷11《致禽狝兽于郊》)
刘秉璋研究思考灵活、通达,往往不做繁琐考录,而揆以人之常情进行解释:
“江汜”、“江渚”必有其地,不必拘于一处,其义乃通。(《静轩笔记》卷6《戊申戊甫戊许》)
文人之笔,一时兴到,何必实有其人,抑何须亲其事?(《静轩笔记》卷6《溱洧》)
其实偏旁同异,无关宏旨,亦不必深考也。(《静轩笔记》卷7《况瘁》)
九谷之属,应有尽有,如谓今之所谓黍、稷、粟者,非古之黍、稷、粟,而别求其物以实之,则非所敢知矣。(《静轩笔记》卷8《九谷》)
总体看来,刘秉璋对《诗经》暨经典文献的论述,大多着眼于已有争论或问题,其观点基本上是从前人所论中择善而从,论题和考证并不系统、深入,即使稍加辨析,也多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上的公案做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简单判断,没有特别深刻的见解;所引证文字中,不少没有标明出处或作者,往往断章取义,并不是严格规范的学术方式;观点与方法兼采汉、宋,不拘今、古,未有明确的门户归依、学说宗仰的倾向,和清代汉学家、今文经学家以及治宋学者强调学有所出、门派归属显然不同。
此书的内容只是刘秉璋为教育子侄应考而作的常识介绍,其性质虽然决定了内容不能太专深,此书自然并不能全面反映刘秉璋的学术思考,不过,从一般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论定,《静轩笔记》反映了刘秉璋学术的基本状况和水准:《静轩笔记》内容驳杂,基本上是抄检前人旧说,缺少创见,表明刘秉璋学术水平不高,不是专业的学者,没有入流于当时学术圈子。
三、刘秉璋与清末社会文化之流变、分野
进士出身的刘秉璋没有成为学者,谈不上学术成就,亦不是著名诗人(流传下来的诗歌只有数首)、散文家,原因是他生活在清末乱世,身为朝廷倚重的国之栋梁,主要精力并不在治学,学问只是他的闲暇爱好而已。尽管如此,其学术思考中也有一些新的因素乃至特点,尤其是所折射出清末学术发展的态势以及所属军政集团的特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 学术思潮的分合与起伏
处于封建末世的晚清是各方思想碰撞、社会激烈变革的时期,作为社会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晚清学术自然无法屏居于时代浪潮之外。就刘秉璋学术活动对清末学术演进形态的反映而言,有如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汉、宋合流。道咸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日趋精良完备开始自我整合与更新: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宋之争渐趋消歇,汉学如日中天,以压倒性姿态取得胜利,考据学“几成为清代学术的代名词”*张立文主编,陈其泰、李廷勇著:《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宋学虽退居其次,然亦未至绝境,赖有倭仁、吴廷栋、罗泽南等人延续学脉;而今文经学在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人的手中臻于繁盛。与此同时,多方又明显呈现出兼采乃至融合的倾向,这一点在重臣曾国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详论参见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他主张:“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68页。作为深受曾国藩器重的刘秉璋,在学术取向上兼容汉、宋,并非偶然。当然,刘秉璋对今文经学不太关注,这是他和晚清激进的改革派不同之处。
二是西学东渐。伴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国门渐开,来自西方的新学大兴,介绍外国政史地科的著作纷纷出版,进化论、新史学先后登上学术舞台,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的指导下,学术命题、治学方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身处于东西古今交汇点并且直接与洋人打交道的刘秉璋,面对新学与旧学的“两面夹击”,他的选择与态度颇值得玩味,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晚近普通知识分子群体中守旧一派的观念与立场。其著述中涉及西方文化、政治、法律乃至舞蹈艺术之议论俯拾即是,如:
欧洲人崇拜英雄,于其本国开创之事尤乐道之。英国大王阿尔夫内得兵败匿于乡间,为村妇炊饼,不熟,大受呵责。适军报至,敌众大败,迎归故都。村妇知为王,自谢乞宥。大王笑曰:“不意坏尔饼,汝亦宥我。”无论史书说部均艳称之,究竟有无其事不可知,彼时英犹土著,王室族类究竟已否融入条顿血液亦不可知。顾以为国情切重之如此,吾人在先闭关自守,知有己国而已,更无有他国,以与之比,遂不知如何。而始为国犹之乎人居其乡,则人人皆同乡,不知如何而顾全乡谊也。通商以来,相形之下,宜渐有国家思想矣,执干戈,卫社稷,非人人之所能试也,非时时之所能有也。若爱护古迹,则人人能为,随时所有,姑以此始焉。免疲精神于无用之地,是所望于今之君子耳。(《静轩笔记》卷4《读书不可以文法断定时代》)
欧美各国听讼之法,先使以口亲耶稣而后出言,以明勿欺,犹存古意。(《静轩笔记》卷12《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
西人跳舞中有所谓“狐步”者,庶乎恰合。(《静轩笔记》卷15《以狸步》)
刘秉璋在其《诗经》学研究中,《朝阳夕阳》一文爬梳“夕”字的字义演化过程,文末指出“宋人解经,尚在萌芽,非其学之浅也,时代进化尚未至也”,已自觉运用时代进化之观点;《鼒》提到“欧人以掘地考古之学信为有益,但不可束书不观耳”,虽然对西方考古学的认识过于简单幼稚,但还是承认考古学在历史考证中的作用,更难得的是有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意识,尽管相比而言在他心目中还是世间已流传了千百年的书籍更值得信赖。由此可见,刘秉璋视野之开阔,对西方文化了解之渐趋深入、通达。
(二)淮军与湘军、淮军与桐城派的精神疏离
曾国藩率领其建立的湘军集团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使本来危在旦夕的满清政权暂时渡过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不过,内外夹击之下,从此大清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态也逐渐发生改变,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端就是曾国藩对理学和桐城派散文的自觉倡导,在散文创作上出现湘乡派以及“曾门四大弟子”。在曾国藩及其湘军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曾国藩一手栽培的学生且在桐城派故里——桐城以及江淮间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及其淮军,纵横晚清政坛近四十年,虽然在军事、外交、实业等领域除旧布新,功勋卓著,影响深远,在思想和散文创作上却竟然没有传承老师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和“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皖籍同乡吴汝纶,一开始共同师事曾国藩,后来吴汝纶还长期在李鸿章幕府担任幕僚,为李鸿章掌机要文翰,二人交往密切,可是,从现存李鸿章与吴汝纶文集中却看不到二人切磋论文的情况。试想,以李鸿章当时之身份和影响力,如果他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晚清的历史包括文化和文学史乃至近代史则要完全重新书写。
对上述现象及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解释,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尔敏先生的研究和分析。王尔敏先生通过大量人员数据分析指出,“淮军中大军旅之统将二十六人中有科名者五人、捐职一人,与湘军领袖多数均有科名不同”*王尔敏:《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李鸿章“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是以淮军军幕并不护持文人,维系文风。与湘军幕府相较,自大为逊色。鸿章出身幕僚,并以曾国藩传人自居,而于幕府规模,则稍不尽师承。此一分歧,亦足显示两人政治作风之不同”。*王尔敏:《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页。正因为文化层次高低不同,“以政治地位而论,仅湘籍分子,任督抚者已二十四人。并时地方权位之盛,无与伦匹。淮军次于湘军,战役则并未参与西北西南。人才则李鸿章之外,重要领袖亦不过十人。政治地位,只有李鸿章一人权势煊赫。其余任督抚者不过四人,即加上外籍幕府人物,亦不过十余人。”*王尔敏:《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页。王先生通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发现,湘军和淮军主要人员身份存在明显差异,一为科举人物,一为没有科名的农民、行伍、世职、军功等,文化程度差异明显。曾国藩治军强调价值观之引导,尤重理学之作用。李鸿章生活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曾国藩,曾国藩面对的还主要是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而李鸿章面对的主要来自外来势力,他看到的是传统思想的有限性,更关注学习外来先进技术,所以,他不太注重文化建设、学术研究以及文学活动。刘秉璋与潘鼎新进京参加会试即拜李鸿章为师,和李鸿章有师生之谊,进入淮军也是李鸿章亲自奏请朝廷任命之结果,后来在跟随李鸿章平捻过程中与李鸿章以及淮军诸将不合,曾于同治八年灭东捻后以父病乞归隐退。虽然刘、李起初关系密切,刘秉璋也始终受到李鸿章的重用,但是,刘秉璋似乎更受曾国藩赏识,几乎引为己用,原因就在于刘秉璋的进士身份及他们对文化学术有共同的爱好,志趣相投。
我们循着王尔敏先生的思路进一步观察,淮军核心骨干多来自合肥、庐江、舒城、巢县*根据《淮军志》“淮军统将表”统计,432人中,主要是合肥、庐江人,附近的巢县、舒城也有一些,而安庆地区不多,其中桐城5人(包括周寿昌、程学启)、怀宁2人、潜山1人、太湖1人。,而桐城派的主要人物所分布的桐城、怀宁、潜山、太湖等地,虽都属安徽,但二者并不重合。尽管皖、湘之别远大于合肥、桐城之别,但是,在文化趣味方面,湖湘更接近于桐城。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政治军事文化群体更自觉地传承了湖湘区域兴盛的理学传统,同时,桐城派的精神亦符合他的兴趣。姚鼐所创建的桐城派,虽标榜“义理考据辞章”兼顾,其实,在乾嘉汉学盛行之时,其批判汉学、捍卫理学的现实性是明显的,比如方东树《汉学商兑》,因此,曾国藩继承桐城派衣钵正是理所必然。刘秉璋虽然文化气质接近曾国藩,但是,毕竟长期在重视事功的李鸿章集团内活动,他也就没有进一步像曾国藩那样偏好理学,也没像曾国藩那样熏染桐城派精神气质和习惯。
综上所论,刘秉璋的学术活动没有进入晚清主流学术圈子,而刘秉璋一生的宦途起伏是李鸿章领导的、纵横晚清政坛逾四十年的淮军由盛转衰的缩影。在科举考试出身主导的清代政坛,偌大的淮军中像刘秉璋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骨干居然只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李鸿章重实用谋略,轻视文才,反映了晚清内外交困的时代环境下实用主义思潮的盛行。李鸿章甫一去世,梁启超《李鸿章传》即做出了精确的评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明确指出李鸿章识力之不足,影响了其对大势的判断,而识力显然主要来自学术思考与学术积累。轻视科举为国擢拔栋梁之才重要作用,轻视传统道德文章,忽视洞察世事的学术文化,无疑严重限制了淮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对淮军乃至晚清最终命运产生了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李鸿章同时代的张之洞,在事功方面虽然不及李鸿章,但是,他崇尚文教,所提出的“中体西用”之思想方案虽不能纾解当时清廷之困,不过,百年之后在中西文化关系依然待解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时间充分证明,张之洞好学尚文之高瞻远瞩不能不令人佩服,同时,我们将比梁启超更加遗憾地“惜李鸿章之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文人事迹编年汇考”(13&ZD1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