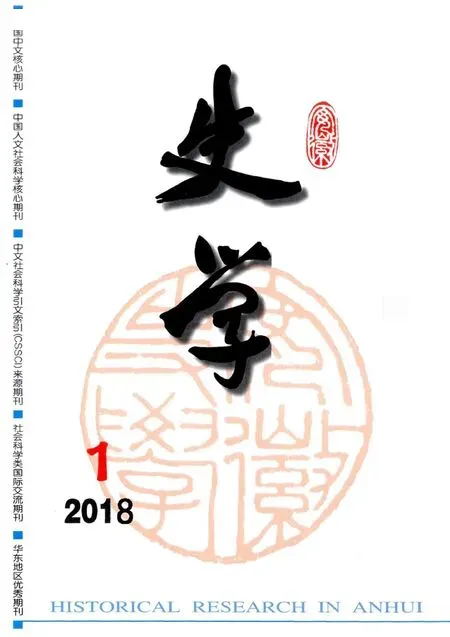美国海外“和平”形象宣传运动探略(1953—1955)
胡腾蛟
(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20世纪50年代,让世界信服美国的“和平意图”成为美国重大宣传主题之一。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至1955年7月23日日内瓦峰会期间,美国政府几乎同时启动了“和平的机遇”(A Chance for Peace)、“和平的原子”(Atoms for Peace)和“开放领空”(Open Skies)三大宣传运动,力图全方位塑造美国海外“和平”形象,藉此团结“自由世界”与击败共产主义。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欠缺。*相关成果限于:Martin J.Medhurst,“Eisenhower’s ‘Atoms for Peace’Speech:A Case Study in the Strategic Use of Language”,Communication Monographs54(June 1987);and “Atom for Peace and Nuclear Hegemony: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of a Cold War Campaign”,Armed Forces and Society24(Summer 1997);Ira Vhernus,Eisenhower’s Atoms for Peace,College Station:Texas A&M Press,2002;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06,pp.159—180;John Krige,“Atoms for Peace,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and Scientific Intelligence”,Osiris,2nd Series,Vol.21,Global Power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6);胡腾蛟:《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原子和平宣传》,《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8期。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对
上述运动的文本解析,试图勾勒出美国海外“和平”形象塑造的总体图景,进而推进美国公共外交研究。
一、和平宣传政策的制定
这一时期,美国重视和平宣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反击苏联和平宣传的需要。二战后以来,苏联一方面持续强调“为和平而战”,宣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侵略好战的,严重危及世界和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另一方面利用“和平共处”或 “正常化”、“缓和”等修辞,吸引中立国家甚至是反共产主义国家的关注。*Frederick C.Barghoorn,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pp.86—87.这对将和平自诩为内在品质的美国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势必加以反击。早在1950年7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告诫参议院对外关系小组委员会时就说:“在国际斗争中……真相必须得到揭露……让整个世界信服我们宣称的和平意图就是真相。”*Martin J.Medhurst,“Eisenhower and the Crusade for Freedom:The Rhetorical Origins of a Cold War Campaign”,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27,No.4,Rules of the Game:How to Play the Presidency(Fall,1997),p.652.
其二,维系美国核霸权的需要。苏、英先后于1949年和1952年成为有核国家,公然追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美国核垄断被打破。对美国来说,世界原子格局既然已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完全将原子当作一种机密的做法无益于自身霸权的维系,相反,原子信息的有限公开很可能有利于展现美国技术优势,从而对共产主义形成有效威慑,并阻止因共产主义“核讹诈”而导致“自由世界”的分裂。因此,美国政府不再固守禁止原子信息传播的政策。
其三,化解世界舆论压力的需要。自1952年11月美国实施“常春藤行动”,频繁进行核试验以来,世界各地爆发宏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强烈谴责核武器与尘埃给人类带来灾难,严重冲击着美国海外声誉。1955年6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认为,鉴于“对核武器的普遍恐惧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美国应当立即通过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在迫切需要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关于正受关注的核辐射后果的国际研究或信息交流”。*Follow-up report on overseas reaction to 21555 AEC statement on the effects of high-yield nuclear weapons.Report.Jun 8,1955.CK3100085270.DDRS.因此,如何有效化解海外舆论压力,维系美国“和平”形象成为美国官方的宣传重点。
鉴于上述诸多考虑,美国将和平宣传当作一项国家工程,制定了完善的宣传政策。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协调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国务院、新闻署、国防部、中情局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部委参与其中。从内容上看,它可分为传统和平与原子和平两大维度;从策略上看,可分为常规活动与主题运动。
(一)和平理念及价值宣传政策的制定
美国决策者将“和平”视为其内在价值。在他们看来,崇尚和平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信仰,他们信奉民族自决,关切人类社会富足、自由与尊严的实现,美国非但不是苏联所宣称的奉行殖民政策的“自私的战争贩子”*Analysis of U.S.Ambassadors’ reports throughout the world.Report.Oct 1,1952.CK3100101175.DDRS.,反而是世界和平的真正“捍卫者”。1947年,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强调“实力确保和平”的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爱好和平国家的力量仍然是对侵略最大遏制的世界里。如果当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放弃维系这些责任的手段时,世界稳定就可能被摧毁。”*John Fousek,To Lead the Free World: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124.1952年,美国进而提出“力量确保迈向和平与自由之途”的概念,将“和平”与“自由”关联在一起。*Nicholas J.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1945—19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76.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更是将意识形态力量看作是冷战获胜的关键,要求海外宣传活动强有力地诠释美国和平的普世意义。1961年,肯尼迪鼓吹“自由抉择的世界”,喻意“人类尊严、政治自由、自主、文化独立等”。*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Schlesinger)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undy),June 19,1961.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25/d124.总之,从美国官方不断炮制的概念来看,“和平”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成为攀附美国核心价值的衍生语。
新闻署是美国和平价值的主要宣传者。1954年3月1日,它确定的“战略原则”是,致力于显示“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民族共享的基本信念与价值”,包括“信奉世界和平、相信人类和国家之间的博爱能够在联合国内消除其分歧和推动合作”等;美国应当通过“非自我夸耀的方式”展现“美国抵抗侵略的能力”和支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构建”。*Scott Lucas,Freedom’s War:the US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2—203.
(二)和平主题宣传政策的制定
不过,对美国冷战斗士而言,在苏联密集的“和平攻势”以及汹涌的世界舆论面前,美国和平理念及价值的宣传显得过于温和,因此,他们还特别注重更具针对性的主题宣传:原子为和平服务与裁军。
其一,原子为和平服务。按照国务院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看法,长期以来,公众对美国原子武器存在“相当大的误解”,认为原子的使用必然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或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这主要源于矛盾性声明;缺乏向公众提供确切信息;原子武器禁用声明;媒体对核尘埃的夸张报道;英美官员和公众对“核武器”、“原子”、“裂变”和“聚变”等词语的滥用。当然,美国认为造成“误解”的首因在于苏联对上述“困惑”的充分操纵。*Information program reviews ways in which to inform the public about the U.S.policy on the stockpiling and use of nuclear weapons.Memo.CK3100148549.DDRS.

1955年8月,新闻署将“和平”确定为第三大全球性主题,试图使世界相信美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代表着和平并致力于和平”。*Appraisal of status of key USIA programs in various areas as of 6/30/55.Aug 11,1955.NSC5525,Part 6.CK3100309162.DDRS.
其二,裁军。包括常规裁军与核裁军两方面。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出现后,核裁军谈判成为美苏博弈焦点。美国认定国际舆论站在苏联一方。1956年8月行动协调委员会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呈交的报告指出,自50年代初美苏等国频繁进行核武器试验以来,“国际社会的不利态度始终针对美国而并非苏联和英国”。*Nuclear energy and related information.Aug 15,1956.CK3100451017.DDRS.艾森豪威尔对此所持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实施包括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在内的全面裁军,并将建立防止“欺骗”行径的监督机制作为谈判前提。他实际上是将核裁军宣传视为一项心理战,并非真正实施。1953年10月出台的NSC162/2号文件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列为同等必要的武器。1954年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确定美国奉行的政策是,将不会通过任何谈判的方式来“控制或废除核武器”。*Lawrence S.Wittner,Confronting the Bomb: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5.
对美国来说,虽然两者都涉及原子技术,但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旨在将外界的注意力从美国核军备优势转移到苏联常规军事优势上来;后者强调扭转外界对原子技术“威胁性的文化意义与形象”*Laura McEnaney,“Cold War mobi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otics:the United Stated”,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38.的看法。基于上述考量,1954年,美国新闻署确定自己在裁军宣传上的作用是:“展现美国军事实力的平衡性图景,并帮助证实此为美国出于纯粹防御目的的需要。新闻署继续利用在联合国框架内就裁军问题进行重大磋商的可能性,以显示美国正在真诚地探寻某种控制军备的适当保障手段。”*Status of 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s of December 31,1954.NSC5509.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9/d185.
二、“和平的机遇”运动
(一)“和平的机遇”演讲的缘起
1953年3月4日,获悉斯大林病危,总统心理战顾问C.D.杰克逊立即致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卡特勒(Robert Cutler),强调这将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真正巨大的宣传机会”;美国应快速制定一项“促进苏联帝国真正分裂”的战略,达到既搞垮苏联又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目的。*Examination of propaganda policies and actions in light of death of Stalin.Mar 4,1953.CK3100256140.DDRS.
早在1952年11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就初拟了一份应对斯大林去世的心理战草案“翦除行动”(Operation Cancellation),编号为PSB D-24。国务院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情报”来证实它;杰克逊认为它“没有价值”,需要一个更大胆的新计划。杜鲁门总统对此也不满意。*Lowell.Schwartz,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Kremlin:US and British Propaganda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Palgrave Macmillan,2009,p.162.经修改后,该草案后来最终成为NSC161号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杰克逊的推动下,当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最后决定:(1)总统向媒体发表一项相关声明;(2)相关部委拟采取的行动有:中情局撰写一份关于斯大林权力移交后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和南斯拉夫影响的新评估报告;国务院发表政策声明;心理战略委员会协助心理战顾问制定一份应对斯大林去世的心理战计划。*Discussion at the 135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ated 3/4/53.Memo.Mar 5,1953.CK3100129312.DDRS.
按照上述要求,9日,杰克逊与心理战略委员会、麻省理工学院诺斯托(Water Rostow)教授共同完成新计划的制定。它强调美国对苏基本目标仍限定在NSC20/4、NSC68、NSC114和NSC135系列文件的基本精神内,即运用“心理战”击溃苏联共产主义。具体来说,通过包括总统发表演讲、举行高层会议在内的“最初主要行动”,彰显“美国推动和平世界进步努力的严肃性”,同时推动苏联集团的分裂;总统演讲“服务于此目的”,是“目前心理战略赖以存在的主旨”。*Two copies of a draft outline for a plan for United States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wake of Stalin’s death.Memo.Mar 9,1953.CK3100117921.DDRS.
10日,中情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即使马林科夫新政权日后发生权力斗争,也不会导致苏联蓄意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但极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继续强调对西方敌意的持久性。*CIA report to estimate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death of Stalin and of the elevation of Malenkov,March 10,1953 [NSC Staff Papers,NSC Registry Series,Box 4,Special Estimates 5—15 (4)]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declassified/fy_2012/1953_03_10.pdf.11日,国务院明确反对杰克逊的新计划,建议美国实施更谨慎的方略。国务院可以“撒播关于新政权的疑虑、困惑[和]不确定的种子”,但鉴于过度刺激苏联“卫星国”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官员不应“抱有苏联帝国立即崩溃和解放的过度期望”。*Laura A.Belmonte,Selling the American Way: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55.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Smith)也认为,既然后斯大林政权已经“团结和形成了凝聚力”,届时总统没有演讲的必要。*Memorandum,Gen.Walter B.Smith,to George A.Morgan.Mar.10,1953.6 p.Mar 11,1953.CK3100360905.DDRS.鉴于意见尚未统一,同日,艾森豪威尔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最终就如下问题达成妥协:(1)斯大林之死为总统“从全人类安全、和平以及过上更好生活水平的旨趣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宣扬美国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机会”;(2)负责“冷战行动”的总统特别助理应按照会议精神立即为总统起草一份演讲,并尽快确定演讲时间与地点;(3)由美国国内外所有相关部委协调并持续强化演讲的后续行动。艾森豪威尔还特别强调运用“适当言辞”以实现美国心理战目标。*Discussion at 3/11/53 NSC meeting:CIA led discussion of effect of Stalin’s death;AEC Chairman statement in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nuclear power;U.S.policy regarding Iran.Mar 12,1953.CK3100199124.DDRS.4月23日,修改后的计划最终获批,编号为PSB D-40,同时撤销PSB D-24。
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发表演讲,声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苏联都将坚定地奉行和平政策”。*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06,p.61.短期内,他动作频频:接受联合国关于伤兵交换的建议;部分地接受朝鲜战争中的伤病战俘自愿遣返原则;提议就裁军和原子武器控制问题展开磋商;放松柏林交通管控;发起四国会议以讨论德国柏林空中走廊安全问题;承认联合国秘书长为合法人选;调整反击西方宣传攻势的语调,以强化“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发动世界各地共产党官员与西方社会接触,显示苏联的“社会性友好”。*Soviet peace offensive following death of Stalin analyzed.Apr 8,1953.CK3100296142.DDRS.
然而,上述举措并没有受到美国官方的肯定。4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断定,虽然“苏联无意于在此时挑起一场世界大战”,但“没有理由认为苏联对西方的基本政策做出了任何改变,尽管它显示了很大的灵活性”。*下划线为原文所有,详见Soviet peace offensive following death of Stalin analyzed.Apr 8,1953.CK3100296142.DDRS.16日,中情局再次强调:“没有事实表明苏联对西方的基本敌意已经减弱,苏联统治者已经改变了其最终目标或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已经消失。”*CIA report to 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ent Communist “peace” tactics,April 16,1953.[NSC Staff Papers,NSC Registry Series,Box 4,Special Estimates 5—15 (4).]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declassified/fy_2012/1953_04_16.pdf.为此,心理战略委员会对计划作了调整,将宣传重点转换到强势揭露苏联和平的“虚伪性”和“危险性”上来,一旦苏联不能接受总统演讲,它将“承担最大责任”。*Two copies of a draft outline for a plan for United States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wake of Stalin’s death.Memo.Mar 9,1953.CK3100117921.DDRS;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63.
(二)“和平的机遇”演讲及其后续行动
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向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遇”的主旨演讲,力图将自我塑造成为世界和平的“真正捍卫者”:美国“必定控制和裁减军备;必定将世界从恐惧阴影中拯救出来;必定帮助所有民族的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获得急需的衣食住行用品,完善公正的政治生活,享受自己辛勤耕耘所带来的自由与和平之果”;而反观苏联,“在其设想的世界里,安全……必定建诸于武力之上。这种武力依赖庞大的军备、致命的武器、咄咄逼人的威胁。它奴役邻国,它使所有国家感到恐惧……它迫使他们将前所未有的资源用于军备上。”*Third draft 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 following the death of Josif Stalin.CK3100326127;Sixth Draft,4/3/53,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CK3100326088;Eighth draft 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 following death of Stalin.CK3100326135.DDRS.显然,艾森豪威尔在反共价值镜像中鼓吹“美国生活方式”的“和平”性。两天后,国务卿杜勒斯亦在协会发表演说,讽刺苏联领导人在和平抉择面前踌躇不决:“只要那些不接受道德准则的人仍拥有大量权力,这就一定会继续保持不明朗的状态。”*[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孙闵欣等译:《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演讲结束的第二天,美国立即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向海外集中宣传“美国和平惠及世界”的主旨。在一档节目中,一位自称为阿尔巴尼亚人的主持人称赞艾森豪威尔式和平“惠及全民”;在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播报中,一位评论员强调“我们捷克斯洛伐克,铁幕之后被奴役的民族对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深感欣慰。它终结了遏制时代”。同时,美国还对苏联和平理念进行了系统攻击,斥之为“惺惺作态的”,藉此反衬美国“和平”的真诚。*Shawn J.Parry-Giles,“Militarizing America’s Propaganda Program,1945—55”,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0,p.118.
按照PSB D-40的要求,心理战略委员会成立部际工作小组,负责启动和协调后续宣传运动。总统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杰克逊委员会)指令新闻署负责具体宣传行动。新闻署在首份活动蓝图中指出:“遵循总统4月16日的演讲主旨,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普遍原则转换成为对我们的信息项目富有意义的措辞,并确定世界范围内的行动计划。”它将宣传重点放在演讲的“信仰”与“愿景”部分,表明美国与其他民族享有“共同目标和理想”。规划者还试图将它当作一项“种子”计划,推动“更宏大更富活力的项目,使所有政府机构以及美国人民积极参与其中”。*J.Michael Hogan,“The Science of Cold War Strategy: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War of Words’”,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pp.152—153.
为了确保国内外将演讲解释为“一项严肃的和平建议”,此次运动共散播300万份演讲稿,还广泛播放纪录片、电影和举办展览。据记载,计划确保演讲“在世界范围内比自马歇尔计划以来官方政策的任何声明引发更大兴趣和产生更有利的评论”。还在演讲之前,美国就“将演讲稿赠送至每一位外交官”;演讲当天,向73个海外新闻处输送了整个演讲的电视录像,其中,仅在4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BBC)转播演讲时,受众就高达600万人。5月2日,以35种语言制作的主题纪录片被输送至国外。此外,美国还鼓动国内外报刊和杂志编辑“赞成性”地讨论演讲内容,并向海外输出长达72页、关于世界各地编辑看法的资料汇编。《自由世界》杂志刊登了以相片形式解说演讲的内容,并制作了10个不同版本在中东地区传播;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个人关注演讲中“最能引发他们兴趣的地方”;鼓励商人、劳工领袖、妇女团体在各自圈子内宣讲演讲的“深刻含义”;发动美国团结委员会(Common Council for American Unity)和自由工联(ICFTU)等与外媒接触,以扩大世界影响。*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p.65—66;Document entitled:“Status Report on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Effort as of June 30,1953,and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sychology Strategy Board”,Report.Jul 29,1953.CK3100144608.DDRS.
三、“和平的原子”运动
(一) “和平的原子”宣传的缘起
还在“常春藤行动”实施数月前,军备和美国政策特别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向国务卿艾奇逊递交了一份名为《军备和美国政策》的裁军报告,其中建议应“坦率”地告诉美国人热核武器的可怕后果和更大程度地公布核材料的发展情况。*J.Michael Hogan,“The Science of Cold War Strategy: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War of Words’”,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pp.154—155.1953年5月19日,委员会再次强调,美国原子武器政策应与“自由国家共同体”保持一致;若双方对此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必定会“削弱主要自由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因此,现在应当是“以相当大的举措解决与主要盟友共享原子武器的整个问题”的时候了。总之,报告建议当局应充分认识到“盟友之间就原子军备竞赛问题展开更高层次交流”的紧迫性和实施“坦率政策”的必要性。*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U.S.policy towar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disarmament of nuclear weapons.Report.May 19,1953.CK3100516131.DDRS.
在多方压力下,美国决策层自1953年4月初开始酝酿 “坦率行动”(Operation Candor)的实施。5月底,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相关命令。*Chronology of Atoms for Peace Project,September 30,1954.[C.D.Jackson Papers,Box 29,Atoms for Peace-Evolution (1).]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9.pdf.7月22日,NSC151号文件命令杰克逊为总统起草“坦率政策”的演讲,告知公众“危险时代”的现实。由C.D.杰克逊负责的杰克逊委员会随即阐明了其必要性:“美国人民并没有理解总统关于我们生活在危险时代的言辞的含义。有必要采取更大努力弄清楚我们面对的危险、敌人的力量、抵制这种力量的困难以及冲突可能的持久性。”28日,杰克逊委员会再次强调:(1)将不仅告知公众危及他们自身的危险,而且解释他们正在反击此种危险;(2)对共产主义本质的尖锐解释有助于反击苏联和平攻势与维持停战协定之后的关系;(3)美国军事行动是一种抗衡苏联军事能力的自保行为。*C.D.Jackson and Robert Cutler discuss “age of peril” memo.Jul 28,1953.CK3100307104.DDRS.恰在此时,广告委员会(Advertising Council)负责人里普利厄(T.S.Repplier)向总统助理亚当斯(Sherman Adams)建议,开展一场宣传运动以“克服当前公众对民防、献血和储蓄债券等的冷漠”,寻求美国社会对冷战的支持。*Memorandum regarding “Operation Candor”,July 22,1953.[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s,PS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17,PSB 091.4 U.S.(2).]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7.pdf.
8月12日,苏联成功试爆了一颗氢弹,这比美国的预计整整早了一年。*Discussion at the 16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ld on 8/27/53.Memo.Aug 28,1953.CK3100129354.DDRS.苏联在核军事上的突破使美国认识到必须展现自身的技术优势,以维系对苏有效核威慑。美国官员诺伯格(Charles Norberg)在致克雷格(H.S.Craig)的备忘录中证实了此点:“构想‘坦率行动’以阐明苏联基本的科技潜能……不是披露影响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信息或数据,而是客观陈述西方和美国相比于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技术和工业优势。”*Memorandum,Charles Norberg to H.S.Craig regarding “Project Candor and the Soviet H Bomb”,August 10,1953.[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PS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17,PSB 091.4 U.S.(2).]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6.pdf.9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布关于“艾森豪威尔推动坦率行动”的剪报,强调此次行动旨在“让民众了解国家面临的严峻现实”。*Newsclipping,Washington Post,“Eisenhower Pushes Operation Candor”,September 21,1953.[Charles Masterson Papers,Box 1,Operation Candor.]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20.pdf.
按照总统设想,“坦率行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强调原子能的可怕性,旨在让美国社会警惕“共产主义危险”和苏联核威胁,推动公众继续支持庞大的国防开支;第二阶段凸显原子的“友好”,以消除公众对核武器的恐惧*Letter,Ann Whitman (President Eisenhower’s personal secretary) to Marie McCrum (C.D.Jackson’s personal secretary),January 27,1956.[C.D.Jackson Papers,Box 29,Atoms for Peace-Evolution (1).]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9.pdf.,后续行动为总统在联大会议上发表“和平的原子”演讲。艾森豪威尔指派自己的助理兰碧(James Lambie)负责实施第一阶段的后续宣传运动,继续强调冷战不仅是“即时”的危险,而且意味着世界正处于“危险时代”。为此,兰碧策划一档持续数月之久的访谈节目《危险时代》,由全国四大电视网络承办;共6期,每期时长为15分钟;总统参与首期和末期,以“确保权威的完整性”。同时由广告委员会利用报刊、杂志、电视、电台和车载广告等广泛宣传。*J.Michael Hogan,“The Science of Cold War Strategy: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War of Words’”,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p.155.访谈主题与受邀嘉宾如下:
(1)“共产主义本质”。即它是“对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的否定,致使帮派统治、秘密监控、集体屠杀、背信弃义泛滥成风”。嘉宾为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2)“敌人的能力”。包括“俄国及其卫星国”的军事、经济与科技能力等。嘉宾为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和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3)“对美国的威胁”。包括共产主义对美国经济、人力资源、科技能力的影响等。嘉宾为参联会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将军。(4)“自由世界与联合国”。包括美国与“自由世界”结盟的重要性;“自由世界”在美苏权力争夺中的平衡作用;强化联合国对“侵略的威慑”,“增强自由世界力量”等。嘉宾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洛琦(Henry Cabot Lodge Jr.)。(5)“国内共产主义”。在反共斗争中,美国存在着将“外部军事威胁错当内部政治阴谋”的危险,从而可能导致“民主”与“自由”不可兼得。嘉宾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和联邦大法官小布鲁尼尔(Hebert Brownell Jr.)。(6)“好公民能做什么”。对前述访谈进行总结。呼吁“危险时代”需要美国公民具有“坚韧”的品质以及“美国生活中值得为之奋斗和做出物质牺牲的道德和精神价值”;通过献血、购买债券、纳税、参军和“捍卫基本自由”等方式为冷战做出贡献。嘉宾为艾森豪威尔。*Memorandum regarding “Operation Candor”, July 22,1953.[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s,PS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17,PSB 091.4 U.S.(2).]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7.pdf.
广告委员会是宣传行动的主要推动者。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该委员会除了利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内刊和车载广告等媒体外,还推动劳工、管理、农业、宗教和老兵等社会团体举办主题演讲和出版活动;争取报刊和杂志出版商、编辑、专栏作家的支持;与电视电台评论员、特别项目导演、制片商与备有拖车和影片的参展商合作。总之,强有力的宣传“给数以亿计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Memorandum regarding “Operation Candor”, July 22,1953.[White House Offic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s,PS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17,PSB 091.4 U.S.(2).]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7.pdf.显然,“坦率行动”被美国官方当作一场冷战动员运动,通过告知美国人处在“危险的时代”之中,从而保持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警惕,进而推动国内“冷战共识”的形成。
(二)“和平的原子”演讲及其后续运动
按照第二阶段的设想,艾森豪威尔认为,目前的“坦率行动”“仅向美国谈及原子的危险和美国神奇的报复力量是不充分的,展现的将是荒芜凄凉的图景”,因此,“他想向美国人民所传达的,不是将对破坏而是对希望的关注作为一种结局。这必须从原子解决方案中寻求希望。”*General Outline for Agronsky Program,December 16,1953.[C.D.Jackson Papers,Box 100,Speech Texts 1953(1).]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4.pdf.这样,艾森豪威尔决心向世界发表主旨演讲,以塑造美国和平国际形象。
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大会议上发表“和平的原子”演讲,攻击苏联“拥有巨大的核武器优势、破坏性的报复能力,将在全力以赴的偷袭中动用原子弹”;而美国“认为源于原子能的和平力量并非未来梦想,它就在这儿——现在——今天”。因此,它“决心致力于解决令人恐惧的原子困境,全身心地找到一条途径,藉此,人类的奇妙发明将不会用于自掘坟墓,而是为提高其生活水平作出贡献。”*下划线为原文所有,详见Atomic Speech.Agenda.Oct 23,1953.CK3100358519.DDRS.
演讲结束后,行动协调委员会专门成立原子能工作组,迅速启动了关于总统演讲的海外宣传行动。美国新闻署联合国务院、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民防署,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大量主题宣传册、杂志、展览、电影、电视节目和讲座等,系统刻画了原子能的“友好”形象,彰显美国在与世界分享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仍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具体表现如下:
(1)利用电影电视。新闻署为此制作了系列电视节
目《原子的魅力》;*Nuclear energy and related information.Aug 15,1956.CK3100451017.DDRS.而《原子与生物科学》、《原子与农业》、《原子与医生》、《原子与工业》等纪录片也被新闻署送至海外放映。它们形象地解释了核电的概念,令原子能看起来“更加安全、赏心悦目而可爱”。*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p.170—171;pp.171—173;p.172;pp.174—177.
(2)利用新闻专题。此类文章反复表达“人类的仆人,友好的原子”之类的主旨。例如,《国家地理》常以官方风格阐述利用原子能建设美好世界的主题:“原子爆炸所产生的可怕力量,已被医学、农业、工业和电力领域内难以数计的和平任务所驯服。”*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p.170—171;pp.171—173;p.172;pp.174—177.
(3)利用大型相片。它同样反复表达了原子在工业上和平利用的含义。例如,一幅相片显示了一位技师正在检测一组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植物的情景。字幕解释道:“通过对放射性同位素的成功追踪,研究者已发现一种为植物提供肥料和营养的更好方式。”*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p.170—171;pp.171—173;p.172;pp.174—177.

四、“开放领空”运动
(一)“开放领空”的缘起
1953年5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小洛琦寻求在联大会议上宣传“和平的机遇”,以此作为“和平的机遇”运动的第二个阶段。他设想与心理战略委员会合作,向“自由世界”揭露“共产主义持久威胁的真相”和“确保苏联的任何和平姿态都被看作是一种宣传阴谋”,以“极力挫败苏联的和平攻势”,这便是“洛琦计划”。*Shawn J.Parry-Giles,“Militarizing America’s Propaganda Program,1945—55”,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pp.120—123.由此看来,苏联即使想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与美国达成一项削减核武器军备条约都不太可能。
实际上,自1945年美国提议的巴鲁克核能管制计划(Baruch Plan)流产后,美苏双方之间的裁军谈判已经停止。马林科夫上台后,苏联在裁军问题上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1954年新年伊始,马林科夫发表声明,宣称目前美苏双方缔结一项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协议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严格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机制的建立。数天后,格奥尔基·扎鲁宾大使在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面时指出,艾森豪威尔在联大会议上的提议没有包含禁止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的内容,这对于终止军火库的升级毫无益处;即使少量的核材料受到国际机构的监管,武器的数量还是可以增加;克里姆林宫愿意“为和平冒更大的风险和拓展更多的途径”。*[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孙闵欣等译:《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119—120页。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认真考虑苏联的新立场,仍然将它看作是一种宣传伎俩。
美苏在裁军问题上的真正分歧在于,美国要求实施包括核武器和常规力量在内的全面裁军,并坚持任何裁军协议的签订都应包含建立防止“欺骗”行径的监控机制的条款。苏联则希望在确定控防机制之前就应当禁止所有核武器的使用。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故从1954年4月至1955年5月,美、英、法、加、苏五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裁军谈判毫无结果。
苏联继续逼迫美国在裁军问题上与自己谈判。1954年6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Jacob Malik)宣称“即使遭受攻击,苏联也不再使用核武器”,但他同时要求联大“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确认为战争犯”。9月,苏联驻联合国新任代表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表示苏联愿意阶段性地推进全面核裁军协议的落实。1955年5月10日,马立克又向西方提议,苏联为了支持国际裁军署落实裁军的实质性举措,允许在其境内设置监督站和愿意削减自己的常规军事力量。这意味着苏联接受了此前西方提议的核心内容。*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5,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63—164;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187.
艾森豪威尔虽然对此颇为吃惊,但他早已将依赖大规模核报复能力确保美国安全的想法确定为一项基本国家安全战略,况且1955年1月出台的NSC5501号文件明确将苏联的和平举动视为“未来数年内自由世界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的挑战”,是“一项兵不血刃地击败西方的战略”,严重危及到美国和平战略*Basic U.S.policy in relation to Four-Power negotiations.Report.Jul 11,1955.CK3100177335.DDRS.,因而不可能就上述问题与苏联进行严肃谈判。最终,美国以日内瓦峰会即将召开为由,回避了马立克的上述建议。但同时,出于避免给外界留下拒绝谈判的强硬印象和牢牢掌控话语权的需要,美国必须提出一项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心理战计划来,这样,“开放领空”的设想逐渐浮出水面。
(二)“开放领空”建议及其后续行动
1955年,日内瓦峰会召开前夕,杰克逊、总统特别顾问洛克菲勒(Nilsen Rockefeller)在弗吉尼亚匡蒂科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会议认为此次峰会将为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提供一个反击苏联“和平攻势”的机会,而“开放领空”可作为谈判的筹码。当然,美国深知该建议必定遭到苏联拒绝,但它无疑有助于消除美国作为“好斗的军国主义大国”和“对终结冷战毫无兴趣”的消极形象。*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190.
7月6日,洛克菲勒将匡蒂科会议备忘录呈交给总统。12日,它被当作重要内容纳入白宫机密文件《关于日内瓦裁军谈判的心理战建议概要》当中。文件宣称,苏联“侵略”的“一贯模式”就是“惯用革命性的和平攻势”。在此次峰会中,苏联将同样只是寻求心理优势的实现,“在日内瓦的宣传赌注可能证明比实际的会议结果更加重要”。因此,对美国来说,如果“美国在日内瓦的基本目标必定是抓住世界政治和心理想象”的话,那么它就“需要自己的积极方式”,在四国谈判中尽可能向世界显示美国:(1)正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正义与进步”;(2)准备利用所有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途径,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的道德价值的方法”予以真正实现;(3)正在与伙伴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等。*Summa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roposals fo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Geneva.Jul 12,1955.CK3100192371.DDRS.随后,洛克菲勒进一步提出了美国实施“开放领空”计划的七大理由:有利于美国在裁军谈判中夺得主动权;有助于打破“铁幕”;为美国提供情报;向苏联抛出难题;集中关注人们能否理解裁军实际的和即时的两个层面;揭露苏联倡导的检查机制的“虚伪性”;向苏联展现美国具有更强大的战争潜能。*Summa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roposals fo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Geneva.Jul 12,1955.CK3100192371.DDRS.显然,洛克菲勒将日内瓦峰会当成了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场。事实上,他还忽视了另外一点。这从1958年科学顾问委员会技术能力专家组组长基利安(James Killian)的一份关于突袭政策考量的文件中可得知。他认为开放领空最重要的原因是,若空中侦察与作为最基本检测手段的地面侦察相结合,则为美国提供反击突袭的有效机制。而且,此种侦察机制一旦执行并证实在技术上可行,则能够推动对下一阶段裁军的有效监督。*Description of conditions which make a new surprise attack defense policy necessary.Memorandum.Sep 30,1958.CK3100165008.DDRS.总之,对美国而言,“开放领空”实为一项稳操胜券的建议:如若苏联接受,美国可从对方获取更多情报;若对方拒绝,则为自己带来决定性的舆论优势。
1955年7月18日至23日,峰会召开期间,艾森豪威尔如期抛出“开放领空”的提议。他强调,除非一种“充分支持协议每一个部分”的侦察和报告机制得以确立,否则一项可靠而合理的协议不可能达成。*President Eisenhower’s statements on disarmament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Report.CK3100455487.DDRS.苏联果然加以拒绝。它认为在缺乏裁军协议的情况下,由于权力政治的作用,必定会导致恐惧心理的加剧,进而刺激军备竞赛的升级;但如果双方首先达成一项裁军协议,则能够通过空中监督的方式加以落实。*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Summary of letter from Premier Bulgani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Outgoing Telegram No.022000Z,to the President,Gettysburg,Pa.Telegram.Feb.2,1956.CK3100374600.DDRS.

为了揭露“日内瓦精神”的“虚伪性”,美国政府广泛宣传“开放领空”的主张。洛琦将其吹嘘为“新的世界性裁军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公共信息部际工作小组的指导下,新闻署将“开放领空”确定为中心主题,要求海外宣传机构如同宣传“和平的原子”那般宣传,以迫使苏联接受它。新闻署将宣传册《出于和平的相互侦察》赠送给世界各地编辑和官员;同时在纽约举办同名展览,展示雷达、红外线相机和侦察机等先进设备,凸显美国捍卫和平及“开放领空”的技术可行性;洛琦亲自带领联合国成员国的59位代表参观了此次展览。随后两年内,在世界各地巡展。此外,新闻署还拍摄了解释侦察机工作原理的纪录片;发布故事图片《相片中的新科学》,显示美国向世界开放军备的姿态;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内放映电影《和平之路》;以32种语言在78个国家放映《和平守护者》;美国之音则以英语和其它37种语言对“开放领空”进行密集播报等。*Nicholas J.Cull,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1945—1989,2008,p.129;Kenneth Osgood,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pp.196—198.
五、简要评价
这一时期,美国将和平宣传视为一种可行的冷战策略。其目的无非在于两端:第一,揭露苏联的“和平共处”始终是一种“虚假承诺”,进而使海外民众相信美国所代表的和平较其鼓吹的两大阵营和平共处更有意义;*USIA program detailed.Feb 17,1955.CK3100007014.DDRS.第二,彰显美国既是开放、和平与进步的国度,也是和平价值的守护者,以维系“自由世界”的团结和击溃共产主义。为此,美国几乎同时启动了三场宏大的海外宣传运动。侧重点各有不同。“和平的机遇”运动是美国在苏联领导层更替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反应,着力营造一种冷战解决之途掌握在苏联手中的道德语境;“和平的原子”运动重点塑造友好的原子形象,喻意美国在增进人类福祉方面仍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开放领空”运动则聚焦裁军问题,鼓吹美苏两国应相互开放领空,建立有效的核武器侦察与控防机制。这看似平等,实则由于美国拥有先进的侦察手段而占据优势,势必遭致苏联拒绝,而美国则趁机让其承担破坏和平的罪责。
为了凸显宣传效果,美国将和平话语置于二元对立的价值框架内精心雕琢。它将自我拥有的原子能和核武器界定为“为人类谋福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手段;而将苏联的看作是“人类致命威胁”,并斥之为“帝国主义者”。这种价值分野是美国奉行冷战思维的必然结果。其修辞也体现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话语特征。作为一种富有技巧的政治战手段,和平宣传运动所呈现的修辞及形象具有明显局限性,并不能够带来真正和平。
首先,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既然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何还要频繁进行核试验的正当性。即使是作为美国盟友的西欧国家也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如果说这一点是出于反击苏联“侵略”的需要的话,那么,现在“苏联的和平姿态以及欧洲人意欲卸掉军备负担的想法使其认为来自东方的危险已然甚微”,而美国却继续大肆渲染苏联威胁,其目的必然是出于狭隘的国内动机。*Reported decline in U.S.prestige abroad studied.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ep 11,1953.CK3100194238.DDRS.美国当局炮制“实力确保和平”系列概念,旨在消除外界对美国宣称的目标与大规模军备之间的“困惑”,但就当时的舆论反应来看,此目的显然难以达到。
其次,无法解决美国背负“殖民主义者”骂名的形象困境。战后美国官方对“殖民主义者”的骂名颇为苦恼。总统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指出:“许多国家将我们看作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和牟利者。”*Space,Operations Plan for Outer.Bromley Smith,Exec.Officer,Cover Letter,to the President.Dec.23,1960.CK3100446026.DDRS.中情局也强调,特别是在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关于‘帝国主义’的质疑成为影响美国声望的最大消极因素”。*Reported decline in U.S.prestige abroad studied.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ep 11,1953.CK3100194238.DDRS.应该说,美国海外干预行动与其“和平”形象是相悖的,有违其一向宣称的民族自决和自由原则。著名学者文安立指出,崛起后的美国在与苏联的权力争夺中,在废除欧洲旧式殖民主义的同时,极力诱使第三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追随“美国范例”。随着冷战全球化的推进,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Odd Arne Westad,“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I,pp.8—10.这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但它既不能让盟友满意,也不被新兴国家买帐。正如美国新闻署抱怨的那样,“非洲国家怀疑美国殖民主义国家的身份,而欧洲质疑美国支持非洲的理想。”*USIA program as of 6/30/60 outlined.Jun 30,1960.CK3100321103.DDRS.因此,美国“和平”修辞及形象必定深受其殖民主义行径的冲击。
最后,必然遭致美国权力政治观的强势消解。中情局和行动协调委员会在解释战后美国海外身份困境时强调:“身处世界领袖地位的国家成为潜在大国和那些迫于情势已失去权力的大国忌妒与怀疑的对象。”*Reported decline in U.S.prestige abroad studied.Sep 11,1953.CK3100194238.DDRS.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政治观,即权力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为了确保自身的霸权与防止他国的超越,美国必须拥有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力量优势。遏制苏联,就是遏制它的“实力与影响”。*Lowell.Schwartz,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Kremlin:US and British Propaganda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Palgrave Macmillan,2009,p.106;Histor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CK3100280463,DDRS.尽管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强调运用象征或心理因素击溃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从权力均衡的角度看待美苏关系的一惯做法。*Free world views of the U.S.—U.S.S.R.power balance.Aug 29,1960.CK3100272858.这就决定了它决不会认真考虑自身军事力量的削减,而是追求一种拥有并保持超越苏联的军事优势。对彼时的世界来说,真正的和平就是立即停止核试验和削减军备。而美国显然难以做到。既然无法跳出权力政治的窠臼,那么美国的“和平”形象自然就是虚幻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研究(1947—1961)”(17FSS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