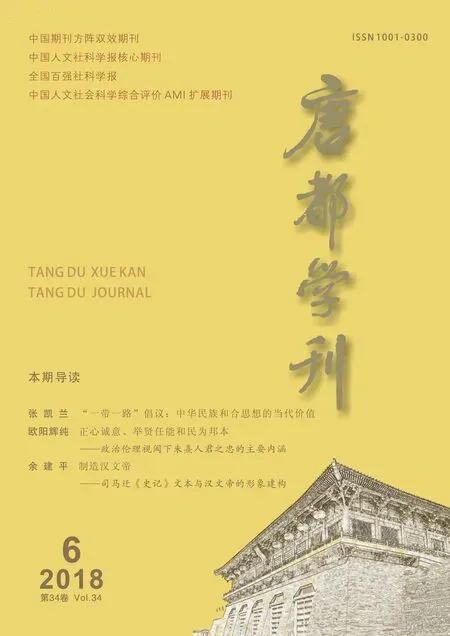陆游角色的冲突、认同及其成因
——兼论其对诗歌风格的影响
田萌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陆游诗风多样,且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清人赵翼云:“放翁诗凡三变。”[1]尤其爱国诗与闲适诗,从艺术风格的产生到嬗变,学界对此论述颇多。而陆游诗歌为何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多种风格状态?与他一直以来的“北伐情结”又有何种关系?此问题似多为人所忽视。本文试结合陆游人生经历、诗歌创作时代背景,从创作心理角度探讨角色问题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并分析其成因。
一
陆游诗歌现存近万首,题材广博,艺术风格各异。钱仲联先生说:“陆游诗的艺术风格,具有奇秀、豪横、沉雄、雅健、空灵、超妙、淡远、明丽等各种特色,而以雄健沉郁和清新圆润两种为主。前者多体现在爱国作品方面,后者多体现在闲散作品方面。”[2]陆游两种主要作品类型表现为雄健沉郁和清新圆润的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表现为浪漫雄奇和平淡质朴。
首先,陆游抒发爱国激情诗歌具有浪漫雄奇的特点。据《剑南集题跋》载:“孝宗一日御华文阁,问周益公曰:‘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对。由是人竞呼为小李白。”[3]2421时人称以“李白”,可见其诗歌之特色。陆游诗歌的浪漫雄奇主要体现于抒发爱国激情诗作中,以回忆与想象笔触,渲染诗歌浪漫放达之风。如淳熙十年(1183)八月作于山阴《秋雨渐凉有怀兴元三首》其一“八月山中夜渐长,雨声灯影共凄凉。遥知南郑风霜早,已有寒熊犯猎场”;其三“清梦初回秋夜阑,床前耿耿一灯残。忽闻雨掠蓬窗过,犹作当时铁马看。”[4]253在山阴平静的现实生活中,遥想曾经从军峥嵘的日子,现境与过去对比愈发强烈,现实生活中求而不得,只能追忆过去或生发想象。又有怀念征战苦寒,如“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4]298虽然征战苦寒,但回想之余,陆游却充满怀恋和赞叹,甚至有一种跃跃欲试之感。陆游以回忆的笔触,勾勒出真实、生动的军中生活,既是对战争的追忆,也是满腔爱国豪情的抒发。甚至现实中的生活琐事,也能唤起陆游对战场的向往。作草书时,想象自己身在战场:“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力槊,势从天落银河倾”[4]131。观一幅马图,想到“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衔枚夜度桑乾碛”[4]88;观秦蜀地图,想到“何当勒铭纪北伐,更拟草奏祈东封”[4]242;醉酒也会想到“何当呼青鸾,更驾万里风”[4]65。诸如此类追忆、想象的诗歌,语出雄豪之余,充满浪漫色彩。此外,陆游诗歌所传达出雄浑奔放的悲愤,又给人以气象阔大、一泻千里的感受。陆游为国家民族危难奔走呼号,对时局深感痛心。如《大风登城》:“我独登城望大荒,勇欲为国平河湟。才疏志大不自量,西家东家笑我狂。”[4]149《枕上》:“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明年起飞将,更试北平秋。”这类诗歌以酣畅淋漓的笔触写陆游为国平虏之壮志,以夸张的描述宣泄悲愤,以激昂高亢的笔调,奠定陆游诗歌壮阔豪迈、浪漫雄奇的风格特色。
其次,陆游诗歌的平淡质朴则主要体现在晚年乡居诗中。晚年久居山阴,陆游诗歌多吟咏山水风物、田园俗事,感慨人生无常、生命年老、怀念友人、对人生厌倦、读书所得、生活记录等琐碎内容具悉入诗,与爱国题材的浪漫雄奇大相径庭。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他(陆游)的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显示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帖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5]陆游晚年乡居诗便是对生活日常作细致描摹、咀嚼之作,富有生活气息而又清新自然。如《幽居初夏》:“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箨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平淡的乡居生活,在陆游诗中变得恬静、美好,充满生活情趣。《与村邻聚饮》:“冬日乡闾集,珍烹得遍尝。蟹供牢九美,鱼煮脍残香。鸡跖宜菰白,豚肩杂韭黄。一欢君勿惜,丰歉岁何常?”则写与村邻宴饮之盛况,平实淳朴,自得其乐。
陆游诗歌所呈现的浪漫雄奇与平淡质朴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特色,固然与其经历、情感相关,但陆游自身的角色作用亦十分关键。
二
陆游诗歌的浪漫雄奇,从简单层面来说,是由北复故土理想与南宋偏安一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由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陆游便以夸张手法,纾解内心的怨愤与不平。如其诗《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4]299铁马秋风,满怀恢复中原的“北伐”之心,但现实政治局势与他的理想之间发生着深刻的矛盾。这样的矛盾都转换为悲愤而喷发于诗句之间。如此豪壮的气质和壮阔境界同样离不开艺术的夸张。“安得龙媒八千骑,要令穷虏畏飞腾”[4]150,以大胆夸张的想象暗指北伐,气势雄浑之余,强烈的感情随着夸张的描写倾泄而出。
纵深来看,则是陆游角色自我界定与被认同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陆游一生为国事奔走,大呼北伐。《剑南诗稿》中,陆游“北伐”类诗歌多集中淳熙年间。退居山阴后,虽有部分此类诗歌,但数量无法与乡居诗抗衡。陆游一生以“北伐战士”自认,而晚年退居山阴,现实身份则是“乡居山翁”,此二者为陆游一生的两大主要角色。
陆游北伐诗歌主要集中在淳熙年间,此时北伐的情绪最激烈。换言之,陆游对北伐战士角色的自认在淳熙年间最坚定。此外,基于对爱国激情的抒发,陆游浪漫雄奇诗歌创作高峰亦集中于淳熙年间。然而对陆游来说,淳熙年间似是多事之秋,几次主要的连续性贬官,亦在此时,且似乎都与“北伐”相关。
陆游一生起落几任官职,四次论罢。据《宋史》载,乾道二年(1166),陆游因力说张浚用兵,被言官所论“交结台谏,鼓唱是非”[6]12057,自隆兴府通判免归。此为陆游第一次被免官。而第二次免官,据《宋会要辑稿》载,淳熙三年(1176)九月,新知嘉州陆游并罢新命,以臣僚言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7]3995。陆游此时在范成大成都府任参议官,淳熙三年三月便有诗《遣兴》:“鹤料无多又扫空,今年真是浣花翁。”《饭保福》:“免官初觉此身轻”[注]此诗作于淳熙三年三月。系年参见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后文诗歌系年均参照此书,便不再一一做注。。由此可知,三月时陆游已被罢官。三月免官之后,九月又罢新命。而三月免官之因,史料却未有确切记载。陆游在范公幕府时常流露出强烈的北伐情怀,如其诗《中夜闻大雷雨》《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等。而此时范成大更多关注的却是民生、政务。李致洙《陆游诗研究》亦云:“范成大调任四川制置使,邀请陆游做参议官,二人以文字交,不拘行迹,饮酒赋诗,互相唱和;但对收复中原,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不甚一致,这使陆游感到不满。”[8]此外,陆游在范公幕府,应说官职不低,亦是为国效力之处,可陆游却常有“功名”未立之感,有诗如《楼上醉歌》:“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注]此诗于淳熙二年六月成都所作。《白发》:“平苦乐方外,固与功名疏。”那么,陆游所谓的“功名”究竟指什么?陆游有诗《书叹》曰:“早得虚名翰墨林,谢归忽已岁时侵。”《夜分读书有感》:“终恨无劳糜廪粟,夜窗聊策读书勋。”可以看出,陆游视“功名”并非于翰墨之上。在其诗《游大智寺》中,诗人似乎给出了答案:“平生功名心,上马无燕赵。”可见陆游的“功名”与“北伐”相关。那么三月被贬之因是否亦与一再提到的“北伐”有关联?就在《遣兴》诗之后,陆游紧接着写了《过野人家有感》:“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躬耕”出自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很明显陆游在借“躬耕”写北伐事。陆游被贬后的状态正如《夜读东京记》诗所写:“孤臣白首困西南,有志不伸空自悼。”《闲中偶题》:“楚泽巴山岁岁忙,今年睡足向禅房。只知闲味如茶永,不放羁愁似草长。架上《汉书》那复看,床头《周易》亦相忘。”从陆游对“功名”的界定以及其被贬后欲吐不敢吐而又困顿难消的状态中,可以猜测,陆游此次被贬或许与他诗中一直高亢的“北伐”情结相关。
陆游第三次罢官归乡是淳熙八年(1181),“三月二十七日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陆游罢新任,以臣僚论游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屡遭物议故也。”[7]4002再次因臣僚论其行为不矩而罢官,“屡遭”说明不止一人论其“不自检饬”。在此期建安任上,陆游并不安于罢归两年多再次起复的宦职生活,认为“建安酒薄客愁浓,除却哦诗事事慵”[4]179;“谁知建安城,触目非夙昔。冥冥瘴雾细,潋潋蛮江碧。出门无交朋,呜呼吾何适?”[4]182这样的生活让他感觉到无所事事,甚至夜不能寐,“丈夫无成忽老大,箭羽凋零剑锋涩。徘徊欲睡复起行,三更犹凭阑干立。”[4]185可见,建安的生活让陆游十分痛苦。且常有《前有樽酒行》“主人但欲口击贼,茫茫九原谁可作!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宿仙霞岭下》“切勿重寻散关梦,朱颜改尽壮图空”一类慨叹北伐的诗歌,那么是否陆游因一再执着的“北伐”情怀,触犯了诸多主和派利益而被论罢?
陆游第四次被贬依然是由谏官所论,《宋会要辑稿》载“(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礼部郎中陆游……并放罢。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7]4015白简即弹劾官员的奏章,屡遭说明陆游再次得罪众人;而“有污秽之迹”仍旧含混其辞,并没有说明确切原因。绍熙元年(1190)秋,陆游罢归山阴作《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馀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由诗题可知,陆游此次仍是“因诗”获罪,名由为“嘲咏风月”,而从诗中夹杂着几可不察的不满与怨愤,可以猜测,陆游被贬之因并非只是简单的“嘲咏风月”。陆游于淳熙十三年(1186)至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任严州知州,秩满后除军器少监、礼部郎中。而在此期间,他依然写下大量壮志昂扬的北伐诗歌,如《纵笔》(其二)“丹心自笑依然在,白发将如老去何。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可以说,陆游对北伐有着一种不分时间、地点,执拗地“念念不忘”。或许陆游再次得罪众人亦与此相关。
陆游四次罢官归乡,均由臣僚所论,且或多或少都与执拗的“北伐”情怀相关。我们从陆游的一次次被贬可以断定,他“任官”最大诉求便是“北伐”,且坚定地以“北伐战士”自居。然而一次次地被罢官,正是当局对陆游“北伐战士”角色连续性地、毁灭性地直接否定,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和伤害。在罢官归乡之初,就某种情况而言,陆游来不及置换自己的身份,便被现实强行置换了心理状态。然而这是他内心根本无法接受的,就必然会发生冲突,这时的冲突是现实中山翁身份与“北伐战士”角色间的冲突,以及自我角色认定与角色被认定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些冲突结点正是陆游出现优秀作品的重大结点。这与创作心理上的规律相契合——诗人的创作心理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当他现实的身份和自己理想的心理状态出现剧烈冲突之时,便是他创作出现飞跃的一个时代。在角色的自我认定与现实认定以及现实身份冲突的作用下,陆游便用梦幻的笔触,以浪漫雄奇的诗歌来填补错位,使自己平复。而每一次平复后,他依然认定自己为“北伐战士”。但角色的回归与认同,又换来政治当局更剧烈的否定方式。那么,以几次被免官为关键点,在矛盾、冲突与纾解痛苦的双重作用之下,陆游数次“出仕”与“退居”被牵联成一个大的时区范围,这一时段正是他创作的飞跃期。也恰巧在这一时间内,造就了陆游诗歌的浪漫放达与壮阔豪迈。那么,陆游浪漫雄奇的“北伐”情结诗歌主要集中在淳熙年间便也找到了答案,因为陆游主要的几次贬官都在淳熙年间。
然而,陆游晚归山阴后的生活并没看上去那么乐观。正如其《秋兴》:“白发萧萧欲满头,归来三见故山秋。醉凭高阁乾坤迮,病入中年日月遒。”[注]此诗写于淳熙十年,陆游于淳熙七年十二月自抚州归山阴,至此时已有三年。《衰病有感》:“衰与病相乘,山房冷欲冰。在家元是客,有发亦如僧。”《病中作》:“破裘缝更暖,粝食美无馀。摩诘病说法,虞卿穷著书。身羸支枕久,足蹇下堂疏。”[注]庆元四年(1198)作于山阴。等诗中一再写到的,陆游此时身体羸弱多病,饮食粗粝,生活条件也不尽如人意。交织的矛盾以及生活的困顿,让陆游更加痛苦。那么为何他能写出《起晚戏作》:“地偏身饱闲,秋爽睡殊美。老鸡每愧渠,三唱呼未起。厨人罢晨汲,童子愁屣履。惰慵虽可嘲,安静良足喜。心空梦亦少,酣枕甘若醴。不学多事人,南柯豪众蚁”[注]此诗作于淳熙十年八月、山阴。一类诗中所传达的农家生活的平淡与安逸?
这种平淡,是陆游晚年当身份与心理状态完全吻合时,诗歌创作则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如嘉泰二年(1202)陆游奉命入都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第二年修成后,陆游便主动辞官归乡。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当大面积的时间开始冲决诗人雄心之时,他的笔触就会发生转移。他可能会放弃对自己理想执着的、执念的描写,转而彻底放逐自己,把自己放逐在平淡的生活当中。然后用表面的、乡村的、原野的乐趣来彻底置换自己的写诗性格。可以说,越是描写农村生活闲适、安逸,陆游心中越是痛苦挣扎。因为平淡的生活不但不能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能唤起很多痛苦的回忆。虽然此时的陆游早已变成一名乡野老翁,但那些枕剑疾呼、对“北伐”的坚持与执拗,陆游并没有完全放弃,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放弃努力,此时陆游对自己角色的认定则是“北伐战士”与现实“乡居山翁”的角色完全合一。所以浪漫雄奇与平淡质朴,都是创作风格的本质,这是由于陆游自我的角色期许和认定与时代对自己角色的认定,以及自身对时代认定之间的冲突与认同所造成的。
三
陆游之所以会有角色冲突与认同间的矛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执着地以“北伐战士”自认,坚定的“北伐情结”是其核心所在。那么时局是否适合北伐,陆游屡被论罢的政治背景如何,他对时局的认知又是如何?
首先,关于备战“北伐”大将变更背后的政治现状。乾道八年(1172),王炎被调离四川宣抚使任,孝宗派虞允文接替王炎经略川陕,以图北伐。陆游此时在王炎幕府任干办公事,恰巧外出阆中公干,在回程途中得知王炎内调消息,连夜赶回兴元。《嘉川铺得檄遂行中夜次小柏》正写于陆游得檄归南郑之时:“黄旗传檄趣归程,急服单装破夜行。肃肃霜飞当十月,离离斗转欲三更。酒消顿觉衣裘薄,驿近先看炬火迎。渭水函关元不远,著鞭无日涕空横”[注]参见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晋书·刘琨传》载刘琨与祖逖为友,共以收复中原为志,曾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字里行间都写出了陆游归程之紧急。最后一句,陆游借“著鞭”刘琨典故指北伐事,因王炎内调,北伐无望,陆游内心忧急如焚。《归次汉中境上》写于归兴元府境内:“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踏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4]47诗中对北伐无望之忧虑更加明显,“良时”指王炎内调事,故在陆游看来北伐良时已失。王炎经略川陕四年,周必大《除王炎枢密使御笔跋》云:“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除王炎为枢密使,依旧宣抚四川……初,炎与虞允文不相能,屡乞罢归。”[9]又《玉堂杂记》:“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是时参知政事王公明炎在蜀三年,屡求归。”[10]王炎主战决心一直很强,正如陆游《谢王宣抚启》中所道:“践危机而志意愈坚。”[11]41且王炎宣抚四川之时,周必大代孝宗作制词《王炎除枢密使加封邑制》说到:“西顾未宽,则藉精神而折千里;群方庶定,则还英俊以强本朝。”[12]可见王炎是带着孝宗北伐愿望经略川陕,王炎在蜀多年,被召回后,孝宗马上任命虞允文接替王炎四川宣抚使之位继续备战北伐,而王炎又与虞允文“不相能”之事甚至被周必大写在《除王炎枢密使御笔跋》中。且虞允文此次入蜀,孝宗在临行前嘱托:“陛辞,上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允文曰:‘异时戒内外不相应。’上曰:‘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6]11799孝宗与虞允文定下了“北伐之约”。以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那么此举是否希冀虞允文此行能挽救北伐颓势?然而“北伐之难”,即使虞允文殚精竭虑地治理四川,直至积劳成疾于淳熙元年(1174)过世,也未能成行。以陆游当时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干办公事”的职位,对北伐备战状态、幕主王炎在朝中之地位以及朝廷对“北伐”大将任命的微妙变化不可能毫无察觉。陆游一心北伐,那么,在接到王炎调离的檄文,即使不能再在幕府任职,其第一反应也应是思考下一任四川宣抚使之人,北伐备战是否继续。而陆游最强烈的第一反应只是一味地感叹北伐无人、良时已去,此举又是为何?是否陆游在深夜接到檄文的第一时间而倾吐于诗歌中的“北伐”现状就是他对实势的一个判断?
其次,双方国力、民力方面。淳熙年间,陆游的爱国诗创作较为密集,北伐呼声较高。此时之南宋,孝宗于隆兴二年(1164)与金签订“隆兴和议”,虽然使其恢复之志受到挫折,但孝宗依然以虞允文、王炎等从事蓄战之事,以嗣抗金。虞允文的去世,对孝宗来说是沉重一击,因朝中再难寻可依托之大将。且淳熙年间,朝廷党争中主和的“道学党”占上锋,此时南宋政治氛围主流已不倾向于北伐。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6]464。驻守四川多年的吴璘临终之时亦曾嘱托孝宗“无轻出兵”[13]。从以上诸多条件,均可看出,淳熙年间,就政治环境而言,不可轻易出兵。而在经济和民力上,南宋亦不足以支持长久的北伐之战。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緡钱六千百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14]289而此时支出,仅中都吏禄兵廪之费一项就近乎一千五百万[注]参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出支三十六万。宣和侈无度,然后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连年用兵,然犹月支不过八十万。至淳熙末,朝廷无事情,乃月支百二十万,而非泛所支及金银丝绢不与焉。以孝宗恭俭撙节,而支费拟于宣和,则绍兴休兵以后,百司宫禁循习承平旧弊,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削故也。”。且军费开支消费更甚,“乾道三衙、江上、四川大军新额宗四十一万八千人,殿前司七万三千人……其后诸军增损不常,然大都通不减四十余万,合钱粮衣赐约二百缗可养一兵,是岁费钱已八千万缗,宜民力困矣。”[14]405-406仅此便可看出此时南宋国力、民力之现状。虽然“隆兴和议”后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修养生息,但仍不足以支持朝廷庞大的军费开支。
陆游是有着一定政治眼光的。《宋史》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6]12057陆游认为经略中原,陇右为军事重地,所以应“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6]12057。陆游视陇右为重要战略根据地,大将张浚亦持此种战略眼光,其上书言:“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15]4367“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15]4370汉中地区为蜀地门户,与东南地区命运紧密相连,陆游的判断,有着一定的战略眼光。又,自建炎元年(1127)始,利州西路便一直由以吴璘为首的吴氏家族镇守,虽东西二路时有分合,吴氏家族的势力亦延伸到利州东路[16]。吴璘之子吴挺骄纵姿意,倾财结士,屡次过误杀人。陆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王炎认为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陆游却认为吴挺遇敌未必不败,且若其有功,必定将会不可驾驭[4]12057。后吴挺之子吴曦叛乱,正应验了陆游之语。可以看出,陆游识人,亦有一定的洞察力。那么以陆游的政治眼光和洞察力,对当前南宋的经济、民力不可能毫无认知和权衡。
而此时之金国统治者为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据《金史》载,世宗性仁孝,沉静明达。时完颜亮南伐,(金境内)天下骚动,加之“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而“海陵(完颜亮)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盼盼,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17]203可见完颜亮南侵,尽失人心,加之金自太祖以来,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值世宗即位之时,金之国力、财力、民力已无法承受战争的消耗。世宗即位后诏“旧人南征者即还,何以处之。必不可阙者,量用新人可也”[17]123。签订协议,修养生息,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史载“(世宗)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17]203-204,甚至有“小尧舜”之称。由此可以看出,金人连年征战,国力、民力疲于应对战争损耗,世宗在位期间的整顿和发展使金“天下大定”,从其国力、民心所向以及君主意愿来看,此时已不再适合发动南征之战。陆游在诗歌中曾有自注云:“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洞悉必具报。”[4]323“洞悉具报”几个字可以看出,陆游当时对金方军情了解是十分详细的,那么对金国内状况也不可能没有了解。以陆游的政治谋略,亦应不难看出,宋金之间一旦发动“北伐”之战,以双方的境况来看必是长期的持久之战,而双方国力似乎都不能支撑长期战争。
再次,社会心理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在世人观念中,宋、金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权已深入人心。如在《金史》中自“隆兴和议”签订后至大定二十九年(1189)[注]即孝宗淳熙十六年。,几乎每年正月或三月“万春节”,均有“宋、高丽、夏遣使来贺”的类似记载,可见当时的南宋作为与高丽、夏同等地位的外交国,与金在淳熙年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外交关系。且南宋时出现大量使金诗,如马扩《使金和赵良嗣》中云:“未见燕铭勒故山,耳闻殊议骨毛寒。愿君共事烹身语,易取皇家万世安。”诗人将世道安稳寄希望于议和使金。且对沦陷于金的中原区域,在南宋人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和祝穆编《方舆胜览》,均未包括金人统治的中原地区。祝穆子祝洙跋曰:“洙又尝记先君子易箦时语‘州郡风土,续抄小集,东南之景物略尽;中原吾能述之,图经不足证也。’”[18]1238其言政治原因南北相隔,无法著录中原地区,却也在另一角度客观阐明南宋江山版图、政治格局如此之事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盖中原隔绝,久已不入舆图,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18]1239可以看出,在时人观念中宋、金之分已十分明显。而陆游《锦亭》诗云:“诗未落纸先传唱”,指其在成都时与范成大相和之诗;又《春愁曲并序》中言:“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颇为人所传”[4]262。陆游自云其作品在民间十分流行,换言之,陆游对当时民间的主要趋向,是有一定了解的。那么时人如此之“观念”,陆游亦不应无所感知。
综合当时备战北伐大将变更的情况,国力、民力、财力以及时人观念来推断,当时的宋金关系,最好形态或者说最大可能,依然是维持当前现状、保持和平状态。因此,不论就时局还是朝廷风向而言,北伐形势并不乐观。陆游屡次论罢也应与此不无关系。而对于所有情势、状态,陆游也绝不应无所耳闻,所以陆游“北伐战士”与“乡居山翁”角色间的互动是个不断挣扎过程,那么为何陆游在知晓时局动态的情况下,仍然对“北伐”有如此浓重的情结,以致于自我角色错位,甚至与时代出现隔膜、产生巨大裂痕?
四
“北伐”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僖公》:“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19]指齐桓公征讨山戎一事。“北伐”,依字面来看,即指出于某种原因而发动的北上之战。南宋以前,中国古代历史上已有多次规模较大、略有影响的北伐,但性质、目的各不相同,大抵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维护政权正朔。如汉光武帝刘秀为汉室政权正统而对王莽之北伐,后建东汉;三国时期蜀汉刘备以汉朝宗室之正统,维护政权正朔为由,发动历时多年的北伐之战。其二,维护中原正统,收复失地。如西晋建兴四年(316),晋愍帝司马邺降匈奴,晋室南迁。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建立东晋,大批流民纷纷南渡,偏安一隅的东晋士人视中原为正统,从未放弃收复失地之愿望。自此,南朝开始了前赴后继的“北伐”之战。诸如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开始的祖逖北伐,以及后来的庾亮、殷浩北伐,又永和十年(354)开始的桓温三次北伐,之后的谢安北伐,义熙五年至六年(409—410)刘裕北伐;刘宋元嘉年间,宋文帝三次北伐;南朝梁武帝时期陈庆之北伐;陈太建九年(577)吴明彻北伐等。其三,民族间的北伐征战。如战国秦开大破东胡;秦一统六国后,蒙恬率军北击匈奴;西汉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之战;唐朝太宗贞观年间、高宗显庆年间与东、西突厥之战以及北宋为争夺“燕云十六州”而发动的“雍熙北伐”等。虽成败胜负各异,但从一次次北伐行为可以看出,北伐是中原士人固有的传统情结。
就陆游个人而言,北伐既是传统情结,也是对金态度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北伐”是陆游对金态度的终极指向,因为陆游的“北伐”情结,有着诸多内涵。首先,陆游所谓的“北伐”,指因异族侵犯所失固有领土的收复之战,也就是为收复北宋失地之战。这种观念可上溯至南北朝时期,面对外族入侵,中原土地沦陷,中原士人更倾向于借助“北伐”来维护领土完整,保持国家统一。祖逖立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20]1695冉闵亦曾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20]2793对中原土地的占有及依恋,在传统士人观念中深深扎根,不可动摇。宋人李纲为相时,进言高宗:“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若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蠭起为乱。……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6]11257其言中原地理位置之重要,认为中原一旦丧失,即使退居东南也很难自保。此语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单就其对中原的看重而言,也可见时人的“中原情怀”。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中原情怀,使得士人面对中原土地沦陷时,都会自发寻求“北伐”来收复故地。这是一种民族传统观念的体现,这种性质的“北伐”是中原士人面对疆土沦陷时的固有传统。其次,在陆游看来,“北伐”是为维护民族正统感之战。中国古代士大夫,有着根深蒂固的华夏民族“正统感”以及居主中原正统的观念。作为典型“传统士大夫”,陆游的“北伐”情结与维护领土完整、“维护民族正统感”的中原士人传统一脉相承。深刻的士大夫传统观念,与陆游的出身、家室、学识关系密切。陆游出身于山阴陆氏[注]陆游在《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奉直大夫陆公墓志铭》《陆氏大墓表》《陈史老传》中对自己的家室均有所叙述。,自汉以来,陆氏便为士家大族,世代遵守孝悌修身之传统。始迁山阴者为陆游七世祖陆忻,至其四世祖陆轸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直昭文馆,赠太傅;曾祖陆珪,国子博士,赠太尉;祖父陆佃,历仕三朝,官至尚书左丞,赠太师,封楚国公;父亲陆宰以朝请大夫直秘阁,历官淮南、京西转运副使,封会稽开国子,赠少师。陆氏家族先后在朝为官者有数十人之多,陆游出身于传统的士大夫之家,其士大夫思想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此外,陆游家学渊源颇深,祖父陆佃师承王安石,治经四十余年,博览群书;父亲陆宰亦是用功读书之人,家富藏书。陆游《读苏叔党汝州北山杂诗次其韵》云:“吾幼从父师,所患经不明。”[4]655陆游童年时便在父亲的指导下,以读经为重。自幼习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且《宋史》载,陆游十二岁能诗文,嗜书如命,《宋人轶事汇编》载有:“陆务观作书巢以自处,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曰书巢。”[3]2423自幼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加之陆游对经典的嗜读,是陆游学识获取、更是陆游深刻的传统士大夫思想之来源。而陆游自身又是严守传统士大夫言行的人,《后村诗话》载:“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决。”[3]2419陆游与唐婉伉俪情深,直至晚年对此事仍有介怀,但只因“二亲”,便出其妻。不难看出传统士大夫观念在陆游思想里根植之深,那么陆游坚决以“北伐”捍卫民族正统感便不难理解。再次,对陆游而言,“北伐”可复归文化正朔。建立在不可动摇的“民族正统感”基础上,中原传统士大夫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优越性。这在北宋士大夫的使辽诗中,已有体现。苏辙《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其三:“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其四:“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两首诗均笼罩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又以“蛮貊”“虏廷”等语汇代指辽,“蛮貊”常指落后民族,而“虏”为贬义,有“粗野、凶蛮”之意。外露的文化优越意识十分明显。王水照先生亦曾指出:“北宋使臣们一方面借用辽人之口对本朝作了自我赞赏,另一方面又对辽地的穷陋予以鄙薄耻笑。”[21]到了南宋,民族矛盾愈发尖锐,于南宋士大夫而言,金人入侵不光是对领土和政权的侵害,同时也是对文化的僭越和伤害。文人在作品中常以轻视的口吻称呼金人,如:辛弃疾“自是不日同舟,平戎破虏,岂由言轻发。”[22]陆游“一日天胜人,丑虏安足醢!”[4]298……又张孝祥《六州歌头》“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23]以洙泗二水,弦歌之地,染牛羊腥膻,指礼乐之邦被野蛮占领。似乎以“腥膻”“腥臊”指金人占据中原,是南宋士大夫的共识,如曹勋《癸未御前帖子》(其三)“中原久已困膻腥,攻守知惟断乃成。”曾丰《践司理李季牖》“中原染腥膻,岁月亦云久。”晁公溯《中原》“中原北望连虎牢。遗老略皆死草茅。腥臊千秋万岁殿,尘埃四通五达郊。”……从“虏”“腥膻”“腥臊”等词语,都可看出南宋士大夫对金人的不屑与嘲弄。少数民族入侵,对古代中原传统士大夫而言,是对民族正统感的动摇,也是对文化优越性的僭越与侵犯。陆游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对这种侵犯感的体会只会更加深刻。且陆游年少经历战乱,正如其《诸暨县主簿厅记》中所云:“建炎、绍兴间,予为童子,遭中原丧乱,渡河沿汴,涉淮绝江,间官兵间以归。”[11]1117年少亲历乱离的经历,让陆游深切地体会到这种侵犯感和僭越感及其所造成的痛苦。由此,促成了陆游具有强烈华夏民族观念的爱国情怀,从而寻求“北伐”来一雪宋人前耻。
也正因如此,“北伐”倾注了陆游诸多的诉求与希冀。情感上,陆游既希望“北伐”能成全其满腔爱国之情,又希冀藉“北伐”满足对故土的眷恋。宋金划江而治的政治现实,对敏感文人造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压抑。无论朝廷对金态度如何,罹落南方的文人都会慨叹故土,怀恋北方。陆游在王炎幕下亲临战争前线,这种政治情形,不免会促使陆游怀念过去生活,对此时国家境况产生无奈与遗憾。陆游希望北伐能消除这种怀念和遗憾,并使其满腔爱国情怀得到归宿。正如《观长安城图》诗:“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4]87“三秦父老”“王师”“散关”等词,均可看出陆游对“北伐”之希冀与期盼,同时也表达了陆游故土难舍之情。又如《山头鹿》:
呦呦山头鹿,毛角自媚好,
渴饮涧底泉,饥齿林间草。
汉家方和亲,将军灞陵老。
天寒弓力劲,木落霜气早。
短衣日驰射,逐鹿应弦倒。
金盘犀箸命有系,翠壁苍崖迹如扫。
何时诏下北击胡,却起将军远征讨?
泉甘草茂上林中,使我母子常相保。[4]471
诗中借鹿写人,通过对鹿安危不定命运的描写,暗指当时金统区人们生活安危不保的状态。陆游期待北伐能够使国家平定,百姓生活安稳,同时也表达诗人对故土、对故国百姓的眷念与挂怀。政治上,陆游希望通过北伐,收复失地,国家统一。如《夜观秦蜀地图》诗:“散关摩云俯贼垒,清渭如带陈军容。高旌缥缈严玉帐,画角悲壮传霜风。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吾皇英武同世祖,诸将行策云台功。……何当勒铭纪北伐,更拟草奏祈东封。”[4]242以“夜观秦蜀地图”为契机,写到往日军中生活,又写现今境况、报国之心,直陈以“北伐”之事谋取天下平定,国家统一。又“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4]86陆游对北伐的期待之心、必胜之意都通过“堂堂中国空无人”这一句声激厉疾地呼唤而表达出来。文化上,陆游则希冀通过北伐,中原政权回归正统而使文化回归正朔。《中夜闻大雷雨》:
雷车驾雨龙尽起,电行半空如狂矢。中原腥膻五十年,上帝震怒初一洗。黄头女真褫魂魄,面缚军门争请死。……从今身是太平人,敢惮安西九千里![4]110
此诗由夜中闻雷雨大作,联想到“中原”之事,黄头女真即指金人,诗中描写收复之战后的胜利景象,慷慨雄壮,感情激昂。最后一句“从今身是太平人”更从反面点明此时中原地区之“不太平”——失地未复的政治现实。诗人借“上帝震怒”将中原“腥膻”洗去,指北伐胜利,中原政权回归正统后,改变被野蛮破坏掉的礼乐之邦,“腥膻”去除,文化回归正朔。对陆游而言,“北伐”因有着特殊内涵,而承载了其在情感、政治、文化上的深切厚望。与此同时,“北伐”既是对领土一统的恢复,也是对以陆游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因“少数民族侵略”而造成的情感和思想创伤的治愈。
正是由于“北伐”的诸多内涵以及作为传统士大夫对北伐政治、情感、文化的诉求与希冀,支撑了陆游执着的“北伐情结”,使他一直以“北伐战士”自认,不断地在现实与北伐期许中挣扎,而“北伐战士”与“乡居山翁”两种角色的冲突与认同,则造就了陆游诗歌浪漫雄奇和平淡质朴的风格特征,使其成为南宋诗歌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