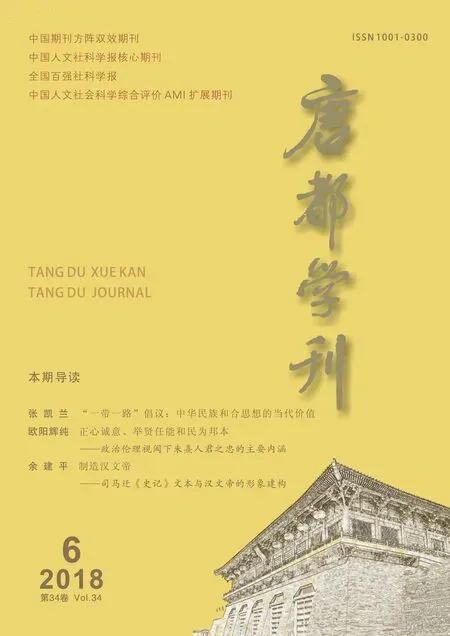论新时期陕西动物小说的文化反思与审美诉求
高春民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当下,以书写人与动物生态关系的动物小说成为洞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叙事文本,是生态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故事情节、主题内涵,还是叙事模式、艺术追求,动物小说都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较强时代意义的文学样式。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涌现了大量的动物叙事文本,如贾平凹的《怀念狼》,京夫的《鹿鸣》,叶广芩的《老虎大福》《黑鱼千岁》,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及红柯“西域系列小说”等等,为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地域文学经验。本文以贾平凹、叶广芩和红柯的动物小说为主要对象,从文化反思的视角对其进行探究和阐释,挖掘其间蕴涵的生态思想与审美诉求,反思与批判人类对待自然的理念、行为及方式,以期培育人们对大自然的亲和之情和审美之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理想。
一、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人类中心意识的猖行对于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有着不容小觑的推波助澜之作用。从普罗泰戈拉到笛卡尔,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被倡导并深入人心,从此人类与自然的疏离便拉开了帷幕。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人类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并对自然万物施以了涸泽而渔的征服与奴役行为,几乎泯灭了对自然万物内在价值最低限度的认可与敬畏之心,致使人类在对待自然的错误之路上愈行愈远,最终给自然和自身都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尤瓦尔·赫拉利曾说,正是这种罪恶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具有神一般能力、本来应该成为宇宙间“正能量”的智人,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贪得无厌又极具破坏力的怪兽,结果给地球生态带来了一场“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1]3。自人类诞生以来,已经与自然大地安然相处了千百万年,为何时至今日,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愈发显得如此紧张?究其原因,是人逾越了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序位且对这种逾越缺乏基本的理性认知和清醒反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学者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人类只是自然公寓的临时租客[2],仅此而已。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人从属于自然界,但自然界却从来不曾属于过人类,人仅仅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和自然公寓的匆匆过客,人不能逾越或遗忘自己在自然界中应有的位置而一味地以我为中心来考虑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顾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与整个自然世界的运行法则。
不可否认,任何生物在生理本性上都有唯我意识,都把保护自身作为其生存的目的[3]。人类亦不例外。由此来看,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利用和消费自然资源是理所当然且必须的,但是,这种利用和消费一旦超出了自然可承载的限度,一旦危害到了其他生物物种的基本生存,便是不道德的且不被自然世界的运行法则所容许的。《怀念狼》中,因为狼威胁到了人的生命安全,出于人类生存考虑,猎人要打狼,这是使命使然。但商州地界上的狼已经濒临灭绝的境地,已经无力对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猎人还要打狼,这或许是个体性情所致。更甚者,认为“人见了狼是不能不打的,这就是人”[4]190,便是人类中心意识在作祟了。傅山将猎狼作为实现其人生和职业价值的天职来看待,在人与狼相互对立的价值前提下来看待人与狼之间的关系,这种意识是不折不扣的以人为主体、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对此,贾平凹是持批判态度的。狼的存在与价值是其在生态系统的生态序位决定的,人不能以一己之喜恶来擅自判定。狼的灭绝,是以傅山为代表的人之不理性的残忍行为所致,这必然使人类自身走向合法性的反面。贾平凹以狼不在了,人却需要狼、怀念狼、呼唤狼的情节来结束小说叙事,其对于人类中心意识的态度便昭然若揭了。
人类中心意识固有的意念是以人自身的视角去看待人之外的一切,以人自身的习惯与喜恶来认知人之外的一切,有时虽并非出于恶意,但却对人自身和其所指向的对象都造成了伤害。任何生物都有自身固有的生理特点和物种习性,尊重动物的生理特点与物种习性,便是对人类中心意识的一种反省。叶广芩的动物小说中对此有自觉而深刻的意识。她指出:“有时候我们不要自作多情,自作主张,人为地去指导动物的生活,以为什么都会按照人的设计而存在,这实在是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5]有时人出于“善意”去帮助动物,初衷是为了动物有更好的归宿,不料这种违背动物“意愿”或习性的行为却成为它们灾难或悲剧命运的祸首。人们习惯地将自身的固有意识强行移加到动物的生命之中,然而对动物来说并非是福音。《熊猫“碎货”》中,人们将熊猫供养在牢笼之中,让其过上人类认为“丰衣足食”的安逸生活,其实人们根本不懂得熊猫最想得到、最需要的是返归山林,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家园的渴望。《狗熊淑娟》中的熊仔,若不是出于“善意”的地质队员将其收养,它或许会在大自然的家园中安享一生,然而却在“人老珠黄”“一无是处”之后成了人类餐桌上的饕餮大餐。可见,叶广芩以平俗的日常生活叙事,告知我们以人类为中心来对待人之外的自然万物,对人类来说可能是一种利益和意愿的实现,但对自然万物来说却是一种价值的丧失,甚至是灾难。
美国思想史学者纳什认为,一个裁剪的过于适合人之需要的自然界将毁灭裁剪者[6]。在人类中心意识的诱导之下,人类总是习惯性地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类的价值需求与爱憎喜好来认识和改造自然万物,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原本丰富多样的自然世界,变得不再斑斓多彩,而是黯然无光;不再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人或许满足了自己的私愿,却是以失去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最终也将在裁剪自然界的过程中日渐腐蚀自然之根,成为一种孤命自怜的物种。因而,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人类这种自尊自大的自我中心意识了,如果继续肆意妄为,一意孤行,我们在失去斑斓多彩的自然家园之后,也将在精神与生命的荒芜中迷失人类自身。
二、欲望主义反思
在众多关于生态危机发生根源的探究中,人类无限的贪婪欲望是其中之一。尤瓦尔·赫拉利曾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结语中写道:虽然现在人类已经拥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对目标感到茫然,而且似乎也仍然感到不满……我们对周遭的动物和生态系统掀起一场灾难,只为了寻求自己的舒适与娱乐,但从来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甚至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1]393-394。人类的贪得无厌使人在心理和精神两方面都无法得到满足,疯狂地攫利与过度的消费只能加剧人类的饥渴,也毁坏着自然界的生态系统。
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是生态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对人类来说,欲望是指对物质财富、功名地位及除此之外的具有象征性之物的需求。从理性上看,对欲望的满足应该以生存为基本前提,如果将占有作为对欲望追求的目标,那将会陷入欲望化的泥淖中难以自拔。《鹿鸣》中对鹿王峰峰美丽无比的鹿角的追逐,凸显了人类将占有作为满足需求的邪恶之性。从医学上讲,鹿茸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普通之物,但小说《鹿鸣》中对峰峰鹿角的追剿看重的并非是鹿茸的药用价值,而是对珍奇稀有物质的占有之欲,是对身份、地位象征意义的追求。为了各自的目的和欲求,几股势力围绕着鹿王峰峰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追逐,显示了人类贪婪无耻的人性。当以征服和占有为目的的邪恶欲望无限膨胀时,人类意欲征服与占有的对象便面临着无法逃避的灾难。正如小说描绘的,整个西部大地地广物博,物产丰富,然而却找不到一块适合鹿群生存的净地,处处是邪恶和充满着欲望的陷阱。作品通过揭示鹿群无处可逃的生存现状,表达了对人类无穷无尽欲望的强烈谴责与深深的愤慨之情。
为了生存,我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我们对物质的追求不以正常生存为索取前提而以占有为行动目标,人的欲念将被无限制地放大,这必将给自然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时毁灭的也是人类自身。《可可西里狼》中,杜光辉以其亲身经历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由仅为满足生存需要而猎杀动物到完全脱离“需要”而变成为“占有”而猎杀一切可以换来金钱的动物的过程,揭示和批判了人类欲望的无尽和贪婪。在无限膨胀的金钱欲的驱使下,人类贪婪的欲望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拥有现代化猎杀装备的盗猎者蜂拥而至佛爷的圣地,开始了人类欲望的全武行。他们不分季节不分大小、不分多寡地对野生动物施以灭绝人性的屠戮,可可西里到处是被遗弃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等野生动物支离破碎的尸体,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当人对物质的欲求陷入了走火入魔的阶段,便是欲望之欲望了。欲望之欲望是异化了的人性畸形的表现。《黑鱼千岁》中,儒对猎物的追求便是对满足欲望之欲望的追逐,是一种变态的或异化的欲望。儒对猎物有一种发自本能的猎杀之欲,一种情不自禁的性情冲动,他不是为了猎物而猎杀,而是为了在猎杀猎物的过程中享受这一过程本身。如小说中所写:儒盼望着猎取过程长,拖延得越长越好。猫儿逮老鼠是个自娱的过程,猫逮到老鼠并不马上吃掉,而是抓了又放、放了又抓,要将猎物细细地玩个够。现在儒就是这种心态,他逮鱼不是捕杀,是一种游戏,内中的乐趣只有参与的人才能体会[7]。席勒曾说,只有人在游戏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对于儒来说,满足捕杀猎物欲望的过程,就是在享受游戏本身带来的自由,是一种发自性情的满足。由此可见,叶广芩对儒的这种欲望之欲望的展现与揭露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欲望昌盛之时,便是人性异化和人类灭绝之始。书写欲望驱使下的人性之变异将生态文学的欲望化反思与批判推向了高潮。
在人与动物关系的书写中,欲望化的生态批判的目的是在警示人类主动限制贪婪欲望的同时,也在呼吁人类应该担当其应有的责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够运用理性来科学指导自身行为的物种[8],而且我们已经在自然界中享受了太多的特权,因而人应该运用理性最大可能地克制欲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克里考特指出,我们时代最急迫的道德问题,就是我们所负有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9]。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受益和破坏性最大的物种,理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所有生物的生存和整个自然界存续的重担,自觉地将人类的贪婪欲望关进合理性的牢笼之中,为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运行,也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贡献应有之力。
三、和谐共生的审美诉求
当下的动物小说将人与动物之关系置于对立、对抗的模式中进行叙事,为的是通过对人与动物对立与冲突关系的书写,凸显人类对动物的残忍伤害与生存空间的恶性挤压,进而对人类错误对待动物的理念与行为展开文化反思和批判。然而,一些动物叙事文本摒弃了这种对立与冲突的书写模式,将人与动物统一起来,变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关系为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间性关系,构建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共同生存于自然界之中的美好图景,以表达作者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诉求。其实,从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之中处于生态序位上的每个生物体来说,生物个体之间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只有生态序位的高低之别。从生物个体之于生态系统的贡献来言,人不见得比一只狼或一只昆虫贡献大。从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作为生命形式,任何生物体身上都拥有一种天赋的道德权利,即不遭受不应遭受的痛苦的权利和享受应该享受的愉快的权利。动物的生命和尊严与人一样,也应该获得人类同样的尊重[10]。动物与人一样有着天赋的灵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这种灵性和尊严是与人建立和谐共处之关系的伦理前提。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已不再是冰冷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也即程虹所说的“我和你”的关系[11]。同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应该是“我与你”的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人类,也不是非人类,而是以人类和非人类为共同中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是互为主体的间性关系,而非单方面的主体关系。人与动物同样如此。在众多的动物叙事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人类主人公能像对待人类自己一样对待动物的,都会得到动物的报恩,人与动物之间必然是和谐的,反之必然得到动物的复仇,人与动物之间必然是对立、冲突的关系。
《长虫二颤》中,二颤将身边的动植物视为自己亲密的伙伴,与它们建立起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平等关系,共同享受自然界赐予的阳光、水源和食物,没有伤害动物之心,也没有视动物为异类的戒外意识,因而能与周围的各种动物自在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山鬼木客》中古人类研究学者陈华返回山中,与那里的岩鼠、四脚蛇、云豹、猢狲等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可见,动物生命具有内在的灵性,生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外在限制,彼此共感谐振,领受宇宙大生命对单个生命有限性的救渡[12]。只要遵从大自然生存合法性的规则,尊重动物个体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性,将动物当作人一样作为具有内在价值和独立生存权利的另一主体,人与动物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彼此的和谐相处。反之,则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局,如《黑鱼千岁》中的黑鱼与儒,《怀念狼》中的猎人与狼,等等。
《怀念狼》中,作者在勾勒猎人与狼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之外,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道士与狼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以傅山为首的猎人将狼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人与狼之间是见面分外眼红的冲突关系。而老道士与狼之间却是平等友善的和谐场景。原因就在于老道士视狼为独立的存在个体,他对狼的关心、理解与照顾,是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众生平等的信念与狼建立了相互信赖的间性关系。当他归西弥留之际,仍然挂念着狼:“我这一去,它们来了找谁呀!”[4]147正是老道士将狼作为另一个生命主体,并给予理解、尊重,关心和爱护,人与狼之间才充满了和谐温馨的人情意味。而在猎人心中,人见狼就必须打,否则就不能为人,他先在地把狼作为异己的对立面来看待,这就堵死了人与狼两个主体交流的可能性,人与狼的关系自然是剑拔弩张的!
其实,在新时期陕西动物书写中,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审美诉求展现得活灵活现的作家是红柯。在其动物书写文本中,人与动物之间不是异己的对象化的关系,也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主仆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彰显、互利互惠的亲密友爱的伙伴关系。熟悉红柯作品的读者都知晓,他的许多小说中都有这样一组关系存在:如《美丽奴羊》中的屠夫与奴羊,《奔马》中的司机与骏马,《鹰影》中的孩子与苍鹰,《大河》中的熊与老金家,《西去的骑手》中的盛世才与狼,等等。在这些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动物与人之间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彼此独立、平等友爱的相互印证与彰显的关系。同时,在红柯笔下,太阳、月光、兔子、苍鹰、羊甚至还有花草树木等自然物都被赋予鲜活可感的生命,有生命的动物和无生命的植物与人完全融为一体,他们都是自然界的精灵,没有高低贵贱,人和动物作为生命形式彼此是独立、平等且具有主体性的,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神话的世界中,一切都充满诗意、安详静谧而又不失原始的生命活力。
在其他动物小说作品中,动物本身成了被人为赋予的具有种种象征意义的文本意象,是寄寓了作者某种思想感情或道德品质的指涉物。而红柯不同,他没有像其他动物小说作家那样赋予动物某种道德品格或文化内涵,他笔下的动物是原原本本的生灵,人与动物之间演绎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融、神合,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彼此没有贵贱、主次之分,他要赞美与歌颂的正是动物身上所体现的原始的天真与淳朴[13]。在生命与生命的交融、神合之中,人与动物两个主体之间达到了彼此合一、物我两忘。在此过程中,人将外部世界逐步内化入自我经验之中,将其变成了“属人”的世界。同时,人也以此拓宽了生命,从生存的局限和狭小的自我空间中突围而出,在和谐共在中突破了生命个体的有限性,实现了生命的升华与无限的绵延。
可见,动物小说无论是将人与动物置于对立、对抗中进行叙事,以开展文化反思和批判,还是在人与动物和谐关系的勾勒中表达和谐共处的审美诉求,其根本旨归是借人与动物之关系来暗射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味的对抗或冲突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人对自然的敬畏或崇拜关系,而应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间性关系。这种间性关系建构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因而,对人类来讲,应该在自然界可承载的限度之内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应该对自然抱以敬畏之心,同时要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与观念,努力克制人类欲望中的贪婪之性,培育对待自然万物的审美心性与亲和之情,审美而非功利地看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以缓解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