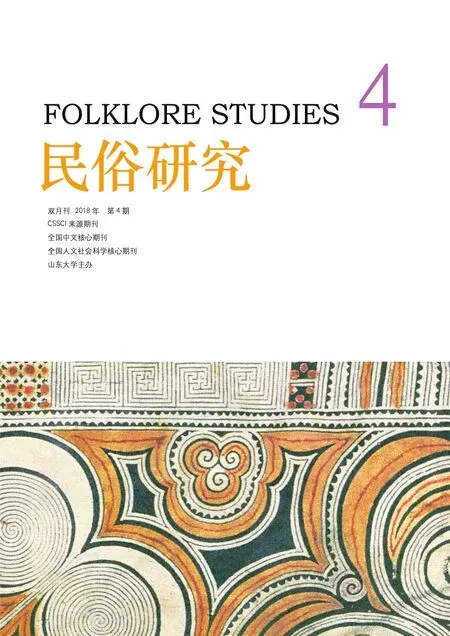《世说新语》女性称谓和性别文化
马 丽
当前性别语言研究较多关注现代汉语时期,较少涉及中古文献,致使难以全面呈现汉语的性别文化。《世说新语》是一部研究中古汉语语言的重要材料,本文拟从女性称谓角度切入,管窥魏晋时期的性别文化。在此,笔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余嘉锡先生校注的《世说新语》为具体参考对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此书除正文外,还包括刘孝标的注和余嘉锡先生所引用的同时期文献。
一、姊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德行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页。
余嘉锡所引出自《淳化阁帖》中王献之写给郗道茂的书信。两人原为夫妻,后离婚,王献之在信中表示歉疚与想念。王献之以“姊”称呼其妻,这与现代汉语情侣间“哥哥”“妹妹”的互称并不相同。王献之的母亲郗璿是郗道茂的姑姑,郗道茂的父亲郗昙是王献之的舅舅,两人是真实存在的亲戚关系。
魏晋时期士族婚娶,多注重社会地位的对等,如琅邪临沂王氏家族王凝之与陈国阳夏谢氏谢道韫联姻,太原晋阳王氏家族王坦之与南乡舞阳范氏范盖联姻,大族之间具有互为配偶的裙带关系。出于“亲上加亲”“强强联合”的考虑,一些近亲之间也建立了婚姻关系。王氏两代娶郗氏女,献之和道茂是姑表姐弟,两人是交表婚,故以“姊”称之。
士族女子婚嫁往往被要求门当户对。《方正》篇载桓温为儿子向王坦之求其女,王述得知后大怒:“兵,那可嫁女与之!”虽然当时桓温已经大权在握,但在太原王氏家族眼里还是不够档次,“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配不上自己家族的女子。这个故事的最后是桓温把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达到联姻的目的。又如《贤媛》篇载汝南李氏络秀为“门户计”嫁与周浚。魏晋时期社会通行的婚姻观念对于女性而言,可“高攀”,不可“下嫁”。王献之所属的琅邪临沂王氏家族,郗道茂所属的高平金乡郗氏家族,都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显然是门户相当。然而即使是士族高门,也敌不过王权。王献之后来离婚,另尚简文帝女新安公主,郗道茂只好投奔伯父,郁郁而终。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揭示的婚姻的意义:“六朝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页。在宗法制度下,君权与父权结合,政权与族权结合,婚姻只是政治、权术的手段而已,女性几乎没有婚姻自主权。
两汉时期,在决定子女婚姻方面,父亲比母亲拥有更大的权力。“迄今为止,尚找不到一个母亲的婚姻决定权大于父亲的事例。只有在父亲死后,母亲才有可能决定子女的婚姻。”*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这种情况到了魏晋时期有了松动。《贤媛》篇载王济欲将妹嫁兵家子,其母钟氏以“必不寿”为理由拒绝了这门婚事。据《晋书·王济传》,王济“年四十六,先浑卒”*(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7页。。也就是说,王济在给妹妹做婚配时,他的父亲王浑是在世的,但我们只看到母亲钟氏的身影,她的意见决定了这桩婚事。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魏晋时期婚姻关系中,男尊女卑的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如前文所述的《方正》篇里王述决定子孙辈的婚姻,历史上有名的“东床坦腹”王羲之也是由郗鉴决定做女婿的,父权掌握了婚姻的主导权。在离婚权方面,也是如此。王献之以尚公主为由离婚,郗道茂只能选择接受。与褒扬贞节烈女的社会主流文化不同,魏晋女性可以再婚嫁。《假谲》诸葛恢女儿丧夫后被家人设计强行再婚嫁给了江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离婚后被兄长逼迫再婚,当时的社会舆论并不以女性守节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对于女性离婚、再婚并不过多干涉,显示了当时多元的婚姻观。
二、“妇女”与“尚书”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女,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上《方正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8页。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下《方正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2页。
《方正》篇中周叔治因为要与兄长别离而伤心落泪,这让其兄周仲智很看不起,将弟弟比作“妇女”,表达不屑和轻视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夏启‘家天下’标志着男权社会的完全确立,女性歧视从此以后就有了显性的表现。”*刘福根:《汉语詈词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女性低于男性一等。周仲智将女性称谓冠之于男性头上,一方面是生气弟弟的儿女情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望,认为男性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应该坚强勇敢、积极乐观,“啼泣”是男性女性化的表现,是不可取的。
《惑溺》篇中王导的爱妾雷氏因为干预政事、收受贿赂,被蔡谟戏称为“雷尚书”。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当男女性别与特定社会角色并无显著的关联偏向时,性别词“男”“女”都能作为构词语素缀加,如“男孩子/女孩子”“男朋友/女朋友”等。但当有关联偏向时,会出现性别范畴内性别标记不对立的情况,一方有性别标记,另一方没有性别标记,如“司机/女司机”“护士/男护士”。这是因为在一般认知模式中,一些社会角色被认为是仅由或通常由某个性别来充任。“尚书”这个词语本身并无性别限定,原则上男女都有可能担任,但在进入父系氏族之后的古代社会,女性没有从政的机会,尚书类职官称谓在性别角色认知中被限定为男性。蔡公将男性称谓冠之于女性头上,一方面是讽刺王导没有管理好妻妾(所以《世说新语》将这个故事归入《惑溺》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认为女性的角色应该是贤妻良母,母教不出闺门,而非“预政事”“纳货”这类乱纲纪的事情。《尚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在古人看来,女人干政是祸国的根源,妲己、褒姒、杨贵妃等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祸”。
性别词语所反映的性别角色,包含了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传统社会对两性所赋予的角色期望是不一样的,早在《诗·小雅·斯干》就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之语。这反映古人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期许,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男人得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它“包含一个由个性特征、社会角色、行为和身体特征联结而成的网络,并具有连锁性的复杂关系,因此性别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在各种社会背景下的行为的推断”*[美]玛丽·克劳福德、[美]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许敏敏等译,中华书局,2009年,第108页。。“浓眉大眼”“柳叶眉”“威武”“温柔”之类的词语,虽然字面上没有性别限定,但在传统文化里却有性别指向。这种性别指向,反映的是人们根据性别因素作出的相应的认识,认定某性别的人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行事。《世说新语》中这两例性别称谓异用,将女性称谓用于称呼男性,将男性称谓用于女性,反映了当时的性别刻板印象。
三、贫 道
既而烈宗问妙音尼:“荆州缺,外闻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出家人,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内外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上《识鉴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0页。
妙音是东晋有名的比丘尼,文化修养很高,在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烈宗因荆州刺史一职咨询妙音,交谈中妙音以“贫道”自称。佛教传入我国后,自西晋时期开始出现女性出家人。发展至东晋,比丘尼很多与上层社会往来,受到帝王、后妃、官宦、高僧等上层阶级的支持,比丘尼除了为他们诵经祈福、宣扬佛法外,还参与政治活动。例中的妙音尼以其名望,成功为殷仲堪谋求到荆州刺史一职。
“道人”“道士”原指有道之人,被宗教借用后用于称呼从事佛教、道教信仰活动的人。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为宣扬佛法、团结信众,在传入之初依附道教而行,“佛教徒大量借用道教方术的用语,包括称谓……和道教徒共用‘道士’、‘道人’、‘道流’这样的称谓”*俞理明:《从〈太平经〉看道教称谓对佛教称谓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随着佛教教义的发展和自身影响力的提升,佛教足以自立并与道教分庭抗礼,唐代始出现“贫僧”这一佛教徒专用的自称。对此,张鷟:“(稠禅师)曰:‘陛下将杀贫僧,恐山中血污伽蓝,故此谷口受戮。’”*转引自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
佛教将出家修行的人按照性别分为“比丘”和“比丘尼”,在中古汉语时期,佛教徒都自称为“贫道”,并无性别之分。南朝萧齐僧伽跋陀罗《善见律毗婆沙》卷十六:“若人偷比丘尼衣,不得言是贼,但言此人取贫道衣去”;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卷四:“贫道有一苍头,即为随喜”。这都是女性出家人的自称。所谓贫道,唐朝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十四:“涅槃云:沙门那者,是本音也。或云乏道,或云贫道也,此皆谦虚自收也。”《佛学大辞典》:“贫道者,乏圣道之义,是沙门自谦之称。”*丁福保主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71页。佛教宣扬众生平等,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积极发展女性参与宗教,“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和发展,是佛教深入社会的标志之一”*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4页。。佛教徒自称没有性别区分,正是佛教基于众生佛性、吸引普罗大众信教参教这样的信念。明朝始有女性佛教徒自称“贫尼”,周履靖《锦笺记·协计》:“老旦上:贫尼极乐庵庵主是也。”*转引自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至此,佛教徒有了“贫僧”“贫尼”性别对立的自称。
佛教文献语言按照受原典影响的不同,可分为“汉译佛经、中土人士的佛教撰述和以宣传佛教教义为目的的文学作品等”*朱庆之:《佛教混合汉语初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页。。其中汉译佛典直接受到梵语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土撰述和佛教文学作品较少受到外来语的影响。通过语料库检索,我们发现女性出家人以“贫尼”自称,只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佛教典籍汇集编成的《大藏经》中并无使用。也就是说,出家人自称的性别区分,是世俗文献在明清时期创造出来的,不是受外来语的影响。这与汉民族本土文化有关。儒家理念男女有别,对出家人自称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
四、结 语
与宋明时期理学占据主导地位不同,在中古汉语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魏晋玄学兴起,儒学礼制尚未严格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父系家族伦理还没有取得全面支配性力量。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班昭著《女诫》,但在魏晋时期“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性别专制体制还只是指导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个性鲜明,“和正史《列女传》‘贞女亮明白之节’的性格完全不同”*逯耀东:《〈世说新语经〉对个人形态的描叙》,载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第146页。。无论在家庭生活、社交场合或者宗教领域,都能看到女性活跃的身影。婚姻虽然是政治手段,但女性并不需要守节,离婚再婚在当时被视为正常。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低,她们通过婚姻或宗教手段参政议政。以上即是我们通过《世说新语》几个女性称谓所了解到的魏晋性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