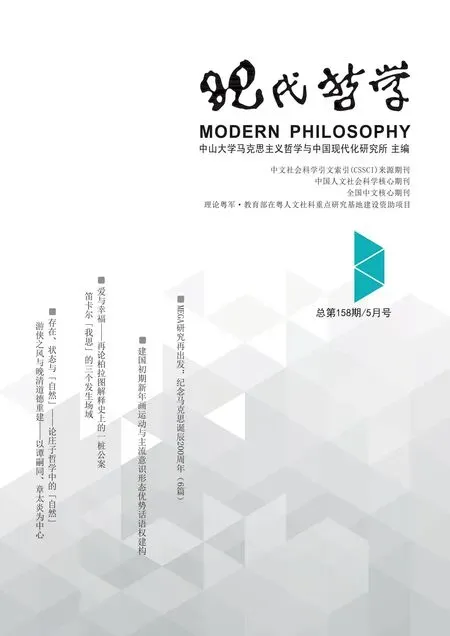存在、状态与“自然”
——论庄子哲学中的“自然”
罗安宪
“自然”作为一个概念,主要是一个道家用语,主要见于道家典籍。“自然”一语,《老子》5见,《庄子》8见,《列子》6见。儒家的十三经,无一提及“自然”。先秦儒家者中,只有《荀子》2见。其他重要典籍,《孙子兵法》无见;《墨子》1见,见于《经说上》,为后期墨家著作;《国语》无见;《战国策》1见。
一、“自然”之义
何为“自然”?《老子》《庄子》《列子》只用其语,不释其意。汉以后,王充、郭象始对“自然”作出解释。王充曰:“天动不欲以生,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在他看来,“物自生”、“物自为”即为物之自然。“自生”、“自为”之“自”是相对于“他”而言的。自然之物,谓物之如此,是自己如此,而非他物使然。对此,郭象进一步说明:“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庄子注·齐物论》)*[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0页。郭象指出,“自生”非“我生”。“自”不同于“我”,“我”是有意的,“自然”、“自生”之“自”是无意的。“自然”即是“自己而然”,这样的“自然”也就是“天然”。“自然”之被称为“天然”,是言其“非为”也。“为”可能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为”来自外在方面、外部力量,即因“他”而为、因“他”而如此、因外在力量而如此,就此而言,“自然”之“自”是相对于“他”而言的;“为”来自内在方面、内在力量,来自内在的意愿、意志,即因“我”而为、因“我”而如此、因内在力量而如此,就此而言,“自然”之“自”是相对于“我”而言的。“自然”是“自己而然”,是“自生”;既不是“他生”,也不是“我生”。“他生”即是因外在力量而生,“我生”即是因内在力量而生。“自然”既没有外在的力量,也没有内在的力量;既没有外在的强迫,也没有内在的压力,所以是“天然”。
因此之故,我们才能明白,在老子的思想系统中,“自然”是一个不同于“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概念。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二十四章)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虽然也是“自”,但其“自”是有意的,是因于内在力量而如此,因“我”而如此。“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不同于“自然”,更重要的是:“然”是“非为”,而“见”“是”“伐”“矜”是“为”;“然”是顺向的,是无为、无意,而“见”“是”“伐”“矜”是逆向的,是有意、强为。“自然”是“天然”如此,“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是强“为”而如此。
过去讲“自然”,只强调其没有外在力量的一面,没有注意到还有排除内在力量的一面。蒋锡昌说:“古书关于‘自然’一词,约有二义:一为‘自成’,此为常语;一为‘自是’,此为特语……《老子》所谓‘自然’,皆指‘自成’而言。”*蒋锡昌:《老子校诂》,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14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67页。“自然”非是“自是”,亦非“自成”。老子明确反对“自是”,而“自见”“自伐”“自矜”亦是“自成”。刘笑敢说:“自然并不排斥外力,不排斥可以从容接受的外在影响,而只是排斥外在的强力或直接的干涉。这一点对于理解自然的概念和无为的意含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说来,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意思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完全不承认外力的存在和作用,而是排斥直接的强制性的外力作用。简单地说,自然强调生存个体或行动主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动因的内在性,与此同时,必然地要强调外在作用和影响的间接性。”*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211页。此说非是。“自然”的关键,正是要排除内外的动因,不只是外部的动因,还有内部的动因。
郭象讲“自生”非“我生”,“自”不同于“我”。又讲“自然”即是“自己而然”,“自己而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而然”是顺向的,是无意、无愿、无求的,是无内在力量的;“自己而是”是逆向的,是有意、有愿、有求的,是有内在力量的。老子讲“自然”不同于“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正是强调“自然”是无内在力量的。老子讲“无为”,也是强调“自然”这一无内在力量、无内在意愿的性质。老子提出“自然”,甚至可以说,其重点不是排除外在力量一面,恰恰是为了排除内在力量、内在意愿一面。
对于“自然”一语的使用,对于“自然”之义的把握,老子与庄子是一致的,但其思想倾向则有所不同。老子思想的主体是社会政治论,庄子思想的主体是人生论。老子讲道,是要为他的社会政治论寻求一个根基;庄子讲道,是要为他的人生论寻求一个根基。老子讲“自然”,是为了明道。在老子哲学中,“自然”是从属于“道”的,“无为”是从属于“自然”的。“道”是第一层次的,“自然”是第二层次的,“无为”是第三层次的。老子要人通过“无为”而达到“自然”,通过“自然”而接近道。由“无为”而自然,由“自然”而与道同在,而归道、而守道,这是老子的思想逻辑。*详见罗安宪:《论老子哲学中的“自然”》,《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第36—43页。庄子讲“自然”,也是为了明道。但庄子讲道、讲“自然”,都是为了将道、将“自然”与人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是要让人明白人的本然,明白本来的生活状态到底如何。
二、社会状态与精神状态的“自然”
人的最初的存在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都认为是一种“自然状态”。不过对于“自然状态”的描述,他们二人不甚相同。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4—95页。。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而平等的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
庄子也认为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种“自然状态”。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缮性》)
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个“自然”的状态。自然状态之为自然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人的自然状态,是人的精神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其精神状态是一个“淡漠”的状态。“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淡漠”是就人的精神状态而言的。“淡漠”二字在《庄子》书中还有多次出现,都是讲人的精神状态。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机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胠箧》)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
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
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刻意》)
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刻意》)
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刻意》)
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山木》)*本文引文的黑体部分,为作者所加。
“淡漠”的精神状态,是自然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是人原始、原初的精神状态,也是人最高的精神状态。淡漠是道德的体现,是“天地之道”,是“圣人之德”。“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道本来是自然的,人遵从“天地之道”,即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即是“圣人之德”。所以,在庄子看来: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至德之世”,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当然,这种最好的社会状态,不是存在于人类的未来,而是存在于人类的过去。统治者“不尚贤”,老百姓“不使能”;统治者“如标技”,老百姓“如野鹿”。这就是《老子》第十七章所说的“太上,下知有之”。老百姓只知有统治者,而统治者不是旗帜、灯塔、舵手,只是一个“标枝”、一个死树干,他不过问、不干预百姓的事务,所以民众如野鹿一般,自然而又自在地活动、生存。因此,“百姓皆谓我自然”。在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人们的行为都很端正,却不知道什么是“义”;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却不知道什么是“仁”;每个人对他人都很实在,却不知道什么是“忠”;每个人的行为都很正当,却不知道什么是“信”。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状态是一个“阴阳和静,鬼神不扰”的时代和状态。在这样的时代和状态,“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万事万物都不曾受到任何伤害,所有的生类都能得其天年。人虽有知,但却无所用之,这是一个所谓“至一”的时代和状态,是“自然”而无为的时代和状态。“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郭象解释说:“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551页。成玄英解释说:“莫之为而自为,无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当是时也,人怀无为之德,物含自然之道焉。”*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551页。物守其本然之道,是为自然;人守其无为之德,亦是自然。
“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知的最高境界不是“知”的最高使用,而是“知”的不使用。《老子》第七十一章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人们一般将“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解释为: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高明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是有问题的。这种解释未解其中真意。因为虽然“知道自己不知道”比“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要高明,但“知道自己不知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不留于知,不留意于知,以不知为知而不用知,才是真正高明的。吕惠卿曰:“道之为体,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虽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则其心庸讵而宁乎?故曰不知知,病。”*[宋]吕惠卿:《道德真经传》,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第2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687页。知“不知”之知,进而不用“知”,这才是“知”的最高境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
“知”的最高境界是“以为未始有物”,是目中无物、不用心、不用知;“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封”是界限、区分、差别。“未始有封”,是对物不作区分,不作辨别;“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未始有是非”,是不对事物作是非然否的区别与判断。
人类最初的状态是一“莫之为而常自然”的状态,是“人虽有知”,而“无所用之”的“至一”的状态,是人的精神“淡漠”的状态。“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及燧人氏、伏羲氏为天下,德始下衰,其标志是“顺而不一”。成玄英曰:“燧人始变生为熟,伏羲则服牛乘马……浇淳朴之心,散无为之道。德衰而始为天下,此之谓乎!是顺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551页。林希逸曰:“知有理之可顺,则其纯一者已离矣,故曰‘顺而不一’。”*[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4页。“不一”是有了区分、辨别、用知的心,而不再“至一”如如。“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神农、黄帝之时,德又下衰,其标志是“安而不顺”。成玄英曰:“神农有共工之伐,黄帝致蚩尤之战,祅气不息,兵革屡兴。是以诛暴去残,吊民问罪,苟且欲安于天下,未能大顺于群生者也。”*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552页。“安而不顺”,是为安邦治国而不顺应民众自然纯朴之心。“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唐尧、虞舜之时,德又下衰,兴治国化民之术,背离自然之性,以文博为饰。成玄英曰:“离虚通之道,舍淳和之德,然后去自然之性,从分别之心。”*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前揭书,第553页。自此,“民始惑乱”。
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庄子进而连“治”亦反对,反对治国化民。在庄子看来: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宥》)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在”是自在,“宥”是宽恕。之所以提倡“在”,是因为担心天下之人“淫其性”;之所以提倡“宥”,是因为担心天下之人“迁其德”。尧治天下,天下之人“欣欣焉”而“不恬”,即不淡漠;桀治天下,天下之人“瘁瘁焉”而“不愉”,即不欢娱。尧与桀,其所为相反,而其使人背离自然恬淡的本性,却是一样的。所以,当有人提出如何治天下的时候,庄子一般是反对的。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在庄子看来,“顺物自然”,以淡漠的情怀和心态对待一切,天下自然安宁。“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缮性》)治道的根本其实不是治,而是“养”,是养护,“以恬养知”,“以知养恬”。
“知”的使命与作为恰恰是不作为,是养护、维护原始的自然而恬淡的本性。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下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也,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在宥》)
黄帝为天子,向广成子请教“至道之精”,广成子认为黄帝不足以语至道。因为至道的根本是自然,而黄帝之所作所为,却有背于自然。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大宗师》)
“黥汝以仁义”,“劓汝以是非”。教人以“仁义”、“是非”,是要教人知善、为善,而仁义、是非之观念一旦形成,就像人的脸上刻了字,人的鼻子被割掉一样,再也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也不能回到原来自然、纯朴的状态。“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缮性》)企图通过学习与修为,以回复到原始的状态,那更是不可能的,求知、求学,只会使人离原始状态愈来愈远。吕惠卿曰:“缮性于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学以求复之,则滋远矣;滑欲于俗,其患常在趣舍,以杂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则滋昏矣。”*[宋]吕惠卿:《庄子义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0页。人本来是自然、是明,通过学习而求自然、而求明,只能是愈发不自然、愈发不明。
三、情感状态的“自然”
“自然”不仅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德充符》)
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的“自然”,表面看来即是“无情”。但此“无情”不是无一切情,而是无“物之情”。“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物之情”即是对于外在之物所具有的依恋、依赖之情。庄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是不受外在事物的干扰,而仍继续保持情感之自然。
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遁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是道德的本然状态,是人精神的本然状态,也是自然的状态。能保守这样本然而自然的状态,“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由此而“德全”,而“神不亏”;由此,“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破坏虚无恬淡的本然而自然的状态,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庄子还曾说: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
过度的情感、夸张的情感,是不自然的情感,同时也是有害的情感,是要屏除的情感。自然的情感一方面是不夸饰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情感,同是也是真实的情感。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伪而晚闻大道也!”(《渔父》)
真情感是内在心理的真实感受,也是其不加造作的自然感受。强与真,一是勉强,一是真实;一是造作,一是自然。林希逸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即‘至诚感神’之意也。强哭、强怒、强亲、真悲、真怒、真亲,此六名甚精切。真在内者,神动于外,言有诸中,必形诸外,神动者,精神感动于外也……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前揭书,第254页。真是真实无伪,是不待造作而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者,无伪、无为,故其天然、自然,“圣人法天贵真”,正因其“自然”。
四、余 论
《庄子》一书,“自然”一词共8见,就存在与状态而言共4见,已如前所述。其余4见,大体非实意用法,而是虚意用法,其意大体为“顺其然而已”“顺其自然而已”。
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天运》)
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天运》)
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秋水》)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田子方》)
“应之以自然”,“调之以自然之命”,其意均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尧、桀之自然而相非”,有因时而顺势的意思,“无为而才自然”,是不勉强的意思。这些都只是“自然”一词的实际使用,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庄子关于“自然”之论,是与他的人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庄子论“自然”,非是就自然而论自然,更非就自然事物而论自然,而是就人而论自然,是就人的存在而论自然。在庄子的哲学里,“自然”是一种状态,一种社会状态,一种人的存在状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情感状态。这种社会状态、人的精神状态、情感状态,不仅是一种原初状态,是不待造作的真实状态,也是一种真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