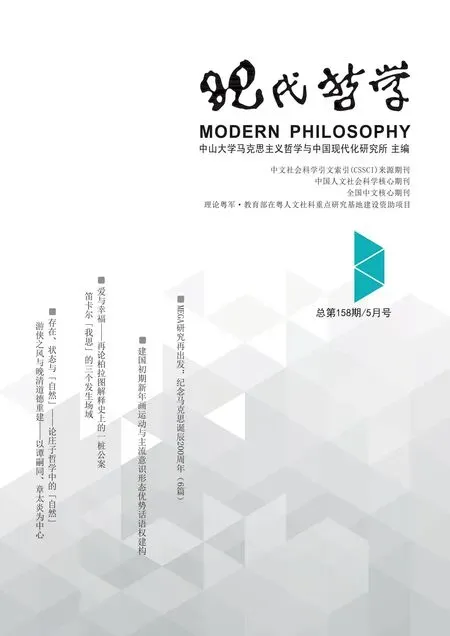历史与理论:毛泽东的《共产党宣言》阅读史透视
罗建华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最早被完整地译介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也是自“五四”时期伊始的毛泽东阅读史与思想发展轨迹中最不容小觑的影响因素。从毛泽东本人对此书的提及与评论,从其阅读的总次数与频率,以及接受此书中的科学方法论之后,从思维方式与实践范式的格式塔转变等多个维度加以综合判断,该书对毛泽东所构成的影响并不是给他增添几条结论和原则,而是彻底刷新了他的“三观”,使毛泽东的知识与思想结构从“混沌”状态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下变得清晰与简明,进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关键一环。因此,严肃而深入地考察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历史,剖析他从此书中所捕获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与科学方法论,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尤其是将其放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线索中加以考察时不可或缺的研究域。
一、回溯与考察:毛泽东阅读《共产党宣言》背景与历程
从清末民初伊始,《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便开始在国内各类报刊上出现,但在“五四”之前找不到毛泽东读过这些史料的证据,而从“五四”时期开始毛泽东从不同读物零散地读取了《共产党宣言》的不同内容。李大钊于1919年5月和11月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大量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断,并做出尝试性的诠释。*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自《新青年》创刊以来,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与鼓励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这一刊物的热心读者,而且深受其影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页。据此,大致可以判断这些重要的论断便是毛泽东最早接触的《共产党宣言》“碎片”。而且,自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开始,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毛泽东在上井冈山之前几乎从未间断过对各类报刊的阅读。因此,毛泽东也很有可能阅读过在此前成舍我、张闻天、李泽彰所摘译的内容。
尽管毛泽东于1936年7月回忆并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分享过初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重要经历,指出在第二次去北京之时阅读了陈望道的全译本*[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而且陈望道后来也曾回忆,说自己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于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版本至今未能找到。*贾林志、王相溪:《考察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前前后后》,《山东档案》2001年第3期。众所周知,时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去了上海。根据现有材料推断,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记忆存在些许误差,他在北京首次阅读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应当是由罗章龙等人组建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所油印的版本,而陈望道的译本很可能是后来在上海阅读的。当然,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陈望道译本的影响作用之大是毋庸置疑的。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重译的仅56页的《共产党宣言》,被以各种形式反复重印直至193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必读的文献。*[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在这一时段,由于已明确将自己界定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不再是一种尝试性的理解与选择性的阅读,而是将其视为解决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雪中之炭。因而,这种阅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吸纳活动,而是充分结合现实革命实践,使这一文本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超时空“对话”。
早在1939年底,毛泽东自己就说,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已经不下一百遍,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仍旧每年都读此书很多遍。1943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在未来的半年时间里亲自率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1本便是《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延安时期是中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塑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本人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力图使马列经典从党员干部扩散到广大人民群众,使这种理论真正起作用于群众,成为群众奋起反抗的精神动力源泉和进行自我改造的科学方法论武器。更为有趣的是,从1954年秋天起,毛泽东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学英语,而学英语比较好的办法无疑是找准兴奋点,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英文材料,因此他选择了马列经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相对而言,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英文版的生字比较多,对未曾留洋亦未曾接受过专门的英语阅读技能训练的毛泽东而言,显然有不少阅读障碍。但是,他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攻克了这一困难。在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作了大量详细的批注,而且每次重读都会补注一次。*龚育之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94页。可见,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有很深厚的情感,甚至能用如醉如痴来形容。而毛泽东对此书锲而不舍的阅读,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资源的青睐,呈现出他无比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及对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持之以恒地加以学习并运用的进取与拼搏精神。
在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这一著名论断,警示党员干部防止分裂主义入侵党内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此时,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已到最后的定性与处理阶段。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说: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还提到《共产党宣言》有诸多序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1964年8月3日,毛泽东批示其秘书林克:“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1页。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十分渴望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获取丰富营养。
二、透视与重释: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层理论解读
自从“五四”时期初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后,这一文本便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接纳,这种影响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止步于对这一经典文本的巨大作用的简单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毛泽东究竟从此书中读出哪些思想理论的问题严加探讨。纵观毛泽东的《共产党宣言》阅读历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生成、阶级分析方法的建构、独立自主的精神与自由的个性、改造世界的意识与思想,以及对理论体系建构的长期性的认识等,都与此经典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阶级斗争理论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雏形的建构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斗争的论述。此书开门见山地提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9页。。毛泽东说,读了它“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由此可以判断,一方面,1920年的毛泽东并未读过恩格斯于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因为在这个序言中恩格斯已经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判断;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虽不是单纯论述阶级斗争的文本,但毛泽东在最初读此著作时,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及其实现路径的阐述较为敏感。在1920前后所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毛泽东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前揭书,第22页。。重要的是,这种对理论的选择性吸收并不是出自一种感性判断与纯粹的个性化冲动,也不是只抓住文本的只言片语不放,而是深刻结合了当时的宏观历史境遇和政治背景。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言:“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们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随着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强行入侵,在全国各地大量掠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极大压缩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奋起一搏就成了中华民族重获生存空间的唯一路径。《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维度,恰好契合了当时中国革命一触即发的特定历史境遇,满足了中华民族对科学革命理论如久旱等雨一般的渴求。
对毛泽东而言,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一种短暂的启蒙,而是渗透到他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对他的理论与实践构成深层的持续性影响。毛泽东曾说:“我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极具号召力的响亮政治口号:“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这个新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都实质性地异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将旧世界迅速打破后才有可能建立的崭新国度。因此,直至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阶级斗争理论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未消退,甚至延续至毛泽东晚年。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对晚年毛泽东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全部是积极的。1966年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等人汇报工作时说道: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前揭书,第553页。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论断本身没有明显漏洞,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如何进行政治斗争以及如何把握阶级斗争的限度等问题。
(二)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后,才“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前揭书,第22页。。在隐藏于《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方法论中,长期占据毛泽东思想与认识结构主导位置的显然是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以极为严谨的方式阐释了这一方法:多重复杂交织的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到来后,被强行撕裂为两股绝对对立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各阶级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无产阶级巨大革命力量的充分肯定,极大地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对毛泽东而言,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是一种呈现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的方法,而且具有更为深广的认识论意蕴。在40年代初期,他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得出基本结论: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9页。。易言之,在毛泽东看来,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真实现实以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路径。
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国外学者大多根据在阶级斗争具体实现路径层面的区别而强调两者的差异性,而不注重剖析两者的内在理论逻辑连续性。譬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认为,根据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入解读能够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胜利是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美]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的论述与剖析中,并没有将农民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创造力量加以描述和阐明;而毛泽东却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对潜藏于农民阶级的创造性与革命力量给予极大肯定。这里,迈斯纳的潜台词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一种“扩张式解读”。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是欧洲的阶级状况以及演变历程,而毛泽东则是根据中国实际做出了相应的从具体结论意义上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客观分析。因此,仅对理论的具体论断加以对照,便武断地抛出结论的研究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前揭书,第17页。。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群众,不仅是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热心肠,也不再是像青年时期那种简单的“圣贤救世”思想的呈现,而是基于群众史观的深层滋养,强调潜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力量之巨大是无可比拟的,是少量知识精英所不能够取代的。经过对中国革命斗争现状的不断考察,毛泽东发现中国的农民由于常年备受封建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与剥削,拥有的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农民阶级从数量上看比工人阶级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积极发动农民阶级这一强大革命主体,而不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工人阶级。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农民具有两重性。1959年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党内理论家们一同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具体化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2页。从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具体论述的点评能够看出,毛泽东明显意识到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必须勇于超越具体结论。
(三)独立、自由与个性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对独立性、个性与自由加以肯定和宣扬。此著作本身就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其性质与理论目的内在地决定了它必须具备极强的革命号召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前揭书,第468页。。资本主义将封建等级制度与观念夷平的同时也将人的尊严与自由抹杀了,在超越封建主义弊病后又不可避免地在其内部产生巨大的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具体地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绝对对立,因而革命无可避免。只有通过革命方能摧毁阻碍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独立性、个性与自由的机制,也只有通过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够祛除自身所具有的诸多诟病,最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个性和自由。因此,“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前揭书,第491页。。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将获得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的资格,也就意味着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再受压制,人的个性亦将得以张扬。
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第十一部分讨论的是党性与个性问题,其中明确地指出,关于独立、自由与个性的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入阅读,毛泽东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前揭书,第482页。凭借对中国历史的掌握,并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加以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财产被地主阶级所强行占有,地主阶级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却削弱甚至取消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独立性、个性和自由的资格。因此,之所以要将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正是要带领他们一同追求本该属于他们的独立、个性与自由,或者说,通过革命将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垄断的独立、自由与个性归还人民群众。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含义完全不变的情况下沿用这些概念,而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毛泽东文集》第3卷,前揭书,第416页。。在他看来,能独立工作甚至有能力创造和发明世上本不存在的器物,又能本着集体主义精神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人,以及既不随声附和又与盲动主义保持距离的人,才真正拥有创造性的个性;而破坏性的个性主要指只为理论表述上的标新立异、抢人眼球而生造理论概念与框架的行为,以及视个人利益为主要实践目标而不顾及集体利益与长远发展的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当然,独立、个性与自由本身既是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福祉的手段,又是无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方能够实现的目标,那么对独立、个性与自由的获取就没有“完成时”,而是永远处于“进行时”。
(四)改造世界的双重维度
关于真正的哲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论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过。这一论断被誉为马克思的哲学宣言和“新哲学”的萌芽与诞生,也有学者称之为“第十一论纲”。当然,马克思在此文中并未对改变世界的具体路径详加讨论。但是,《共产党宣言》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为发动群众以改变世界而精心撰写的革命行动纲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理论掌握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必然性的论证是逐层推进的。首先,积极肯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必然性,同时指出资产阶级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改造力度。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提到,《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页。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西方国家的“新思想”的侵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强行将软弱无力的封建主义思想大厦大规模地敲碎,中国在产生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也使农民破产而成为“半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到来,给予世界一次巨大的改造,这一浩浩荡荡的潮流是无可抵挡的。可是,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初便埋下了祸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是无法在自身体制之内完成自我更新的,因此需要依靠外界力量对其进行“外科手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彻底改造了封建社会乃至全世界之后,自身又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终极旨趣是全人类的福祉,要解放全人类就必依靠工人阶级潜在革命力量的释放。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展开,而是将自己置于无产阶级一边,因为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就等于没有立场、没有明确的敌友,其理论也就不可能具有革命性。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前揭书,第377页。在毛泽东的理论语境中,“群众”一词有着特殊的政治意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囊括于其中,而是有所特指,诸如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被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其基本含义与马克思所言的“无产阶级”的概念虽有差异却较为接近。易言之,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发动备受压迫、多灾多难的人民群众,而这种思路与灵感恰恰是《共产党宣言》给予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该著作所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基本思路与理论灵感,而是大胆地对其加以推进和发展,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刘林元:《要重视实践主体主观世界的改造——论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哲学命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毛泽东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曾明确指出,改造世界应当“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联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至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改造世界的理论,就有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两个重要的维度。
(五)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
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必定建立在理论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基础上,而理论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需要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的长期过程。*《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283页。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之所以必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取决于两个维度:第一,客观事物的本质呈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展现的;第二,主体认识能力的相对有限性,决定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不断累加和拓展。具体到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最初是发轫于感性认识,是基于自发性的斗争实践所产生的粗浅认识,以及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进行的情绪化的破坏行动。《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但它却仍不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实际上,此著作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它为资本主义本质的研究破了题,并开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先河。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谈到:“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无论毛泽东是否在此前已认识到《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线索中仍处于非完整阶段,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此前并未对这一问题表过态,而此时他明确指出它的未完成性,加之1959年所谓的“蹩脚一点”的评论,足见毛泽东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与过程性。这种对经典著作的点评,从侧面彰显了毛泽东的去权威情结与倾向。如若认识不到经典著作的未完成性,对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不够重视,极容易浇灌出教条主义。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不断突破已经有具体结论与论断,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丰富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关键在于,毛泽东此时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并非纯粹出于理论问题的探索,而是与其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正因为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过程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历史性,所以对阶级分析方法以及阶级斗争的具体实现路径的探索亦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完结,而是需要继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究。由此,“不断革命”理论以及让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锻炼和自我提升的思想便可获得一种理论支撑。当然,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不仅仅源自这一特定的理论源泉,也源自他对官僚机制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现象和两极分化问题的一种抗拒,源自对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率”的担忧和对跳出“怪圈”的激进实践尝试。它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导致的实践失误与教训无疑都已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资源。
三、再思与评价:毛泽东研读《共产党宣言》旅程的当代启示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永远无法完结的重大课题,由此延伸出来的课题便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史,无疑能给我们提供深刻的启迪。
(一)研读经典文献: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重要路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不是将具体论断烂熟于心而是要掌握其中的科学方法论,这并不是后来的继承者们在长期的理论文本阅读与学习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体系创建者那里就已明确了的。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6页。马克思的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具体结论与原则,而是构筑了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的崭新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和探讨使用的科学方法。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具体论断,必须不断将其放入生动具体的实践加以重新理解,在与实践的科学结合中赋予原有理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与制约,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本身就需要一种去教条和反教条的思路。
列宁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3页。这一论断不仅是对恩格斯的提示性的话语的延续,更是基于对自身所积极倡导并参与的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与提炼。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生成,最重要的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与认识,但亦不可否认其基于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与批评而建构全新理论体系的维度。对于列宁而言,对前人的理论文本的批判即使能使自己的理论逻辑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也不足以促成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洞见。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实践而言,生硬、干瘪的理论结论是没有力量的,现实实践需要的是能够正确引导实践主体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极力强调对方法论的掌握与运用不是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忽视乃至舍弃基础之上,相反,必须将大量阅读经典文献视为掌握科学方法论的根本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言:“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只有深入研读经典文献,才能准确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二)结合现实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必经通道
纯粹的理论文本解读工作是相对容易的,这需要的主要是在基本的理论逻辑指引下所构筑的理解能力与想象能力,而对现实实践的关照则是复杂多变的,时常是布满荆棘的。毛泽东并不懂德语、俄语或日语,他阅读马列经典著作主要是中译本以及少量的英文版。可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党内那些懂得德语、俄语或日语的理论家们,甚至很快就超越了他们。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能顺利地越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文本和苏联教科书的理论话语表层结构,敏锐而深刻地洞见隐藏于其中的本真革命精神、哲学思想精髓与科学方法论。毛泽东为何会具备如此超乎常人的本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将经典文本置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加以把握,又运用经典文本中的思想与方法对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加以分析,使理论文本与现实实践形成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生成无与伦比的革命斗争智慧。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21、422页。他甚至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强调:离开实际调查的结果只能是产生机会主义或者盲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前揭书,第112页。毛泽东拒斥隔岸观火式的理论思辨,而力图扮演一个革命与建设理论的践行者角色。
之所以必须结合现实实践才能够正确理解和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归根结底,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实践性。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进行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的建构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刻透视基础上,揭露长期被“公平交易”外衣所掩盖和遮蔽的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真正秘密,解开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的谜题。其次,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的一切理论皆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终极目标,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积极掌握人民群众这一历史的真正创造主体。
(三)超越具体论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超越经典文献中的具体论断、理论话语和表层叙事逻辑,深究暗藏于其中的科学方法论要素,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内在规定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4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建之初,其创建者便已明确强调其理论提供的不是需要加以顶礼膜拜和严格遵从的“圣旨”,不是用于束缚复杂易变的实践的教条,对理论文本的解读也不应是非反思的死记硬背,而应当带着批判的眼光历史地加以审视和剖析。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进程中,迷恋具体结论以至于出现对理论创建者犹如偶像崇拜一般的情绪化赞扬和吹捧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可以说,对具体论断的教条主义式的迷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亚于其他领域,这无疑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必须深究的课题。
问题显然不在于经典文本本身,而是出在阅读主体对文本的阅读方式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的,教条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而是来自对经典著作的误读与误判。*《毛泽东文集》第3卷,前揭书,第418页。对经典文献的研读不能是对词句换一种表述方式进行简单解释,而是需要深入到其内在理论逻辑线索,超越具体结论与论断的束缚与规约。卢卡奇也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9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连续性的保障机制不是产生于对具体结论的顽固坚守,而是在于掌握其中的科学方法。易言之,对具体论断的大胆超越不仅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精准运用的根本前提,是从根本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