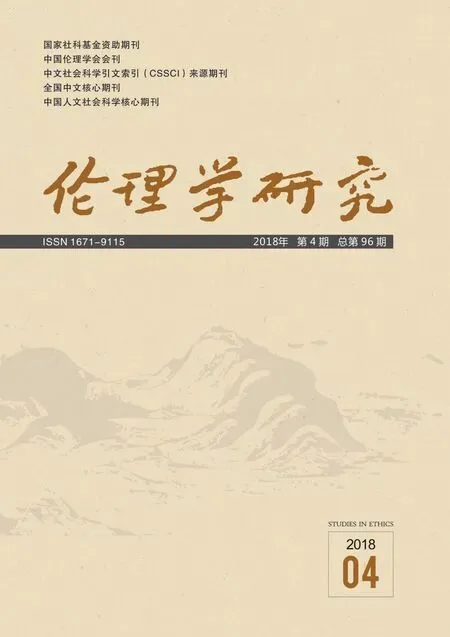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特色与实践效应
韩玉胜
乡约是一种由地方德高望重的儒家士绅发起、民众自发参与、以道德教化制裁社会行为的民间教化组织。中国历史上最早真正意义上的乡约肇始于北宋吕大均兄弟在陕西蓝田推行的《吕氏乡约》,后经理学大师朱熹考证、增损和编辑而声名远播、广为效法。明代大儒王阳明基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深刻认知并结合当时南赣地区的社会舆情,创造性地制定出颇具心学色彩的著名的《南赣乡约》并取得显著效果。阳明此举引发弟子争相效仿,尤其嘉靖以后力倡乡约者大多出自阳明门下,阳明后学不约而同地将阳明心学尤其良知之教的学术精义融入乡约,掀起一场以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导的乡约道德教化运动。研究阳明后学乡约教化是我们认识良知学说在晚明民间社会展开的一个重要向度,它在基层社会所触发的实践效应亦值得关注。
一、“阳明后学”的乡约活动及教化诉求
从地域范围观之,阳明后学乡约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集中在江右、泰州和岭南地区,尤以明代嘉靖年间吉安府各县乡约活动为盛。江右地区是发起和践行乡约最活跃、最成功的区域,这主要得益于“江右王门”弟子大多掌握地方行政实权或在当地颇具威望,使得他们实行乡约更具天然的政策优势和民众基础。“江右王门”乡约活动以《安福乡约》、《永丰乡约》最具代表性。
《安福乡约》由阳明弟子程文德(明浙江永康独松人,字舜敷,号松溪)、邹守益在吉安府安福县推行。嘉靖十五年(1536),浙中王门学者程文德来任安福知县,他借鉴《南赣乡约》以及临县永丰、永新两地的乡约内容和基本经验,与乡里诸贤商讨制定《安福乡约》。邹守益记载了程文德与当地贤能人士齐聚泮水议论举乡约等政事的场景,他们当时热情十分高涨,以至“眷然不能别”[1](P68)。虽然程文德在安福仅任职八月,但《安福乡约》效果显著且影响深远,程文德以后安福县令继任者大多效法此举。阳明弟子安福人王时槐赞誉道:“吾邑当嘉靖间永康松溪程公来为令,特行乡约,民俗丕变,迄今五十年,民追诵之不衰。”[2](P241)毛介川、吴尹节将安福的乡约经验用于以“难治”闻名的新昌,举《新昌乡约》取得显著效果,“期年而俗奋然以变,耻于讼,争以礼义相高”[1](P203)。邹守益是《安福乡约》核心参与者和民间推进的骨干力量,曾专门为《安福乡约》之推行作《乡约后语》、《立里社乡厉及乡约》等文以示支持和宣传。即使后来因故离开安福转任他处,邹守益也不忘极力为之宣传和传承《安福乡约》的实践经验。他曾任职广德州判,离任时将《安福乡约》赠与接任广德知州的夏臣(字弘斋),后者在此基础上推行《广德乡约》,邹守益为之作《广德乡约题词》。邹守益对各地乡约活动也颇为关注:他陆续为《永新乡约》、《永丰乡约》、《新昌乡约》等撰写序言;阳明弟子孙景时任长洲县县谕之际建乡贤祠,邹守益为之作《长洲县儒学乡贤祠记》;以诗句形式盛赞乡约,如《观龙生起文家举乡约》[1](P1295)、《连山书屋温乡约简诸生》[1](P1298)等。邹守益对《南赣乡约》更是大加赞赏,认为王阳明将《蓝田乡约》那般“世族大邑之法”施用于南赣的“山谷之民”、“村童野叟”,将蓝田吕氏兄弟的“贵族经验”成功转变为应对“村童野叟”的地方实践,足见先师仁爱之心[1](P794)。
王阳明弟子季本(明浙江会稽人,字明德,号彭山)是推行乡约尤为活跃的一员,他曾在揭阳、永丰两地任职期间大力推行乡约。正德年间,季本与薛侃在潮州揭阳制定《榕城乡约》①加以推行。薛侃(1486—1545),字尚谦,号钝子、常思子,又号中离,明代潮州府揭阳人,岭南王学代表人物。正德十四年(1519),薛侃与王阳明告别从赣州返回家乡潮州,他不仅将以良知学说为核心的阳明心学带到岭南地区,亦在《南赣乡约》基础上积极运用阳明学说作为思想指导在家乡开展乡约。起初,薛侃提出的乡约内容有十条(约为十事),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数年以来,官无一卒入乡,乡无一词在官,租粮早完,鼠窃屏息,置物弗守,遗失可追,居者日裕,逃者日归,民甚便之”[3](P392)。嘉靖丙戌(1526),本为御史的阳明弟子季本(字彭山)因“言事”被贬为揭阳主薄,将薛侃的乡约扩展为三十四条在当地普遍实行,起初支持者和反对者参半,实行一年之久明显改观,“盗息讼简,奸无所容,时临各约巡视,善士扬眉,恶人涤虑,社学师生日夜习诗演礼,盖庶乎弦歌之意,识者以为三代可以立回”[3](P392)。可见,季本和薛侃在揭阳地区推行乡约取得相当不错的实效。
嘉靖十三年(1534)季本调任吉安府,阳明弟子聂豹积极恳请永丰知县彭善、吉安知府屠竹墟借鉴季本在揭阳地区的乡约经验施诸永丰。嘉靖十五年(1536),阳明弟子季本和聂豹在永丰县推行《永丰乡约》。《永丰乡约》在揭阳乡约基础上进行了条目扩充,内容更加细致。聂豹推行乡约的热情十分高涨,他为《永丰乡约》作了后序,详细记述了永丰乡约的由来历史,突出强调了乡约的教化本质,明确推行乡约是乡大夫明德、亲民的职责所在。他还为临县《永新乡约》作序,赞扬陆粲以乡约改变了“治乱无常”的乡村不良风气[4](P51-52)。邹守益对聂豹承先师之教以行乡约的举措颇为赞赏。他说:“双江聂子悦先师之教,力量气魄一日而千里。故按闽守苏,历平阳,慨然以身狥主而庇民。其劳于邑,则举丈田,立乡约,兹复眷焉。”[1](P136)后人亦对聂豹举乡约评价颇高:“居乡深念细民利病,若恫在躬,如均赋役、立乡约、广城垣、赈饿恤患之类,事不殚述。”[4](P625)
当时吉安府其余各县的乡约活动阳明弟子也多有参与。《永新乡约》由永新知县陆粲(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人,字子余,一字浚明)主持,陆粲并非阳明门下弟子,但他实行乡约得到王门学者甘公亮(字钦采)的支持,“佐之行乡约以化俗”[5](P432)。陆粲曾就乡约求教于邹守益和聂豹并深得二人赞许。聂豹说:“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予谓陆子于是举也亦然。”[4](P50)邹守益说陆粲推行乡约“毅然以靖共自厉”[1](P55)。阳明弟子罗洪先曾参与吉水县乡约的刊刻与推行。吉水县毗邻南安、赣州,与闽、粤、赣三省交界,常有流寇流窜于此,正德初年吉水乡宦曾昂、知县周广纳乡约于保甲,对当地治安卓有成效。嘉靖二十四年(1545)、三十九年(1560),吉水县再度盗贼横行,于是曾、周当年的乡约再度被拿出重新刊刻推行,罗洪先为之作序。
不同于“江右王门”大多以居官为政的身份推行乡约,泰州学派大多以平民或退休官员的身份参与乡治、推行乡约,主要代表是罗汝芳。罗汝芳的乡约活动和思想主要收录于其门人编刻的《近溪罗先生乡约全书》,主要包括三个乡约文献:嘉靖四十二年(1563)罗汝芳任职宁国知府之际,他“爰循古人乡约之规,用敷今日保甲之意”[6](P750),其论集《宁国府乡约训语》对“圣谕六言”进行详细诠释;万历二年(1574)罗汝芳刚就职云南腾越州,当地乡士就延请他宣讲乡约和圣谕,前来听众如云,以至商旅不行、经旬罢市,他在演武场和明伦堂等地的讲会内容整理而成《腾越州乡约训语》;《里仁乡约训语》则是罗汝芳居乡期间在临田寺的讲论集汇。
历史文献中也不乏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记载。比如,王门弟子杨储(字符秀)“居乡务善俗,乃立乡约”,去世当年仍以七十七岁高龄“率行乡约,冠服竟日无惰”,并嘱咐儿子“犹率行乡约”[7](P757);罗洪先门生胡直在治楚期间,与乡人胡汝贤订立《求仁乡约》[7](P519),以此平息了当地强盗势力,并将自己在四川、湖北期间的乡约经验呈交当地政府推行,据《西昌县志》记载,胡直“卒乡贤祠”[7](P1207);万历二十一年(1593),阳明再传弟子刘元卿“奉邑大夫命,举乡约于复礼书院”,刘元卿担任乡正宣读彰善事迹并书之于册[8](P48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的来说,制定、推行和参与乡约是贯穿阳明后学民间教化活动的一条主线。共同的学术传承和移风易俗的社会追求使得阳明弟子在乡约事业上共同参与、相互支持、相互借鉴,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在明代基层社会掀起一场以乡约为载体的颇具心学色彩的乡村教化运动。
二、以阳明心学为思想特色的乡村道德教化
较之历史上其他乡约,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最大特色是它带有鲜明的阳明心学色彩,即阳明后学的乡约活动是一场以阳明心学尤其良知之教为理论支撑的乡村道德教化运动,或者说是阳明心学理论在乡约活动上的具体运用。
第一,将举乡约视为一项拯救乡村社会世道人心的“治心”举措。乡约的产生缘于“以成吾里仁之美”[9](P567)的教化诉求,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则凸显了心学思想在乡约教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热衷心学的阳明弟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以心学思想推行乡约的思路。在阳明弟子看来,乡村社会治乱之根源在于能否兴教化以“引人向善”而非徒恃政策法令以“驱民为善”,乡约就是那种适应乡村社会的“根治人心”的道德教化手段。聂豹在为《永新乡约》所作序言中说:“慨德礼之教渐微,法令之持难久,思有以为之所也。彼徒事夫法令以持民者,非不可以矫目前之治,然法以我在而行,亦或有时而沮,沮则民散而复作乱矣”[4](P50);在《永新乡约》序言中又说:“自夫王者之跡熄,而乡井之教浸微,后世愿治之君,不知出此,徒欲以法把持,谓足以禁暴寝奸,驱民为善,而祗以乱之矣。譬之委禽于笼,纳兽于槛,而求其咸若遂生,有是礼乎?”[4](P51)“德礼”与“刑罚”乃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思路:前者致力于“治心”,通过道德感化以及榜样力量来“引人向善”,让犯过之人从内心深处彻底悔过;后者则致力于“治身”,依靠严刑峻法来“驱民为善”,让犯过者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为恶。虽然法令是维持乡村秩序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但它并非始终可以奏效,一旦失效必然祸乱纷争,且这种“刚性”的依靠外力束缚的统治方式过于束缚而缺乏“自由”,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因此,虽然阳明后学推行乡约大多具有官方背景或接受官方指导,但他们并未借助手中权力迫使乡民为善,而是一再强调乡约的本质应该是“治心”而非“治身”,“治心”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政策法令则难以产生这种持久的效力。正如王时槐所言:“夫所贵于善治者,非徒以法制惩于违犯之后,而听断晰于微暧之情也,必也勤善使耻于蹈邪,崇让使耻于攘讼,明分使耻于逞乱。其可乎?是故莫善于乡约之行矣。”[2](P240)质言之,阳明弟子认为乡约本质上是一种诉诸内心的道德教化,而非依靠外在约束而产生效力的单纯规约。但他们也注意到这种诉诸内心的教化方式绝非易事,邹守益在评论《南赣乡约》时说:“身之死则知重之,心之死则不知重,其亦弗思焉耳矣!”[1](P974)身体有恙足以引起重视,内心堕落往往难被察觉而让人浑然不知。显然,这些认知带有深刻的阳明心学烙印。
第二,要求约众以戒慎恐惧、省察克制之心时刻警惕自身的细微恶念。阳明心学将传统哲学中的“慎独”精神推演到极致,发展出一套专门应对自我“恶念”的严格细致、果断彻底的修养功夫。王阳明特别强调要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域”用力,将那些“恶念”消灭在萌芽之际。他说:“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10](P17)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平乱期间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教化难题,他以心学思想为指导并结合当时南赣地区的社会形势创造性地提出《南赣乡约》,不仅成功破解贼患之乱,当地社会风气亦焕然一新。阳明弟子薛侃与季本在潮州推行乡约时特别重视微恶、细善。他们在《乡约》中“申戒”这部分说:“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极而不可赦。今有善而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自幸,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3](P375)阳明弟子邹守益为《永丰乡约》所作序言中说:“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微渺而忽之,则善根不植;既萌而后决之,则恶蔓不可胜禁。夫其恶蔓不可胜禁也,而欲以诛戮速一切之效,是谓不教不戒,不免于罔民,岂曰痿痹,将剥发肤而溃心腹矣!”[1](P58)也就是说,阳明弟子将心学那种“治恶”学问充分运用到乡约理念设计之中,他们意图通过乡约提醒民众,恶的养成往往根源于难以觉察的细微之事,要提防日常不觉之小恶,善于积累日常难察之善行,从而日益精进、远离为恶。
第三,特别重视“良知”在践约实效中的关键作用和特殊意义。阳明弟子普遍认为“良心”或“良知”是决定乡约最终落实的关键因素,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乡村社会能否真正形成扬善抑恶的社会舆论,从而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罗汝芳居乡期间曾在里仁会社讲解乡约,当时正值夏日酷暑,然人们专心听讲毫无一丝扰动,罗汝芳认为这就是人的内在良知在起作用。他说:“盖是吾人之生,不止是血肉之躯,其视听言动,个个灵灵明明,有一个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往常乱走乱为,只是听凭血肉,如睡梦一般,昏昏懵懵,不自知觉。”[6](P764)如果唤起良知良能,则一时通感,“如沉睡忽醒,则中心耿耿,便于血肉形躯顿尔作得主起。”[1](P764)罗汝芳进一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规约都是良心的自然显现,他在为乡民讲解乡约条目时就指出,向善并非难事,人天生具有亲睦友好的情感基础,只要在生活中逐件去做即可。他说:“夫乡里之人,朝夕相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内如妇女妯娌相唤,幼如童稚侪等相嬉,年时节序,酒食相征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强而然。”[1](P745)再如,薛侃《乡约》规条最后专门设有“良知”一节,曰:“良知者,人心自然明觉处也。见父知孝,见子知慈,此良知也。遇寒知衣,遇渴知饮,遇路知险夷,此良知也。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当恭敬自恭敬,当是非自是非,此良知也。人惟是欺此良知,则争讼诈罔,无所不至。若依而充之,知是则行,知非则止,有则曰有,无则曰无,人人自太古,处处自羲皇矣。竟有何事?”[3](P391)可见,“良知”是薛侃对施行乡约的最后心得,如若人人都能发明良知,自然全善无恶,移风易俗也自然不是问题。然而,良知和良心人人均有,阳明弟子肯定了约众在求善问题上“吾性自足”、“机会平等”的道德主体性,这一点与阳明致良知学说精神根本一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核心要领就是强调行为者那种求之在“我”、得之在“我”、行之在“我”的主体精神,当然这并非一种试图将“自我”凌驾任何事物之上的“精神妄想”,而是凸显主体自我在任何行动实践中所应具有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而良知良能又人人兼有,王阳明为原始儒家那种“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成圣可能找到了最切实的本原依据,演绎出“个个人心中有仲尼”、“人皆可以为圣”的道德进路。总之,阳明弟子将阳明心学尤其良知学说作为开展乡约的指导思想,开辟了一条最终诉诸约众良心和良知的面向庶民的成德之路。
三、阳明后学“乡约教化”的实践效应
教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阳明后学这种颇具心学特色的乡约教化在民间社会触发了一系列实践效应:
第一,展现出一种以乡约为载体推行道德教化来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理想信念。保甲制度是宋代以来官方控制乡村的主要手段,这种参照军事管理模式的户籍管理制度引起地方自治力量和乡民的强烈不满,严酷保甲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秩序不容乐观,加之连年征战导致乡村社会凋敝、百废待兴。在这种背景下,乡约以移风易俗为归旨、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自由出入为原则等更加贴近民情的组织方式自然颇受欢迎,儒家士绅倡导乡约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试图通过自我组织和道德教化的形式来重建乡里秩序的实践倾向,以“知行合一”为圭臬的阳明心学融入乡约就更加凸显了乡约的这种实践特质。纵观阳明后学的乡约文献,他们在乡约序言或后语中一再凸显乡村教化在整个社会教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甚至认为如果“乡村不教”何谈“天下教化”。邹守益将乡村教化视为天下教化的“起点”,他说:“乡村者,天下之积也。使一乡一村皆趋善而避恶,则天下皆善人矣”[1](P791),“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1](P55),“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乡始。”[1](P57)邹守益曾为此作过一个形象比喻:乡鄙聚合而成邦国,邦国聚合而成天下,犹如指之于胫、胫之于股、股之于腰那般精气相贯、命脉相系。那么,究竟要将乡村社会建设成何种秩序呢?阳明弟子普遍将乡里社会复兴的目标指向儒家所推崇的那种三代时期的理想社会,他们习惯用“隆古”、“犹三代之人”、“三代之隆”、“三代之遗”等词汇描述乡约实行的理想效果。比如,邹守益评价《永新乡约》说:“岂独古道之不复哉?”[1](P55),评价《永丰乡约》说:“恻然独有古之遗焉”[1](P58),评价《南赣乡约》说:“三代之风可庶几乎?”[1](P794)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隆古比闾州党之仁,相保相爱,相救相赒,若心腹臂指,脉络融液,强无凌弱,众无暴寡,智无欺愚,合爱同敬,迁善改过,而莫知为之者”[1](P203)的理想社会。可见,阳明后学赋予乡约以浓厚的历史使命感,他们将推行乡约作为一项振兴乡村社会的崇高事业而积极践行。
第二,积极援引民间宗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融入乡约教化极大增强了其民间权威性。民间宗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是共同地域内的基层民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宗教信仰,虽然民间宗教缺乏正式宗教那种严密的信仰体系和宗教经典而显得相对自发、零散、难以解释,但它根植于民众生活习性而深深俘获无数信众。阳明弟子将这种具有广泛信众基础的民间宗教尤其它们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纳入乡约,将里社、读誓、乡厉等带有宗教色彩的教化方式植入乡约规条是阳明后学推行乡约的一大特色。比如,在嘉靖年间,邹守益就曾作《立里社乡厉及乡约》一文以助推《安福乡约》,文中记载了乡约与里社、乡厉等综而行之的境况,“立里社一坛,以祀五土五谷之神;立乡厉一坛,以祀无祀之鬼;立会饮读誓之法,以抑强扶弱,习于敦睦。是以和气孚洽,神降之福。而民德归厚。法久以废,阙然不讲,民庶无所劝惩,鬼神失其凭籍,饥馑相仍,风俗日偷。”[1](P790)里社乃祭祀土地神的处所,乡厉则指乡里中无亲族等祭祀的鬼,会饮读誓就是聚会期间全体成员对着神灵饮酒发誓,这些都是当时民间所信奉的神灵力量。聂豹对《永丰乡约》的评价说:“今观礼制诸书,教民一榜,期间所载里甲之制,和睦之喻,社厉之文,宴誓之章,亦皆神道设教。”[4](P51)薛侃、季本的《榕城乡约》试图借助一些宗教手段达到纠过戒恶的功效,在会约前一日设置“香案告谕牌”,会约当日除了选读圣谕、县谕,更要设置祭坛、祭拜神明,并以发誓的口吻齐曰:“若有二三齐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3](P381)可见,阳明后学十分善于利用那些当时乡里社会惯用和带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宗教教化手段,这无疑在向约众宣示:“凡是加入‘乡约’之人都必须作出庄重的许诺:对自己的善恶行为不能有丝毫隐瞒,而且还必须对神明发誓。这个说法已经含有善恶报应必由神明主之的含义。”[11](P69)
第三,自觉演绎“圣谕六言”使得圣谕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圣谕六言又称圣谕六条、教民六条、圣训六条,是朱元璋提出颁布天下用于教化民众的官方文件,内容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演绎“圣谕六言”是明代社会教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也构成了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实践基调。宋代以降,乡约多以《蓝田乡约》为范本,王阳明《南赣乡约》成为乡约与圣谕结合之成功典范,嘉靖以后阳明弟子承继这一思路基本围绕诠释“圣谕六言”开展乡约。其一,极力凸显“圣谕”指导地位。比如,邹守益在《永新乡约》开篇就讲:“我高皇帝之锡福庶民也”[1](P55),在《永丰乡约》序言中说:“高皇帝裁成辅相之仁”[1](P58)。再如,薛侃、季本在潮州推行《乡约》,开篇就是“圣谕”和“县谕”,乡约集体活动开始前首先宣读《圣谕》《县谕》,并伴有相应的叩拜仪式,这些相当于最高统治者以及地方政府对乡约的要求,意味着在官方思想指导下开展乡约,或者说严格遵照官方文件精神实行乡约。其二,以“圣谕为纲”进行“条目分疏”。比如,《永新乡约》就是“演圣谕而疏之”,“孝顺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训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为之目十有四”[1](P55);再如,在《安福乡约》基础上订立的《广德乡约》则“首以皇祖圣训,而疏为二十四目。”[1](P825)其三,说理与情感相结合的圣谕诠释。罗汝芳是这种圣谕诠释方式的典型,他对《圣谕》尤为推崇,甚至将“圣谕六言”视为传承“尧舜之道”的教化经典,他在担任宁国府知府期间曾结合王阳明心学思想大力宣讲《圣谕》,其宣讲娓娓道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听众云集,极大推动了圣谕六言在基层社会的落实。总之,通过诠释圣谕乡约活动能够获得更多官方支持而推行更加便利,从而为圣谕走向民间、步入百姓日常生活开辟了一条现实道路。
第四,试图关注和解决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具体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强烈现实关怀。阳明后学的乡约活动并非仅限于自我规约的道德教化,亦试图真正解决事关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他们以乡约为依托制定一些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具体实用的生产自救、生活自助措施,“将理想主义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12](P99)是阳明后学乡约活动的显著特点。邹守益就曾以乡约为依托在安福县开展过筹集灾粮来应对灾害年头的措施。1545到1549年安福县淫雨成灾,稻粮无收,灾害连年,邹守益作《书乡约议谷簿》一文倡议“举义谷”。所谓“义谷”就是义捐赈灾的谷米,即让富裕之家出资谷米来接济灾民,春天散给灾民,等到秋收季节收回,这种“义谷”不会收取利息。然而,“义谷”赈灾过程中依然不乏“私以市恩”、“虚以贸利”、“惰以驰事”等恶劣行为,在乡约会约之日按照情节轻重对这些行为进行处罚,对那些尽职尽责之人则“庆以酒,登于善籍”[1](P818)。从乡约具体条目来看,阳明弟子所倡乡约并不过分注重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它的规条设计更多专注于非常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诸如日常孝道、婚丧嫁娶、待人接物、化解纠纷、解除烦恼等生活事件。可见,乡约不仅是民众自我规约、相互监督的道德教化组织,亦成为基层民众互帮互助、患难与共的生产和生活组织,这也是乡约广受民众欢迎的原因所在。
总之,阳明后学将阳明思想那种专注行为主体内心的严格细致的修养功夫作为推行乡约的精神要义,在民间社会开辟了一条面向一般民众、可具操作的成德路径,推动了阳明学说尤其良知之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落实与认可。这种以心学为精神内核的乡约道德教化又与当时乡村社会秩序重建、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圣谕、根深蒂固且信众广泛的民间宗教、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借鉴不断推动着晚明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注 释]
①此次举乡约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确切名称,《薛侃集》也仅以《乡约》命名。邹守益在《乡约后语》中说:“彭山季子以乡约治榕城”(《邹守益集》,第802页);张艺曦在《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一书中亦称之为《榕城乡约》(张艺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本文拟借用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