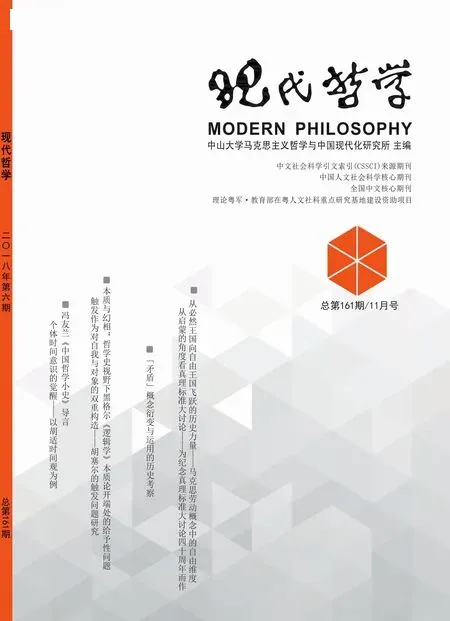宋初的道统论研究
——兼论宋初之尊孟
赵瑞军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宋代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及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宋代,作为唐宋尊孟思潮的重要内容、孟子升格运动的主线之一、并且是与唐宋古文运动密切关联的儒家道统论得以成立。然而,宋初作为唐宋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延承阶段,学界的关注却不够。一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及期刊论文中涉及到,并没有深入、系统性的成果。二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文献资料较多的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对道统的论述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三先生等虽生于宋初,其学术成就主要产生于真宗与仁宗的北宋中前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宋初学者。三是大多数学者仅关注宋代中后期孟子授号、封爵、升经等官方尊孟情况,对宋初由道统论而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并没有充份关注。针对上述情况,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这一阶段儒家道统论,及由其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展开专门研究。
一、宋初学者对道统谱系之论述
清代赵翼说:“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注][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页。钱穆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l页。中唐时期,韩愈为振兴儒学,排斥佛道,解决当时社会弊端,提出了道统论。其《原道》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注][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原道》,北京:中国书店,1935年,第174页。这列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而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真正居于中心位值的是孟子,其余的列祖列宗不过是配享从祀而已”[注][日]市川勘:《韩愈研究新论——思想与文章创作》,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7页。。宋初的一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谱系,虽略有差异,但核心观点大致相同。
柳开为宋初古文学者先驱,有宋初“古文自柳开始”[注]邵博《邵氏闻见录》卷1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古文自柳开始”条、洪迈《容斋续笔·卷九》“国初古文”条,及《太宗皇帝实录》、《五朝名臣言行录》、《郡斋读书志》、《后村先生大全集》皆有论及。之称。其《答臧丙第一书》曰:“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扬雄氏没……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臧丙第一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2页。又《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应责》,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62页。柳开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他甚至有意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如在自述生平时道:“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途,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补亡先生传》,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89页。又《答减丙第三书》曰:“夫圣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则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夫圣人之道,学而知之者,不得谓之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谓之为果也。学而知之者,皆从于师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备耳。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减丙第三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6页。他俨然以得圣人之道自居,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
王禹偁与柳开同时,也是宋初阐述道统论的学者。其《投宋拾遗书》曰:“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投宋拾遗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75页。《再答黄宗旦书》曰:“夫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黄宗旦书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3页。又《送谭尧叟序》曰:“(谭氏)读尧、禹、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送谭尧叟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90页。王禹偁也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
除柳开与王禹偁外,其他古文学者如孙何、赵湘、田锡、贾同等,对道统谱系也多有论述。“一代之名儒”[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宋孙何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86页。孙何的《论诗赋取士》曰:“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注][宋]沈作哲纂:《寓简附录》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页。其复门人的信说:“足下师孔宗孟,交荀友扬。”[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孙何·答朱严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75页。赵湘《文本》曰:“若伏羲之卦,尧、舜之典,大禹之谟,汤之誓命,文武之诰,公旦、公奭之诗,孔子之礼乐……《周礼》之后,孟轲、扬雄颇为本者。”[注][宋]赵湘撰:《南阳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田锡《贻陈季和书》曰:“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注][宋]田锡著、罗国威校点:《咸平集·贻陈季和书》,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2页。虽然孙、赵、田等人对道统谱系的论述与其他人略有差异,但都承认“孔子传之孟轲”这一核心观点。此外,贾同《责荀》曰:“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轲之述也。其言道,则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见其无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贾同·责荀》,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465页。扬孟抑荀,认为孟子得圣人之道,是孔子之后一人,贾同可谓北宋中期后“孔孟道统”确立的先声。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
种放为宋初介于儒、道间的“经生隐士”[注]种放:“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修以养母……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种放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896—9901页。)。其《辩学》曰:“道德淳正,莫过乎周孔,学者不当叛周孔以从杨、墨。自古圣人立教化之大者,则曰孔子;传其道,则曰颜渊潜心乎仲尼矣。后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轲,称‘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焉。’广轲之道,则扬雄,亦云:‘由尧舜文王为正道,杨墨塞路,孟轲辞而辟诸,廓如也。’嗣雄之旨,则曰王通,通曰:‘大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夫子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如通之学者,则曰韩愈,愈尊夫子道,以为迨禹弗及。”[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辩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61—562页。又《述孟志》曰:“盖孔子之道,非轲则不明。”“其道亚孔子而与尧、舜并。”[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述孟志二篇》,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59页。种放列出了“孔子、颜、孟、扬、王、韩”的道统谱系。“种放在终南,太宗召而不出,从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注][明]张燧著、贺天新校点:《千百年眼》,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其“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注][宋]僧文莹著:《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为时之高人。
智圆为天台宗高僧,是宋初致力于儒释相通的佛教学者,为从儒家学派汲取知识,扶树天台之学,对道统论亦有所论述。其《对友人问》曰:“孔子有圣德而无圣位……述周公之道也。孔子没,微言绝,异端起,而孟轲生焉,述周、孔之道,非距杨、墨……扬雄生焉,撰《太玄》《法言》,述周、孔、孟轲之道,以救其弊……隋世,王通生焉……盖述周、孔、轲、雄之道也。唐得天下,房、魏既没,王、杨、卢、骆作淫侈之文,悖乱正道,后韩、柳生焉,宗古还淳,以述周、孔、轲、雄、王通之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驳〈嗣禹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231—232页。又《叙神论》曰:“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可谓写其貌、传其神者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叙神论》,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253页。他列出了“周、孔、孟、荀、扬、王、韩、柳”的道统谱系。
二、宋初学者对“道”之阐述
清皮锡瑞认为宋初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页。。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皮氏所言,宋初学者在阐述道统论时,融贯了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文”与“道”的关联性阐述,有以孟子心性说对抗佛教心性说之意,推动了宋初儒学的转型发展。
南宋叶适曰:“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注][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解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52页。“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注][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告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6页。张岱年说:“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当说是孟子。”[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韩愈阐述道统论时,认为“仁义”是“道”的核心,而“仁义”通过心性的修养来培育。“仁义”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心性”说则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宋初古文学者继承发展了韩愈阐述“道”的观点。柳开《应责》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应责》,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689页。《上王学士第四书》曰:“文不可遽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心正则正矣,心乱则乱矣。发于内而主于外,其心之谓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83页。又《补亡先生传》曰:“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册,《柳开·答陈昭华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91页。与韩愈一样,柳开亦力求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柳开影响了其门人,其学生高弁“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孟子》,喜言仁义。”[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王禹偁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387页
王禹偁也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其《答张扶书》曰:“夫文,传道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7页。,强调文句必须“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58页。。又《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 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文。”[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三黜赋》,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210页。
此外, 穆修《答乔适书》曰:“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穆修·答乔适书》,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13页。又《静胜亭记》曰:“夫静之间,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心乃诚,心诫性明而君子之道毕矣。”[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穆修·静胜亭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432—433页。赵湘《本文》曰:“本在道而通乎神明……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圣与贤……其圣贤者心也,其心仁焉、义焉、礼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则圣贤矣。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世,万世不泯,则固本也……将正其身,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注][宋]赵湘撰:《南阳集》卷6,《本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钱穆曾说:“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則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周程朱子学脉论》,合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宋初古文学者正处于唐儒到理学家的转变阶段,他们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
佛教学者智圆也从孟子思想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道”。其《病夫传》曰:“或议一事、著一文,必宗于道,本于仁,惩乎恶,劝乎善。”[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病夫传》,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 293页。他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8册,《释智圆·三笑图赞》,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 288页。,认为“儒家周公、孔子、孟轲未曾面授,佛教文殊、龙树、慧文亦未尝面授,他研讨荆溪论疏,获得《涅槃》意旨,虽未面受而有所师,故而亦可扶树天台之学”[注]韩焕忠:《佛教四书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智圆论道统的目的是借儒家道统传承的语境来诠释发挥天台佛学。对儒家学者来说,也可借鉴佛教的心性论来诠释发展经学。王禹偁说:“禅者,儒之旷达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册,《王禹偁·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468页。余英时说:“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者,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功臣。”[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5页。智圆对“道”的阐述,无疑为宋学的发展注入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动力。
三、 宋初“道统论”与官方尊孟
“道统论”强调的道德价值及其所具有政治功能,引起宋初帝王的注意。宋真宗曾下诏曰“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注][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祥符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要求文章写作宗经明道。同时,在宋与辽、西夏并立状况下,道统谱系的阐述,对确认宋朝为华夏王朝的正统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此外,孟子所强调的王政和道德观念,对宋初凝结国家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在种放等与宋初帝王关系密切人士推动下[注]种放与宋真宗关系密切,受到真宗器重。《宋朝事实类苑卷》载:“真宗优礼种放,近世无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以顾近臣曰:‘昔明皇优待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宋史·种放传》载:“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真宗)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参见[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种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0页;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种放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897页。),因此孟子及其书逐渐得到宋初帝王的认可。宋朝立国后,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但对这一国策尚需理论上进行系统阐释与总结,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共识。种放作《述孟志》,倡导“施仁义、兴礼乐而行王者之事”,强调“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于天下无不顺也。”[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5册,《种放·辩学》,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59页。《述孟志》推崇孟子,贬霸道,行王道,倡礼义仁政,与宋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具有共识,对宋初凝结意识形态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因此,孟子及其书自然会受到宋真宗认可。此外,柳开、王禹偁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诸多门生亦居宋廷要职[注]柳开的门生李迪斯两度官至宰相;王禹偁的门生丁渭,先后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相职。,他们对道统论的论述及对孟子推崇,也会引起宋廷对孟子的重视。在上述背景下,宋初官方尊孟成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
首先,孟子塑配地方文庙,开地方官方尊孟之始。《礼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注]王云五编:《礼记今注今译》,《祭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422页。《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载:魏齐王正始二年,“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以颜渊配”[注][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0页。,开文庙配享之始。直到唐初,配享孔庙只有颜渊一人。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22人配享孔庙。唐睿宗太极元年,加曾参配享。纵览现有文献,宋代以前,皆无孟子配享的记载。但到宋初,已有地方官员开始将孟子塑配于地方文庙。柳开《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载:“(太平兴国)八年,政事简,秋八月哉生明,撤旧创新,告迁其庙。自颜子及孟子已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宋史·柳开传》载:“太平兴国中,擢升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柳开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9555页。柳开在知润州重修文庙时,将孟子塑配于文庙。这是宋代官方将孟子塑配文庙的最早记载。此后,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宋廷才“以孟轲配食文宣王”[注]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神宗本纪》,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其次,校印《孟子》,撰印《孟子音义》,开《孟子》官学化之始。宋初伴随着镂刻技术的发展及帝王的支持,宋廷对十二经校勘刻印后,又勘印了《孟子》,撰印了《孟子音义》,开《孟子》官学化之始。《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诏国子监校勘《孟子》,直讲马龟符、冯元,说□(书)吴易直同校勘,判国子监、龙图阁待制吴奭,都虞员外郎王勉覆校,内侍刘崇超领其事。奭等言:‘《孟子》旧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文理舛互。今采众家之善,削去异端,仍依《经典释文》刊《音义》二卷。是年四月以进。诏两制与丁谓看详,乞送本监镂板。’”[注]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注][清]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玉海》载:“(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庚子,园子监上新印《孟子》及《音义》赐辅臣各一部。”[注][宋]王应麟:《玉海》卷55,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055页。清人叶名澧曰:“盖宋自大中祥符间,命孙奭作音义,为尊信《孟子》之始。”宋代以前,《孟子》从未得到官方刻印发行,《孟子》与《孟子音义》被宋真宗指令勘印及撰印,并赐予臣工,说明宋初孟子学已进入官学化进程。
再次,《孟子馀义》作为《九经馀义》之一,受宋真宗认可,开《孟子》入经之始。《宋史艺文志》载:“黄敏《孟子馀义》一卷,阙。辉按:此前经学小学类。黄敏《九经馀义》之一。”[注]宋史艺文志补:《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87页。《宋会要辑稿》载:大中祥符五年(壬子)“正月,以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为本军助教。敏通经术,尝著《九经余义》四百九十三篇,转运使滕涉以其书上进,帝令学士晁逈等看详。逈等言所著撰甚有可采,故特有是命。”[注]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宋代以前,《孟子》从未列入经书[注]以往有学者认为,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为《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对此,徐洪兴进行考证,予以否定。其《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一文曰:“蒋伯潜先生说: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蜀石经’( 广政石经),已把《孟子》列入,见蒋著《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3页。据我考证此说不确。‘蜀石经’初刻十经,无《公羊》、《谷梁》、《孟子》。《公》、《谷》于宋仁宗皇祐间补刻入。《孟子》更晚,是北宋末徽宗的宣和年间由知成都的席旦让人补刻进的。证据可见《郡斋读书志》、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等。蒋先生只知‘蜀石经’中有《孟子》,未考其为晚刻,其间相差近一百八十年。”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孟子馀义》作为《九经馀义》中一卷进呈朝廷,说明《孟子》作为经书已得到宋初最高统治者认可,可谓《孟子》升经之始。此后,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被朝廷刻成石经,正式成为“十三经”之一。
钱穆说:“北宋诸儒,乃从韩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于隋举王通,于唐举韩愈,以为儒家道统在是。”[注]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宋初学者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面对“儒者其卒必入异教”[注][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的现实,“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7册,《张景·河东先生集序》,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11页。,其对道统论之论述不仅延长道统的传承谱系,拉近儒家与现实的距离,扩大儒学的生存空间,而且引起宋初帝王对孟子的注意及认可,推动了宋初官方尊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