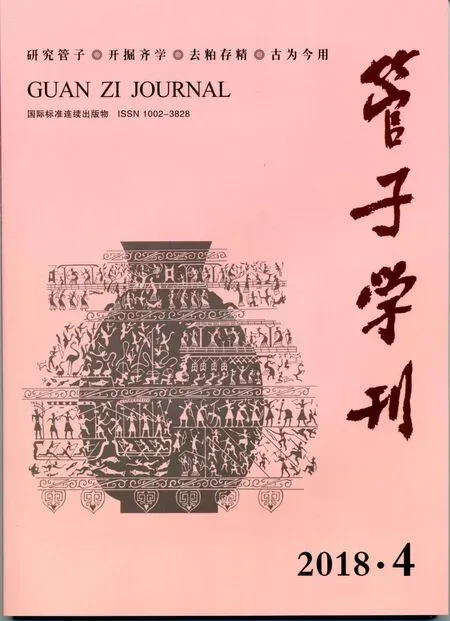“新子学”与民族文化复兴大方向
——兼与陆建华先生商榷
郝 雨
(上海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上海200444)
备受瞩目的“新子学”,自201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而遽然问世之日起,至今已近六年的时光。此后,关于新子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先后举办五届,并有大陆和台湾分别召开的小型研讨活动,也不下十数次。诸多学术杂志发表的专题论文,亦有几百篇。正当新子学越来越走向兴旺之时,陆建华先生发表了《“新子学”断想》[1],和和气气的言语之中,对新子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全面否定。其题目曰《“新子学”断想》,似乎可以因此而少些逻辑。本文也不妨效法,斗胆“断想”一番,且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和能够表达原意,在断想的同时,深入展开一些续想。所以,本文原来的题目就叫《“新子学”断想与续想》。
一
陆文一开始就如此宣判: “无论是从传统的子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子学的角度看,学术界所呼吁建构的所谓新子学也许一开始就背离了新子学。”[1]五六年来众多学者的研究,就这么一步归零了。理由是什么呢?陆先生的逻辑,始终纠缠在“新”“子”“学”这样三个字眼上。最典型的就是这段说法:
从传统的子学的定义来看,新子学可以说是“新子”之“学”,也即新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建构的哲学与思想,或者说,新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研究“新子”哲学、思想的学问。从传统的子学关于“子”的理解来看,“新子”就是指新的哲学家、思想家。当然,如果把新子学理解为“新”的“子学”,从传统的子学的定义来看,则可以指由“新子”所建构的“新”的“子”之“学”,其实质也是“新子”之“学”;也可以指研究“新”的“子”之“学”的学问,其实质也是研究“新子”哲学、思想的学问。由此可见,关于新子学是“新子”“学”,还是“新”“子学”的讨论,没有质的差别。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新子学都是奠基于“新子”之上的,不存在没有“新子”的新子学。[1]
这样论证不禁让人想起人在野外迷路时的“鬼打墙”现象。把三个字左拆一下,右拆一下,转过来,转过去。看上去很严密,其实是把自己套在一个死胡同的圈子里,自己绕不出来了。
其实,至今对于新子学这一新事物,无论学界还是社会上,一直都有各种误解和不理解。陆建华先生这么专业和严谨的哲学教授,都能被概念给绕迷糊,何况一般读者呢!这就非常有必要再次做一些申明,新子学的倡导,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做死学问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新子学并不是要在最传统的治学方法上,单纯从古老的诸子文献中继续挖掘什么新“学”,发现新的字面意义。当然也并不完全排除这样的研究内容。但是,新子学更加宏大的指向,是要探寻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找到真正的复兴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方向和道路。正如方勇先生在《再论“新子学”》中描述的研究规划。“新子学”工作包括三个部分:文献,学术史,思想创造[2]。这是逐步深入的研究步骤,也是并进的三个方面。显然,这里最终的目标是思想创造。所以,我本人也认为,“新子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仍然把子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专业研究,并不只是要在学术理解和阐释上囿于“子”或“新子”等概念之辩,更不是把它作为局限在其传统考据本身的“新”学问。而是要从子学中寻找到真正使我们民族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根本,而最需要找到的就是蕴含在诸子百家之中的中国智慧。
不从这样的层次和境界理解新子学,是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懂得新子学的价值所在的。
二
当然,陆先生既然提出商榷,既然对方勇的“三论”做了认真的研读,是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新子学的深刻内涵的。但是,陆文为了确证自己概念界定的合理性,在行文中专门提出这样的怪论:
剥除方先生这段文字中关于子学复兴的价值、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中西文化发展趋势等的思考,仅就其关于新子学的提出与思考而言,方先生认为新子学是在对“子”的著作、子学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转向子学义理研究”的产物,代表着“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1]
这里必须提请各位方家,要注意整段文字的前两个字“剥除”。把这些真实的用意一“剥除”,可不就剩下他所认定的那些意义了吗?他不想承认的或者是根本未能理解的核心性内容被剥除了,然后就只能通篇搞起玩概念的游戏了。而其实,被陆先生刻意剥除的,才正是新子学所要致力的和追求的。陆先生断想来,断想去,一会儿“传统子学”,一会儿“冯友兰先生的子学”,再就是“新子”来,“子学”去……只是在死概念上做文章,却恰恰把新子学的“魂”,给“剥除”了。不过,这也恰好启示我们,面对众多对新子学的误解,真的需要再做一些更为明确的意义阐述。
实际上,陆先生所“剥除”的这些内容,也还只是新子学内涵的一部分成分和要素。要全面理解“新子学”,当然是可以而且必须在这样的思路上深入下去的,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新子学”之魂。但是,陆先生不仅有意排除和割断这条思路,还故意要将其彻底“剥除”。那就只能离真实的“新子学”本身越来越远了!那么,本文就不妨再回到这个思路,接续这个思路,再次阐述一下非常容易被误解的新子学在这方面的真实用意和文化主张。
当然,我本人既然很不赞同陆建华先生的死抠字眼,死缠字面,甚至死掉书袋的讨论方法,那就不会再去没完没了地纠缠那些所谓概念和定义问题。我认为,“新子学”首先并不是一个有着简单确指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学术范围和文化研究领域。这个概念的所指,本身就应该是尽可能包容的最大泛指。他是一个宏大概念,而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定义的学科名词。所以,我的断想必然会展开续想,跳出概念陷阱,而更多从宏观层面和更高的意义层面阐述我对“新子学”的内涵及意义解读。
三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新子学的魂呢?最近,方勇先生为了回应陆建华先生的商榷,又发表了《“新子学”:目标、问题与方法——兼答陆建华教授》,其中借与陆建华先生讨论之机,对“新子学”的概念、范围、方法、理路等方面近五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新子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总结,以有助于学界深化理解“新子学”。而文章在最后特别谈到:“纵观数千年来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发展,譬犹不同大陆板块之间经由独立漂移转而互相碰撞冲击,原先的矛盾只发生于板块内部,新的矛盾则会从板块内部扩张至板块之间,由单一之个体超越至彼此之关联。百年以来,中西文化之碰撞交流亦复如是……‘新子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试图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3]
“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这就是新子学倡导和创立的魂之所在。
新子学提出和建设五年多来,我本人一直以现代文化学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如果按照陆建华先生那样严格的学科分类,我已经是破了规矩,犯了门户插足的律条。而且在我本学科的许多朋友和同道当中,也多有指责我的不务正业!然而,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就是因为我深刻认识到了这个新子学确实是要“努力寻求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的现代文化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而这不也正是我们的许多不同学科共同一致的大方向吗!五年前,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新子学的文章就是《“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其中就明确表示:“新子学”作为一面新的文化旗帜,必将在整个文化学界更大规模地激越起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潮流。而且,这样一个看似只属于古代文学、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文化的研究范畴。它也为现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方向[4]。
这就是我一开始就对新子学有了这样的理解,也就是一开始就把握到了新子学的魂。于是,我亲自主办了“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现代文化学者视野中的新子学”研讨会,主持了第三届新子学国际研讨会的现代文化学者专场,并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共同主办了第四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大推动了新子学的跨学科影响和发展。
四
作为现代文化领域的研究者,近年来一直处于这样的困扰之中: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由两次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文革”。所以,有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倡导新儒学,认为把儒学接续起来才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说当年打到孔家店是错误的,那就必将涉及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新文化运动是我们中国的文艺复兴,开辟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是新儒学中的有些学者就强调:一切现代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那时把传统文化打倒了、丢掉了,而复兴民族文化,按照他们的常规思路就是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就无形之中陷入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到底孰是孰非的悖论。而现在把“新子学”的概念提出来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要复兴和继承传统文化,应该继承的是百家时代的一种繁荣的、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为什么“五四”时代要打倒孔家店、要反儒家?原因就是,一旦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由百家局限到一家,由一家统治思想领域几千年,那肯定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萎缩。文化是需要活力的,活力是需要竞争和多元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没有问题了。那时的所谓反儒家,反的是由于传统的专制体制而造成的独尊一家的文化局面,所以以反儒家为主要目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推翻,根本改变思想专制的大一统文化局面,从而进入以人为本的文化现代化。这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独尊儒家是我们民族文化衰败的原因之一,而新文化运动中断了儒家为核心的专制性的文化,就是文化历史的大势所趋。因此,我们今天的复兴不能独尊儒家,不能视其为唯一。我们现在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我们就是要重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
五
那么,这样一来,就又遇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被丢掉的呢?传统文化的断裂,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随着对新子学研究的深入,我又逐渐豁然开朗,于是有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发现。那就是,当我们认真考察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第一次断裂,也就是真正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根本性断裂的,是发生在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个事件的间隔时间只有七八十年,显然“焚书坑儒”是一次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至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就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在文人当中的一种学术之争,而且是通过政治手段,是一种人为的强制的力量,作为基本的国策来执行的。这种对百家文化的打击,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文化的断裂。我们必须把这一阶段真正地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地被颠覆,是这一时期。这就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传统文化断裂。
如果按照“两次断裂”这样的说法,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就是针对儒家。所以造成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断裂,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好,认定传统文化断裂也好,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误区,是把当年“罢黜百家”之后所形成的儒家唯一独尊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误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推翻了儒家独尊的这样一种思想传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为鲁迅提出来的把“立人”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思想,也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是错误观念和行为的话,那么,又怎么解释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如果我们把第一次断裂搞明白,我们就会知道真正中国文化最全面、最繁荣的内涵是在先秦,是在百家这个时期。到了汉代发生了断裂,由于儒家独尊,就导致了两千多年一种思想来统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思想上的单一就很容易导致僵化、衰落。所以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这样一个现实提出反传统目标的。这里的反传统所反的这个“传统”,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而是“罢黜百家”之后,“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文化。这样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发现,正是得益于“新子学”研究的结果。
六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发掘和传承传统文化,归根结底重在发扬诸子百家的文化。诸子之学,才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真正源头,才是我们的文化之根。在这个问题上,“新子学”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我们希望当今的现代文化学者以及各个学科的学者,都能更多关注这一新的文化动向,积极参与“新子学”的讨论,打破学科森严壁垒,打通古今学术通道,现代文化研究不再言必称西方。加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让新媒体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在子学精神的全面助力之下,进入崭新时代,开创辉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