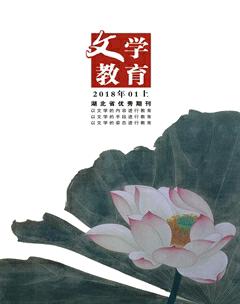从“谪仙”解读看松浦友久之李白风格研究
徐子昭+李梓贤+胡李安
内容摘要:松浦友久由于关注到“谪仙”与李白的高度契合,发现了“谪仙”的属性,并进一步解读出“客寓意识”。“谪仙”与“客寓意识”存在紧密的内部联系,在使用时不免困惑,造成一定程度混乱,笔者提出“谪仙——客寓意识”模式,这一模式其实是松浦友久不自觉运用的。由于生平遭遇、天赋上的一致导致李白对谢朓认同,运用这一模式,可以看出李白的风格来源是谢朓,若没有这一模式,则很可能忽略谢眺。
关键词:松浦友久 谪仙 客寓意识 李白诗歌风格
杜甫曾盛赞李白的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溯至李唐,诗仙尚谪居人世,诗歌风格就受到广泛关注。比及宋元,以至现世,学界对李白风格研究仍在继续。以太白古体风格来源而论,或以为模拟汉魏六朝,或以为源出谢朓。以为模拟汉魏六朝者,有周勋初、王运熙等,以为源出谢朓者,有顾羡季、茆家培、李长之等。王运熙认为:“(李白的乐府歌行和绝句)这两种体裁都是渊源于民歌[1]”,顾羡季认为:“太白诗与小谢有渊源。[2]”前人之述备矣,松浦友久之研究亦在其中,他对李白的风格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谪仙”称号的解读之上。
一.“谪仙”与李白对应:非印象式解读
“谪仙”作为李白的代称,得到了他本人、诗友甚至民间和后世研究者的承认。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一书中有《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篇,盛传于民间,可以窥见“谪仙”称呼深入人心,相比于“诗仙”是与杜甫“诗圣”相对的概念,“谪仙”准确地定位了李白的生平、诗歌成就、行事风格等,从文化含义上讲,“谪仙”成为李白的流传形象。从文学角度,“谪仙”同样值得深入解读。
(一)对“谪仙”进行特别关注
学界对李白的研究,无论是风格特点探讨,亦或是风格来源考证,都会对“谪仙”称号进行关照,然而多是印象式的批评,以周勋初为例,李白被称为“谪仙”是因为“一是神情不凡,二是诗酒风流,三是文才出众。”[3]只停留在“谪仙”形象与李白的代称和表现上,其他亦多如此,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和流传之广泛,被普遍忽视。松浦友久则关注到“‘谪仙人之名,只有在李白这里,才具有独占性、代表性”[4],也就是说,尽管苏轼也曾被称为“谪仙”[5],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临时的,后人并不会以“谪仙”来代称苏轼,而李白却恰恰相反,与“谪仙”一词建立了永久的联系,松浦友久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因为谪仙形象“存在着与李白性格和诗风共通的要素(亲近性)。”[6]可以说,这一见解从现象出发,看到了现象背后的的原因,李白與“谪仙”能够相互依存,本身就值得思考,更何况李白自身也认同这一称呼。所谓的特别关注不仅仅是注意到了“谪仙”称呼,而是在注意到的同时,将其和与之相关的性格、诗风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切入李白诗歌风格研究的角度有很多,从“谪仙”出发属于知人论世,以生平经历佐证诗风。
(二)对“谪仙”属性的解读
基于对“谪仙”的特别关注,松浦友久又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即“(1)才能上的超越性、超俗性;(2)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3)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7]不可否认,这三点概括不无主观性,尤其是第三点,“谪仙”是被贬到凡间的神仙,言论行动可能因为犯了过错而拘谨,并不一定放纵。若是仅从神仙与人的角度来讲,谪居人间的神仙确实没有拘束,因此笔者倾向于将第三点加上“相对于凡人”这个限定于,事实上李白也确实只是相对凡人显得洒脱、放纵,面对自己的理想、报负,他还是有很多忧愁难以排解。瑕不掩瑜,总体上这三点解读非常到位,是“谪仙”和李白共有的特点。
这是浅层次的解读,通过“谪仙”的特点,松浦友久还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就是“客寓意识”。说“客寓意识”是基于“谪仙”提出,主要有以下证据:
首先,松浦友久认为李白的“客寓意识”的源泉是蜀中生活[8],“察觉到自己的出生地与家世的非正统性,因而疏外感和客寓意识逐步加深。”[9],也就是说,李白在蜀中生活并不能找到一种归属感,并且无法得到认同;“谪仙”的得来同样是无法得到认同,如果李白仕途得意、被朝廷接受,他自己也断然不会认同“谪仙”称号,那么只有他在朝廷、乃至在人间都找不到归属感,才会以为“谪仙”之恰切,这也是“谪仙”被李白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找不到归属感,得不到认同、认可,为“客寓意识”与“谪仙”共有,所以“客寓意识”与“谪仙”具有共通性。
其次,松浦友久对二者的解释极其类似。客寓意识可以归纳为“1.生来气质;2.因系异民族、移民之子而培植的疏外感;3.因‘谪仙人称呼而加大力度与幅度的自由、放纵性。”[10]与“谪仙”属性解读是一致的。才能的非凡与生来气质这一点看似没有关系,但是要注意的是,才能的超俗,除了要学习之外,先天的天赋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有没有可能超俗,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超俗的才能也是与生俱来的。《旧唐书》中说:“(李白)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11]就更加证明,少年的才华与志向,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单靠后天是不可能实现的。后两点的表述几乎相同[12],不做赘述。由此可以认为,“客寓意识”的解读是根据“谪仙”解读而做出的。并且,三种要素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一种“一种意识”或者“一种形象”。[13]说明三者都已经是最基本的属性,基本属性一致,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李白因为具有客寓意识,而与“谪仙”形象高度契合,但是松浦友久的研究是逆向过程,由于发现了“谪仙”与李白一一对应的不合常规之处,进而发现,才能上的不俗是因为天生气质就是如此,社会关系具有客体性是因为他是异民族身份产生了疏外感,言论放纵则因为“谪仙”称呼而加深,故综上三点,通过“谪仙”发现了“客寓意识”这一贯穿李白一生各个方面的意识。
二.从“谪仙——客寓意识”入手的风格研究
如前言,松浦友久从李白与“谪仙”之间的高度契合发现了“谪仙”背后的含义,并进一步寻找到“客寓意识”,认为“‘客寓意识是认识李白的‘基准”[14],也就是说,无论是考据李白的生平,或是编纂李白诗文集,都可以从“客寓意识”这一观念出发,对疑难问题进行解决,因为在一种意识的指导下,可以大体推断一个人的作为。李白诗歌风格研究也不例外。endprint
(一)“谪仙——客寓意识”模式
经前文管窥锥指,“谪仙”与“客寓意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窃以为在松浦友久之李白诗歌风格研究中,“谪仙——客寓意识”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
笔者对这一模式的归纳来自于二者之间相似性和使用时的混乱。“谪仙”形象背后有“客寓意识”存在,“客寓意识”背后又存在“谪仙”[15],并且“李白的‘客寓意识因‘谪仙这一形象而增强”[16],二者关系过于复杂。这还仅是概念上的,在诗歌研究中就更加难以把握。论及李白杜甫为何一个难以模仿,一个易于模仿,以及评论时,松浦友久说:“当然,产生这一主要评论基准(尺度)的直接契机,无疑是‘谪仙的称呼;进一步说,乃是作为其不可欠缺之属性的‘客寓性。”[17]显然,这里只想说出“谪仙”,不想说出“客寓意识”,可是二者是在无法截然分开,都发挥了作用,于是便出现了说道“谪仙”就不得不提“客寓意识”的尴尬处境。
基于此,笔者提出“谪仙——客寓意识”模式,至少可以不必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因为这一模式之内相互影响,又带来使用时的便利,是松浦友久研究李白风格的核心。
(二)风格特点研究
“豪放飘逸”是我们对李白诗歌的印象,这一印象深入人心,其程度可以说不次于“谪仙”之于李白。松浦友久认为李白的的诗风是“客体化的诗风”。这是因为李白能够得到“身心自由”,还有功成身退的观念,其中,正是“谪仙——客寓意识”模式发挥了作用,李白是一个“非持续性的责任分担者”[18],他不需要承担责任,不需要对朝廷和百姓负责,因为是客居人间,所以也没有故乡,表现在诗歌风格中就是“怀才不遇的情感”。应当注意,“谪仙——客寓意识”所影响的是李白所有的诗歌创作,而不仅仅是一些看起来比较愤懑、忧愁的诗。由于李白是时间之过客、天地之过客,所以他的诗没有时空上的起点和终点。
“谪仙——客寓意识”模式在李白风格特点研究中地位重要,因为它处在李白生平与诗歌创作的连接点上,这一模式准确地把握了李白生平,也就对风格研究有了正确的指导和帮助
(三)风格来源研究
日本学者往往对诗歌体裁分类观念比较明确,乐府和律绝绝对不会混淆,相互比较时一般也不跨越体裁,而中国研究者在同一诗人的研究中,诗歌往往作为一个整体。但对于李白风格来源的探讨,中外研究者多拈古體诗为例,或者说,由于李白时代诗歌发展体式正在逐渐成熟,能够探讨来源的多是古人已汗牛充栋的古体诗。李白古体诗风格来源,历来说法不一,引言部分已作介绍,松浦友久则认同源出谢朓说。
我们要探讨的是“谪仙——客寓意识”如何在李白风格源出谢朓结论中发挥作用。杜甫将李白与庾信相比较,并以“清新庾开府”来称赞李白,但是松浦友久对此予以否定,“假如以李白自身感悟来寻找‘清新的话,恐怕除谢朓外别无选择,至少不会是庾信。”[19]在此,他认为李白的“清新”风格来源于谢朓,其实李白不仅“清新”风格来源于谢朓,古体诗的诗风都是从谢朓而来,松浦友久对此有暗示:“作为人生的归宿……在与自己诗有同质性的先行诗人的‘诗迹中去寻求,这件事为李白的诗歌和生涯作了某种象征性提示。”[20]也就是说,李白选择当涂青山作为死后长眠之地,而没有回到蜀中地区,是因为谢朓与青山的关系,他为了追寻谢朓的脚步,实际上就是对谢朓的认同。李白与谢朓经历上有着几乎一致遭遇,李白对“谪仙”称号的认同,说明这段遭遇的铭心刻骨,进而也就认同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谢朓。从生平到诗歌风格来源,谢朓与李白相似的生平,就依靠“谪仙——客寓意识”指向了诗风。李白与谢朓具有相同的资质秉赋,只是谢朓为时代所限制,未能够有李白的成就[21]。
所以,松浦友久对李白古体风格来源的研究一是李白的生平,二是埋骨之地不在故乡,三是诗中的形象,这三点都与谢朓联系了起来,“谪仙——客寓意识”模式的作用是帮助生平的研究找到李白所认同的谢朓,否则,没有这一模式,如王运熙,虽然看到李白对谢朓的学习,却将风格来源定位民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三.结语
从“谪仙”入手,对李白风格研究的角度切入比较精巧,一方面,“谪仙”是对李白形象的定位,另一方面,由于定位准确,概括了李白生平,揭示李白内在性格、天赋,而诗歌正是经历或者内在情绪、情感的表现、表达,由此,将李白生平与诗歌联系起来,对于风格探究大有裨益。而对于“谪仙”的解读,一方面是对基本属性的解读,另一方面,基于三点基本属性,“客寓意识”跃然而出。以上是松浦友久进行李白风格研究的思路,完全围绕“谪仙”的理解和解读,但是由于“谪仙”与“客寓意识”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时往往两者并提,且不好把握,所以笔者提出“谪仙——客寓意识”模式,这一模式其实是松浦友久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只是没有归纳出来而已。
“谪仙——客寓意识”模式不仅对李白风格研究有很大帮助,对其他研究诸如李白生平考证、诗文年表以及临终传说等问题都有帮助,虽不能直接代替考证,但可以为考据提供思路。可以说,松浦友久之李白研究还有更多等待发掘。
参考文献
[1]詹锳.李白诗文系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2]王运熙等.李白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3]郁贤皓.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J].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1986(10).
[4]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M]刘维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松浦友久,尚永亮.“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6]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M].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
[7]周勋初等.李白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endprint
[8]周勋初.李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顾随.顾随诗词讲记[M]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李长之.李白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12]周祖譔主编.历代文苑传笺证[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3]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4]李白著,安旗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5]李白著,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注 释
[1]援引自《李白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6月版)第185页.王运熙的主要观点就是李白的古体风格来源是汉魏六朝,尤其是民歌,虽然也提到了李白佩服谢朓,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李白对于谢朓的钦仰,也间接反映了对民歌的重視。”
[2]援引自顾随(羡季)《太白古体诗散论》(收录于《顾随诗词讲记》,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3]援引自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4]援引自松浦友久《“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尚永亮译,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5]苏轼被称为谪仙,据松浦友久考证,材料如后:“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才学》)”.
[6]援引自松浦友久《“谪仙人”之称谓及其意义》(尚永亮译,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7]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页.
[8]观点来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三章标题“李白的蜀中生活——客寓意识的源泉)
[9]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页.
[10]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页.
[11]援引自《旧唐书·文苑传》(周祖譔主编《历代文苑传笺证》(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537页).
[12]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详见后文.
[13]对“客寓意识”解读:“系三者相融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第15页);对“谪仙”解读:“可以说哪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第172页).两则材料都来自《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
[14]援引自松浦友久《“客寓”的诗思:认识李白的基准》(尚永亮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5]松浦友久认为,“‘谪仙是一个具有1.‘天才资质,2.客寓者……”(第13页);对“客寓意识的解读第三点有:“因‘谪仙人称呼而加大力度与幅度的自由、放纵性。”两则材料都来自《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
[16]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页.
[17]援引自松浦友久《“客寓”的诗思:认识李白的基准》(尚永亮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18]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页.
[19]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刘维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20]援引自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志、尚永亮、刘崇德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页.省略号处有省略.
[21]观点来自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刘维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松浦友久认为李白诗歌中有大量的谢朓形象出现,并不仅仅是同病相怜,而是资质秉赋相同。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