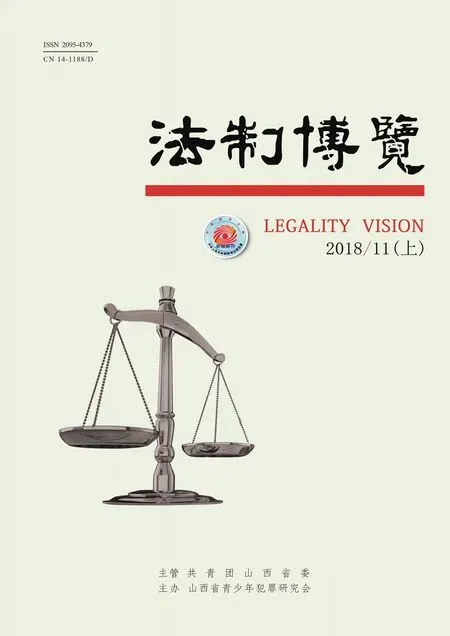完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之我见
林丽华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在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正式将错案追究作为一项新举措予以推广。1997年,“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正式作为执政党文件内容向社会公布。在司法改革背景下,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由此可见,错案追究责任制由来已久,但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错案追究制未能实现其应有之义的原因分析
建立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目的在于确保司法公正。然而,却未能达成制度设计初衷。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存在内在逻辑矛盾,但笔者认为这只能属表象,深层原因是架构法官责任制价值取向的偏差、对“错案”认识的模糊等。
(一)价值取向的偏差。法治国家基于对法官的信任,认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判断权的范畴。为保障独立审判,赋予法官司法豁免权成为法治国家的传统和惯例,虽然他们亦有追责法官一说。相反,我国错案追究制以实体裁判正确与否作为终极关怀,严肃追究办错案件的法官责任,并将之视为实现或体现司法公正、廉洁,减轻社会压力的法宝。同时,通过施加法官以责任,保持了对司法控制的某种需求,易于造成服从和敬畏,使得对司法力量的掌控和运用得以强化。这种“管控”法官的社会心理与审判独立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二)认定“错案”标准不清。因缺乏对程序价值的认可和程序正义的关注,我们在法律制度上习以为常的“错”与“对”,更多是实质意义的。过度追求裁判结论的所谓正确,忽略案件事实认定中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距。于是,不分情形地苛求法官一味地发现真实真相、追求客观真实,违背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客观事实终究无法还原,错案追究注定深陷追责偏差或混乱之境地。
二、法官责任追究制建构的考量因素
(一)将审判权还给审判者。只有当审理者能够独立审判并作出判决结果的时候,司法裁判的质量才有可能得到保证。因此,要想预防和避免冤假错案,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就须明确界定司法产品的产权。当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这一前提,由裁判者负责才有意义。
(二)掌握好相应尺度。在其他条件不变之下,法官责任严厉程度持续增加,其所带来的公正程度实际效用的增加将会变得越来越小。“错案”因其不确定性,追责过严、过宽,都难以起到促进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官追责制度,当满足于宽严适当这一基本要求,方能起到避免司法错误、促进公正司法的功效。
(三)赋予法官司法责任豁免权。一旦出现错误便追究法官责任,这会给法官履职带来重大影响——如履薄冰,进而请示、汇报以期转嫁或减轻风险便成常态,最终损害审判独立与司法公正。当然,若法官违法审判则由法律和纪律处理,不在豁免之列。
三、完善错案追究责任制的建议
(一)将理念转变到保障审判独立上。从对欧美国家比较看,对法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予以规范和惩戒虽是法治国家的通例,但前提是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因此,笔者认为,改革我国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理念转变至关重要,当从限制法官自由转向保障法官独立。即一旦发生“错案”,首先应考虑法官有无豁免情形,如果没有责任豁免情形,再考虑责任追究问题,而非相反。只有实现这种转向,才能鼓励和保障法官独立思考和断案,而不必担心受追责和惩戒,才能调动法官工作积极性。在保障审判独立的前提下,根据权责自负原则,即使进行责任追究,也名正言顺。
(二)转变追责标准。司法活动当然应追究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然而案件的实体判断难以做到答案的唯一性,且实体公正本身就存争议。相比之下,程序公正的标准比实体公正明确、易把握,人们对审理程序是否公正的评判争议不大。法官严格依程序行为是法官在法律内活动的主要标志,是防止司法专横的主要手段,正是行为正当保证了结果正当的高概率。故通过完善诉讼程序规则和法官行为规范,并以追究对程序性规范的违反即可防控实体性司法错误。英美国家均是采用以“不当行为”作为唯一惩戒事由,法德两国则另增了“错误判决”事由。如上文所述,鉴于我国司法裁判现状,完全抛弃对案件裁判结果错误的追责还不现实。因此,我国追责法官标准应从以往专注于结果错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转变为以法官行为失当为主、案件结果错误为辅的二元机制。
(三)扩大追责范围。以往法官责任追究制侧重于关注裁判结果对与错,即法官的职务内行为,而实际上法官的职务外行为于公众对司法公信感观影响更甚。鉴于法官职业特殊性,如果法官存在私下接触当事人等有失司法公信的行为,吃喝嫖赌等有失法官尊严等行为,就会使人们对法官公正行事的能力产生怀疑。因此,无论该失当行为是否影响到裁判结果,均应纳入到法官责任追究的范围。当然,针对法官职务内外行为不同,相应的责任形态亦应有所差异。只要明晰法官职务内外不同责任形态,才能确保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有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