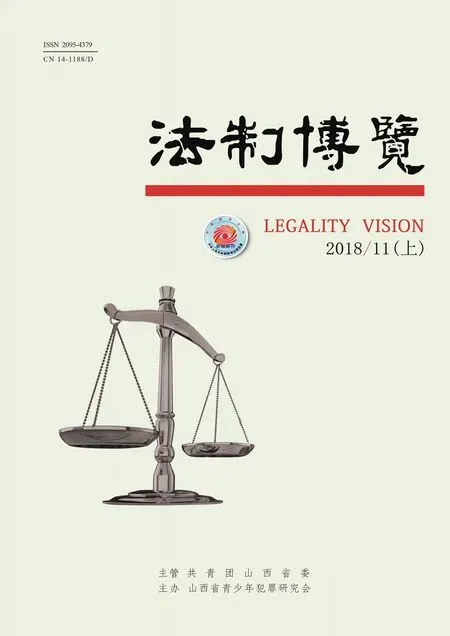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制度构建
柏厚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 阜新 123000
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使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分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且土地经营权能进行融资担保,为激发农村土地生产要素功能、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法理上,解决了理论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争论,将基本人权的发展权在农民融资问题上重新定义,盘活了农民的资产。
一、制度构建必要性
《土地承包法(草案)》的出台,展开了新一轮法律更新辩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等现行法仍保持滞后甚至冲突规定,新规定无法全面实施。
《土地承包法(草案)》规定农民享有土地经营权抵押权,仍有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交易成本过高、不易复制、易生政治寻租等问题,还受到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特殊性的影响,亟需完善法制,以指导新一轮“土地融资”。
《担保法》采二元模式,除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抵押外,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物权法》规定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而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虽禁止抵押,“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二、制度构建设想
(一)土地经营权抵押范围
1.主体资格
(1)抵押人:《土地承包法(草案)》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应列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家庭成员,抵押人不再限于农户,且其流转自主性不再受发包方及个人资产能力影响。
抵押人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但任一成员进行抵押,必须征得全部家庭成员同意,且抵押金应全部用以家庭农业生产。且户主死亡时,家庭成员可抵押土地经营权。
(2)抵押权人:草案规定抵押权人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可以是金融机构。应允许具有相应资质且政府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担任抵押权人,我国地域辽阔,可“因地制宜”,借鉴试点做法,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模式。
2.抵押标的
(1)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目的在于解决土地融资问题,发展农业生产,抵押标的限于农地经营权。
(2)当事人能在抵押合同约定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归属,对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未做规定。
笔者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地上农作物。由于地上作物与土地经营权可以分离,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或转包时,抵押人不实际经营土地,地上作物为承租人所有,或承包方有生产贡献时,一并抵押难以协调当事方利益。
但若地上已有附着物,且抵押人就是农作物所有权人时,农作物所有权可由当事人协商。在其他原因导致土地经营权实现不能时,当事人可依合同约定土地经营权的承担者。
(二)具体设定规则及限制
1.抵押权登记
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确权登记制度,发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的内部承包权流转,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而土地的外部承包权流转,为保护承包权人利益,应办理抵押登记,领取他项权证,抵押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登记与合同不一致的,以登记为准。非因承包方过错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效。
2.抵押担保对象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具有部分社会保障功能,国家政策允许此类土地抵押贷款,但抵押限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身债务。
3.抵押比例和期限的限制
在私人领域和决策中,结果由个人分散而多样化的“货币选票”选中,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充分满足。法律相信农民作为经济理性人,通过私人决策就能内部化外部性,平衡生存与发展,而不替农民衡量风险,做出公共决策。
但紧急情况时,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被迫抵押全部经营权,此时,若承认该抵押,抵押人将难以维持生活,且降低还款可能。因而,可授权各地依自身实际规定一定比例,为农民预留部分生活保障农地,即便该地的抵押权实现,预留地也能保障生活。
另外,土地经营权抵押权不能超过承包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承包期也进行了延长。作为一项用益物权,经营期限和收益及交换价值成正比。故当事人可依贷款额度、贷款用途等因素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的期限,使期限价值与贷款款项匹配。
4.土地经营权抵押权的保护
承包方能很大程度自主决定承包经营权保有,除发包方依法收回外,在承包方可交可不交时,若土地经营权收益大增,超出了抵押合同订立时的预期价值,抵押人可能甘愿违约,使抵押权人受损,此时,为保护农地持续性生产,可依违约作惩罚性赔偿,而非仅支付土地交回的补偿。
(三)土地抵押权的实现
1.协议拍卖。资源配置的好坏,取决于决策者掌握信息的完全性与准确性,在不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集体性质的前提下,公开竞价,最高者得,公开透明且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应将拍卖定为土地经营权实现的原则。
2.无法达成协议时,强制管理的引进。强制管理,指以管理权益优先受偿的一种执行措施。因着眼于农地使用价值,以其收益为执行对象,在农地收益清偿完债务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即回复至债务人直接享有,结合试点,该制度可作为我国抵押权的实现方式。
3.抵押人的优先承租权。抵押人在抵押前,对于未转让过的土地经营权各地可设置保障地。由于保障地规模小、盈利低,法律应赋予抵押人“优先承租权”,即抵押权实现后,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人,拟出租土地经营权的,抵押人可优先承租,对抵押地继续进行农业生产。
4.土地抵押权的转移。抵押权实现时,目前抵押权人资格限制在金融机构,故无所谓继承;即便创新模式下可能由自然人充当第二次抵押权人,该期限受制于承包期,且受让人限于特定当事人,所以不适用继承等继受取得。
(四)配套制度的设置与完善
1.土地价值评估市场。由于行业评估机构泛滥,相互交叉易生矛盾,且土地估价师准入类资格的行政许可已被取消,除房地产评估外,行业资产评估资质缺乏法律依据;而土地价值难以衡量,地上作物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故无需建立地价评估机构,抵押额度的确定可参照:评估价值=承包地年均收益×经营期限+地上附着物预期收入+社会保障成本。
2.交易平台流转市场。可参考试点“重庆土地交易所”做法,在该网站可查询土地交易的有关重要公告、挂牌交易项目以及政策法规等内容。通过土地交易与产权流转进行指导和规范,意向人可在平台发布土地转让及受让意向、融资意向登记等。
3.风险预防及监管。为防止抵押人到期不还款导致坏账,金融机构可设置土地抵押配套跟踪制度,即审查申请人的资信状况、抵押资质、主体适格与否;发放贷款后,监督抵押金使用;最后,依抵押人是否及时偿还贷款等来确定终身信用机制。
推广政策性保险的同时,可由财政出资设立农地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农地金融服务的融资机构因发放农地抵押贷款而产生的本息损失进行一定比例补偿,减少风险积聚。
三、结语
本文结合《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规定,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相较于其他学者的专业建构,创新之处在于富有“意思自治”,充分考虑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当草案上升到实在的法律规定后,将迫切需要此类制度建构参照,希望本文能为立法作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