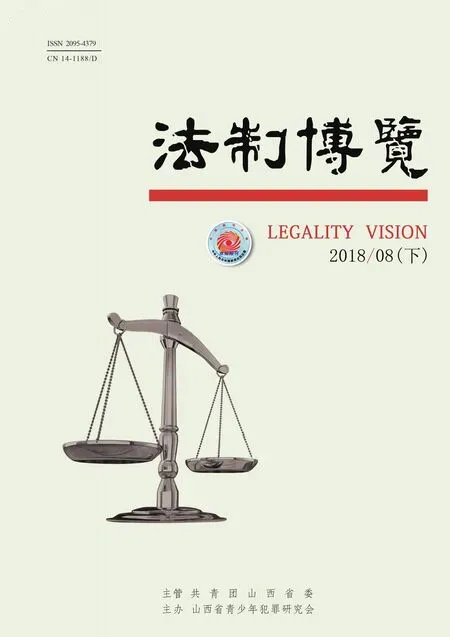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
——兼论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的区别
韩 雪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在20世纪中,在定义国际法概念的过程中,存在将条约认定为特别国际法、习惯国际法认定为一般国际法的通说,这一认知不准确,这主要是因为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之间存在差距,不能视为相等。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为两方面,一是词语混淆,二是对《国际法院规定》的第38条第1款存在理解误区。在现代化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定义国际法,要制定一种更为明确合理的认定标准,正确认识一般国际法,符合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要求,有利于找到一般国际法的本质和构建依据。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当代国际法学中的“一般国际法”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家法的区别
(一)概念范围
站在概念范围的角度上看,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在不同范畴中,一般国际法特指国际法规则的主要范围,面对所有成员,而不是仅仅针对一部分成员。而习惯国家法属于《国际法院规约》中的国际法渊源,特指法律存在形式,以不成文方式存在的一种国际法规则,二者概念定义处于不同领域中,面对对象也不同。
(二)成立条件
在成立条件上看,习惯国际法形成要遵循两大要素,一是国家实践,二是法律确信,这两大要素的判断标准主要以以下几方面为主:第一,国家间外交关系,包括条约、声明以及宣言等外交文书;第二,国际机构实践,包括决议和判决等;第三,国家内部行为,包括国内法规、行政命令以及判决等。而一般国际法并没有系统的成立条件。
(三)正统性
在全球正统性层面上,将习惯国际法认定为一般国际法也是不合理的,站在形成史角度上看,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际法规则,主要是欧美强国间的通行规则,受但是社会环境影响,大部分国家或是地区均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无法参与到国际法规则形成中,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中忽视国际法理论。传统习惯国际法是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在国内立法、法院判决、外交部门行为等实践中总结提取的,形成法律确信,这是习惯国际法的主管依据。随着国际民主进程发展,国际法主体逐渐扩散,平等、民主和公正等观念逐渐渗透到国际社会中,现代化一般国际法强调正统性与正当性。对此,为了掌握和认识一般国际法,需要构建新的规则机制,弥补传统体制的不足,反映出国际现实情况。
二、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家法混淆的根源
从根本上看,一般国际法与习惯国际法的混淆主要来源于“广泛性”和“一般性”的认知混淆,为了证明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必须要具备广泛一致的国家实践,这种“广泛性”很容易理解为“一般性”,若将“一般性”认定为“所有成员的普遍性”,则“广泛性”就无法符合这一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法中的“广泛性”并非要求所有国家参与,这就增加习惯法规则建立的困难程度。一般情况下,习惯国际法规则主要以大国实践为代表,没有表示反对的国家就是默认,进而符合“广泛性”要求,这种默认存在法律拟制性质,弥补普遍性与正统性的不足。
三、一般国际法认定标准
根本意义上看,《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只规定了裁判规范,以国际法院裁判行为为主要对象,而并非是一般法律行为,说明这一规定只是法院审理案件时的参考依据,而国家法的应用实践,并不局限于国际法院或是其他国际法庭。相比于国内社会而言,司法裁判并非是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全球190多个国家,只有66个国家接受和认同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大多数国家作出各类形式的声明,使得国际性法庭只能管理约束特定范围内的争端,大多数国家间的争端不会诉诸法庭,适用性小,这就赋予了国际法庭的裁判功能。裁判功能之外,一般国际法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发挥出社会性功能的作用,可以对国家行为形成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国家来遵守国际法,约束国家采取违法行为,形成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的国家间交往的“共同语言”,沟通职能十分重要。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拟定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使得国际法规则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形成较大的改变,当时学者结合国际社会实际情况,认定为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家法主要规定主权国家利益与权利关系,这是合理的,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这种方式不符合现实要求,国际法形式也是在不断更新和改变中,针对上世纪的主流理论,需要相关研究人员以历史批判性视角进行认识和对待,以实现更大的创新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