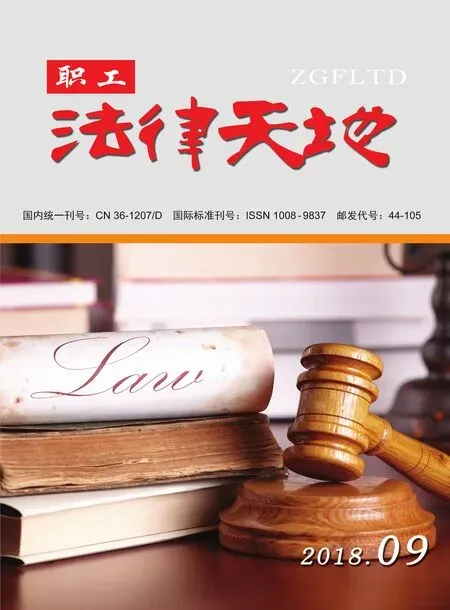刑事推定规则在“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认定中的运用
——以杨某故意伤害案为例
姚彩云 王 乐
(1.100072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北京 2.10007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 北京)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某日上午,被告人杨某林因不满同居女友王某凤与他人外出聚会,两人在杨某林家中发生争吵,后杨某林用水果刀扎刺王某凤腹部两刀,背部两刀。王某凤昏迷后,杨某林打电话给其单位副主任万某平,告知自己扎伤了王某凤的事实,并让万某平快来。万某平马上打电话给其单位主任许某静。二人几分钟之后来到了案发现场,万某平先问杨某林打120了没有,杨某林称没有。万某平打通999之后,到楼下去接救护车。杨某林和许某静一起在客厅等候,期间许某静拨打了派出所的电话报警。救护车来了之后,杨某林协助将王某凤抬上担架,之后一直在家里直至警察到来之后将其带至派出所。杨某林到案之后,在侦查阶段称自己知道许某静打电话报警了,但庭审时称不知道,在二审期间称自己记不清了。被害人王某凤的伤情经鉴定为重伤二级。
二、主要问题
本案中主要问题为如何认定“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是否可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林构成自首。
三、分析意见
(一)分歧意见
一审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某某系自首。第一,杨某某系“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应该认定为自动投案;另外,杨某某在案发后给其单位领导万某某打电话,应认定为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亦系自动投案。第二,被告人杨某某“如实供述了所犯罪行”。虽然杨某某在扎伤的顺序、持刀的方式、扎伤后对被害人有无威胁等方面与在案证据有一定程度的出入,但杨某某到案后始终对持刀扎伤被害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且判决也认定了被告人杨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的犯罪事实”。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杨某某不构成自首。第一,被告人杨某某当庭称,自己没有听到证人许某某报警,不能认定为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第二,被害人杨某某认罪态度不好,对于一些重要的犯罪细节未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二)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一审检察机关的意见,认为杨某林构成自首。虽然本案中无法确切地认定杨某林确实知道他人报警,但在案证据可以推定杨某林已经预知了许某静或万某平到现场之后应该会报警,知道他人可能已经报警了。在此种情形,可以通过刑事推定来认定杨某林系“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这符合刑法解释的要求,也符合自首制度设立的目的。
中国刑法确立了大量推定规则。其中,刑法典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特定构成要件事实,确立了以推定替代司法证明的事实认定方法。而最高人民法院自行颁布或者参与颁布的司法解释,确定了越来越多的推定规范。法律推定可以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1]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当某一事实确认存在时,就可以认定另一事实存在,而不需要再运用证据加以证明。法律推定是可以反驳的推定。事实推定则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根据社会的一般常识、经验法则,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由某一事实的存在推定另一未知事实,从而认定犯罪事实的规则。尽管刑法理论界对推定的概念尚未完成达成一致,但普遍认同推定具有三个关键元素:基础事实、推定事实和常态联系。[2]通过一个案件的基础事实,可以推定出未知的事实,但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并非是确定的因果逻辑关系,而是一种常态关联。在刑法中这种推定的结论由于其结果具有盖然性和可辩驳性,刑事推定的运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应遵循刑法基本原则。
其一,基础事实是已经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基础事实是前提。本案中已经有证据证明的基础事实有:事实一,本案中杨某林平时为人老实,与被害人系多年同居男女关系、感情较深,杨某林此次系因琐事争吵后初次犯罪。事实二,在扎伤被害人之后,杨某林及时拨打了其领导万某平的电话要求其来到现场,万某平和许某静来到现场后,杨某林和万某平进行了正常的交流,之后协助将被害人抬到担架上。事实三,许某静报警时,杨某林和许某静一起在客厅中,许某静当着杨某林面拨打了报警电话,二人距离很近,许某静打电话声音较大。事实四,对于是否明知许某静报警,杨某林在侦查阶段称自己知道许某静报警了,但在开庭时,杨某林称没有听到,后又称记不清楚。
其二,推定事实是司法人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或是经验法则,通过已经被证明的基础事实推定出的法律事实。本案中依据前述基础事实可以推定出如下法律事实:一是依据事实一和事实四,可以判断杨某林在案发之后处于情绪激动状态,对于许某静是否当场报警细节记忆模糊。杨某林在初次犯罪,将自己的女友扎伤,产生了比较大的情绪波动,导致对事发时报警细节记忆不清,所以其供述对于此点前后有差异。二是依据事实二,可以判断出杨某林当时处于意识清醒状态,应当预见到了他人会报警。杨某林在案发后及时打电话,与万某平正常交流,帮助抬被害人等行为反应出杨某林当时意识清醒。一个意识清醒,智力正常的人都能认识到在单位领导到现场之后应当会报警。三是,依据事实四,可以判断出杨某林当时具有听到许某静报警的客观条件。许某静、杨某林二人均在客厅,距离较近且许某静打电话声音大,杨某林客观上具有听见许某静打电话的可能性。
其三,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并非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而是一种常态关联。通过前述基础事实,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推定出来“杨某林对报警事实的认知状态是,预见到了许某静她们会报警,知道许某静可能报警了,但对报警的具体情形存在一定的记忆模糊”,但无法确定地推定出杨某林确实明知他人报警的事实。
其四,在本案中通过刑事推定规则推定出“杨某林预见到了他人会报警,知道他人可能已经报警了”的认知状态之后,将杨某林此种情形解释为刑法上的“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符合刑法的解释原则,符合自首制度设定的目的。一方面,用平义解释的方法来分析,刑法上的明知,不仅包括确切地知道,在某些条款中也包括知道可能的事实。如强奸罪中奸淫幼女的明知,是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或者明知女方一定是幼女,或者明知女方可能是幼女[3]。本案中,杨某林已经预知到了万某平等人来了之后会报警,知道许某静可能报警了,可以认定为刑法上的明知。当然,可能有人会认为“明知”的字义就应该是明确知道,而不包括可能知道或是比较模糊的认识,但这只是日常生活中从平义的角度来理解“明知”二字。平义本身就分为日常生活的平义和法律上的平义,在刑法的语境下,当然要从刑法规范出发做出刑法上的平义解释。刑法上的明知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明确知道肯定是,如刑法中的直接故意,一般是指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导致某种某些结果;另一种是明确知道可能是,如间接故意中的明知行为可能会导致某种后果。因此,刑法并不将行为人只是知道“可能是、可能会”这种存在一定模糊状态的认知排除在“明知”范围以外,而刑法中“明知”恰恰是包含了此种情形的。二是,从目的解释的刑法解释理由来看,将杨某林的行为解释为自首中“明知他人报警”,符合自首制度设定的目的。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设定的目的,来发现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司法解释之所以将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认定为自首中的自动投案,就是因为在此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自动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体现了犯罪嫌疑人事后的悔过态度,刑法支持鼓励犯罪嫌疑人这种在犯罪之后主动改过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更好地保护被害人、及时挽救和弥补被犯罪侵犯的法益之功效。本案中,杨某林预见了他人应当会报警,知道他人可能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仍然在现场等待,这使得被害人得到了及时救助,且杨某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救助被害人。这比较成功地节约了司法资源,亦体现了杨某林的对于伤害他人真诚悔罪态度,还及时弥补了被侵害的法益,将杨某林的行为认定为“为明知他人报警”完全符合自首制度设定的三个方面的主要目的。因此将杨某林的行为解释为自首中的“明知他人报警”,正是遵循了刑法设定自首制度的初衷。
需要说明有两点:一是,案发之后,在无其他任何人知道犯罪事实发生的情况下,杨某林及时、主动打电话给自己单位的领导告知自己扎伤了被害人的事实,并让领导到案发现场,可以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二是,杨某林在案发后有足够的时间、条件逃跑而未逃跑,自愿在现场等待被抓捕,属于“在现场等待”。在许某静、万某平送被害人王某凤去医院之后,杨某林独自在家里,具有逃跑的时间和条件,但一直在家中等待,直至被公安机关带走,属于“在现场等待”。
综上,杨某林在案发后,主动向其所在单位负责人员投案,且明知他人报警在现场等待,均系“自动投案”;且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可以依法认定自首。虽然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4]刑事案件要求最严格的证明标准,但推定规范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司法实践成为推动刑法推定规则合理适用的最大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