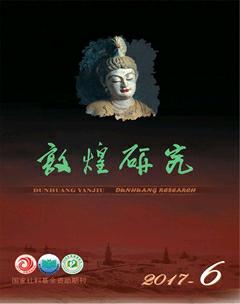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持麈人物
周方+卞向阳
内容摘要: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持麈人物是莫高窟历代洞窟中最早的持麈人物图像。本文论述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两次出现持麈人物的意义与内涵,并指出由第285窟持麈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南朝传入北方的文人意识,是此前莫高窟壁画中所没有的,第285窟麈尾的形制特点也反映了时代风格的变迁和南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关键词: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持麈人物;麈尾;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58-08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Zhu”in the Fresco
on the South Wall of Cave No.285 at Dunhuang
ZHOU Fang BIAN Xiangyang
(College of Apparel and Art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
Abstract: The south wall of cave 285 presents the earliest image of a man holding a“zhu” (horsetail whisk)made from the tail of deer-like animals that endowed the holder with the right to be heard. This paper not only discusses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this figure, who can be seen twice in the paintings,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literati and the spread of culture from south to north. This was a new theme in Mogao murals of the time. The comparison of the shape of the“zhu”in cave 285 with the shapes of the“zhu”illustrated in other caves also serves to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tylistic exchang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t that time.
Keywords: holder of a“zhu”; horse-tail whisk; south wall of cave 285; story painting; Mogao Grottoes
一 第285窟南壁的故事畫
莫高窟第285窟是莫高窟北朝时期唯一有明确纪年的洞窟,也是莫高窟北朝时期的标尺洞窟。第285窟南壁出现的五铺佛教故事画也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这五幅故事画分别是“五百强盗成佛因缘”“化跋提长者姊缘”“佛度水牛缘”“沙弥守戒自杀缘”和“婆罗门闻偈本生”。其中又以“五百强盜成佛因缘”与“沙弥守戒自杀缘”最受关注{1}。本文将研究目光锁定在“五百强盜成佛因缘”与“沙弥守戒自杀缘”两铺故事画中的持麈人物,探讨第285窟南壁两次出现持麈人物的意义及内涵。
二 第285窟南壁的持麈人物
持麈人物在第285窟南壁出现了两次。
一是出现在“五百强盗因缘”中,画面情节对应北凉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梵行品》中所述情节:“乔萨罗国有诸群贼其数五百,群党抄劫为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纵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遂着黑暗丛林之下。”故事画中波斯匿王跽坐于亭阁之中,头戴高冠,内服白色曲领中单,外服黑色对襟大袖袍服,领缘处有白色缘边,袖口有白色褾,为南北朝时中原贵族的常服。右手持麈,食指轻举,似有点化教诲之意。麈尾短柄,形制呈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一个标准的圆形,圆形之上绘有五个圆点状装饰图案,上部呈两个尖角造型(图1)。
二是出现在“沙弥守戒自杀缘”中,画面对应《贤愚经·沙弥守戒自杀品》中所述情节:
时彼国法,若有沙门白衣舍死,当罚金钱一千入官。时优婆塞以一千金钱置铜盘上,载至王宫,白言大王:“我有罚谪,应入于王,愿当受之。”王答之言:汝于我国,敬信三宝,忠正守道,言行无违,唯汝一人,当有何过而输罚耶?时优婆塞具陈上缘,自毁其女,赞叹沙弥持戒功德。王闻情事,心惊悚然,笃信增隆。而告之言:“沙弥护戒,自舍身命,汝无辜咎,那得有罚,但持还舍,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养沙弥。”
图中手持麈尾人物为正与优婆塞交谈的大王。大王跽于地垫上,头戴漆纱笼冠,内穿白色曲领中单,外穿红色对襟襦裙服,领缘处有黑色褶边,袖口有黑色褾,是为中原贵族的常服。右手持麈尾,短柄,但较上图麈尾之柄略长,其余形制与上述相同(图2)。
第285窟南壁所绘麈尾是莫高窟壁画中最早出现的麈尾图像,并非有学者认为的北周时期{2}。第285窟南壁这两例持麈世俗人物无论是服饰、动态,还是麈尾的形制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从绘画形式上看,两位持麈人物形象似乎是遵循了同样的绘画范本:人物褒衣博带跪坐于地,右手持麈轻举,从人物身份上看都是以大王、国王这样尊贵的身份呈现的,从画面情节上看都处于指点迷津、点化教诲的故事情境之中。
三 麈的形制
麈,又被称为麈尾。《说文解字》释:“麋属,从鹿,主声。”[1]《资治通鉴》载:“麈,肿庾翻,麈尾,尾能生风辟蝇蚋。”[2]《埤雅》载:“麈,兽,似鹿而大,其尾辟尘。”[3]《汉语大辞典》载:“古人闲谈时执以驱虫、掸尘的一种工具。”[4]可见,麈是一种用麋鹿类大型哺乳动物的尾巴做成的扇形器具,在古代中国具有辟尘、拂秽、生风辟蝇蚋的效用。东晋王导曾著《麈尾铭》称颂此物:“谁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静暑,虚心以俟。”可知在东晋前后,麈的主要作用是拂秽清暑。endprint
目前可见最早的麈尾图像是东汉晚期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在河南洛阳东郊朱村曹魏墓的墓室壁画“墓主人夫妇对饮图”中,男性墓主身边站立二位男仆,其中贴身站立的一位男仆右手所持麈尾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麈尾图像(图3):“黑色桃形夹板,夹板周边有宽窄两道金线,内饰花纹,夹板外缘绘出赭色麈尾毛,下有柄。”[5]247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壁画墓中石椁的后壁也绘有男主人凭几持麈图像(图4)。八角村壁画墓虽被判断为魏晋墓,但时间上距东汉相去不远[6]。此图中的麈尾形制又与洛阳曹魏墓中的非常相近,可视为同一时期的又一例证。安岳三号墓(又称冬寿墓)的墓主人右手持麈(图5),麈尾夹板上饰有瑞兽图案,此图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所持麈尾的形制与八角村魏晋墓都极为相似,应是源于同一时代的同一粉本。酒泉丁家闸魏晋十六国壁画墓5号墓,壁画墓主人端坐于榻上,左右手相交于腹部,右手持麈(图6),麈的形制與上述相同。此四例皆可视为东汉至魏晋时期麈尾形制的代表。这个时期的麈尾整体呈桃形,四周皆附麈毛,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麈尾形制区别很大,又因为此四例图像绘制时间均早于第285窟所属的西魏时期,所以可被视为麈尾的早期形制。另有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中,吴王孙权右手持麈(图7),此图虽是唐代所绘,但孙权是汉魏之际的人物,因此孙权手持之麈与以上四例形制相近也是合乎情理的表现。以上所举五例图像除了洛阳曹魏墓,其余四例麈尾均由墓主或帝王所持,因此,得出麈尾自古就是高等贵族的贴身使用物件这样的结论应该是较无异议的。
以上五例麈尾均由身份尊贵的人所把持,另外还有单独绘制于画像砖上的麈尾图像,如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后室西壁壁画中绘有悬挂的麈尾,以及嘉峪关新城5号墓,在墓后室南壁壁画中,麈尾与便面同时出现在一块画像砖上(图8)。便面为东汉贵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器物,此图说明麈尾与便面都出现在东汉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此两例麈尾均呈倒挂的圆形,与上述桃形麈尾有了形制上的区别,尤其是嘉峪关新城5号墓南壁壁画中的麈尾,清晰可见麈毫被夹插在一个完整的圆形夹板中,圆形夹板上有曲线装饰,短柄,柄端有绳结相系,似为方便悬挂之用。其他较完整的圆形麈尾可见《洛神赋图》中神女所持(图9)与纳尔逊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线刻画中侍女所持。此两例麈尾下部均呈圆形,尾毫部分被绘制的较为轻盈,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所绘麈尾有相似之处:尾毫都分开为两个部分,圆形的夹板上都有五个小圆形图案装饰。此两例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装饰上看,与莫高窟第285窟南壁麈尾的相似度都极高。因此笔者推测第285窟南壁所绘麈尾与此两例应是同一形制的麈尾,尾毫呈现形式的差别可能是由于画师对于麈毫材质的理解程度、表现手法不同,以及画师绘画水平的差异而导致。
南朝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中出现的持麈人物,与第285窟南壁麈尾尾毫的形制最为接近:均呈两个几何形尖角,然而夹板及手柄部分差异较大,小圆形装饰亦不可见。麈毛呈两个尖角的造型有多件图像例证,又出现在不同的地区,虽然此例与第285窟南壁麈尾的形制还是有所差异,但是可以确认麈毛分为两个部分的麈尾是真实存在过的。尖锐的麈毛与中国古人造物讲求完满和谐的造物观念略有不符,有可能是由于画师的省略表现,才造成了麈毛的尖角造型,现实中的尾毫应是根根分明,呈现出一种近圆形的柔和轮廓。
麈尾是如何与宗教人物发生关联的现已无法追根溯源,可能是因为魏晋时持麈清谈者主要是士林名流、道教人士及僧侣三类人[8]。而在北朝各大石窟中多见的维摩诘持麈说法像说明,至少在北魏时期,麈尾就已经完全被佛教接纳了。对比维摩诘所持麈尾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麈尾实物残件,可知为同一形制,即被描述为“圆上天形,平下地势”的麈尾{1}(图10)。莫高窟历代壁画中除了西魏第285窟南壁麈尾之外,北周至隋唐以后的麈尾都是维摩诘手中所持的形制。据《南齐书》记载,有“异人”名张融,在其病卒后“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麈尾在此被信奉道教的“异人”赋予了复魂的功能。《南齐书》又载:“融(张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陆修静以白鹭羽麈尾扇遗融,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9]721此处将“麈尾”与“白鹭羽扇”合并为同一物。北魏升仙石棺画像中仙人所持之物可能就是这种白鹭羽扇与麈尾的结合体[5]242。而事实上,羽扇与麈尾应分属两物。陆机在《羽扇赋》中写:“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此文将麈尾交至战国时期的人物手中,显然是文学上的隐喻,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麈尾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而此文中明确将白鹤羽扇与麈尾列为两种事物{1}。《世说新语》载“庾稚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稚恭上扇,以好不以新”[10]106。又载“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10]105。此两段分别描述了魏晋时期毛扇与麈尾的故事。“麈尾”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并未与其他“毛扇”类词汇合并相提。可见,“毛扇”与“麈尾”所指并非为同一种事物。孙机先生所言“麈尾外形与扇相似,所以又叫‘麈尾扇”,并无依据{2}。亦有学者认为此时的麈尾可能由于原材料的短缺,已不用麋鹿之尾,而是采用别的羽毛类材质代替,也是尝试将麈尾与毛扇合并为同一类事物的猜测。
麈尾与拂尘同样是两种不同的器物。《正仓院考古记》载:“麈尾有四柄,此即魏晋人清谈所挥之麈,其形如羽扇,柄之左右傅以麈尾之毫,绝不似今之马尾拂尘”[11]。而对比正仓院所存拂尘与麈尾的残件(图11),可以看出两者形制也是相去甚远,“拂尘骨子仅一直棒,而麈尾骨子,则包括柄、镡、吞口、挟板等”[12]。而莫高窟早在北凉第275窟就已出现了明确的拂尘图像(图12),这说明拂尘作为宗教器物的时间并不晚于麈尾,拂尘与麈尾不存在形制上的因袭关系,而是共存关系。麈尾一般由贵族或地位很高的文人所持,而拂尘多由侍从所持。因此,麈尾与拂尘无论是形制上还是使用功能、阶级属性都不相同,不可被混为一谈。王勇认为“后期麈尾,大概因为‘麈这种鹿类动物的锐减及佛教‘不杀生的戒律,难以古制传世,其形制便渐与拂尘混同,形成一种新的道具——麈拂”[12]205-209,此为另一说。endprint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东汉至魏晋时期{4},麈尾呈桃形,尾毫短而尖挺,外轮廓略显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麈毛修剪整理。这一时期为麈尾的早期形制,其作用以拂秽清暑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麈尾形制逐步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圆形麈尾,注重夹板上的装饰,且装饰多样。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麈尾即是此期圆形麈尾形制中的一种,这个时期麈尾成为名士清谈时的雅器。北朝至隋唐时期,以维摩诘所持麈尾多见,与之前松散参差的尾毫不同,麈毛边缘明显经过了修剪整理,呈现出整齐的、“天圆地方”的轮廓,与日本正仓院所藏麈尾实物残件为同一形制,说明此类麈尾从北魏一直延续至隋唐。不同时期的麈尾无论是形制还是功用内涵都有所区别(图13),魏晋时清谈以追逐玄理为诉求,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麈尾的文化内涵也随着清谈的衰落产生了变异,逐步被纳入宗教的仪轨之中,从清谈名士的手中落入神仙异人的手中。当麈尾被宗教接纳后,出现了一些麈、扇、拂相杂的名词,后逐步消失在历史视野之中。
四 第285窟南壁持麈人物的分析
莫高窟第285窟是西魏时期的代表性石窟,该窟整体体现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285窟南壁两次出现持麈人物并不是偶然,他们身上所隐含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加以分析与思考。
首先,麈尾是士家贵族展示身份地位的雅器。《南齐书·陈显达传》载:“显达谓其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9]490王谢是东晋世家大族,累世功名至与君王共天下。麈尾被认为是王谢家物,可说明麈尾是高等贵族才能享用的器物,不属于普通士族或编户齐民阶级。《世说新语》载:“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来,来,此是君坐。”[10]281丞相持麈尾也说明了麈尾的阶级属性。《世说新语》载:“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10]376除此处记载的玉柄麈尾之外,傅芸子在《正仓院考古记》中记载了“柿柄麈尾”、牙装“漆柄麈尾”、“金铜柄麈尾”、柄端紫檀质“玳瑁柄麈尾”的遗存实物。又曰:“按晋时庾亮有诘康法畅麈尾过丽之逸事,可见自晋以来,麈尾已尚华丽,正仓院诸具犹存其风,又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中之吴主孙权所持之麈,与陈品之华饰略同,亦一良证。”[11]90依中华自古造物之惯例,不同材质的使用必然体现出了使用阶级的差异。玉柄麈尾应为最高等级麈尾,持玉柄麈尾之人若非帝王贵族,必为公认士之翘楚。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所见麈尾,分别由波斯匿王和国王所把持,可视为麈之阶级性的又一良证。
其次,麈尾多出现在进行辩谈、析理的场合中。释藏《音义指归》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看麈所往,随麈尾所转为准。”[13]魏晋文士攀附其引导之意,将麈尾视为清谈时不可缺少的道具。清谈一般以问答的方式进行,持麈者为“主”,即主讲人,提问者为“客”,提出问题,请求持麈者析理。清谈时持麈可助析理人“体随手运,散飙清起。通彼玄咏,申我君子”,“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因通无远,废兴可师”{1}。在清谈过程中,主与客,即提问者与析理者的位置可以置换,轮流持麈。辩谈激烈时还会产生“往反精苦,客主无间”的情况,甚至“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10]156。《世说新语》又载“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10]152谈玄论理之前要先解下系在帷帐上的麈尾。若是在没有麈尾的场合,还要使用其他的替代品,否则清谈无法进行。《陈书·张讥传》载后主(陈叔宝):“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14]254。麈尾不至似乎损失了清谈的仪式性,参与清谈者莫不遵守此规则。第285窟南壁二位持麈人物皆出现在交谈析理的情境中,言谈者的话语权由持麈这一细节无声地展现了出来。
麈尾还是一种高级赏赐品,代表了荣誉、对才学的肯定与褒奖。《陈书·张讥传》载后主(陈叔宝)集官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14]254。张讥才学出众,得陈后主亲赐玉柄麈尾。《梁书》卷三七“谢举传”记载:“举少博涉多通,尤长玄理及释氏义。”国子博士卢广叹服其辞理通迈,“仍以所执麈尾荐之,以况重席焉”[14]311-312。赐麈即为恩荣之举。后由于风流名士时常捉持,相习成俗,“虽不谈亦常执持耳”[15],持麈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也体现出时人对于名士风度的追逐与崇尚。
综上所述,麈尾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从拂秽清暑的工具,到名士清谈所持的雅器,后成为宗教人物手中的法器,最后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应为麈尾的全盛时期,麈尾伴随着名士的清谈故事被史书记载下来。莫高窟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麈尾即为这个时期的麈尾形制的代表。南朝名士手中的风流雅器在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两次出现,完善了整个故事情节的需要:无论是在波斯匿王点化五百强盗,还是在与优婆塞交谈的国王畅言汝沙弥舍命守戒,当无责咎的故事情节中,麈尾都作为重要的道具出现。波斯匿王与国王虽为佛教故事中的人物,画师却给他们穿上了褒衣博带式的汉式贵族朝服,手持麈尾,宛若正在辩谈析理中的江南名士,说明在西魏时期,南方文士的风尚已经传播到了敦煌。南北朝虽然隔江而治,相互制衡,但并没有隔绝文化上的传播与交流,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持麈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由南朝传入北方的文人意识,亦是此前敦煌壁画中所没有的。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麈尾不同于龙门、云冈或北朝其他石窟中多见的维摩诘所持麈尾,而是更接近于南朝的麈尾形制,说明西魏时期的敦煌深受南朝文化的影响,有着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是文化上先进与开放的体现,第285窟南壁故事画中的麈尾作为西魏时期麈尾图像的唯一例证,也是对于麈尾历史研究的图像补充。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3.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810.
[3](宋)陆佃·埤雅·卷三:释兽.明成化刻,嘉靖重修本.
[4]罗竹风.汉语大词典[G].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1290.
[5]黄明兰.再论魏晋清谈玄风中产生的名流雅器:麈尾——从洛阳曹魏墓室壁画《麈尾图》说起[C]//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上),2004:242.
[6]董淑燕.执麈凭几的墓主人图[J].东方博物,2011(09):51.
[7]吕品生.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J].文物,2001(04):55.
[8]董坤玉,王宇新.出土壁画麈尾考[J].社会科学论坛,2013(07):85.
[9](梁)肖子颐.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728-729.
[10]刘义庆.世说新语[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06.
[11]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第四章[M].发行所:文求堂.昭和十六年六月一日:90.
[12]王勇.日本正仓院麈尾考[J].东南文化1992(08):207.
[13](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麈尾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12):32-33.
[14](唐)姚思廉.陈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54.
[15](清)趙翼.廿二史箚记校正[M].王树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17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