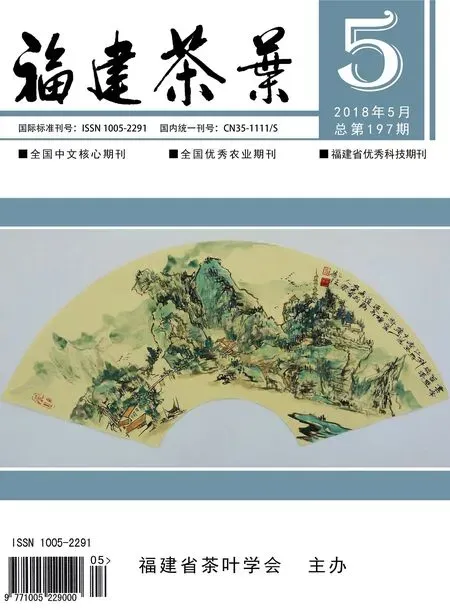基于茶文化的中式茶馆与日式茶室比较研究
闫丹婷
(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重庆涪陵 408100)
茶,在中国传统世俗文化中有着重要而显现的地位,中国老百姓讲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常常借用饮茶来休闲、交流、议事,因此中国形成了各种类型的茶馆;而日本讲究“禅茶一味”的茶道精神,主张通过“茶”达到静思和冥想的目的,因此日本结合禅宗与“枯山水”景观,形成了日式茶室和茶庭。
1 茶的起源与中国茶道思想的形成
1.1 茶的起源
相传5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荼即茶,可见茶被国人认识是因其有解毒的实用功效。唐代大医药家陈藏器认为“茶为万病之药”;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茶在国内大规模饮用也是为学佛过程中提神醒脑之用:“开元中……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遂成风俗”。据记载,茶在我国其实有药用、食用和饮用几种方式,至今,云南的基诺族、景颇族、四川的苗族、彝族还有将鲜茶叶加盐凉拌做菜的习惯。可以看出茶于国人是实用和日常性的,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1.2 中国茶道思想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名僧皎然曾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明代张源《茶录》载“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现代茶文化学大家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潮州)工夫茶“七义一心”,即“中国茶道包涵茶艺、茶德、茶礼、茶情、茶学说、茶导引七种义理。”可见,中国茶道是与茶相关的所有知识的总和,而并不像日本茶道那样以茶为载体,追求个人精神层面的修养和提升。这种差异也许根源于中国茶文化传播的宽泛性和形式的丰富性,这种特性也导致我国形成了多重茶道,简要来看主要有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和世俗茶道。其中的禅宗茶道随佛教东传日本,并最终发展为日本茶道。
2 茶东传日本与日本茶道的形成
茶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始终与佛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导致了日本“禅茶一体”茶道精神的最终形成。
2.1 茶随佛教传入日本
茶最早由派往大唐留学的僧侣带回,代表人物有空海、永忠和最澄,这三位都是当时日本名声很大的高僧。通过他们的影响,茶逐渐传入日本社会。据唐代元和九年《空海奉献表》记载“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记载了空海在长安一边学习一边饮茶的情况。806年,在回国之际,空海将茶籽带回日本,并种植在京都高野山寺等地。另据日本《日吉神道秘密记》记载,与空海同时期的最澄禅师、永忠禅师(这两位分别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和长安西明寺学习佛学,并均于805年返回日本)也分别从中国带回了茶树种子,这些由日本留学僧侣带回的茶籽为茶叶传入日本打下基础。815年日本《类聚国史》载“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记载了永忠禅师在天皇参佛时,奉茶御前的事,茶通过高僧经由日本皇室传至整个社会,形成了日本最初的茶文化。
2.2 日本茶道的形成
日本称茶为道,始自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禅师,他将中国宋代禅师圜悟克勤的墨迹,挂在茶室最重要、最显著位置的壁龛里,让人们在饮茶前,跪在墨迹前,表达对已逝高僧的敬意,茶与禅的结合形成了最初的茶道精神。村田珠光认为“此(茶)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应先欣赏唐物之美,理解其中之妙,其后遒劲从心底里发出,而后达到枯高”。“茶禅一体”的茶室环境和敬畏静思的茶事活动也初步体现出了日本茶道“和敬清寂”的思想。至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视“茶道”为“佛道”,去掉了茶室中一切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古典美,主张“空寂茶”,日本茶道正式形成,千利休也被日本人民称之为茶圣。
3 中式茶馆与日本茶室环境比较研究
由于中日茶不同的渊源和各自赋予茶的不同文化属性,导致了两国茶道精神的差异,这种差异也集中体现在饮茶环境中。茶于中国是实用的、世俗的、大众的、宽泛的,因此中国出现了各种形式、装饰繁简不一的茶寮、茶坊、茶亭、茶楼、茶馆,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变迁和百姓故事的环境载体;而茶于日本是精神的、玄奥的、精英的,因此日本形成了幽雅环境中服务于特定人群的质朴、古拙的茶室和茶庭。
3.1 中式茶馆
3.1.1 中式茶馆的诞生与发展
茶馆诞生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至少晋代已出现了卖茶水、茶粥的流动摊贩;真正意义的茶馆现于唐代;宋元时期茶馆繁荣发展,茶坊里出现了曲艺表演等内容,茶馆环境布置优雅,文化氛围浓厚;至清,茶馆形式更丰富,有以家宅大院改建的高档茶楼,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乾隆年间扬州的茶馆盛况“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茶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不仅有雅致的室内环境,更兼得传统园林景观之美。此类以“故家大宅废园为之”的茶楼还有以亢家花园改建的“和欣园”,以崔园改建的“银塘春晓”;民间有露天布置、陈设简陋的茶摊,如卖大碗茶的“乔姥茶桌子”就“于长堤卖茶,置大茶具,以锡为之,少颈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数十”可见其环境之简。
3.1.2 中式茶馆环境特点
茶与各阶层人民均有着密切的联系,茶馆也因着不同的需求分为多种形式,从环境看大致有园林式、厅堂式、草庵式几种:
园林式:一般按江南私家园林的模式来建造,除中式风格的主体建筑外,还有露天的庭院或园林,亭台楼榭、小桥流水、楹联匾额,讲究与自然的和谐,体现文化的意蕴。其间有民乐或曲艺表演,但绝不直接呈现,而是藏在园林深处,通过隐藏在各处的音响层层传递给茶客,声音袅袅依依、时断时续、或低吟或浅唱,音乐、环境是仅茶的背景。
厅堂式:按古代富裕人家民居厅堂的样式来构建茶馆,这类茶馆一般装修典雅、清幽,家具多选择红木家具或仿红木家具,墙壁以书画装饰,也可陈设一些根雕、竹雕、盆景、奇石花卉等,营造古雅的氛围;也有按古代文人书房来布置的,在茶室内增设文房四宝,家具多选择明式官帽椅和八仙桌,也有竹藤类家具,悬挂文人字画,茶馆和茶室的名称体现文人意蕴。这类茶馆往往会在大堂搭建舞台,表演一些传统曲艺类的节目,如地方戏曲、相声、魔术、杂技等,气氛热闹喧哗,茶客阶层跨度较大。
草庵式:草庵式并非都是露天的,它主要针对广大劳动人民,价格相对低廉,装饰以实用为主,家具或选用高桌长凳或选用造价低廉的竹甚至塑料家具,此类茶馆有些甚至并不会特别干净,如李劫描写的成都茶馆“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泥污,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但这些茶馆毫无疑问是最有生命力的,很多茶客在里面一坐就是大半天。茶馆中还会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聊天、麻将、纸牌等娱乐项目。
现代中式茶馆设计通常将庭院文化融于室内,在一个茶馆中体现园林式和厅堂式两种茶馆的特点,茶馆内的庭院通常“缩千里江山于方寸”。一般而言,现代中式茶馆多运用传统、古典的元素,营造文人雅士高逸品茗的意境之美,让茶客在自由、质朴、轻逸、幽深的意境中,彰显品茶者心性的清高与超然。
2.2 日本茶室
2.2.1 日式茶室的产生和发展
日本茶室环境最早由归国遣唐使制定,但是茶室并非一开始就走禅宗道路,也有皇室倡导的相对富贵华丽的“书院式”茶室。后村田珠光、武野绍鸥两位禅师提倡“空寂茶”,规定了茶室面积,确立了日本茶室装饰风格。千利休则提倡茶室选用草庵式建筑,日本传统茶室自此确立。
2.2.2 日本茶室的环境特点
日本茶室环境主要由茶室和茶庭两个部分组成。茶庭是茶室的前庭,也叫露地,是进入茶室的必由之路。由围篱四面围合,经三道院门和一条掩映在树林中的园路进入茶室,沿路设寄付(门口等待室)、中门、待合(等待室)、雪隐(厕所)、灯笼(照明用)、手洗钵(洗手用)、飞石(即步石)、延段(石块、石板混合铺成的路段)等。千利休主张露地要营造“放眼皆廖寂,无花亦无枫,秋深海岸边,孤庐立暮光”的氛围。因此,茶庭中的树多选用松、竹等日本文化中认为纯洁、清寂的树种;地上累积的厚厚松针,暗示森林的茂盛;步石选用天然碎石,象征崎岖的山间石径;以石材和竹材搭建的洗手钵,象征圣洁的山泉水,洗手钵的尺度一般较矮,茶客需以蹲踞的姿态洗手,从而让其感受人的渺小和佛理的伟大;以寺社的围墙、石灯笼营造古刹神社的肃穆清静,也是茶庭对寺院环境的直接模仿,冈仓天心在《茶之书》曾有“茶室的简朴单纯是模仿禅院的结果”的观点。茶庭中的树木、山石都要保持天然的状态,杜绝一切俗尘的痕迹。松、竹、石与具有象征意义的环境设施配合,酝酿出枯淡的氛围。
茶室是进行茶道仪式、饮茶、冥想的空间,追求“人佛合一”。让人在的空寂、幽玄的环境中,通过人的内省感悟清净幽雅。因此较之舒适其室内环境更讲究“枯寂”的氛围。茶室装饰清雅且有较明显的程式化特征。传统的日式茶室面积都不大,仅有四铺半,约五六平方米,千利休甚至要求茶室做到2叠的极端小间。茶室的进出口(躙口)尺寸很小(高约690,宽约660),仅能容一人弯腰爬进去,体现出日本茶道中明显的宗教倾向。
茶室以“地炉”为中心,四周是客座、点前座和壁龛,在茶室的内部构造上,力求表现不对称美,避免重复,体现出禅宗“无常”的思想;如茶室内的地炉为方形的几何形,立于其旁侧的中柱就采用弯曲自然木柱,木柱的材质不同于中式木制建筑中选用材质优良的松柏做柱,日式茶室的木柱一般为未去皮的杂木,以与整体环境的自然、简陋匹配;
室内的陈设品十分讲究,四壁置古书、插花,悬挂名贵字画。为了配合茶室的小空间,室内的字画幅面一般都不大,选用陶瓷和竹器做插花器,花是时令花卉。墙壁一般贴淡黄色的日本纸,装饰材质也多使用竹、木、茅草等天然材质,茶室的屋顶是茅草或苔草,暗含茶室主人隔绝尘世,清心洁身之意,充分体现出日本禅宗和谐、清净、枯寂之美。
4 结语
中国茶文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影响,茶馆环境也体现出多元丰富的审美特征;日本茶道的形成主要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上层意志和单线式发展,因而其茶室环境体现出茶道推行者的个人意识和单一阶层的思想及审美特征。总之,饮茶环境与人的思想和观念有着千丝万绿的联系,中日茶文化由于其缘起、发展的路径不同、传播的广度不同,茶道思想的落脚点不同,形成了如今中式传统饮茶环境的巨大差异。
[1]吕飞,赵亚男.中国茶的起源学说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131-133.
[2]陈永华.禅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从中日茶道的渊源、特点谈起[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46-50.
[3]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4]柳燕.日本枯山水和茶庭美学比较研究[J].中国园林,2012(3):81-83.
[5]陶文瑜.茶馆[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6]宁晶.日本茶庭的空间构成与茶道仪式的关系[J].艺术设计研究,2015(4):86-89.
[7]汤佳,陈金瑾.探析日本茶室的室内设计之美[J].现代装饰理论,2016(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