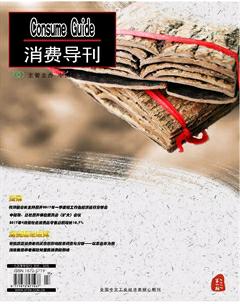刑讯逼供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袁琴武
摘要:司法过程中刑讯逼供的发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我国司法人员人权意识淡薄,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完善,沉默权规定空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司法人员急于破案等因素;完善讯问程序,加强法治教育,培养法律意识,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实施讯问时律师的在场制度等措施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刑讯逼供 逼供原因 遏制对策
一、发生刑讯逼供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人员人权意识淡薄
中国的刑法在起源上与现代法有很大的不同,因受古代一些司法理念的影响,司法人员往往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既然已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再具有法律上的任何权利,不如实供述案件只是在负隅顽抗,完全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出实情。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忽略了法律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刑讯逼供的发生就不难想象了。在司法实践中,就算司法人员意识到其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他们往往会认为,只要能够破获案件,这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二)我国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尽管我国已经确立疑罪从无的规则,但这并等同于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以前,在法律地位上應假定其为无罪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法院专属定罪权规则,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创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还包括嫌疑人、被告人无需自证清白等内容。因而很多办案人员依然持有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自证清白的观念,在其不能自证清白的情况下就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这就为刑讯逼供的产生留下了隐患,往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自证清白时采用暴力行为要求其自认其罪。
(三)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完善,沉默权规定空白
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是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刑讯逼供得来的书证、物证没有明确说明应当直接予以排除。这个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办案机关依然对书证、物证的搜集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心存侥幸,即使是通过暴力手段得来的证据依然具有适用的可能性。而对于沉默权而言,其起源于英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沉默权制度之下,任何人均不能被强迫说出自己有罪的言论。美国立法中也对沉默权的具体内容有较为明确的规定。然而我国立法没有沉默权的规定,反而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有口供是不可以定罪的,且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一般应当予以排除,然而很多案件中口供都对案件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尽可能的搜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口供成了大部分案件破获的关键证据,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采取刑讯逼供获取口供,在此过程中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若不然,就会被采取一定的“措施”。
(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大多发生在侦察部门,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接触最多的。再加上在侦查阶段案件情况一般是保密的,讯问的时候没有律师及其它人在场,侦查人员有较多的选择权,暗箱操作的状况时有发生,导致了监督机关形同虚设。冤假错案的出现大都与刑讯逼供、司法的互相监督缺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监督机制监督力度尚且需要大打折扣,处罚相关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更是难以实现。况且刑讯逼供行为的立案、侦查都是在事后,此时对于证据的搜集更加不利,被害人本来就处于弱势位置,没有足够的举证能力。另外,公安机关对于强制措施有很大的决定权,除了逮捕措施的决定权在检察院、法院外,其他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都可以决定。原本公安人员就是刑讯逼供的主要人员,此时再加上在强制措施上有很大的决定权,对于其讯问过程的监督就愈加艰难。
(五)多重破案压力,导致司法人员急于求成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侦查部门都有明确的考核体系,案件的侦破与办案人员的奖赏、晋职等挂钩,而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侦破的案件。巨大的破案压力面前,办案人员往往急于求成,为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交代案件而使用暴力手段,产生刑讯逼供的情况。同时,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信息的极速传递,群众对政府的关注度加大,一些舆论炒作往往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风,对办案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另外,公安机关形成固有的办案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比如限期破案、命案必破、招标破案、领导批示等等,在这些压力下侦查人员难以用常态的、理性的心态对待案件。多重压力造成办案人员一味的追求破案率,因急于破案而刑讯逼供。
二、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对策
(一)完善讯问程序
1.改进讯问时的录音、录像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或录像规则,针对不同侦查机关的规定是不同的。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对讯问进程使用全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在充分考虑实际状况下,这样区别对待是没有问题的。毕竟公安承办的案件占了大部分,全都录音录像成本过高且没有必要。而检察机关侦办的案件是职务犯罪案件,比公安机关的数量少得多,并且这些罪犯往往学历高,经验丰富,背后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顺利的拿到笔供,呈现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大。但是,我国对于审讯的地点及录音、录像的机关并无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在案件办理中自审自录,录音、录像制度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因此,笔者认为,就审讯的地点而言,应当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内,并由看守所进行录音录像,倘若出现刑讯逼供的行为由看守所承当连带责任。这样,整个审讯过程就形成了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录音、录像监控制度更能施展发挥功能。endprint
2.逐步推行隔离式讯问制度
刑讯逼供现象发生在侦查阶段的几率是最高的,这与强制措施的决定机关有很大关系。笔者认为,应该逐步实现让不承当追诉职能的法院作为强制措施的授权机关。同时,要逐步实行隔离式讯问制度,在讯问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让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远程审讯(比如通过远程视频进行审讯),这就使得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身体接触的机会,从根本上杜绝了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现象。
(二)加强法治教育,培养法律意识
就我国当前的现实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依然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缺失。司法人员常常为了破案不择手段,其中部分司法人员根本不知道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也有一部分知法犯法,没有正视法律的威严。归根结底,刑讯逼供行为的存在还是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没有依法做事的自发性。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模式和根本措施,是一个国家广大人民权利得以保证的重要措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爆发与法治观念不强,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潜在隐患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控制刑讯逼供,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培养其法律信仰,具有客观的必要性。只有司法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方能在司法过程中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控制刑讯逼供行为,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勇于维护本身权益的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法律给予公民权利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自身的权利,如果每一个公民的权益遭到侵害时都能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护,那么也会让刑讯逼供的行为得到控制。实践中,很多刑讯逼供行为得不到惩治与被害人消极维权的态度有关,违法行为不被揭发、追究,只会让更多的违法行为发生。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转变这种懈怠维权的意识,刑讯逼供者才会真正有所顾虑,从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1.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非法手段或经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应当排除适用,现阶段我国刑诉法的立法中的排除证据主要包含供述、证言这两类,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在很多案件中,刑讯逼供行为获得的供述、证言都得以排除。然而我国对于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总体上显得态度模糊,没有直接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取的物证、书证直接排除适用。笔者认为,从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角度而言,刑讯逼供逼取的物证、书证同样应当直接排除适用,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刑讯逼供,不能为刑讯逼供行为预留任何空间。因此,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有利于消除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侥幸心理。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沉默权在美国发展较为完善,不但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适用于证人,很大程度的保障了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促进了司法程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当前立法虽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证明本人有罪的权利,但同时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一立法模式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大打折扣。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沉默权,那么司法人员就会认为其不供述或者不认真供述的行为是不可以、不应该的,以刑讯逼供获取口供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如此,为了限制刑讯逼供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很有必要的。
(四)确立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
偵查阶段是查清案件真实情况的决定性阶段,由于侦查活动的秘密性,这个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也有较大的潜在危险。假如律师在场的话,当讯问机关出现违法行为时,律师可以当场向侦查机关提出,假定侦查机关不予改正,可以向相应的司法机关提出控诉。这就能够对侦查活动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既能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又能限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