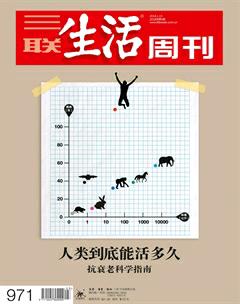在瑞士工坊,修复故宫古董钟表
杨聃
修复之后的六枚古董机芯不仅焕发生机,还填补了各自几近空白的历史。曾经的它们告诉我们时间,如今的它们见证了时间。
联合修复
经过耗时四个多月、累积近千工时的实际操作,六件钟表文物机芯重新回到紫禁城,再次被“植入”200多岁的“身体”里,为历时三载的文物修复国际合作项目画上了句号。这是故宫博物院钟表藏品的机芯部件第一次出国“就诊”。
“2007到2009年,故宫博物院与荷兰自动音乐钟博物馆也有过一次合作,不过那次只是校准了自鸣钟的音调,在音乐方面他们是专业的。”故宫博物院文物钟表保护修复专家王津对我说。此次,故宫博物院选择合作的机芯专家是瑞士卡地亚制表工坊。
故宫钟表馆有千余件18至19世纪的机械钟藏品,在还没有《我在故宫修文物》系列纪录片之前,好些人对王津的工作内容不太了解。他开玩笑说,有人会觉得,“在故宫修钟表,那是给故宫里的表换电池吗”?事实上,大部分时间王津都在做钟表的“抢救性修复”,让疏于养护的机械结构不再被氧化腐蚀,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拒绝工作的齿轮重新运作起来。他常感叹,故宫钟表馆的藏品一辈子也修不完。
虽然钟和表的原理大致相同,但要修复这六款直径小到3.5厘米、大到7.5厘米的机芯,势必需要更多精密的仪器。“分针传动轴氧化、摆轮夹板螺塞多处被戳穿、摆轮夹板断裂……”在《故宫博物院点交单》上每一款机芯的问题都被详实地列了出来,而跟其相关的历史信息只是简明地写着——时代:清。
六款机芯都被定为“二级”。据王津说,这是早期“老账”上的标注,大部分故宫博物院院藏都属于这个级别,只有少数大型复杂的孤品被定了一级,还有一部分零散的、没经过修复的钟表处于未定级的状态。
初期考察阶段,卡地亚的修复团队发现六件钟表文物在机芯内部都标注了“London”字样,从内部结构到装饰风格都沿袭了英国制造的特征,比如摆轮夹板只有一个触点,时针、分针采用的是甲虫针和火钳针(Beetle & Poker)风格。通过在《英中钟表年鉴》和《瑞士钟表匠以及世界各国钟表匠大辞典》等文献上搜索表盘或机芯标注的钟表匠姓名,他们一点点拼凑起跟这些钟表文物相关的蛛丝马迹。最终确认了方案之后,由王津师徒等四人组成的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组分为两拨,先后前往位于瑞士拉夏德芳(La Chaux-de-Fonds)的卡地亚制表工坊,与其共同完成修复工作。2017年2月,王津的徒弟亓昊楠带队先行“护送”机芯出发;5月,王津等二人抵达瑞士跟先前队伍完成交接,留守等待将文物送回。
当看到负责实际修复工作的凯拉(Micaela)时,王津说他当时心里有点打鼓:太年轻了。但他也知道瑞士的情况比较特殊,在瑞士有7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虽然米凯拉只有25岁,跟机械结构打交道的时间已经不下10年了——她一边在卡地亚钟表修复部门工作,一边在当地的制表学校任教。得益于瑞士成熟的钟表产业教育体系,他们的技艺是从小在专业学校里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加之毕业后进入工厂实践操作而习得的。相比之下,国内像亓昊楠这样的专业人员,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接触钟表修复工作,遵从传统的师承制,跟着师傅从一张白纸开始,一步一步口传心授,累积经验。
在瑞士,王津每天早上坐7点21分那班火车,经过五分钟车程到达拉夏德芳,7点半准时打卡进入工坊,开始修复。除锈、打磨、烧蓝等看似寂寞的工作在他看来是跟每一个零件的对话,这也更让他佩服那些最初的设计者们。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零部件,为了让机芯正常运作,某些无法修复的零部件即便要重制,也会尽可能“做旧”,跟其他部分在外观上保持一致。“发条断了就接一下,这样可能比原来的短了。原发条上满了可能表演个15回,修完就剩10回了,那也够用了。”王津解释道。他希望后人再次拆开机芯时,看到的还是本来面貌。
合作修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双面镀金表编号182994机芯缺失的四根指针,这时离计划中回国的日期只有一周多的时间了,远在故宫的亓昊楠已经把古董钟体修复完毕,期盼着机芯的归来。电话中,他感受到了师傅王津隐隐的忧虑。
“卡地亚一方希望重新制作指针,而我们因为是文物,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补补配。”亓昊楠解释说。这一原则被故宫钟表修复组严格恪守着。即便故宫藏钟并不是每一件都被详尽地登记造册,但大多是成对儿的,可以相互参照。对于未能找到史料参考的孤品,只能保持原状而不可“凭空创作”。所以,若要修复这款零件缺失的机芯,必须要给它“找回身份”。但年代久远,唯一的线索只有表盘上的“John Ilbery London”字样。
历史上伊伯利(Ilbery)这一姓氏在英国、瑞士和中国的钟表界声望颇高,仅安帝古伦拍卖会上拍出的标有“Ilbery London”的钟表就多达129件。2012年,伊伯利的一块表甚至拍出了50万欧元的高价。当年伊伯利的产品几乎所有都出口到了亚洲市场,尤其以“中国表”而闻名。原本伊伯利设计简洁的机芯只抛光而不加修饰,为了迎合中国市场的偏好,工匠开始对部分机芯进行装饰,从那以后雕刻装饰之风日渐兴盛。这些装饰工作通常在日內瓦完成,不只是机芯,表壳也镀金或饰以珐琅,并仿照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风格用珍珠镶边。此次修复的故宫双面镀金怀表就属于这类经典之作。
修复团队翻查了数千件古董钟表文献,终于在苏富比的拍卖记录中发现这款双面怀表是成对儿的,并从其姊妹款的拍卖信息中确认了制作年代约为1790年,最后根据资料上指针的形状和材质,复刻了缺失的四根指针。
时间的见证者
铜镀金狮驮规矩表,铜镀金嵌鲨鱼皮透花表,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这些记载在故宫文物档案里的名字取得有些拗口,看实物就觉得生动、有趣多了。以眼前这对儿刚刚经过“芯”脏复苏的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为例,木质基座上三层结构的造型,看似强调装饰性,实则暗藏功能。endprint
底部八面雕花的箱体是个音乐盒,旁边的小机关一碰,就能听到舒缓清脆的旋律。伴随着韵律,正面处于第二层的人偶开始“调皮”地左右摆头。围绕在他身旁的四头大象寓意“太平有象”,共同顶起了一个玛瑙箱,外部包裹着镂空的镀金花纹。用料这般豪气,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是个“修颜箱”。打开一看,工具还挺齐全:小剪刀、镊子、耳挖勺等整齐有序地卡在各自的位置上,其中对称放置的两个小小玻璃瓶,推测是装香粉之类的容器,还搭配了取粉用的袖珍小勺。修颜箱的开盖上顶着一只小表,简洁的白色表盘上,罗马数字小时刻度外圈叠加着阿拉伯数字分钟标识。
在故宫的钟表藏品中,像这样轻巧的座钟只是少数,大部分是体积更大、机械结构更复杂、表演功能更多的机械钟。
相傳最早给紫禁城带来这类舶来品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1年,他给万历皇帝进奉的礼物中除了世界地图、铁丝琴外,还有自鸣钟。大小两座自鸣钟深得皇帝的喜爱,因为宫内无人会调试,利玛窦则以养护皇帝的钟为契机,实现了留居京城的目的。清代初期,西方传教士经由澳门或广东把早期钟表带入国内再运送进宫,成了讨好中国皇帝的重要手段。1707年,第一位瑞士钟表匠来到宫廷,随后法国也开始以印度公司的名义与中国进行钟表贸易。这样的“钟表外交”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
继法国钟表之后,18世纪可以说是英国钟表独占鳌头的时代。清朝的广州官员不惜重金购买新颖华丽、做工精细的钟表进贡。据《乾隆朝贡档》的不完全统计,乾隆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为佳。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
自乾隆时期开始,钟表贸易有了迅猛发展。那段时期的欧洲座钟融合了法国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代的钟表风格。有数据显示,1770年还只有一家欧洲钟表企业与中国做生意,到了19世纪增加到了十几家,甚至有欧洲钟表企业在广州、上海、香港和天津设立办事处,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种贸易势头才被中断。
如今留在故宫博物院的机械钟藏品也是世界少有了。王津记得2006年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的人员互访时,访客对故宫博物院的院藏钟表之多惊讶不已。虽然他们对史密斯的英文著作《故宫钟表图书目录》早有印象,其中记载了来自18世纪的英国钟表约有70件,出自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等30多位钟表匠师之手,但实际的数字,比那还要多。即便是大英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也不能准确判断某些机械钟表的由来。
相应地,当王津看到大英博物馆的钟表收藏时也诧异了一下。“在没去之前,我还在想他们几千件馆藏得占多大地儿啊?”去了之后才发现,与大部分欧洲博物馆相似,大英博物馆的钟表藏品即便时间轴更长,但都以怀表和手表居多,座钟和重型机械钟很少,更别说像故宫里的种类这么丰富了。他还记得一拉开大英博物馆保管柜的抽屉,就能看到百十来个标着编号、包裹仔细的机芯静静地躺在里面,有的已经被氧化得黑成一团。当时他们负责保管和修复的师傅只有一人。算算时间,现在那位老先生也该退休了。
看着眼前重新焕发生机的钟表文物,王津感慨无论是设计还是修复,匠人只是文物漫长岁月中的一个过客。生命终将归于尘土,时间永恒于世。作为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他们有一种使命,和时间赛跑,让这些文化和技艺的载体,尽可能长久地留存于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