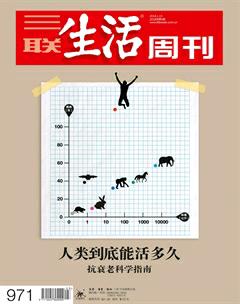状告波音:MH370空难家属的漫长诉讼
夕迟
美国时间2017年12月19日,站在被告席上的MH370制造商波音公司驳回了中国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前,这些家属的努力填满三年零九个月的日与夜,但在法律上,从未指向一个足以宽慰人心的结果。这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拓荒”——这架迄今没有踪迹的飞机承载了太多疑团,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一般概念的空难。
生离死别催生了执念和伤痛,也放大了家属之间的分歧,每一个选择背后,都藏着一个艰难的故事。
把波音送上被告席
从美国法庭回来后,花甲之年的文万成想要好好学英语,从零开始。
他刚参加完针对MH370制造商波音公司的诉讼——一个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9日在哥伦比亚地区法院召开的听证会。全程英文对答的美国法庭让文万成骤感无力。12月22日下午,一身黑衣、神情疲倦的文万成,在从机场回来的地铁上,对我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这是一场复杂且注定漫长的起诉,它尚未进入质证环节,只是围绕马航失踪诉讼战中的一环。
路很长,希望也微茫。文万成等家属的委托律师张起淮向记者介绍,家属的索赔诉求,关键在于“飞机失事的直接和近似结果,是由一个或多个有缺陷和不合理的危险情况,以及波音的侵权行为和不作为造成的”。依据是,迄今没有找到失事现场,似乎表明——波音飞机的水下定位配备是“无效的”。
这是中国家属第一次站在原告席上对波音公司进行民事索赔,而波音实质上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倘若追循前例,这仍将是一场至今看不到未来的官司——保守估计有七八年的诉讼拉锯。首例发生在2016年美国家属针对波音的诉讼,论据相似,却至今毫无进展。
与波音一起被送上被告席的,还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罗尔斯-罗伊斯有限公司和安联保险集团。针对他们的民事索赔,2017年11月21日,在北京的一次庭前会议上被讨论。会上情形,按张起淮的说法——仍在“互相推诿、推卸责任”。“失望”成了原告家属的一致感受,有人已经患上抑郁症。
“我们都感觉很愤怒。”49人中首位起诉家属李秀芝对我说。这一次她因为签证问题未能赴美,但李秀芝坚决地“要为孩子讨公道”,丈夫去世早,上半辈子,她拼尽全力供女儿去英国留学,下半辈子,本该女儿奉养她,可那天刚满27岁的女儿登上了MH370航班,她至今仍在为女儿充手机话费。
疲惫的起诉,无期徒刑般的等待,组成了239名失踪乘客家属三年零九个月的生活。然而,从文万成这个连手势都充满力量的老人身上,似乎没有一丝斗志被时间磨损。“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说法,我不能告了,孙子来告,孙子的下一代,也要告,我们要一代一代人告下去。”文万成平静地说。
从那一刻改变的生活
2014年3月8日,MH370航班载着文万成的独生子文永胜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告下去这个决定便如宇宙公理一般,决定了他的世界从此如何运转。
文万成几乎每个月都来北京。从海关出口到地铁机场线的复杂路线,他已轻车熟路。开始艰难熟悉的,还有飞机构造、地理、法律、计算机等知识。这些努力和以此获得的掌控感让他心安。“什么也瞒不过姓文的。”他曾对记者这样说。
退休前,文万成是一名特务兵,参与过情报工作。在“找出真相”的毕生使命面前,他重操旧业,孜孜以求。另一位马航失联乘客家属姜辉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文大爷有一次和一名家属聊天,说出一句话仿佛是宽慰:“你的儿子(即使不回来了)也是烈士。”家属敷衍回答说是,文大爷据此判定这个儿子来自政府某部门,当场对家属宣布了这一“发现”,依据是——普通人不可能认证成为烈士。这是否经得起推敲?在推动生活一天一天向前的努力面前,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文萬成对我说,前两年他从一个又一个“可能知道点什么的人”——官员、记者,甚至保安那里套话,一粒又一粒沙子积起来,坚硬的事实和柔软的希冀,支撑起属于他自己的强大逻辑:儿子一定还活着。其中,某些“独家信息”让文万成成了部分家属眼中的“能人”,比如,在所有家属之前拿到了登机录像,以及早期和解家属的名单——一份连律师也拿不到的名单。
把沉甸甸的箱子拽上地铁安检传送带的时候,文万成弯下腰,动作有些缓慢,黑白交织的头发泛出汗水的光亮。似乎只在这一刻,这个像石头一样倔强的老人才显露出一点吃力。这些东西太沉了。
一大箱子几千页的诉讼材料,还有电脑里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超过2000G的资料;在美国心事重重却必须惦记买礼物“讨好”儿媳妇的沉重,以及“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条朴素逻辑的压迫。飞机杳无音讯,没有一片已发现的残骸可以被精确“认证”,这意味着希望与绝望在无限漫长的时间里紧紧依附。
实际上,早在2016年3月7日,张起淮和12名家属就在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递交过庭前会议诉讼材料。他起先觉得“一年半左右才可能有信儿”,但诉讼因为种种困难中止,证据的采撷依旧漫长,现在,一年半过去了,他再度走进这里,这次,他估计要三年才能有结果。
文万成舒缓的生活时钟定格在出事那一天清晨:打开电脑看新闻,震惊地读到头条,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航班消失,儿子就在那架飞机上,是他开车送儿子出差去机场的。
至今“儿子出差还没回来”仍是这个家庭谈及这件事的固定说法。可是这次出差实在太久了,小孙女在日记里写想爸爸,还自己对家里摆放的佛像磕头,盼爸爸平安。
文万成从不愿和记者谈论与悲伤有关的任何东西。
他心里有一种担忧,马航的事情过去这么久,“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会透支公众同情,反而不利于关注度。“踏踏实实、用法律的力量解决,才是正理。”文万成说,而他所定义的“解决”只有一种:找到飞机,儿子回家。
“实际上,我们索赔,比方说一千万几千万,价开得更高,就是逼着他们找飞机,你要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啊,你就得找到飞机才能证明啊。”
张起淮说,本次起诉的49名原告代表14名失联乘客的家属,涉及36个家庭,诉请赔偿金额少则1000多万元,多达7700多万元。
文万成向我强调,对波音,他没有明确的恨意。令他寝食难安的是马航搜索工作的搁浅:必须通过巨额索赔,才能把作为搜索技术顾问的波音倒逼出来,寻找飞机。
而新马航在庭前会议上认为,责任应归于老马航;老马航则认为飞机没有坠落在马来西亚,搜救和他们无关;波音公司给出的观点是——飞机质量没有缺陷,不是他们的责任。
不同意见的权利
在所有用力追求“真相”的家属中,文万成的努力显得更激烈,姜辉曾说他很佩服文大爷的勇敢。但2016年3月,姜辉把文万成踢出了家属联络微信群。
“我当时没有选择,必须把他踢出去。”姜辉对我说,很坚决,又纠结地强调他不得不这么做。“他当时已经把一个底线给打破了……”“也没有做得这么绝,文大娘还在群里,有什么消息文大爷还是能看到的。”姜辉叹息。
点燃导火索的是那份文万成一点一点打听出来的“和解”名单:接受马航推出的“5万美元先期赔付”者,名单里有39人,根据后来发布的确切信息,约有60多人。
此前,姜辉和文万成的矛盾早已浮现。文万成和张起淮在事发当年就号召大家抱团维权,出于对张起淮代理李天一的反感,姜辉一直不信任张起淮,文大爷觉得这无疑“拖慢了寻找儿子的进程”,这是他最不能释怀的事。而姜辉支持的律师吴晨,在早期,也因在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家属与马航谈判的律师团中,“没站在家属一边”,遭到文万成反对。
最初,由于家属和马航针对赔偿报价差距较大,律师团曾试图与家属确认是否接受和解协议,协议的基础是马航“全面免责”。
“他们根本不是帮家属说话的。”文万成声音激烈地对我说。
签了那份协议的家属,从共同承担伤痛的亲人,变成了“背叛者”。但难以回避的现实考虑是,放弃这笔钱,选择诉讼,结果便遥遥无期且未必乐观。张起淮本人在当时接受采访时也认为:“走诉讼程序最终究竟能拿到多少赔偿,谁都说不准。”
据姜辉所说,文万成把那份名单抛在了群里(谈到此事,文万成摇头,“没有,没有这事”),这份名单在群里搅起轩然大波,那39人瞬间成为辱骂的靶心:“认钱不认人”;“年轻媳妇想再找个主”;“飞机上是你义父”……
飞机消息茫茫,失望煎熬成愤怒。尤其是,马方的初期事故报告只有5页纸,是张起淮口中“所有空难报告里最简单、最敷衍潦草的一个”。对很多家属来说,不督促马航好好找飞机,却为了拿一笔钱承认马航“免责”,这种选择看起来无异于“拿钱买命”。
家属张川(化名)告诉我,在微信群将近一年反复质疑的同时,家里也爆发战争。张川的丈夫在飞机上,那笔赔偿款对一个顶梁柱倒塌的家庭很紧要——老人要赡养,孩子也要供养,更何况找人本身就是一场看不到花费尽头的征途。但张川在家庭会议上谈及此事时,婆婆声泪俱下地说她不要丈夫了,先是怒骂,而后哀求,过了一个月,脑溢血犯了,住进了医院。
一个本就受伤的家庭就此隔阂不断。张川的母亲不满亲家对女儿的态度,两家裂痕渐深,张川刚上小学的儿子被严格的“合同”束缚,只能姥姥家住一个月,奶奶家再住一个月。
“人肯定一定是要找的。”张川对我说,连续用了两个强调词。至今,家里有关丈夫的物品一样都没动,牙膏放了一年,她觉得过期了不能用了,就再去超市买一管,还是放在那个位置。
“当时大家都是不理性的,其实接受赔偿和选择和解完全是两个概念,有些拿了钱的家属,一样在坚持找人。”姜辉对我解释。但“找到飞机”的诉求那么庞大而艰难:“本来所有家属扭成一股劲儿向馬航要人,力量多强。可是有人拿了钱,你拿钱了,大家就感觉你不用心找人了,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就不强了,可能就是这个心理吧……是的,我自己不会要这个钱,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各有要的原因,比方说缺钱、家里有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们没有办法。”
名单抛在群里那天,姜辉发出一段留言:“我们建立微信群应该是互相取暖,携手和肇事者共同战斗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家属之间的屠宰场。”
在姜辉看来,携手战斗包括坚持,也包括力气用尽了停下来——他认为这是他和文万成的“主要矛盾”。谁也不知道这个已被定义为“空难史最大疑团”的飞机事故能不能等到结果。很多家属年纪大了,支撑不下去了,选择离开团队。姜辉会祝福他们好好生活下去。“甚至真有要钱不要人的家属,血缘比较淡的那种。”姜辉皱眉,“但这也是他们的选择。”
姜辉性情温和,声音平缓。作为群主,他的性格成为家属对立情绪的黏合剂,被很多年龄更大的家属尊称为“大哥”。他和文万成至少有一点相似之处:从不自承悲伤,即使MH370航班带走了他的母亲后,很多熟人都觉得姜辉衰老的速度清晰可见。他自认坚强不及文大爷,等待的日子里,姜辉幻听,失眠,没有食欲,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应激障碍”。他很长时间不敢看母亲的照片,有时走路走到父母家,看着那扇窗户,也不敢上去。他总是混乱地想着很多事,比如母亲从窗户探头叫他吃饭,母亲洗好的衣服应该挂在那空荡荡的衣架上。
儿子没有死,对文万成是笃定的信条,但对姜辉和更多家属来说,那是一份忽明忽暗的希望,敌不过一日一夜拉长的时间。
一次,姜辉想帮父亲收拾房间,被父亲拦住了,说别动,等你妈回来收拾,“你弄得不对她回来又得叨咕”。姜辉无法平静地接下这句话,甚至不能与父亲对视。
面对记者,他十分谨慎地选择了“没有消息就不能证明人是生还是死”的表述,但母亲是不是还活着,他说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就像他从来没有迈进母亲的房间,那一分脆弱,被他藏在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
但姜辉的坚持不少半分。MH370失联事发后,姜辉辞去工作,专职找人,这在马航家属中极罕見。辞职前,姜辉是公司的销售骨干,年轻有为,挣下了当时觉得够半辈子花的钱。“把人找回来才是这辈子最值得做的。”姜辉说。
三年过去了,金钱上的压力渐渐浮现,他也没放弃,一头扎进了由技术资料和复杂线索组成的生活中。在和马航的沟通会议上,他抛出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给出的卫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数据在哪儿?飞机上四个ELT一个可以人为关掉,另外三个不能,是这样的吗?
报道说,马达加斯加有飞机残骸,他亲自去找,和毒蛇、鳄鱼擦身而过,在大浪中稳住几乎就要倾覆的小船。但有家属认为,他的这一努力也意味着“背叛”——去确认“飞机已经不在了,人也不在了”可能是事实。
尽管彼此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牺牲,但在和我的谈话中,文万成和姜辉对双方的努力成效、价值观都有质疑,这也是马航家属之间大小矛盾的一个缩影。
“就拿请律师来说,家属都是分成三拨的。”姜辉说,并伴随哲理地感叹:生和死是多大的事啊,当你手底下的选择意味着生和死,它就能放大所有分歧。
但对文万成来说,三拨律师,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大家都得盯着别人,“这就能督促大家把事干好”——而其中的过程,团结、温情,抑或争执,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个目标:找到儿子,还是开着那辆离别时开的车,把儿子带回家。
放弃比坚持更难
2017年11月21日,作为马航MH370引发的首起民事索赔案的原告,李秀芝在下午2点出现在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原告席上,随她呈堂的还有整整14箱辛苦收集来的证据。“她是第一个,往后还长着呢。”文万成对我说。法律程序逐步启动,让这个坚称“只相信法律”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希望的另一面是等不到希望的无力。很多家属在三年零九个月的消磨中放弃了。“身体跟不上。”一个网名叫“北方”的中年男子对我说。从小养在他家的外甥和干儿子在MH370航班上。两年来,马航家属每周去外交部重申“找飞机”的诉求,但“北方”一直没去,他腿里长着骨刺,这使得燕郊到城区两小时的车程成了无法负担的重量。
一直以来,对马航家属而言,放弃与“背叛”之间有一种难以置辩的逻辑,这让“北方”沉浸在不见天日的愧疚中。除了工作,他几乎不出门,甚至不再愿意出房间——之前他常常整日整夜待在儿子的房间不愿出来。北京冬天供暖之前,寒风勒紧他的骨刺,有时疼痛难耐,有时也让他感到安心。说不定孩子在某个孤岛上,也只有冰冷的地面可以睡。
“北方”有他的坚持。见到我那天,他带着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有关MH370航班的每一条新闻,每一条或真或假的“消息”,甚至每一个在孤独时刻跳到他脑海里的“可能性”。积累一部分,他就把它们打印出来,寄给他认为可靠的机构,希望能够“推动一点儿东西”。
“这架飞机(MH370)被一个UFO绑架了,或者掉进了时空隧道里。”我指着这一段给他看,“北方”摇摇头,认真地看着我:“飞机没有找到,也就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如果外星人拿孩子做实验呢?”
而另一条猜测——为了“不可示人”的目的,飞机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特工劫持并“技术”坠毁,也让“北方”琢磨了一阵那“不可示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结论似乎超出了命题本身:“我对美国一直印象就不好。”
“不能排除任何一线可能。”在我采访的家属中,这句话众口一声。少了一个亲人的生活必须继续,那一丝希望也始终在燃烧。但文万成和姜辉都知道,竭力作战的队伍在变小,时间终究融化了一些东西。
文大爷走后,群里很少再有争执,“放弃”渐渐被视为一种选择,而不再斩钉截铁地“归入敌营”。群里不多的聊天回归抱团取暖的朴素初衷。北京家属会定期发照片到群里:某天又去外交部强调诉求了,外地家属则回复一句“加油”,一束鲜花。
“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决定不再参与诉讼)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不是说你要多少钱,重要的是你放下了一块事,这个事情是你们无法承受的。”姜辉的代理律师吴晨曾这样劝慰愧疚的家属。
但如何能真正放下呢?一些家属告诉我,他们用各自的方式用力修复着生活,虽然失去的空洞仍一戳就破。一位大姐对我说,她在离家最近的寺庙里一次又一次进几千元的香,急迫盼望着“功德”尽快“兑现”为孩子回来的消息,却在希望和绝望的震荡中流干了眼泪。另一位大姐经人介绍见了一个“很灵”的算命先生,说女儿肯定能回来,她白天靠这股力气支撑,却害怕夜晚,仿佛黑暗会撕裂伪装。
即使倔强如文万成,也有藏在战斗姿态之下的另一面。面对媒体,他斗志激昂,但只有律师张起淮知道,文万成有时候说了一会儿话就落下泪来,他觉得这就是知道儿子可能回不来了,“哭得呜呜的”。
无论如何,回归是一条注定漫长的路。2017年12月24日,一条新闻发到沉静已久的马航家属微信群里:澳大利亚为MH370事件立纪念碑。消息注明了因为机上乘客状况未明,碑上没有名单,乘客们被称为“失踪者”而非“逝者”。
但这照样在群里烧起了一轮怒火:“强烈抗议,想既成事实吗?”“不要脸的,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狗,赶紧好好卖你的羊绒!”“我们就要和他斗、斗、斗、打、打、打!”
也只有在梦里那些时刻,平静属于他们。在一个家属的梦里,飞机还没有起飞,妻子拉住丈夫的手,没让他上飞机,一切都停留在那个时刻,直到梦醒。
醒来之后,他们必须面对的,仍然是冗长而无奈的现实。最初接近500人的家属群,一半人已经默默退出。
因为希望的光芒看起来太微弱了。美国法官并未宣布波音诉讼下一次的审理日期,其他4名被告尚不知何时进入正式的起诉程序。而且,迄今国际上对MH370的全部起诉,都不了了之。“那些新闻越看越绝望。”一位家属对我说。至于何时能“拿到一个说法”,律师和专家各有解答:3年,8年,10年,甚至如文万成所说,一代一代人就这样告下去。
“我的儿子也会相信我。”文万成平静地说。在家里,他格外重视孙子孙女的英语学习,爷爷干不动了,他们会把担子接下去。
(林小陌对本文亦有贡献)